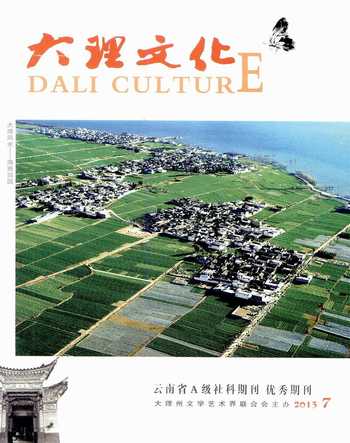那漆黑的老屋
马云海
那漆黑的老屋,其实共有两间:一间坐西向东,一问坐北朝南。
坐西向东的是主房,矮小,住人。土抬梁,两层,墙由两截组成,下半截是自生的,上半截是用泥土版筑而成。整间屋顶呈三角形,用木架及椽子撑起,由前厦、后厦与厦子三部分组成。用稻草编扎覆盖,即今天所说的草房。房子的地面层,格栅为三格,用石竹划片编扎后再用泥巴糊平,堂屋正中靠后山墙有火塘,靠右边一格是爷爷的卧室,靠左边一格是父母的卧室。卧室门旁,架着上楼的梯子,楼层也用石竹划片编扎好铺在楼楞上,堂屋上面没有用泥巴糊平,两边的楼层都糊平了。据说。堂屋上面的不糊平,是为了便于晾晒玉米,只要把地里收回的玉米撕开外皮后放在上面。就根本不会发霉;糊平的是便于安放谷物。厦子下。右边是客房,记忆中由哥哥住,与爷爷隔小窗而居:左边是灶房,灶用土基简易造成。主房不知是什么年代建成的,从我记忆开始就是漆黑的了。
坐北朝南的厢房是畜圈,土抬梁,由两层构成,结构要比主房简单,上楼下圈,楼上堆放着父亲到山上砍来的木料与一年四季要用的草料,剩余的空间闲置着,割了青草之类就直接背到楼上倒起,需要喂牛马时再上去直接撒在圈里。圈门开在左屋山墙正中间,向阳,太阳一出就可以照进畜圈。如今想起还是很环保的。
两间房子前面是用泥土版筑的墙,方整地围成一个长方形天井,门开在主房的右山墙边,路边有一个水塘,直接与阴沟相连,水塘靠哥哥住的客房前有一个简易的花台,是姐姐和我一起砌成的,种满了粉团花、太阳花、片茶花、海棠花等等。春天来了,还是春意盎然的。天井很方整,较宽,于是被父母将其分离了一部分,用小树条编栅起来后,种上了甘蔗。每到甘蔗成熟时,就是我们几姊妹的甜蜜时光了。正南方的围墙外种了一棵大京桃,味道鲜美甘甜。围墙内种了一棵泡柑,八九月成熟后,肥肥胖胖的,果皮是鲜橙黄色,煞是诱人。天井正东边的围墙里,种了一棵黄果,树形高大蓬松,果子也是累累硕硕,光彩夺人。
我家的这两间老屋,据父亲讲原来不是在这里的。我们家先前是佃农,和金光寺租田耕种,曾祖父非常能苦,至今在其墓碑里还写着:“穿半截裤,著百年鞋。晨草三篮而后食,夜眠三更即劳作”的文字。值新旧社会交替时,进行土地调整与人的身分确认,我们家第一次确认为佃农,所以最古老的别处的祖宗房产没有被改给别人。后来,因为我家当时有二十多人吃饭,牛马骡子较多,而且曾祖曾经买过一些廉价的田地,带领全家人自己耕种过几年,是名副其实的土地拥有者。在“补课”的过程中,升级为最高级成分。于是,祖宗房屋就被彻底改到别人的份上,丝毫不剩了。全家二十多人只得枝分如树,已经成家的,各领妻儿谋生,年纪尚小的由老人照顾,到处临时搭窝铺寄居,从零开始。我家的两间老屋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次第起建的。
住在漆黑的老屋里,一家人发生着悲欢离合的故事。
爷爷是一个忠厚老实的人。关于他的生活琐事,就只记得,他经常约我去采药,采回来后到街上卖给一个老中医,他给人治病,也给牲畜治病,至于他如何在人与畜之间进行适当的转换,我就不得而知了。其次是带我到山上去采伐腐朽的松树根,背回来卖给街上做线香的老奶奶或老头子,当然,这家收购松根的人家也就是老中医家。爷爷喜欢去串门子,我就追他的路,一开始说好自己走的,走到半路上,我却不讲信用,硬是要爷爷背我走,软磨硬泡,爷爷拗不过我,只得背起我。他摩挲着我的脚后跟,说:“你真调皮,还会哄爷爷的。”后来,爷爷病了,腿脚几乎丧失了行动能力,始终就是坐着,靠在我家灶房旁边的一棵柱子上,吃饭、大小便都要帮助他完成。有一次,我和爷爷搞恶作剧,明明爷爷撒尿后,要喊我帮他倒尿,我就假装是聋子,爷爷喊不知多少遍,我都没有动。还是爷爷说:“快点,倒了尿,我给你几个核桃。”我才活蹦乱跳地去给爷爷倒了尿,实际上,我并没有接过爷爷递给我的核桃。爷爷摸摸我的头笑着说:“这小子,还和我开玩笑。”不知熬过了几年,爷爷终于熬不住了,他于一个阴霾的午后,也就是我读二三年级放学回家时。离开了这个可爱的世界。家人都很哀痛,父亲到村子找人帮忙后,用一只羊的标准给爷爷办理了丧事。失去亲人的感觉是一个幼小心灵难以理解的经历,爷爷都安葬几天了,有一天我还问父亲:“爷爷怎么还不见回来?”父亲憨厚地回答我说:“爷爷,不回来了,他守山去了。”多年后,我才明白父亲的意思。奶奶是我没有出世就离开人世了,关于她的轶事就根本不知道了,只是听父亲说起过,奶奶曾经做过妇女主任。
院子里的甘蔗熟了,我和姐姐经常砍几根要好的,拿到圈楼上吃,目的是不让甘蔗的皮子弄脏干净的地面。母亲对吃甘蔗是有讲究的。记得母亲说:“吃甘蔗,要从尖子吃起,这样就会越吃越甜;从根子吃起,就会越吃越淡。”我们是始终铭记母亲的教导的。有一次,甘蔗还没有熟,我等不及,就到地里掰了几棵玉米秆来代替甘蔗吃,味道是很不错的。可是,不小心,在用嘴修玉米秆时,突然划破了我手腕内侧的一股青筋,可吓伤了我。没有出血,青筋冒了出来,也不怎么疼痛,我就跑到屋里,七翻八翻,找到母亲的剪刀,把冒出的青筋剪断,用布作了包扎。后来也就没事了,只是至今还留有一个小窝儿在手腕内侧。
在院子里,夏天的晚上,我们姊妹之间,包括临时来玩的堂姊妹经常在一起戏耍。诸如捉迷藏、老鹰叼小鸡的游戏是经常举行的。那时的玩耍是没有限制的,自由自在,轻松愉快。记得有一次,我们捉迷藏,哥哥和姐姐一组,我和堂妹一组。为了躲得严密些,我和堂妹钻到了一个深洞里搂在一起,虽然那时还没有明显的性意识,但堂妹那软酥酥的乳房或多或少已经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有月亮的晚上,母亲也会给我们讲故事和猜谜语。母亲最爱给我们讲的故事是《王玉莲救母》,其中有一个情节我至今不忘:据说王玉莲排队等人家给发散稀饭,排在右边,人家从左边散起:排在左边,人家从右边散起;排在左右两边,人家从中间散起。一句话,王玉莲的面分始终是没有的。不知是什么原因,王玉莲会是如此的悲怆。还有就是《老催撇》的故事。大意是说:有两个孩子在家里。母亲到外边做活去了。有妖怪假装成妈妈回家来诱惑孩子的事。其中,有一个孩子太老实,被妖怪骗了,吃掉了手指与脚趾;有一个孩子相当聪明有智慧,老妖根本拿他没办法,只得灰溜溜地离开,连孩子的家门都不得进去。父亲有时也给我们讲故事。他的故事主要是以《慌张三的故事》为主,间或夹杂一些诸如《聊斋志异》之类的鬼故事。有时候,父亲和母亲还有竞争比赛较量谁讲得更有吸引力的意味。猜谜语是经常进行的节目了。那些谜语,有字谜,有物谜,有人谜,举不胜举。母亲爱叫猜的最有代表性的谜语是:“大理下来一条象,一个屁股拉三样。”(打一农具)“高山头上有家人,石灰粉起不留门。”(打一种物体)“高山头上有一蓬葱,千人万人数不清。”(打一种物品)父亲猜的代表性谜语是:“床边有个坑,跳下去就一腰深”(打一用物)“头有黄豆大,一间屋子装不下”(打一用物)……记得那时我们要猜出谜底来是要用很大的智慧的,有一些是猜得很快,有一些猜了几天,有的至今都没有猜出来。
白天是十分繁忙的。父母亲都是起早贪黑地干活,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有时去得很远,有时去得很早,有时还要在晚上加班,直到十点钟左右,干累了,生产队熬一点用糯米熬的稀饭。清清的,味道很淡,但那是那时的最佳补品了。每家人打给一碗还是两碗,要看劳动力的情况。稀饭打来了,父母是很舍不得自己吃掉的,总是留给老人或者孩子。那时爷爷已经去世,我和妹妹就经常是父母优待的对象了,哥哥和姐姐,毕竟稍大了些,被父母开除了优惠名单。就是因为白天父母到大老远做活去了,我在家带妹妹,马上就要到吃晌午饭的时候了,母亲还没有回来,妹妹已经饿得哭喊不止,我没有办法哄妹妹,只得背起妹妹去找干活的母亲。谁知,越是小心越是出麻烦。走到一个山沟边,突然脚下一滑自己和妹妹都滚了几个老翻跟,好在没有受伤,我们依旧去找母亲。说起跌倒的经过,母亲不住地安慰我,妹妹倒是若无其事地吃奶。还有一次,也是送妹妹去喂奶,回家时,姐姐背着妹妹,我走在前边,突然有一条“黄鳝”从脚前钻进草丛去了,我简直喜欢得不得了,翻了又翻,始终没有找到,尽管姐姐说那是蛇并非黄鳝,那时我哪里分得清黄鳝与蛇的区别在哪里。后来才知道蛇是生活在旱地上的,黄鳝则在水田或水沟里。如果再把水蛇与旱季藏在潮湿背沟深处的黄鳝混在一起,在当时,我恐怕更是根本无法区分了。
那时的粮食是按劳分配的,我家人口多,只有父亲和母亲两个劳动力,于是每年分到的口粮就少得极为可怜了,寅吃卯粮的说法一点都不夸张,因为两个劳动力充其量只能确保基本粮。分红就没有分了,而且还要退出一部分基本粮。在这种情况下,哥哥和姐姐只得被迫回家支援父母劳动,尽管如此,也是于事无补的,因为未成年劳动力是廉价的。即使做的活不少,得到分值充其量只是成年人的几分之几。这样,家里缺粮的问题就十分严重了。左邻右舍也好不到哪里去,只得到遥远的山头借粮,借来玉米救急,下一年偿还人家大米。关于粮食紧缺的情况,挖草根、吃树皮的记忆于我是没有这样的经历了。最悲惨的记忆是:一日两餐,只能调面糊吃,没有食盐,只得到石灰塘里,打一点石灰水来替代。而且这样的日子不是一天两天,是持续了几年的。平时没有肉食,连菜油都少得可怜,记得有我一个堂叔的老岳母到我家看到后说:“你家吃的油,还没有我家的洗碗水上漂着的多。”每到逢年过节,家里使出吃奶的劲割一两斤肉来煮吃,孩子们总是狼吞虎咽,第二天不是拉肚子就是晚上伤食,过节了,本来是孩子们盼望的日子,却总是在盼望中害怕,在害怕中盼望。
哥哥是一个勇敢的人。因为家里条件艰苦,还读着初一年级,就约着寨子里伙伴去烧炭。我也和他一起去,我们总是忙活到深更半夜,有几次直接忙得连家里都赶不上回来在山里歇宿。害怕窑子不接火。还得第二天去凑火,主要原因是担心到时间了,许好给炭老板的日子耽搁了,对不住人家。对于哥哥勇敢的记忆是有一次哥哥吃过饭后去上厕所,厕所在一棵大花椒树下,那天,太阳暖烘烘的。突然,我听到哥哥紧促的叫声:“佛海,快出来一下。”我急忙赶出去,原来哥哥正双手紧紧拽住一条大蛇的尾巴,脚蹬在墙上。看到情况后,我迅速回家,找来锄头和刀子。首先我们用刀子划破了蛇的肚皮,鲜血淋漓,蛇依然把大部分身体钻进石夹缝里,看见划破蛇肚子无效,我就用锄头逐一撬开石夹缝,最后一条大蛇终于被我俩扯了出来,丢在地上,一顿好打。我和哥哥之间是非常友好的。记得我第一天去学校读书。才下第一节课,我的学习用具就不知飞到什么地方去了。哥哥知道后。根本没有责骂我,只是说丢失了算了。他又重新给我买来了铅笔和作业本。说真的,至今我也不知道,是谁居然当着我的面,拿走了我的文具。
哥哥生病的记忆是我永远无法抹去的。他不病时是好端端的,病情一发作就变得语无伦次,给他自己和家里都带来了严重的损失,经过精心的调理,哥哥终于恢复了健康。谁知,上帝对哥哥是极端不公平的,让哥哥得了重病,又在几年后将哥哥接走了,理由是哥哥到山上去烧炭,天寒地冻,得了伤寒病,回家后上吐下泻,治疗无效。父母怕耽误我的学习,没有将哥哥去世的消息告诉我,放假回来了,我才知道。当时,真是充满了“百年三万日,一别几千秋”的人生凄凉感。
母亲的一场大病也让我记忆犹新。是一种严重的胃病,面黄肌瘦的,父亲领母亲到处打针吃药就是没有疗效。有一天晚上,我下自习回家,母亲把我们四姊妹叫到床边坐好,父亲也在旁边。母亲轻轻的有气无力地说:“孩子们,我可能活不了多久了。假如我走了,你们要好好听你们父亲的话。”听到这里,我哭得昏过去了,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凄凉的话语,不知几时几刻,到我醒来时就已经是天亮了。母亲没有走,父亲一大早又带着母亲去大田坝治疗,几天后回家,母亲好多了,气色也有了好转。
我读高二那年,姐姐出嫁了,虽然不是远嫁,但是此事于我总是耿耿于怀,因为我当时认为一家人是应该团团圆圆一辈子在一起的。这个梦想,再次于1995年妹妹出嫁时,遭到了沉重地撕破,似乎是血淋淋的。《红楼梦》里众姊妹“长大一个走一个”,“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的悲剧意识沉重地袭人我心灵深处,就像一条毒蛇时时咬啮着我的心肝,让我到现在都隐隐伤痛。
1983年冬天,在父母亲和哥哥姐姐的努力下,我们家又增加一问大主房,座东南向西北,三架五行的房子,父亲说本来是要盖五架七行的,但是作了折中,是用正宗茅草建盖的。这种草非常牢实,而且老鼠不敢啃,麻雀不敢搜,是上好的建筑材料,仅次于瓦房,那时我们村里只有两间瓦房,我们家的已经是二等房子了。可惜,这间房子很傲气,盖了一间,别的两间都受到了挑衅。第二年,我们家就将漆黑的老畜圈拆除了,并将围墙作了重新版筑。至此,黑漆漆的老屋就只剩下坐西向东的那一间了,始终在我们的心里盘桓,就像脸上的一个疤痕一样。
1986年9月,我考入了永平二中读高中。三年时间里,我带着全家人的希望,带着母亲对我的教导,带着别人对自己的嫉妒与讽刺,用近乎残酷的要求发奋学习;三年时间里,几乎没有睡一个安稳觉;没有浪费一分钟可以利用的时间,没有空耗一丝一毫多余的精力;我全力以赴,不留余力,废寝忘食,专心致志。皇天不负有心人,1989年9月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云南省大理师范专科学校就读,成为了我们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在没有考取大学之前的艰苦岁月里,孤独是免不了的。然而孤独却可以更好地学习。高考结束后的一天。我心情凝重,到我婶娘家下边的一条水沟边散步。沟边长着密密麻麻的树丛,无论从哪个角度,没有人能够看得见我。此时此刻,家婶在和一个外人讲起我在外边读书的事。因为她们压根就没有见到我,所以她们的讲话就是生龙活虎的了:“听说,老佛海就要毕业了,恐怕是考得起的。”“啊妈呀!咋可能。真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婶娘说。我在沟边一声不响,顿时觉得伤心不已,但这样的嘲讽更是激发了我的学习热情。
大学是考起了,供读大学的压力就不得了了。父亲不舍昼夜地在澜沧江边烧炭;母亲和妹妹,要么到山上挖药,要么到山上砍柴,要么在寒冷的冬天到澜沧江边的悬崖峭壁上割山草回家卖给那些需要用山草盖瓦房的人家。有一天,妹妹赶着我家的一匹枣红马去砍柴,都要到家了,那匹马似乎遇到鬼一样,不是朝前走,而是朝后退结果从悬崖下砸下去了,吓得妹妹哭着回家。父亲也是很倒霉,抬着一棵木柴要送到炭窑里去,不小心碰到了路边的树枝,结果顺山坡翻滚了几十个跟头,差点丢了性命。幸亏,我们村里的三奶奶和邻村的阿文兵以及洼子田的陈之兴叔叔的抢救才脱离了危险。如果不是三奶奶及时发现了摔伤的父亲,恐怕父亲就会那样离开我们了。
1994年,我家的那间黑漆漆的老屋,连同父亲他们刚刚建起几年的茅草屋,被我彻底连根从地上铲除了,盖起了两间崭新的瓦房。因为茅草用不到了,村里的有一个按辈分叫叔叔的人家又从我家廉价买走茅草。
岁月匆匆,人生易老。白头发已经长出来许多根的我,回忆起当年黑漆漆的老家,连同记忆也是黑漆漆的。现在,我还住在那两间瓦房里,还有我的父亲、妻子和孩子。母亲于三年前离开人世。
或许,用不了多长时间,我此时此刻居住的两间瓦房也要成为孩子记忆中的黑漆漆的老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