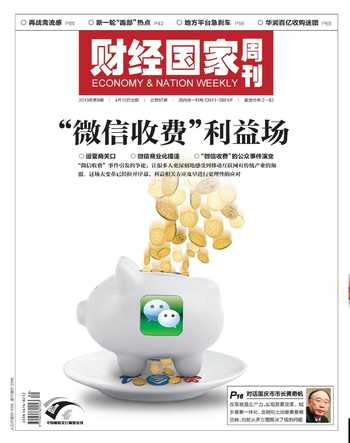非典十年带来了什么?
马岩
2013年春爆发的禽流感疫区,暂时集中于长三角的“三省一市”,此次战役的主战场位于上海H7N9禽流感定点收治单位——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这座酝酿于SARS盛行之时,集科研、教学、预防、治疗和隔离等功能为一体的公共卫生医疗机构,在沉寂近十年后终于发声:其病原微生物应急监测实验室全球首次检出人感染H7N9。
“十年前在离上海市区遥远的广阔地带建立庞大的医院,成了很多人的笑柄。在偏离市区的金山,一个占地面积超过很多大学的传染病医院,一整套一流的医疗设备,少得可怜的几个病人,今天再也没有人去怀疑当初专家们的意见。”该中心的医学博士孔晓飞说。
“即使发生比SARS再强的传染病,我们也有办法应对。”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曾光说,经历了十年前的SARS,公共卫生事业受到了重视,公共卫生专家的建议受到了重视,国家应对流行病的策略已经做了调整。
走进中南海
十年前的SARS,为中国大陆留下了5327人感染、349人死亡的伤痛;它像一面镜子,反映出被长期忽视的公共卫生问题,成为中国公共卫生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和里程碑。
2002年底,SARS便现身广东,被称作“怪病”。随着春季的到来,形势愈演愈烈。
2003年4月2日,时任总理温家宝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要把控制SARS疫情作为卫生工作的重中之重。8日,卫生部将SARS列入法定管理传染病。14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来到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详细了解SARS疫情。
“SARS之前,社会普遍还认为治疗是重要的,而预防并不重要。”曾光回忆道,那时候的他和其他公共卫生专家一样,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当时似乎是这样一种观点:只要能治就不怕。所以领导层和社会公众的关注点,都主要放在医疗和科学家身上,关心寻找、确认病原以及研发疫苗,较少有人重视公共卫生专家的意见。
时至今日,SARS疫苗也并未完全研发成功,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抗病毒药物的副作用却在患者身上逐渐累积。而传染病犹如森林大火,需要隔离带阻止火势蔓延,公共卫生专家正是要为政府如何采取隔离措施出谋划策的。
实际上,在疫情爆发之初,2003年1月曾光就随卫生部的专家组去广东进行过调查,并在全世界最先发现SARS只有在近距离、出现临床症状的情况下才会传染的特性。
他回忆说:“最初,人们更愿意相信临床治疗,后来又求助于被冠以高科技之名的疫苗、特效药。等到公共卫生专家的声音真正被倾听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是第三波了,已经错过了防控的最佳时期。”
2003年4月21日,卫生部发布的疫情显示:“截至当天,全国共累积报告病例2001例,其中医务人员456例,死亡92例。”
此后,疫情出现井喷,开始集中爆发。仅北京一地,每天新增病例都在100例以上,最严重的一天,收治的病人超过150人。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作为公共卫生专家的曾光开始介入高层的决策。他先后被聘为国务院SARS督导组成员、首都SARS防治指挥部顾问,频繁出席各种会议,为抗击SARS出谋划策。
2003年4月28日,SARS疫情最为关键的时期,他受邀来到中南海为中央政治局讲授“非典型性肺炎的防治”。曾光回忆,作为公共卫生专家的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兴奋,因为他迈入中南海的一小步,意味着中国公共卫生的一大步,领导层的高度重视将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送上发展的快车道。
公共卫生专家们“参战”使得SARS很快“铩羽而归”。“SARS怎么来的,目前还没有一个定论,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它是怎么走的,”曾光不无自豪地说,“非典是靠隔离消灭的。”
五公属性
2003年7月,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SARS疫情解除。因SARS走上“台前”的公共卫生事业,并没有因此重回“幕后”,而是“开始重新回到其固有的‘五公属性,即公有、公益、公平、公开、公信”,曾光总结道。
SARS之前,包括疾控中心在内的整个公共卫生系统正处于转型期——由过去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向半事业单位过渡。这一转变意味着公共卫生系统不仅要承担原有的公共卫生工作,还需要自己挣钱养活自己。
在这一格局之下,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胡永华表示,公共卫生机构的主要精力都用在生存和挣钱上,“过去能力最强的做业务,而现在能力强的搞创收。由于经费不足,很多业务都已名存实亡。”
SARS后的这十年中,全国各地对公共卫生的投入都有几十倍甚至成百倍的增长。全国公共卫生系统开始了空前的大规模建设。政府投入117亿元解决国家、省疾控中心的硬件设备升级问题,其中负压病房、信息报告系统以及监测预警系统就是典型例子。
“非典后,中国公共卫生管理体系逐渐完善,基本形成以卫生部疾控局和疾控中心为核心的公共卫生系统,前者主要负责政策制定、研究和部署,后者主要负责执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卫生经济与管理学系主任刘国恩说。
“与一般医疗相比,公共卫生服务的确得到了长足发展,”刘国恩认为,这一方面来自于其公共服务的属性,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其相对一般医疗服务投入要小得多,即投入产出比更高,资金使用效率更高。
“SARS之前,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得不到外界重视,不仅有体制上的问题,公共卫生界自身也存在问题,”曾光坦言。随着国家投入的增加,公共卫生系统重新回到全额拨款时代,他认为已经到了公共卫生事业回归固有“五公”属性的时候了。
曾光谈到,公共卫生是一项公共事业,它应以捍卫和促进民众健康为宗旨,其应该具有五个基本属性。
第一是“公有”。公共卫生事业的“公”要大于教育、文化等其他公共事业。教育可以私立办,例如民办大学,但公共卫生事业不能私立。公共卫生必须由国家拨款,不能允许利益集团介入。
第二是“公益”。公共卫生事业应该是做对公众健康有意的事,而不应该是去追求利润。
第三是“公平”。公平体现于人人享有卫生保健。越是弱势群体,在公共卫生方面越是应该得到照顾。例如在城市里的外来务工人员不能在本地接受疫苗接种,这就形成了客观上的不公平。
第四是“公开”。公共卫生涉及千家万户,必须要让公众拥有知情权。
第五个“公信”。公共卫生需要做到的是公众响应、公众相信,这样才能够形成共识。
“相比于致力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一般医疗服务改革,以预防和监控为手段的公共卫生服务已步入正轨。”刘国恩说道。
公共卫生事业的转折点
曾光总结的导致SARS早期“战局不利”的诸多原因中,第一条就是缺乏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案。
SARS之前,中国没有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案,没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认定和分级标准,也没有预定一旦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的指挥系统,更没有对此的分级负责制和岗位责任制。
2003年4月1日,时任副总理吴仪在视察疾控中心时,对在场的人表示,她此行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推动中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整套机制的建立。这是国务院领导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出应急机制的建设问题。
此后不久,国务院公布出台了《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条例》。
这份被认为是“公共卫生事业的转折点”的法规条例,从起草到提交审议,只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开创了中国立法的“SARS速度”。
2006年7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国务院召开全国应急管理工作会议,会议中温总理强调要求各级人民政府都要以“一案三制”的工作建设为重点,大力全面针对应急管理进行加强,做好各种紧急事件的应对工作。
“应急预案从传染病涵盖到整个公共卫生领域,再到各种潜在的社会安全事件。”曾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