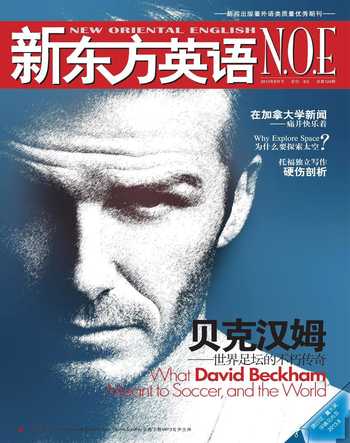在加拿大学新闻——痛并快乐着
于娜
国内与国外的新闻学教学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方面都存在一定差异。而且,在国外学新闻学还要面临语言和文化差异方面的障碍。因此,我在加拿大学新闻学时遭遇了不少痛苦和煎熬。但同时,我也收获了很多知识和快乐。我的加拿大留学生活就是在这样痛并快乐的过程中度过的。
学习——压力山大
北美大学的新闻学专业对申请人语言的要求之高是其他专业少有的:几乎所有新闻学硕士项目都要求申请人的托福成绩在100分以上,美国部分名校的新闻学专业甚至把托福成绩标准定在108分或者110分以上。入学后,新闻学专业的各个科目都要求学生采访和写稿,因此留学生必须克服对英语不自信的心理障碍,大胆地与外界进行口头交流,而且要在英语写作上下苦工。这对于刚入学的中国留学生来说意味着很大的挑战。不过,后来我慢慢发现,在大量采访和写稿的压力下,留学生只要够刻苦,很快便能适应这样相对严苛的语言要求。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在实践中不断锤炼是快速提高英语水平的最好法宝。
语言方面的障碍比较好克服,但要克服文化方面的障碍就不那么容易了。由于对国外环境和当地文化缺乏认知,再加上国内外对新闻学的认知存在巨大差异,中国留学生在文化方面遇到的障碍十分巨大。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留学生在国外学新闻学专业的人比其他专业的人要少。记得刚到学校报到时,我和另一位中国女孩就被教授们挨个“问候”了一遍,他们很好奇为什么我们要来国外读新闻学专业。后来我才了解到,我所在的国王学院大学(University of Kings College)以新闻学院最为著名,而该大学自1789年建校以来,这似乎是第一次招收读新闻学专业的中国留学生,可见中国人在加拿大读新闻学是一件多么稀罕的事情。再后来,我还了解到,国王学院大学的很多教授是多次获得新闻奖的一线记者,就连我的很多同学都是加拿大广播公司的记者或者是大学讲师。相比之下,我的学识和实践经历显得不值一提,这让我倍感压力。不过我想,既然来了,就得踏实学,不与他人比高低,只与自己比进步。这样也就安下心来学习了。
采访——苦乐相伴
学新闻学肯定少不了采访这一环节。对于学新闻的学生来说,无论大作业还是小作业往往都要通过采访才能完成。在采访过程中,我认识了不少朋友,也长了不少见识。多数情况下,采访都比较顺利,我能如愿收集到自己想要的资料。但在采访过程中,我也吃过不少苦头。
在我的印象里,所有采访中最悲惨的一次要数今年2月份去一个寄宿家庭采访的经历。加拿大的很多家庭住在远离市中心的郊区,这里房价不贵,环境优越。虽然很多人在市中心上班,但由于每家每户都有私家车,上下班很方便。但对于没有车的我来说,要去远离市中心的寄宿家庭采访,来回交通就成了大问题。
当天采访结束时,已经是下午6点钟了,而且还是风雪交加的天气。我到达公交车站时,发现自己刚巧错过了一班公交车。当时天已经黑了,车站附近没有任何咖啡店或加油站可以让我避寒,我只好缩在一个露天停车场的越野车后面勉强避避风。2月正是加拿大最冷的时候,郊区温度又比市区低好几度,而且这里的房子低矮,挡不了风,所以我感觉寒风都是呼啸着从耳边刮过。在那儿站了一会儿后,我的耳朵几乎失去了知觉。本来我想狠狠心打车回家,但是一想到从这里打车回家恐怕要花掉半个月的伙食费,就下决心咬牙继续等。在等候的时间里,我几乎担心自己会在风雪里被冻成雕像。一小时后,当公交车的灯光照进我的眼睛时,我瞬间热泪盈眶,心想:“终于得救了!”等我挣扎着想要从越野车后面站起来时,才发现自己的手脚已经快动弹不了了,睫毛上也挂着霜,连眨眼睛都感到费劲。因为这次采访,我严重感冒了一周。
当然,采访带给我更多的还是愉快的回忆。加拿大是一个重视新闻自由和信息自由的国度,哪怕是像我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新闻学留学生也有机会采访到一些“大人物”。我曾经采访过新斯科舍省、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四省教育部的相关负责人,加拿大语言协会秘书长,加拿大国际教育局副主席,魁北克省康考迪亚大学新闻发言人以及圣玛丽大学的副校长。采访这些人之前,只要你提前和其所在部门沟通,讲清楚采访目的和采访请求,就能通过电话或者邮件进行采访。在加拿大如此轻而易举就能得到采访重要人物的机会,这让我充分感受到这个国家对新闻和新闻工作者的尊重。除了采访“大人物”,我还采访了很多普通人,并和其中不少人成了朋友。采访不仅帮我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作业,还帮我打开了眼界,丰富了阅历,收获了成长。
改稿——受尽煎熬
前面已经提到过,在北美读新闻学对留学生的英语水平要求很高。然而,中国留学生即使英语水平再高,也难以达到母语人士的水平。这就意味着中国留学生写稿件的水平要差本地学生一大截。而且,加拿大的新闻体有自己的格式要求,即“加拿大媒体标准格式”(Canada Press Style)。这些标准格式被写成了厚厚的一本书,包含了无数的细枝末节:什么时候用数字全拼,什么时候用阿拉伯数字,什么时候能用缩写,什么时候不能用缩写……起初我根本记不住这些要求,所以教授返给我的作业经常满篇红色,作业里的语句表述倒问题不大,主要是写作格式不符合加拿大的媒体标准格式。
在新闻实践中,由于对新闻的不同认知和个人的偏好差异,编辑和记者对同一篇稿件的看法可能有所不同,这就会引起一些改稿“纠纷”。而在学校,不同的教授对稿件的标准也常常不同,有时甚至相互矛盾,令学生头疼不已。比如说,我有一门课的教授坚决反对在新闻标题中用疑问句,而另一门课的教授却非常提倡用疑问句作为新闻稿的标题和开篇。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在写稿和改稿时就会非常迷茫,在不知道教授偏好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虽然在国外的大学,和教授据理力争并不是什么稀奇事,有意见分歧也都可以讨论,但如果学生稿件的标准与教授所提倡的标准相左,下场只能是得到一个不高的分数。
改稿最折磨人的地方还在于对文章结构的调整。我在国王学院大学学的是调查性新闻报道,所以我的毕业项目是一篇深度报道。我收集了六百多页研究资料,采访了三四十个个案。我茶饭不思地花了整整两周的时间才把这么多研究资料和采访整理、精简成一篇生动的深度新闻报道。而当我把呕心沥血写成的15页深度新闻草稿拿给导师看时,得到的回复只有一个:结构需要调整。这对我来说简直是一道晴天霹雳:15页的稿子啊,要重新打乱原文结构,按照更合理的结构搭建文章的框架,这基本上就意味着要重写!后来我才知道,这不过是第一道霹雳,在此之后,我又被“劈”了两次,都与调整结构有关,每一次都把我折腾得晕头转向。有时为了优化结构,我不得不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得到的信息全部删掉,那时真是觉得伤心又无奈。但是在一次次的修改过程中,我的确发现,文章在叙述结构上越来越合理,行文逻辑也越来越清晰。
我的毕业项目导师是加拿大著名报纸《多伦多星报》(The Toronto Star)的深度报道新闻记者Robert Cribb,曾经多次卧底进行调查性报道,在加拿大获奖无数,也编写过很多新闻教材。所以,尽管我在收集资料和改稿过程中被他多次“折磨”,但是跟随他做项目的四个月里,我的新闻素养得以快速提升。
直播——忙碌又刺激
在上手机新闻这门课时,我与其他九位新闻学专业的同学需要完成一场图文直播活动的任务。直播的对象是加拿大哈利法克斯市(Halifax)在8月份举行的街头表演艺术节(Busker Festival),需要我们以图片、文字、视频等多种形式在网络上对这场活动进行直播报道。说起来,这场直播既有趣又令人崩溃,不过最后总算有惊无险。
我们十个学生被分为了两组,其中六人组成了Field Team,赶到活动现场采访、拍照、拍视频,然后将资料通过无线网络上传。另外四人组成Newsroom Team,守在位于学校的演播室内,负责主持、介绍背景资料和监控整场活动。我被分到了Newsroom Team,以两组之间联系人的身份参与直播活动。
在这次直播过程中,我见识到了国外的新闻工作者对新闻的认真态度。在直播前,我们就一遍一遍地开会,商讨直播的重点关注对象、需要的设备、每位成员的分工以及在报道时应注意的原则等。在直播开始之前,我们调试了设备,所有成员按时到达各自负责的地点,检查网络,然后进行模拟直播,试着上传图片、视频和文字,直到确定一切准备就绪,大家才略作休息,等待着迎接挑战。
直播开始后,我们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忙碌与紧张。在直播的过程中,什么差错都有可能出现,我们丝毫都不能放松。比如直播开始后,一位同学忽然发现,采访小组成员上传的一张照片把艺术家的名字拼错了。这在新闻报道中是不可原谅的大错误,我们所有人都为此倒抽一口凉气。好在演播室的成员迅速采取行动,对这个错误进行了核实和改正。此外,无线信号中断、视频和图片上传失败这样的技术问题也频频发生,让我们的心里始终绷着一根弦,一刻也不敢放松。而直播要何时转移到下一个话题,如何引起观众注意,又要在何时结束整个报道——这些都需要直播团队成员间的快速沟通与决定。采访组和演播室小组的所有沟通都由我来负责,所以在那几个小时里,我一边守着两台电脑监测微博平台,一边接听响个不停的手机,忙得不亦乐乎。
另一方面,作为联系人,我还有一个责任是“堵枪眼”。虽然我被分配到了直播室,但是如果采访组忙不过来,我就要奔赴海边的艺术节现场支援。从学校到海边走路大概40分钟,我得背着监测和拍摄两套装备(一个四斤重的笔记本电脑、一个手机拍摄铁支架、一大一小两个三脚架)。不过,幸好采访组工作进展比较顺利,我不用那样冲锋陷阵。如果真要背着那么重的背包去海边,我估计还没到现场自己就晕在半路了。
这场直播从设备调试到最终结束耗时九个小时,所有同学都累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不过大家都学到了很多直播技巧,也体会到了直播过程中的紧张、忙碌与多变。虽然大家抱怨说长期直播的话肯定会得心脏病,但同时心里又觉得这样的工作很刺激、很快乐。
在加拿大学新闻学的这一年里,我开阔了眼界,扩展了学识,提升了职业素养,磨练了品格意志。我享受这样痛并快乐的学习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