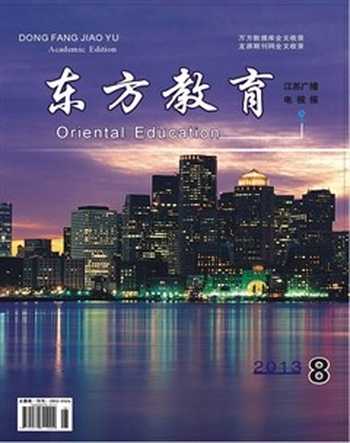唐彪《家塾教学法》的写作思想
刘荣
【摘要】唐彪是我国明末清初的教育家,其著作《家塾教学法》在总结历代写作思想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阅读实践,提出了较完备的写作基础论和方法论体系。唐彪认为阅读和写作是紧密联系的,阅读是写作的基础,他还根据自己的写作经验,结合学生写作的心理特征,提出了多做、多改、一题多做、精研细琢等写作方法。
【关键词】《家塾教学法》;写作思想
唐彪认为阅读和写作是紧密联系的,它们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是花与蜜、蚕与丝的关系:“蜂以采花,故能酿蜜,蚕以食桑,故能成丝。倘蜂蚕之所采食者,非桑与花,则其成就必与凡物无异,乌得丝与蜜乎?乃知士人所读之文精,庶几所作之文美,与此固无异也。”[1]对此观点,仇兆鳌在“序”中也作了精辟的论述:“盖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不汲汲于为文而文愈工,此唐子辑书之大意也。” [2]阅读是“养其根”,“加其膏”,写作是“俟其实”,“希其光”。只要“养其根”就能“获其实”;只要“加其膏”,就能“希其光”。其含义是很清楚的:阅读是写作的基础,写作是阅读的应用,二者是紧密联系,浑为一体的。[3]
阅读对写作的作用有:第一,积累材料。唐彪认为童子开始读书,应该让他多读学问、政事、伦理、品行等方面的书,这样在作文时就能有所取材。如果前期不进行资料积累,腹内空空,一定写不出有过人之处的好文章。第二,阅读可以熟悉文题。通过分类读文,熟悉不同的文题,可以周知题窍,做起文章来就得心应手。唐彪主张多读经史古文:“故读经史、古文,则学充识广,文必精佳;不读经史、古文,则腹内空虚,文必浅陋。” [4]第三,阅读可以扩充才思,流畅笔机。学生通过阅读文章,理清作者思路,可以拓宽自己的视野,达到扩充才思的目的。同时,学生对文章十分熟悉以后,在作文时就会自然而然的加以运用。为此,唐彪建议初学者先读唐宋古文,并且要随读随解。因此,唐彪认为只有坚持读写结合,以读促写,才能写出气味深厚,丰采朗润,理有馀趣,神有馀闲,词尽而意不穷,音绝而韵未已的涵养之文。
阅读是写作的基础,这是唐彪写作思想的基础论。学生要想写出好文章不仅要进行大量的阅读,还必须掌握一定的方法。
1.文章要多做
唐彪对学人重读轻做的弊病进行了批评,认为“学人只喜多读文章,不喜多做文章,不知多读乃藉人之工夫,多做乃切实求己工夫,其益相去远也”[5],并指出了这一弊病存在的原因:学生有畏难之心。学生之所以畏难,一方面是由于“内无家学、外无师传”,导致“学无根底,识不高,不能置身题上” [6]。另一方面是学生的畏难情绪使然:“人之不乐多做者,大抵因艰难费力之故,不知艰难费力者,由于手笔不熟也。” [7]
要消除学生的畏难之心,一方面要在阅读上下功夫,精读、细读,“与我为化”。另一方面则要多做文章,“盖常做则机关熟,题虽甚难,为之亦易。不常做,则理路生,题虽甚易,为之则难。” [8]但是,唐彪所谓的“多做”并不是指实行题海战术,多做是指在学生阅读达到一定量的基础上,围绕某一命题运用已习得的方法,表达自己观点,检验自己写作水平。在作文的过程中,学生应认识到以下几点:首先,要在充分阅读并熟悉各类文章的写作方法并借鉴前人有益经验的基础上开始作文,这样才能行文流畅、呼之欲出。若不熟悉各题做法,没有一定的知识和方法积累,作文只能是一件难之又难的事情。其次,作文的过程应该是循序渐进、灵活多变的,“若荒疏之后,作文艰难,每日即一篇、半篇亦无不可,渐演至熟,自然易矣。” [9]过高地要求自己,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反不利于文章的写作。再次,不可因为习作的不佳而生懈怠之心,懒于做也。习作不佳而懒于作文,以至于以后习作更差,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一次不佳,再作一次,随着时间的推移,认识的提高,一定可以使文渐佳。最后,要想使文章取得进步,学生可以借鉴唐彪提出的专一致功的写作方法。唐彪曰:“平常作文,非不用力,然未用紧迫工夫从心打透,故其获效自浅” [10],做文章应专一致功,即专门抽出一至两个月的时间,发愤作文,这样才能有所提高。并且在文章写成之后,尚需请教明人详阅,则这样才能认识到文章的好坏,“不然又无益也。”
2.文章宜多改
唐彪曰:“文章最难落笔便佳。如欧阳永叔为文,既成,书而粘之于壁,朝夕观览,有改而仅存其半者,有改而复改,与原本无一字存者。欧公尚然,人可以悟矣。” [11]因此,唐彪认为“文章不能一做便佳,须频改之方入妙耳” [12],提出了教师修改和学生自改的改窜方法。
教师修改学生的作文应“随其立意而改之”,立足于学生的思路,把可改之处进行修改,不可强改,“改亦不佳者,宁置之。如中比不可改,则置中比,他比亦然。” [13]盖不可改而强改,徒劳无益,反而增加学生对所作之文的隔膜,使学生难以理解。“惟可改之处,宜细心笔削,令有点铁成金之妙斯善矣。” [14]对于教师修改过的文章,学生应认真阅读,“细心推究我之非处何在,先生改之妙处何在” [15],以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由于教师门徒众多,批改作文又耗时费力,不仔细修改学生又不能受益,唐彪提出了在教师的指点下令弟子将文自加细点,提掇、过渡、出比、对比,皆自划断的改窜方法,认为阅者可省思索之劳。
唐彪认为文章“捶炼而后精,不捶炼,未必能精也。淘洗而后洁,不淘洗,未必能洁也。” [16]这就是说一篇精美的文章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落笔之时与脱稿之后,应该加以润色。但是,“文章初脱稿时,弊病多不自觉”,唐彪建议文章写成之后,先搁置一段时间,然后再反复修改。这样做是有据可循的,一方面,学生在写文章的时候,思路可能不够开阔,“心思一时多不能遍到”,过数月之后,“遗漏之义始能见及”,所以易改。另一方面,写作初稿时,学生可能“执着此意即不能转改他意”,而数月过后,“心意虚平,无所执着,前日所作,有未是处,俱能辨之”,所以易改。因此,文章写成之时能改则改,“不然且置之,俟迟数月,取出一观,妍丑了然于心,改之自易。” [17]
3.文章需一题多做
佳文最难得,一篇好的文章不是一挥而就的,需要经过反复的思考、锤炼。唐彪把作文形象地比喻成攻玉:“今日攻去石一层,而玉微见,明日又攻去石一层,而玉更见,再攻不已,石尽而玉全出矣。” [18]而“攻玉”之法,除了上文提到的改窜补正,唐彪还提出了精研细琢的深造之法:“如文章一次做不佳,迟数月将此题再为之,必有胜境出矣;再作复不佳,迟数月又将此题为之,必有胜境出矣。” [19]这种改窜旧文,重作旧题的深造之法即“一题多做法”。
古今中外,即使是大家名家,他们超凡脱俗的作品不过数十篇,最多的也不超过百篇,其他的都是平淡无其的平庸之作。那些超凡脱俗的作品,“或系一时而就,或系数日锤炼而就,或系他年改窜而就,非拘定一日所作也。” [20]因此,学人不必因一时之间自己的文章不佳而生退怠之心,更不能将它毁弃,权且暂时搁置起来,迟数月,仍以此题再作,“有一篇未是之文,反触其机,即有一佳文出焉。” [21]
对于学生而言,一题多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学生的第一遍写作是在拿到题目之后就开始的,他们在简要分析题目并在大脑中搜索相应材料的基础上就形成了初稿。这时学生往往会顾此失彼,急于想表达大脑对于这个题目的第一印象而忽略了其他内容。文章写成之后,虽有不满之处,却执着于第一印象,不舍得删减。把题目搁置一段时间以后,学生重新写,由于有了第一次审题立意的基础,学生会更多地关注其他细枝末节并用更多的精力来谋篇布局、修辞炼句,从而写出一篇较高质量的文章。
4.文章必细研作法
前述阅读是写作的基础,文章要多做,文章宜多改,文章应专一致功,文章需精研细琢等属于唐彪写作思想的“基础论”和“基本方法”。对于学生而言,只有基本的理论和方法指导是不够的,还需要认真锤炼作文的技巧。唐彪在《读书作文谱》第六卷专论作文的总体大法,即一篇文章的写作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几个主要环节的处理方法,包括临文体认,细思神理;布格定局,善于变化;修辞用字,锤炼润色等。
临文体认,细思神理。拿到一个题目之后,首先要审清题意,“必不可轻易落笔”。把握了题目的虚实之后,要构思全篇的布局,“定一稳当格局,将所有几层意思,宜前者布之于前,宜中者布之于中,宜后与末者布之于后与末。” [22]构思布局时还要根据题意确定篇幅的长短,“题无可阐发者,不可使之长,长则敷衍枝蔓矣;题应重阐发者,不可疎令短,短则意不周详,词不遂畅矣。” [23]还要根据题之长短虚实,定表述之分合详略,“短题贵分,分则意思多,议论亦多,文未有不优者;长题贵合,合则头绪不纷,说理减省,布置整齐,词彩冠冕,文亦易于见长也。” [24]
布格定局,成竹在胸。唐彪曰:“作文之时必须定一格,以为布置之准则,而文乃成片段。” [25]因为“文章全在布置,‘格即布置之体段也。这就是说,在临文体认之后,要选取一个角度来布置段落,做到成竹在胸。要在充分了解题理、题窍、种种运用法的基础上布格定局,“若能知夫题理、题窍与种种运用法,则一题虽有多格,必能辨其孰变、孰正、孰下、孰高,意欲为此,机亦来随,词亦来应也。” [26]
修辞用字,锤炼润色。唐彪以写“华实俱成”、“文质兼美”的目标,从语言风格形式和声调等方面,对如何修辞用字进行了多角度的论述。一方面,唐彪强调词以达意,不可不修饰字词,“捶炼而后精,不捶炼,未必能精也。淘洗而后洁,不淘洗,未必能洁也。” [27]另一方面,唐彪反对过分修辞琢句,浮靡雕绘,“古人谓不必修词者,非欲废如此之词也,但不欲浮靡雕绘也。古人谓必宜修词者,亦止欲词如此也,岂尚浮靡雕绘哉?” [28]
参考文献:
[1]、[2]、[4]-[28] [清]唐彪辑著,赵伯英、万恒德选注:《家塾教学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
[3] 万恒德,读写结合成一体[J],盐城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