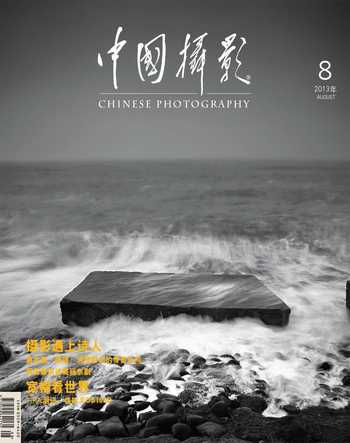“牺牲”
陈建中
今天早晨坐在桌前准备写专栏,突然停电了。连在网上的无线信号突然消失,搜索到一半的网页戛然而止,留下一片空白页。
这是礼拜天,我在内罗毕一所大学的宿舍里。
每天都习惯了的网络生活在这一瞬间突然终止。窗外传来远处教堂清晰的歌声和近处不远的鸡鸣。索性合上电脑,带着录音机向教堂走去。
一班年轻男女正在跟着老师练习合声,此起彼伏的男女和声随着老师的点拨时断时续。老师带着斯瓦希里口音的英语虽然对我来说不太容易听懂,但提到的一些词我明白她教导学生的要义。她反复强调着“牺牲”(sacrifice),教导她的学生,要练好和声需要的是个人的牺牲精神,我的理解也就是全身心的投入。
前一天,和我同事一起去内罗毕最大的一个贫民区。听说那里一帮热爱足球的孩子用废旧报纸自制足球来练习。车到目的地,看到的是一个没有草坪修饰的泥石球场,孩子们在满是碎石的球场上奔跑,既没有专业的球鞋,也没有像样的球网,但是每个人的专心致志渗透在每一次奔跑之间。
艺术是什么?体育是什么?那一时刻,我想得更多的是:摄影是什么。
摄影可以是一个动词,也可以是一个名词。作为动词,摄影除了按快门的这个行为之外,更多的是摄影这个行为的社会意义和作用。而作为名词,除了照片这个物体标本之外,更重要的是摄影作为一个信息传播媒介的社会影响和效果。所以无论作为动词或者名词的摄影,很重要的都是心的感受和表达,而摄影的行为或者媒介物只是心灵感受和表达的中介过程。
物质的发展和诱惑在这个世界上既快速地在纵向上由北向南的成长,同时也在横向上由西向东的扩散。技术的更新期越来越短,广告的刷新率越来越频,社交媒体把人每一秒地拴在不断的刷新中。快速的生活节奏很难使人有机会停下来喘口气,听一听自己的心跳,看一看别人的眼神。越来越多的人跟随着广告把摄影设备做着周期性的更新,在一次旅游的末尾筹划着下一次旅游的开始。
不记得在何处看到一篇摄影交流的心得,一个资深的风光摄影迷教导跟随他的摄友们,要拍得好的风光照片,需要多看风光明信片。记得很久以前,当时的美国《大众摄影》有过一篇摄影技术发展展望的文章,其中预测未来的图片范式识别系统可以将摄影史上所有著名照片的构图范式储存在相机里,当摄影者移动相机取景时,只要取景框中的画面构图和储存的经典图式相吻合,相机便可自动将此情此景拍摄下来。好在至今这种模式吻合优先的摄影技术还未问世,否则每家每户的电脑相册里都储存了相同的精美图片,而且明信片市场一定垮台。
这样的摄影,无论从行为上还是作品上,其实都是一种快速求成的捷径意识,这种意识很容易借助物质的支撑来实现。自从20世纪末数码技术开始大规模渗透以来,摄影在技术和经济约束上完全脱离了自19世纪30年代发明以来的层次界限,但在摄影行为的社会意义和作用以及媒介的社会影响和效果上,却还在依样画葫芦的圈子里兜兜转转。所有的创新除了技术层面的旧翻新或形式层面的元素替换,很难看到那种有着“牺牲”精神的忘我尝试,那种泥地上练球的一腔投入。摄影的媒介越来越普及,但是摄影的行为和摄影的形式却越来越单一。
的确,时到如今,摄影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几乎尝试无遗,这就给摄影者的自我“牺牲”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在聆听着那班年轻人练唱时我就感到,真正的“牺牲”是那种精益求精地寻求那不经意间忽略了的完美细节,而不是刻意地去追求那绝对相似的经典范式。摄影的创新,或许就在摄影的行为意义上始终挑战自己为什么去按下快门,在摄影的形式效果上永远质疑自己为什么去舍弃或者强化画面的元素,就好像踢球,追求的是球的运动以及结果。
行文至此,电来了,我又回到了那个虚拟的空间。相似和相异的形式和信息又充满了屏幕的搜索引擎窗。如何从这些纷繁的信息里解脱,像那班练唱的年轻人,用“牺牲”来换取独特的完美,这也成了摆在我面前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