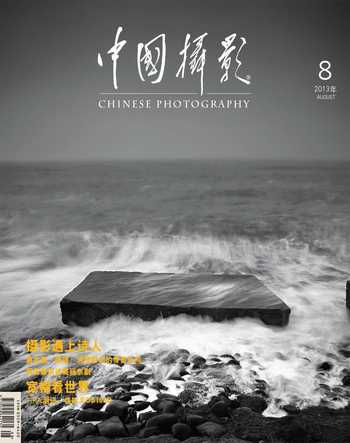肖像摄影中自主和自由的权利对我很重要
唐晶



T:我们的访谈通常都从简历开始,所以请先向中国的观众介绍一下您以前的经历吧!
S:我在比勒菲尔德和杜塞尔多夫学习过视觉传达。先是从比勒菲尔德开始然后转到杜塞尔多夫,我在这里也一直做摄影助理,杜塞尔多夫挣钱的机会要好一些。后来我在杜塞尔多夫毕业并拿到了学位(旧学制的Diplom)。这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
T:您跟谁学习的呢?
S:我当时所在的杜塞尔多夫应用科技大学(并非我们常说的“贝歇流派”所在的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是没有班级制的, 所学的东西很广泛。我给一个美国摄影师比尔·斯图尔特(Bill Stewart)做助手,他是一个很老的美国商业摄影师,从他那里我学到了很多在摄影棚拍摄的知识。我的教授莫森是个强调观念和图形的人,所以我找到了一个连接点,把书和照片结合起来,这是我感兴趣的地方。在应用科技大学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能够学到很多关于印刷的知识,这些体现在我和卡特娅(Katja Stuke)[8]现在所出版的书上面,当时是完全没有想到的。
对于摄影我起初的想法很幼稚,我只是单纯地去拍,并不知道摄影应该用来干什么。幸好我的父母都非常好,他们也没有问什么,而是完全放手让我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给商业摄影师做助手,完全没有机会接触艺术学院或“贝歇流派”的摄影师。桑德的作品我是很久之后才看到的。那时我对摄影杂志更感兴趣一些。通过理查德·阿维登(Richard Avedon)的“在美国西部” 系列( In The American West),我也研究过许多像阿维顿这样摄影师的作品,从中学到很多技巧。罗伯特·梅普尔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1946-1989)对我的影响也非常大。通过对他们作品的学习,我慢慢地总结出了我自己的东西。我差不多从1999年才开始从事严肃的当代观念艺术创作,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有人看中了我第一本摄影集上的作品,然后科隆摄影与文化收藏基金会开始收藏我的作品。那时他们成系列的收藏有纪实摄影传统的作品,比如桑德和贝歇。我的作品也被列入其中,从此我开始专注于当代观念艺术方面的创作。
T:我见过很多拍摄亚文化和年轻人的作品,为了得到强烈的画面氛围,它们多半是令人不安的场景、晃动的画面和伴随强烈阴影的闪光。比如黛安·阿勃丝的作品刚发表的时候就一度给人非常不舒适的感受。但是您的作品有非常干净的画面和光线。您是如何做出这样的选择的?
S:这里的重点其实反映的是人和人之间的相互看法和反应,而不是人们对图片本身的美学做出的反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观众的反应可能也会发生改变,这其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观众带着怎样的期望去看展。有时在博物馆挂上彩色照片就能起到令观众震惊的效果。所以我只能说,我们不能泛泛地认为文化是“脏”的或者类似什么,这一点可以结合我的作品来说说。我的作品不是因为我觉得什么东西“脏”或是什么而表现某种具体的对立,我用的是另外的方式。南·戈丁和黛安·阿勃丝她们那么去表现是没有问题的。还有沃尔夫冈·提尔曼斯,他也是完全不一样。
如果我们现在谈论亚文化或与之密切相关的青年文化,我感兴趣的则是对个性的追求以及身份认定。我就是这样进入到音乐和社会的领域:音乐怎样影响社会和年轻人,其中产生了什么变化,人们如何看待偶像等问题。比如说摇滚和朋克音乐在中国流行得比较晚,不过当我们在北京时也找到了一些独立唱片店,都是些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我们也听了许多的演唱会,比如朋克、乡村摇滚、重金属等。所以我也在中国拍摄了一些照片。
T: 这些您都拍了并做了展览吗?
S:是的,都在我最近的一个项目《幻想俱乐部》里面,可以网上在线观看。我只做了8本小批量的艺术家手工书,最近也可能会做多一些的版本。
中国是一个流行音乐和青年文化运动开始得相对较晚的国家,它将怎样来接收这些外来的文化?不过在中国谈论音乐,谈论青年文化或者亚文化归根结底还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和卡特娅也去过北京一些小型酒吧和俱乐部,比如MAO Livehouse、老what酒吧、D-22俱乐部等。音乐提供了一个平台,它使人们聚在一起,人们通过对音乐的思考找到一种展示自己的方式,从父母一辈的思想以及主流文化中分离开来。
T:我个人的印象中,欧洲的亚文化比如朋克、哥特和摇滚等都有很强的政治和历史背景,对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亚洲的类似的亚文化都有一种很“甜”的感觉或是很强的娱乐性,您怎么看待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区别?
S:我觉得你说的“娱乐性”很有意思。我有一本画册叫《角色盗窃者》,这本书中我所努力表达的,其实是我对这种“娱乐性”严肃认真的观点和视角。
这个系列我是从杜塞尔多夫开始拍的,因为日本文化对这个城市的年轻人影响很大。年轻人被一种完全陌生的文化吸引并接受了这种文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再谈论和思考身份认定的问题,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不光只是Cosplay,还包括任何一种通过服装、装扮和面具来(将自己)归类的形式。这种扮演的结果是人们可以通过服装的形式明显地增强自身的辨识度,在室内更是如此。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角色扮演者的房间中拍摄,因为我需要这种强烈的对比。他们中的很多人还在家中和父母住在一起,感觉像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角色。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日本动漫,会发现其中很多严肃的主题和角色。刚开始玩Cosplay的年轻人会完全沉浸在故事情节当中,他们每天放学之后花上几个小时投入其中,自己动手做服装道具,这是我欣赏和尊敬他们的地方。所以在我的作品中我可以把这种想法更强烈地表现出来,我觉得这很有意思。
T:您刚才提到年轻人学习漫画和动画?
S:我的意思是说这些年轻人很努力地研究动漫中的人物角色,比如说他们可以尝试不同的性别和角色。男孩可以去扮演女性角色,女孩也可以反过来扮演男孩。年轻时可以尝试各种新鲜事物,这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成长过程,这是非常宽容的一种现象。如果拿朋克和摇滚等亚文化形式和Cosplay做一个对比会发现,Cosplay是相对封闭的,它并不是一个青少年运动,也没有试图去改变这个世界。它只是一个自身循环的运动。这在欧洲、加拿大等我工作的地方都是如此,在美国我和角色扮演者的交谈比在日本的更公开,而且我在日本也没有那种到处都是Cosplay扮演者的感觉。2006年我和卡特娅拿到奖学金去日本,在那里认识了两位很友好的策展人,她们帮了我们很大的忙。我们去到一些比较隐秘的地方,比如一个普通的活动大厅,很多玩Cosplay的年轻人通常都在里面换衣服,这样外面的人都看不到他们的服装道具。
T:我自己有时候也想拍一些关于Cosplay的作品。但是当我一想到这个题材头脑中马上就出现了您的作品。我不觉得我能比您做得更好或是找到其他的可能性了。所以接下来其实是一个关于摄影作品相似性的问题,比如说“贝歇流派”的摄影师,他们一开始拍的几乎都差不多,那么您怎么看待这种摄影中的相似性?
S:这种相似性只是因为摄影的题材总是相似的。摄影的基础是你对什么感兴趣,什么打动了你。如果有人说对cosplay感兴趣,那么你就得认真思考打动你的到底是什么。有人尝试过照着我拍摄的照片找到同样的扮演者,又一样地拍摄一遍。我看过这样的照片,觉得这样的照片真差劲,根本不需要再拍一遍。但是有意思的是,这种类似的现象总是不断发生。在研究和学习的过程中你可以这样去效仿,一旦这个过程结束后你必须要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基本上可以这么说:“OK!我对Cosplay挺感兴趣,但是我能用它来做什么?”这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另一方面来说我知道很多角色扮演者会用很多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展示和拍摄(他们注重的是服装本身和角色的展示,从中获得乐趣),我觉得这个没意思。同样,他们会觉得我的作品没有意思,这些都是无所谓的。我们注意的是完全不同的方面。肖像摄影本身是一直存在的,问题在于人们怎么看待它,用它来做什么,怎么通过它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念。当然从纯粹的美学角度来说摄影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比如说它可以是挂在墙上的一张照片,也可以出现在杂志和画册的一个角落。它可以很巨大,也可以非常小。它的材质可以高亮发光,也可以是绒面不反光的。而所有的这些表现形式,都会影响这些图片以及和图片之间的对话。
比如说“日本亚文化”系列(J-Subs),如果观众先只在网上观看,再看实际版本,都会吃惊地发现,原来这些照片这么小。他们肯定会想:杜塞尔多夫的摄影师拍的浅灰色背景的肖像,那自然是两三米高的照片。而事实上它们就是这么小而已。
T:嗯,这就是您作为摄影师个人的选择?
S:是的。在这个系列我想把我所拍摄的全部作为一个整体都呈现出来。照片的原文件其实是很大的,但当我把它们排成三排时,观众可以把它当做一张照片来看待。当然我也可以把它们重新排列或者单张展示。作为一个观看者我所看到的是社会的一个片段,成千上万的符号和标志等等。
T:那么在“日本亚文化”系列中,为什么拍摄对象都不是看向镜头的?
S:这有几个原因。首先一个是只有四分之一或是四分之三面能很好地表现这些人物的头发造型。这其实是个挺无聊的理由,但是有时就是如此。比如易洛魁人(Iroquois)的莫西干头(Mohawk Hairstyle)[9],如果从正面拍摄就只看到一条线,其他什么也看不到了。发型作为一个标志,要传达我想表现的东西就必须让观众很好地看到。所以侧面拍摄是从视觉上表现符号的一个选择。
不过这其中我觉得恰恰重要的就是他们这种没有看向镜头的目光,不管是向左还是向右,它们不仅仅打开了一种空间,而且是一种思考。这种思考是我对肖像摄影的一种理解,它能拓展自身(肖像摄影的含义),也是我特有的一种表达方式。我作为观看者得到了很大的自由,进入或参与到拍摄对象(的世界)中,同时拍摄对象也有很大的自由。这种自由的权利是我非常看重的。
T:现在我理解了。可以这么说,当拍摄对象直视镜头时,无论哪种方式,其实就已经是一种摆拍的状态了。因为他们被告知现在处于一种拍摄的状态。如果像您这样拍摄,人物好像就被什么打断了注意力,而处于一种思考的状态。
S:是的,如果别人的目光没有跟我直接对视,那我们之间就不会产生直接的对话。作为一个观看者我通过其他人的想法来思考问题,因为我并不知道别人在想什么,于是我通过照片来独立表达自己的想法。
如果拍摄对象看着镜头,那么我们就必须始终主导对话,我们必须引导照片上的那个人,因为他看向我们,就再也看不到其他地方了。这是一种固定的模式和固定的图片,拍摄对象失去了控制自己的权利, 不同的观众对照片的评价也都是一样的。所以我选择这样处理,要求拍摄对象不要看向镜头,不要笑。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停顿,好像人沉浸在他自己的思想中。对我来说(观众)可以用这种方式进入我的照片或是我们之间的对话。
最后还有一个理由是,如果观众不是持续地看着被拍摄对象的眼睛,那些带有象征意义的小东西就会变得格外明显,比如说那些小徽章、贴纸、或是掉落在肩膀上的发屑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这些东西都变得有视觉上的意义,相对来说人们对这些东西会感觉更明显和获取更多其他信息。
T:您还有另外一个“盲人”系列,它们也属于亚文化的范畴吗?或者这是另外的一个拍摄项目?
S:并不是所有我拍的东西都得归入亚文化,亚文化包括的范围很广。青年文化、亚文化、反文化、另类思维,这些才是我作品所表达的核心内容。
“盲人”也是我一个比较长期的拍摄项目,它的意义在于,作为一个用照片与外界进行沟通的视觉工作者,我该如何与这些完全生活在无图形世界的人达成理解和交流。照片是否有其他的表现形式?这些是否又会产生另一种交流?这一点也从摄影集的名字中很好地体现出来。
“盲人”这个系列被我收录在《幻想俱乐部》一书中。封面上的这个小女孩从未看过这个世界。此时她面对镜头,看起来像是在享受着这种相互间的交流。于是我问自己:我作品的意义究竟在哪里?观看和摄影的意义又何在?相比视觉其实感官更为重要,这一点在“盲人”这个系列中显得更为强烈。人们怎样表现身份认定和个性特征?比如许多人通过发型来表现。然而这些对于盲人来说毫无意义,因为他们看不见这些符号也无法解读和获取信息。不过也有一些盲人青少年,他们喜欢嘻哈和朋克音乐,也想模仿他们的偶像那样打扮。他们也和朋友逛街买衣服,让其他人知道自己的喜好。也许在其他人看来这并没有什么意义,这种被其他人的否定引起了我的兴趣。事实上我所做的这些让我在盲人的世界里感觉很不自在,从这一方面来说还是回到了身份建立的问题,我该如何给自己定位。
T:您后来和卡特娅一起做了很多有意思的摄影项目,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这些项目。首先您能介绍一下你们的合作吗?
S:我们到现在已经一起工作了13年。在“B?hm/Kobayashi”的网页上可以看到很多信息。我们第一次认识是在布伦瑞克摄影博物馆(Museum für Photographie Braunschweig)参加展览。我们从1999年开始做杂志。我们把所有一起做的杂志、书籍、项目和展览都衔接在一起。后来我们共同策划展览,比如说“反摄影”(ANT!FOTO)和“反摄影宣言”,通过这些把我们各自的兴趣结合在一起,在这些项目中也介绍了很多其他的艺术家及作品。
T:“B?hm/Kobayashi”是你们一起建立的一个出版社吗?
S:不是的,它只是一个出版项目的名称。以前我们出版的杂志叫“伯姆女士”,“伯姆”或是“伯姆先生”。后来我们到了日本以后,有了一个日本名字“小林”(Kobayashi),我们觉得把这两个名字放在一起听起来很不错,这样我们就像一个全球化的公司了。这是一个比较自由的项目,有时候我们做杂志出版,有时候以这个项目的名义做展览。这个项目其实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好像突然作为另外一个人,在这个人的名义下可以自由地尝试摄影的各种想法,同时也不会影响到作为摄影师做的那些正式的作品。
T:那么“伯姆中心”(B?hm Handelszentrum)是不是一个画廊呢?
S:不是的,那只是一个网络的展示空间。在“B?hm/Kobayashi”项目中,我们只是展示了我们自己的作品,我们当然也对其他摄影师的作品非常感兴趣。所以后来我们就做了“伯姆中心”,它是一个网络上的展览空间,它是对真实展览空间的一个记录然后在网络上展示出来。不过出于对“反摄影”这个项目的偏爱,也许什么时候我们就不再做网络展示了。我们还是对把图片悬挂到墙上在空间中做真正的展示更有意思一些,网络毕竟只是一种比较廉价的展示方式。
后来杜塞尔多夫市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场地办展,那种感觉太棒了。在真实场地中看展跟坐在电脑前观看虚拟展览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体验,而且环境也不一样,在真实展览中能使人更加进入到作品中。
T:再请介绍一下“反摄影”这个项目,是从2010年至2012年的一个长期项目吗?
S:是的。这几年我们在杜塞尔多夫做了三次大的展览作为“图片周末”的活动,由颜料盒艺术中心(Künstlerverein Malkasten)提供的空间。颜料盒艺术中心是一栋非常漂亮的超过150年历史的老房子,这里经常会有作品在酒吧、餐馆或陈列柜中展出,所以它和那些白色立方体式的现代建筑看起来很不一样。它后面还有一栋建筑,我们邀请了著名的摄影收藏家威廉·舒尔曼先生(Wilhelm Schürmann)做了一个他的藏品展。舒尔曼先生是德国著名的摄影和艺术收藏家,他的藏品展也非常成功,也由此带给我们许多新的想法。
T:我觉得“反摄影”提出的主题非常好。“摄影可以是什么?它是草稿、装置、记录和态度”。
S:是的,我们需要一些挑衅。我们本来只是要一个宣言来做杂志,但是现在我们每一次展览都做了杂志和访谈,所以我们既有了作为杂志的宣言又有了展览。我们没有打算要一辈子去做这个项目,但是我们已经做了三年,它接下来如何发展,我们将拭目以待,因为做一个展览真的是需要做很多工作。
T:“反摄影”项目中我对一个雕塑家拍的自己作品的照片很感兴趣,通过“反摄影”的杂志和宣言,我突然意识到,哦,摄影原来也可以是这个样子的。
S:我们每次当然都是找了很多优秀的作品来展示,每次都是6-8个艺术家的合展。这样当你去看这个展览的时候,会对摄影有一个很好的感觉。不过你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人们可以去思考,摄影的其他功能和多样性是什么。比如你说的皮娅·史泰特伯伊默(Pia Stadtb?umer)[10],作为一个雕塑家她做了很多优秀的作品。我们问她:“你制作雕塑的每一步是不是都有照片的草图?比如说一个小孩,从各个方面和角度拍摄下来并做成雕塑?”她说:“我这辈子的工作其实都是这样做的,摄影是我雕塑的基础。”她给我们看了她的照片记录,我们可以随意寻找我们感兴趣的东西。那确实是些很好的照片,冲洗质量也很好。当我们最终看到她的一个白色雕塑时,我们又在她的摄影中看到了这个雕塑的一个阶段,摄影打破了对这个雕塑的一种氛围。这些照片是我们感兴趣和想展示出来的。我们帮她放大和装裱了这些照片,这对她来说也是一种实验,不过她非常地开放。与一个信任你的艺术家工作真的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我们也很高兴看到摄影捕捉的雕塑制造中的一个过程。她确实是个很好的例子(反摄影主题中提到的摄影作为草稿和记录)。
T:您在自己的网站上销售杂志和画册,这些都需要国际标准书号(ISBN)吗?
S:一般是不需要书号的。如果要的话,小批量印刷的书号大概是60-80欧元。也有一些非常传统的出版社,他们有自己的工作系统。如果他们没有书号系统的话,很多资料和书就无法查阅。其实现在只要在谷歌中搜索,就能查到想要的书目。所以对于我们这样小批量印刷的出版物来说,书号不是绝对必要的。由此也发展出来一些摄影的独立书展,比如说 “单行本巴黎”(Offprint Paris)[11],都是一些作者自己制作的摄影小书,不知道哪些顾客会来买或是什么样的人会感兴趣,但是却做得非常有意思。
T:您接下来有哪些工作计划?
S:《幻想俱乐部》我已经做了很长的时间,现在摄影集已经完成,接下来要开始做打印的产品,还有7月份在法国阿尔勒和明年在瑞士的展览。所有这些事情都必须精工细磨。
其他的工作我还得分类整理然后再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做。我并不急着立刻开始新的作品,因为之前的作品现在还需要细细品味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