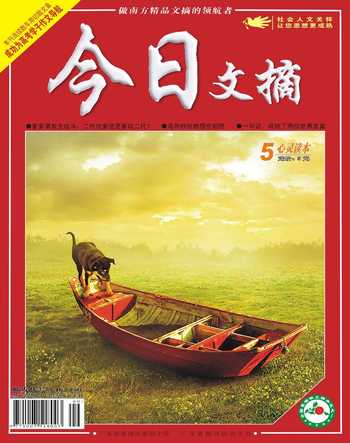一方小小的瓷盘
余显斌
案头有一个瓷盘,白色的,但又不是纯白,白中透出隐隐约约的青蓝色,如天光中透出的薄雾,如似醒非醒的梦,如淡淡的天青色烟雨。总之,青色很淡,几乎看不出。
其余,再无异色,也无其它图案。
这样最好,我喜欢纯洁、简单,无论是做事,还是对人对物,都是如此。
一日清闲,我到河里转悠,清清的水里有几颗鹅卵石,颗颗滚圆,大的如鸡蛋,小的如珠子,我拾起来拿回家,无处可放,堆垒在盘中,再倒一点水,既有山的雄奇,又有水的娇媚,一盘之内,奇山秀水,荡漾在目。写罢文章,面对瓷盘,想象中,山在放大变高,水在变宽变深,自己摄衣上山,看万山红遍,暮云遍野,湖水荡漾,竟感到一身轻松,洁白如月。
不久,孩子把石子拿去,参加学校一个展览,再没拿回来。
空空的瓷盘里,只有一盘清水,泛不起一丝涟漪。
那日,写罢文章,想想,去了房边。房边有一沟渠,一泓清水缓缓流过,水虽小,却也汩汩有声,做断金声,做碎玉声,到了缓处,也聚了一个小小的水塘。水塘中有几星绿,是浮萍,有嫩绿色的,也有墨绿色深绿色的,一粒粒仿佛攒足了动,在凸显着自己的生机。
我一时震惊于这绿。
回家时,我随手捞了几星绿,放在盘中,一盘白水立马有了生机:盘是青色的,浮萍是绿色的,再加上一泓清水,潔净淡雅,如王摩诘的一首小诗。
受浮萍的启发,我又去了河里,在清清水中舀了几尾小鱼,极小极小,粗仅一线,只有两粒眼珠在滴溜溜地动。放在瓷盘里,这些小家伙虽小,却也知道甩尾,虽逗不起水花,却把水逗出一圈圈涟漪,搅得浮萍也随水波一漾一漾的。
有时,太阳光从窗户照下来,白亮亮地照在盘子上,浮萍在水中的影子形成一个个逗点;小鱼的影子淡淡的,一会儿停止,突然又像受到惊吓似的,一摆尾,钻到几粒浮萍下面去躲了起来。
瓷盘,竟成了我一方思想散步的小花园。
一日,有个搞收藏的朋友来,坐在桌前和我品茶,随意地交谈着,渐渐不谈了,眼睛盯在瓷盘上,许久,赞叹道:“这盘,是古物啊。”
我停了喝茶,不相信地望着他。
他让把盘中鱼儿和浮萍,还有水倒入一个玻璃缸中,然后用手巾小心擦干净瓷盘,翻来覆去地看看,又用手指敲着,当当地响。
最后,他用手机给瓷盘拍了照,走了。走时,一再嘱咐,小心,说不定一出手就是几万呢。
这一说,我拿着瓷盘手立马都发颤了:我几时一次性拿过几万元?从来没有过。
朋友一走,我马上把瓷盘小心地用卫生纸包好,装入箱中。以后写作,每次结束,我都会打开箱子,小心翼翼地拿出瓷盘验看一遍,生怕一不小心不见了,或者出现个小缺口。
人在赏玩外物时,如果不带丝毫的物欲,就会有一种轻松,一种享受,如果一旦赏玩带上某种物欲和金钱,则不是人在赏物,而是物在玩人。
一直过了半个月,那个朋友在南方打来电话,说他问了他老师,是赝品,不值钱,大胆用吧。
我心一凉,凉过之后,又一阵轻松,拿出瓷盘,把玻璃缸中禁锢已久的小生命都转移到瓷盘中,浮萍在盘中舒心地绿着;鱼儿,大概觉得宽敞些了吧,尾巴甩得更欢了,竟逗起了几朵水花,溅在脸上,清凉凉的。
这一刻,我的心也清凉凉的,像它们一样欢快。
原来,一颗没有物欲之累的心,竟然如一片羽毛一样,洁净,浑不着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