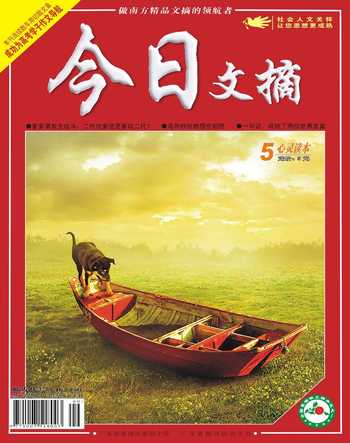最终是人格成就
2013-04-29 20:42:16厉勇
今日文摘 2013年9期
厉勇
法国作家杜拉斯,以私人化写作闻名,但翻她的书,惊见一篇《给范文同主席的信》,她替一位在押政治犯鸣不平:
“他关在您的监狱里已有十年之久了。我给您写信是想提醒您别把他忘了,他仍在押,病了,也老迈了。我并非在要求您釋放他,我只想把自己的声音加入到其他人的呼声中去。他没有犯过任何罪过,只是本着他的良知生活罢了。还要提醒您,本世纪所有的‘政治犯今天都成了英雄,而审判他们的‘法官,都永远地成了杀害他们的凶手,这是值得记忆的。”
仅凭这封短札,即使她再没别的作品,“杜拉斯”这个名字也将被世人记住。
爱因斯坦,这位科学史上最繁忙的人,参与了那么多与“生命事务”“良心事务”紧密相连的事:1914年,参与反战团体“新祖国同盟”;1927年,在巴比塞起草的反法西斯宣言上签名,参加国际反帝大同盟,当选名誉主席;1932年,与弗洛伊德通信,讨论战争心理问题,全力反对法西斯;1950年,反对美国制造氢弹……
若知识带给知识者的信仰与人格保险,不足以成为他们关心“人类事务”最有力的武器和驱动,那么,科学和艺术用什么来答谢人间寄予的期冀和伟大赞誉,仅仅是产品、技术和娱乐吗?
苏联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罗茨基在致哈维尔的信里建议:“你不仅要把你的知识传达给人民,某种程度上还要医治那种心灵疾病,帮他们成为像你这样的人……通过向你的人民介绍普鲁斯特、卡夫卡、福克纳、加缪或乔伊斯,也许你至少可以在欧洲的中心,把一个国家变成一个有教养的民族。”
在大师级人物那儿,你都会发现一个共同点:他们的生命关怀力大得惊人,除了自己的专业之外,其身上还有众多的“外延”,比如反恐怖、反战争、反种族歧视。总之,凡涉及人类生存的根本性问题,他们都很少缺席。荣格说,“学术的最终成就是人格成就”,大概也是这个意思。
猜你喜欢
小学生作文(低年级适用)(2021年9期)2021-09-24 13:24:06
华东科技(2021年8期)2021-08-18 06:27:40
江苏教育(2018年15期)2018-11-21 11:04:44
卷宗(2017年34期)2017-12-28 00:44:52
视野(2017年7期)2017-04-18 07:54:50
黑龙江史志(2017年1期)2017-03-10 13:52:32
读者(2017年5期)2017-02-15 17:14:13
出版广角(2016年12期)2016-09-29 16:47:38
环球时报(2013-02-08)2013-02-08 18:42:52
小雪花·初中高分作文(2009年7期)2009-11-16 05:4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