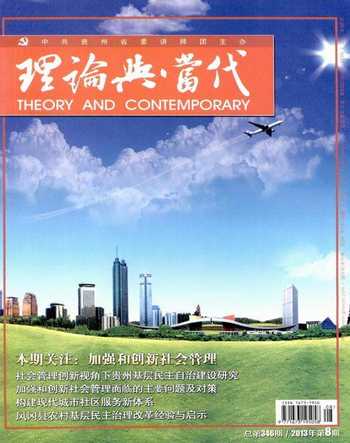基层统计造假的根源在哪里等
王金友在6月19日的《浙江日报》上撰文指出: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广东省中山市横栏镇2012年上报工业总产值85.1亿元,经核查,实际为22.2亿元,虚报62.9亿元。这个结果,把不少人都吓了一跳。现在吹牛的人很多,但也鲜见胆子这么大的。这些吹牛者的胆子,到底从何而来;很简单,从没有人追查。要想查很容易,只要一家一家核对镇里工业企业的生产情况,就可以一清二楚。但没有人干这种事,县里不查,市里省里更不查。像这次被核查曝光的概率,比兔子撞树还低。其实一般情况下,统计造假的起因不是下边而是上边。首先,是上边给下边下达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比如你这个乡镇把吃奶的劲都使上,也只能完成产值1亿元,而上边却给你下达了必须完成3亿元的“光荣任务”。如实报,要挨批评甚至“此官不保”,吹着报,则受表扬得赏识,前途一片光明。更重要的是,那些成功的吹者和不成功的不吹者,都成为自己身边活生生的典型。看近几年暴露出来的统计造假案例,就会发现,这些问题多是“隔级”核查和通报。按理说,一个地方的领导,是很容易发现下级的数字造假的。但由于利益相连。他们不仅自己不查不问,而且极力为其遮遮掩掩。所以我们应该明确一个观点,虚报是造假,纵容虚报和保护虚报也是造假。今后如果像惩罚贪污受贿一样处理浮夸虚报,可能就没有人敢随意造假吹牛了。
近四千万高龄农民工归宿何方
赵昂在6月20日的《工人日报》上撰文指出: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2年我国共有农民工26261万,其中50岁以上的高龄农民工占15.1%,共计3965万人,而2008年时高龄农民工仅为2569万。这些50岁以上的高龄农民工中,许多人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第一批外出打工者,为何这些高龄农民工选择,或者说不得不选择继续工作?其中的原因是多重的。农民工工资虽然在近几年连续增长,但是,在这些高龄农民工的青年时代,农民工工资并不高,他们在20余年甚至更长的打工生涯中,并未随着城市面貌的日新月异而完成个人的财富积累。造成这些高龄农民工不得不继续工作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缺乏相应的社会保障机制。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到2012年,外出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只有14.3%,参加医疗保险的只有16.9%,而在第一代农民工外出打工的时代,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对于他们而言更是天方夜谭。10年后,这些高龄农民工真的再也扛不起水泥,搬不动砖头了,妥善解决高龄农民工的养老和医疗问题,已经刻不容缓了。
专家,莫把自己变“砖家”
诸大建在5月31日的《解放日报》上撰文指出:在眼下的中国,存在着两种走极端的危险。一类是,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中许多知识分子热衷参与学术GDP竞赛,两耳不闻窗外事、自娱自乐写论文;另一类是,一些喜欢发表意见的人往往缺乏学术底蕴,却到处发表蛊惑人心而无知识含量的观点。当下有一些媒体型知识分子,或多或少具有以下特征:一是越过自己的专业,利用媒体这个公共平台,以专家面目对各种领域事件随意发表言论;二是或者提出超越国情的激进批评,或者为滞后的理念蛮横辩护;三是背后往往潜藏特殊利益,比如某些股评家就是这样。事实上,专业知识分子不一定是媒体知识分子,但媒体知识分子必须是专业知识分子。可惜在当下的社会舆论氛围里,只要敢于在公共场合开骂,似乎就能自认为或被认为是专家、知识分子了。于是媒体知识分子变得廉价,专家变成了“砖家”。当然,真正意义上的媒体知识分子不是没有。如当年同济大学校长李国豪在宝钢面临下马危险时,挺身而出为宝铜发展提出科学依据。这里可以看到,专业化能力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如果真正有一批有知识有担当的媒体知识分子存在,真正有一批学有所长的学者能够在相关社会领域发表与个人利益无涉的看法,那么“砖家”的市场自然就会萎缩,专家的社会公信力就会得到增强。
樊纲:我唯一可以提的建议,就是专业
樊纲在5月24日的《人民政协报》上撰文指出:最近有人老问我,今后什么产业好?我说,你别听我的。我要说一个产业好,你信了,他也信了,一窝蜂全去做这个产业了,最后全出产品了,这个产业马上成为过剩产业,产品到时候只能当白菜卖。在中国,我不认为哪个产业是夕阳产业。我们要弄清楚,真正有哪个东西是以后几十年中国不需要的东西?很少。中国在发展,每一个行业都值得去做。做企业是很难。但经济学家唯一可以提的建议,就是要专业、专注!最近几年,有些企业家说不景气,有些企业也倒闭破产。当然这里一定有宏观背景的问题,但是仔细问一下,那些破产的企业,过去几年干什么了?他一定在东张西望想着转产的事,资金也转移出去了,人的精力也不在那了。这么激烈的市场竞争,你不专注了,别人在那专注,别人在那研究品牌、研究市场、研究渠道,一旦风吹草动、经济危机一来,你不倒闭谁倒闭?为什么我国做的皮鞋、袜子就是皮鞋、袜子,为什么意大利做的皮鞋、袜子就是时尚产业,可以引领潮流?我认为,最主要的问题是,在意大利,一家会有几代人兢兢业业搞那个皮鞋、袜子,搞到最后引领潮流,才能够成为时尚产业。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各行各业都有大的发展前途,但都需要各行各业能够专注发展。
中国式用药
李月亮在第10期的《意林》上撰文指出:德国同事卡尔来济南不大适应气候,感冒了。同事们都关怀询问:吃药没?没吃赶紧吃啊。对这种关怀,卡尔比对气候更不适应,私下里问我:感冒不是依靠自身免疫力就能好吗,也需要吃药?第二天,卡尔到我家做客。我妈见他鼻涕一大把,又有点发烧,也一再劝他吃药,完了还不由分说把大药箱搬出来,找了几种来给他吃。卡尔看我妈那么虚张声势,以为中国的感冒比德国厉害,犹豫着决定吃点。可是拿到药的时候他又想不通了,问我:一日2~3次,一次1~2片,到底两次还是3次,到底一片还是两片?我说,都行,你根据症状自己看着吃就行。卡尔简直被吓到了,连连摇头:那怎么行,按最低标准,一天是两片,按最高标准,一天有6片,这怎么吃?于是决定去医院看看。在他的概念里,大医院都要预约,于是坚持去小医院。到了诊所,医生见来了外宾,挺重视,问卡尔:你想打针还是吃药?卡尔又不解:你是医生,我应该听你的。医生说那打针吧,好得快。可是他很快发现,医生说的打针,不是打针,是输液。他从来没输过液,并且以为要死的人才输液。他瞪大眼睛看着护士给自己上吊瓶,欲哭无泪。过了一会儿,来了母女俩,妈妈看样子跟医生挺熟了,进门就问输了5天药了,咋还不见好呢。医生看了一眼小孩说,那今天再换一种,反正咱这儿就这几种抗生素,换着打呗。卡尔听得眼睛都直了。医生给他开了3天的药,但第二天,他死活不再去了。后来他说,他以前在美国待过,美国人也爱吃药,但是他们不会乱用抗生素,为什么中国人用药这么随便?我说,抛开医生乱开药不说,老百姓爱吃药这事说到底还是一种文化惯性,跟中国的很多事情一样,说起来谁都知道不对,但做起来又都照着不对的去了,要改,还真得慢慢来。
张元济拒子承业
刘占青在第13期的《做人与处世》上撰文指出:1932年,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张元济的儿子张树年从美国留学回来后,打算通过父亲的关系到商务印书馆工作。但张元济拒绝了。张元济告诉儿子,进商务有三不利:一是对你不利。你若进了商务,必然会有人吹捧你,你就会失去刻苦锻炼的机会,浮在上面,领取高薪,岂不毁了你的一生。二是对我不利。父子同一处工作,我就要受到牵制,尤其在人事上,很难主持公道,讲话无力。三是对公司不利。你进公司,这将开一极为恶劣的风气,必然有人要求援、人人都有儿子,大家都要把儿子塞进来,这还像什么样的企业、最终父亲的这番话打消了张树年进入商务印书馆的念头。
从日本厕所看到的
刘云枫在5月27目的《中国青年报》上撰文指出:多年以来,我走了多半个中国,许多地方的厕所除了脏,就是臭。欧洲的情况也不好。历史上,欧洲曾几次暴发毁灭性的瘟疫,粪便处理不当是重要原因。但《他们来过日本》(1965年)一书,引述16~17世纪去过日本的传教士的话说:“(日本)厕所内部一尘不染,还放着一个香盘和裁好了的厕纸……每当客人离去后,扫厕所的人会将其彻底清扫一番并撒上干净的沙子。厕所旁会有一大罐清水和其他洗手所需之物。”实际上,在当时的日本,个人甚至并不具有对大便和小便完全的所有权和处置权。江户时期,东京人口有百万之众,其中将近一半的人口是居住在长屋中的外地打工者。房东和房客是这样划分所有权的:大便归房东,小便归全体房客所有。房东和房客,都将其作为肥料卖给江户方圆10英里的农户,或以此交换农民的农产品。一个人的大便值多少钱呢?美国学者苏珊·B·韩利在其所著《近代日本的日常生活》中指出:一般来说,10户人家一年大便的价格超过一两半黄金,刚好相当于19世纪早期一个农民的月收入。不过,经济并非唯一原因,另一主要动力是风俗和信仰。日本号称十万大神,厕神也是其中重要的一位。据说,厕神容貌绝美,主生育和收获。野田圣子曾任日本邮政大臣,也是“高干子弟”,可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东京帝国饭店做厕所保洁。上司来检查,问她马桶洗得干净不干净、野田圣子二话没说,自己从马桶里舀了一杯水,喝了下去。她的誓言是:“就算洗厕所,也要做一名洗厕所最出色的人!”
专家解读王岐山反腐战略
据第19期的《中国新闻周刊》报道,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履新后的反腐战略日渐明确,其反腐决心可窥一斑。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对此进行了解读。李永忠指出,据我的观察和了解,王岐山在反腐方面的战略构想可以从他自己的两个重要观点来概括:信任不能代替监督;打铁需要自身硬,正人者先正己。从这两句话能看出来,他的战略主张有两个方面:其一,纪检监察力量必须加强,首先要加强自身队伍的纪律性。最近强调的清理会员卡活动、清理会所腐败等,都凸显了这一点。其二,加强整合。要缩短战线,集中精力打歼灭战。他近日对巡视工作的强化,正是出于这个目的。王岐山强调当前反腐要以治标为主,治本是方向,前者要为后者赢得时间。因为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和纪检监察体制改革,都未有实质性进展,因此不可能以治本为主,所以王岐山的强调很客观。中国的改革到了三个不得不突破的关口:第一,政治体制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关口;第二,两极分化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关口;第三,反腐困境到了不得不突破的关口。其中,反腐作为改革突破口最为合适。第一,它能取得最大的共识;第二,口径较小,涉及面较小,震慑度很高。
贪官为何仕途一路“绿灯”
据6月18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涉嫌严重违纪被组织调查,云南省楚雄市市长赵万祥因涉嫌受贿被批捕……据媒体报道,倪发科在担任六安市委书记的近十年里,就曾收受某矿业集团“超过了普通刑事的贿赂”,但仍于2008年升任安徽省副省长;赵万祥在担任大姚县县长一职时,就出过一些经济问题,却“没有下文”,直到近期才被提起。这似乎是一个惯常套路:某个贪官“落马”后,公众才惊觉其被一路“带病提拔”。但在东窗事发前,即使通过各种途径举报、信访,都不能影响一部分贪官的“升官发财”之路。统计数据佐证了这一直观印象:近日,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田国良主持的一项研究显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103个副省部级(或享受副部级待遇)以上领导干部的腐败案例中,约有六成(63%)的案主,在作案之后仍然获得提拔。有媒体梳理出与倪发科同在一省之内长期工作的王怀忠、王昭耀、何闽旭3名省部级官员的贪腐经历,发现“带病提拔”已与贪腐数额巨大、持续时间长、家庭腐败、情妇问题等一道。成为这些官员腐败的共性特性,“几乎无一例外”。令人费解的是,“带病提拔”的贪官在事发以前,往往仕途坦阔、一路“绿灯”。“可以说,利益是这些‘带病官员能获得提拔的重要原因之一。”反腐专家林喆指出,“现在有一部分官员‘拉帮结派,结成某种利益团体。一些上级领导要保证自己亲近的人上来,不管他是否有问题。比如一个领导班子中,三个常委都是我推荐的,以后贯彻我提出的决议就比较方便,这就是一种利益牵扯。”林喆认为,对于“带病提拔”官员的推荐者,妊要时须进行“回溯”。“贪官‘落马后,应该去查当年是谁提拔的、谁推荐的、领导当时是怎么通过的。推荐者应负推荐不当的责任,纪检部门监督不力,也要负责任。”
如何避免“能吏”腐败
邓聿文在6月17日的《中国经营报》上撰文指出:刘志军本是铁路最基层的一名养路工,但最后能做到掌管铁路发展和政策制定的一方大员,相信并不仅仅依赖于坊间传说的“桃花运”。客观地说,刘志军在主掌铁道部的8年里,对中国铁路的发展,是做了些事情的,用“能吏”来形容之,或许也不过分。然而。也要看到,在这8年里,铁路体制改革停滞不前,安全事故频出,腐败丛生。据悉,刘志军主掌铁道部期间,是非常强势之人物,强势到连国家想分拆铁道部都无可能。刘是个有着政治野心的人,高铁大跃进实际上成了其博取政治升迁的资本。这是刘在8年部长任内对建设高铁情有独钟,而对铁路体制改革无动于衷的原因。因为相对于发展,改革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不大可能成为其政治升迁的资本。因此,刘案的教训是深刻的。它告诫我们,要遏制这种将一个行业的发展作为领导博取政绩的“赌注”并由此造成的系统性腐败,必须切实拿出决心,进行制度之重构乃至推进政治改革。清除官场的朋党陋习
6月19日的《第一财经日报》刊登社论说,最近中纪委从纪检系统开始清退会员卡的活动,个别省份也开始更大范围的“清退”,最终这样的活动肯定会推向全国。针对“会员卡”进行反腐,绝不仅仅是对奢侈消费宣战,一个更加深刻的原因就在于,通过会所和会员的隐秘方式,官与官、官与商更容易结成“朋党”,进而产生权钱、权色交易。今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在干部教育培训中进一步加强学员管理的规定》,明确要求:“学员在校期间及结(毕)业以后,一律不准以同学名义搞‘小圈子,不得成立任何形式的联谊会、同学会等组织,也不得确定召集人、联系人等开展有组织的活动。”其中的“小圈子”就是一种“朋党”形式,既然不能组织“同学会”,那么以高尔夫球会或者各种高档私密活动为名义的“小圈子”就成为上上之选。在官场中,从一个圈子到另一个圈子,从一个朋党到另一个朋党,其形式和花样总是繁多。坊间流传着“人生四大铁:一起同过窗、一起扛过枪、一起嫖过娼、一起分过赃”。在朋党圈子中,每个人都不干净时,这样就最安全。我们相信,有些官员或许会因为加入这种朋党获得超乎想象的庇护,结成利益共同体。但还有更多的恪守底线的官员,因为不愿也无法加入这种朋党,进而以个体的力量对抗朋党,这样的结果往往是“劣币驱逐良币”。作为害群之马的朋党人数或许不多。但是却足以毁坏整个部门,乃至整个系统的风气,最终祸国殃民。唯有严惩官与官、官与商的朋党,方能澄清吏治,还百姓以太平。
慈善模式创新
刘敬文在6月12日的《晶报》上撰文指出:今年高考语文广东卷的作文题是一道以慈善公益为主题的题目。一个富翁捐赠给三个贫困家庭,第一个接受了,第二个也接受了,但声明以后会偿还,第三个拒绝领取。富翁捐助给第一个家庭,代表着一种传统的慈善模式,你施我受。效果怎么样呢72005年,达沃斯论坛上那些世界上名气最大的人打算给非洲最贫困的国家坦桑尼亚捐赠100万元的蚊帐,以帮助穷人们预防疟疾,可是,这些蚊帐一发放就流入黑市,疟疾的发病率仍然没有下降。富翁捐赠的第二个家庭,受助者采取了一种契约偿还的方式,这其实是现在越来越普遍的注重效率和可持续的新模式。再以蚊帐为例,后来名流们又准备到非洲另一个国家马拉维去发蚊帐,这次就学聪明了,引进了商业管理的技术和手法。公益组织通过马拉维的乡村诊所,以50美分的价钱卖给了孕妇和5岁以下的孩子,护士们每卖出一顶蚊帐,可以获得9美分的提成,这样就确保了蚊帐的发放率。同时,公益组织通过马拉维的私人部门渠道,以5美元一个的价钱把蚊帐卖给城市中富有的人群,这部分的盈利,可以补助蚊帐低价卖给诊所的亏损,使得整个项目自负盈亏。这个做法,让马拉维5岁以下儿童使用蚊帐率大大提高,患病率大大降低。就一个发蚊帐的事,不同的发法带来的效果却不一样,慈善公益人能够从商业管理技术里学习更多,而不应仅仅停留在道德高涨的热情中。
中国企业输在细节
宋文洲在第8期的《中国企业家》上撰文指出:我刚到日本留学不久就发现,我的日本同学们根本不聪明,无论是考试还是写论文,他们都不是我的对手。但有一点我绝对不如他们:细节。比如在绘制图纸的时候,我的纸面一般比他们的脏。在手写文字时,我的字比他们的潦草。教授经常当众批评我。有一天我向教授解释说,我小时候没有训练过画图和写字,所以不像日本同学们那样熟练。教授马上说:“其实我批评的不是你的图和字的质量,而是你的态度。你的图和字怎样都行,但你不应该在图纸空白处留下手印,写字时不应该连笔。”听了此话,我恍然大悟。日本同学从小就养成了保持工作环境干净的习惯,字也是慢慢写。而中国教育的目的就是考试,能解难题怪题是本事,清洁和工整往往被看成雕虫小技。我经常参观中国内地、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工厂。说实在的,就技术和设备而言,中国不但不比别人差,反而更先进的例子有很多。但我们和他们之间差别在细节。中国工厂不是没有规范,而是缺乏彻底的执行。我有个生产高端消费品的朋友,他现在不用国内的工厂。因为国内的工厂成本比国外高。中国工厂什么都有,就是出厂合格率上不去。为了保持合格率,我朋友不得不扔掉不合格的产品。扔得多了,成本自然急速上升,还不如直接委托国外工厂生产划算。中国产业的升级,中国民众的幸福,取决于中国国民从上而下的态度改革。那是循序渐进、一点一滴的个人态度的进步。几十年前,胡适就曾批判中国人的“差不多主义”,今天我还深感差不多注意害死人,这不能不让人悲哀。
古代如何问责冤假错案
倪方六在5月23日的《羊城晚报》上介绍说,在先秦时期,中国古人就开始防范审判不公和司法腐败。《尚书·周书·吕刑》中便提到了刑法审判的五大弊端:依仗官势、挟私报复、暗中做手脚、索受贿赂、谒请说情。若法官在这五方面有失检点,判罚不公,其罪过与犯人相同。为了防止官官相护,还出台了举报奖励制度:如果同事能主动检举揭发枉法官员,不只可免予处分,还能顶替枉法官员职位,享受相应物质待遇。有的人甚至因办错案子而自责偿命。在现代司法界评价甚高、春秋时的李离,官职相当于晋国最高法院院长。因为误听误信。错杀了人,李离十分自责,拘禁了自己,判了自己死刑,尽管国君晋文公重耳都替他解脱,但李离仍拒绝赦免,伏剑自刎。此外,先秦还有纠察制度,为受害方提供申诉渠道。《周礼·秋官》中便有“禁杀戮”的官职,负责纠察法官擅用斩杀刑罚的行为,对故意不受理案件、阻挠他人投诉的法官,一经查出,呈报后即严惩,“以告而诛之”。古代对犯人的羁押期限也有严格的规定。古代称羁押为“囚禁”,法官如果不按规定囚禁犯人,要承担刑事责任。万一案子判错了,怎么办;中国古代在这方面有详细的规定,主要有同职公坐、援法断罪、违法宣判、出入人罪、淹禁不决五种情况,分别论罪。其中,最突出的是“同职公坐”责任。指的是所有参与具体办案的人员,在判决书上均要签字,如果将案件错判了,均负有连带责任,即过去常说的“连坐”。如果非工作失误,采取虚构事实、增减案情的办法,将案子错判,即所谓“出入人罪”,惩罚更重,法官要遭“反坐”:判处和犯人相同的罪行,即误判犯人死刑的,出事法官也犯死罪,且“死罪不减”。
部分地方政府大肆举债
据6月12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国家审计署目前发布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公告显示,一些省会城市偿债率指标偏高,2012年,有9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超过100%,最高的达188.95%,如加上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债务率最高的达219.57%。有13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偿债率超过20%,最高的达60.15%。“目前,地方政府举债已成为比较普遍的现象。只要有条件、有机会都会这么做。”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丁茂战说。财经评论人杨国英曾撰文指出。在近年来基础设施建设已相对饱和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投资;中动之所以仍难消退,除与“保增长”的政绩诉求相关外,还与部分地方政府主政官员的关联利益有关。众所周知,在地方政府财政预决算体系仍不健全、招投标仍存在形式或实质的不透明之下,地方政府通过持续举债,不仅可以推动相关行政主导型投资,实现“保增长”的短期政绩,更可以由此为关联人的利益输送提供便利。丁茂战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为了政绩透支未来的做法不无原因。“部分地方政府的领导风险意识差,为官主要考虑当下政绩,明天之事明日再说,保不准即将升迁或调整更好岗位走人,并且越是在可见时间里可能提拔的人,借钱越无所顾忌。目前,传统政绩导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以GDP、城市建设、形象工程为导向的问题普遍存在。如何科学合理地衡量经济发展的质量,在许多地方没有引起足够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