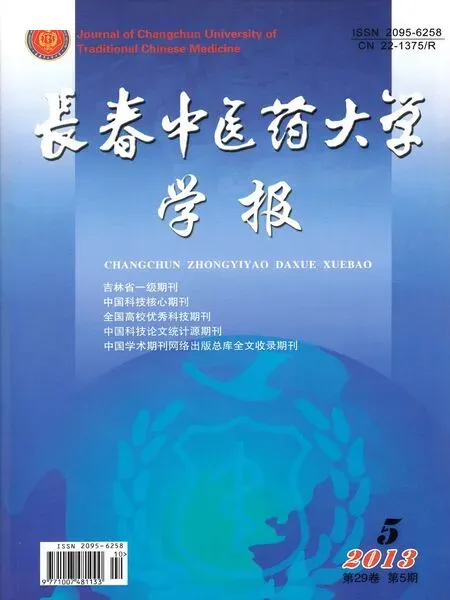肛门病术后电针白环俞镇痛效果及其对血清前列腺E2的影响
王玉立,任天女,指导:高 玲,周建华
(1.长春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长春 130117;2.长春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长春 130117;3.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肛肠科,长春 130021)
肛门疾病是临床多发病,其术后创口的剧烈疼痛成为困扰患者和临床医生的医学难题。近年来,电针白环俞镇痛在临床上取得了良好效果,但其机理方面的空白阻碍了这一治疗方法的发展。本课题旨在从致炎致痛因子PGE2角度探讨肛门病术后电针白环俞镇痛的机理。现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均选自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肛肠疗区2012年8月-2012年11月混合痔患者60例,男30例,女30例,年龄最小18岁,最大74岁,平均43.5岁。
1.2 诊断标准 本观察病例均符合《痔诊治暂行标准》中的诊断标准[1]。
1.3 纳入标准 1)符合混合痔诊断标准;2)年龄在16岁以上,75岁以下者;3)患者术后自身疼痛判定视觉类比量示范表[2](VAS法)测定的分值≥4分。
1.4 研究方法 采用患者针刺前后自身对照的方法,通过对照患者针刺前后疼痛程度和血清中PGE2质量浓度,从分子生物学角度探讨肛门病术后电针白环俞阵痛的机理。
2 治疗方法
对符合纳入标准的患者作自身疼痛评定,采血检测血清中PGE2的含量;针刺双侧白环俞,针柄连接频率调为100 Hz连续波德电针治疗仪,给予点刺激,留针30 min后起针;起针后,再次对患者进行自身疼痛判定和采血检测血清中PGE2含量;对照患者针刺前后的疼痛程度以及血清中PGE2含量的变化情况,记录并分析数据,最后采用SPSS 17.0统计软件采用配对t检验进行统计分析。
3 疗效标准与结果
3.1 疗效标准
3.1.1 疼痛的量化标准 视觉类比量表(VAS法):用10 cm长的线段,分成10段,分别极为1、2、3、4、5、6、7、8、9、10分。最左端为0分,代表“无痛”;分值<1分为微痛;1~3分为轻度疼痛,疼痛不影响睡眠;4~6分为中度疼痛,疼痛影响睡眠;7~10为重度疼痛,无法入睡;最右端为10分,代表“剧痛”,见图1。
3.1.2 疼痛判定方法 自身判定:患者在医生的指导下,患者根据其感受程度在直线上的相应部位作出记号,标记处即为疼痛分数。

图1 自身疼痛判定视觉类比量示范表(VAS法)
3.1.3 疗效标准[3]临床痊愈:证候分数减少量≥95%且患者症状及体征消失或基本消失;显效:证候分数减少量≥70%,<95%且患者症状及体征明显改善;有效:证候分数减少量≥30%,<70%且患者症状及体征略有好转;无效:证候分数减少量<30%且患者症状及体征均无显著改善或加重。
3.2 结果 见表1~表2。

表1 2组针刺前后疼痛分数比较(±s,n=60)

表2 针刺前后PGE2含量比较(±s,n=60)
4 讨论
中医理论认为,肛门病术后的疼痛为“三因学说”中的不内外因中的金刃所伤,其经络受损、气血运行失调,出现局部的气滞血瘀,故而不通,不通则痛。现代医学从生理和病理学角度分析了肛门病术后疼痛的起因及其发病机制,认为肛周术后伤口暴露、排便时受到牵拉刺激、伤口瘢痕组织压迫神经等内外界理化因素的刺激持续作用于机体的肛周感受器,诱发局部神经元的兴奋产生动作电位,兴奋沿着相应的感觉传入神经向中枢神经系统传递,通过各级中枢的整合后机体产生疼痛的感觉和反应[4]。
白环俞穴位于第4骶后孔处,脊髓神经节段S4阶段的神经前后支穿过第4骶后孔,肛门脊髓神经节段也是S4阶段,同属于一个脊髓阶段,所以刺激白环俞穴位时,引起局部酸麻重胀痛轻度不适感。针刺刺激通过脊髓负反馈调节机制抑制肛门术后造成的疼痛[5-9]。PGE2是一类重要的致炎致痛因子,可作为疼痛和促伤害介质直接激活伤害性感受器引起疼痛,从而提高痛觉感受器对致痛因子的敏感性,同时PGE2也可启动疼痛介导的信号转导通路[10]。
本研究显示:患者血清中PGE2的含量与患者的疼痛程度呈正相关,PGE2作为重要的致炎致痛因子,其质量浓度在电针后随着疼痛的缓解有所下降,提示:致炎致痛因子PGE2介导的信号转导通路可能参与了电针白环俞镇痛针刺镇痛的过程,电针治疗过程中可能阻滞了疼痛信号传导的同时也对PGE2的产生起到了抑制作用。本课题通过检测针刺前后患者的疼痛分数以及患者血清中PGE2的含量,不仅明确了电针白环俞的镇痛作用,也为电针白环俞治疗肛门病术后疼痛机理的研究开启了一扇门,确定了PGE2在镇痛过程中的作用。弥补了多年来电针白环俞治疗肛门病术后疼痛的理论上的空白。
本课题虽然明确了PGE2在电针镇痛过程中的作用,但也不能排除其他镇痛因子的参与。由于经费额度有限、临床患者观察量少和临床研究时间短等原因,本课题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如无对照取穴、未进行远期疗效的观察、实验室检验项目较少等。今后应进一步规范针刺镇痛的补泻手法、增加对照穴位、进行远期疗效的观察,以得到更加客观、更有说服力的临床应用依据,以便于从多角度了解电针白环俞镇痛的机理。
[1]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肛肠外科学组.痔诊治暂行标准[J].中华外科杂志,2003(41):699.
[2]Huskission EC.Measurement of pain[J].lancel,1974(2):1127-1131.
[3]郑筱萸.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S].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2:260-276.
[4]刘博.肛门病术后疼痛的机理及预防[Z].第十五届中国中西医结合大肠肛门病学术交流会议,441-444.
[5]罗永芬.腧穴学[M].10版.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
[6]刘乡.以痛治痛——针刺镇痛的基本神经机制[J].科学通报,2011,46(7):609-616.
[7]贾春生,马小顺,李晓峰,等.耳针沿皮透穴刺法对多种痛证及功能障碍的临床研究[J].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2012,28(4):604-605.
[8]张世平.电针操作标准化存在的问题及建议[J].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2012,28(4):582-583.
[9]王顺,刘军,王威岩.张缙教授论针刺补泄[J].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2012,28(4):629-630.
[10]Montine TJ,Milatovic D,Gupta RC,et al.Neuronal oxidative damage from activated innate immunity is EP2 receptor-dependent[J].J Neurochem,2002,83(2):463-4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