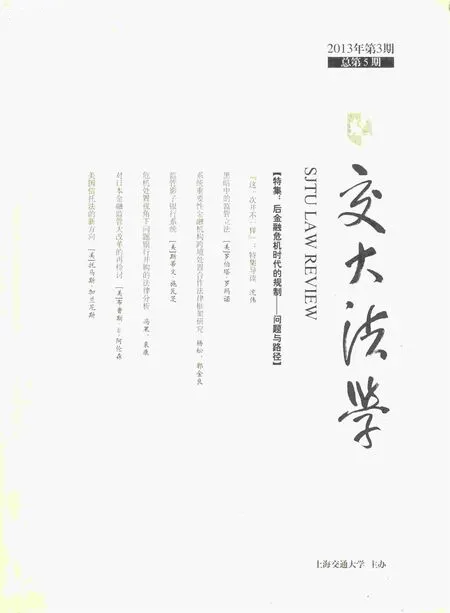“这一次并不一样”:特集导读
沈 伟
关于最近这一次横扫全球的金融危机以及危机对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带来的惨痛创伤和危害的论述汗牛充栋,举不胜数。〔1〕这方面的著作和论文以美国学者居多,知名度最高也是危机之后首先从法律角度反思经济危机的是波斯纳。见Richard A.Posner,A Failure of Capitalism:The Crisis of’08and the Descent into Depression(Cambridge,MA and London,England: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and Richard A.Posner,The Crisis of Capitalist Democracy(Cambridge,MA and London,England: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金融危机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制度反思和修复。这样的循环出现在最近八百年间的每一次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前前后后,构成了周而复始的危机和后危机图景。但是这样的循环从来没有造就危机的终结,但成就了一次胜过一次的新的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危机发生的频率和规模有愈演愈速和愈演愈烈之势。是次的金融危机还催生了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也有了“两次触底”之类的新危机名词。
每次金融危机对国家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全球经济治理秩序都会产生相当甚至是深刻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萧条和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彻底推动了证券市场监管和证券法的变革。以此为契机,证券法和资本市场的管制得到了完全重构,吸收了全新的监管和立法理念,采用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信息披露制度。此后,全球主要的证券和资本市场都沿用了以披露制度为核心的证券监管模式。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直接推动了区内相关国家更新本国的商法体系。以美国和世界银行为首的西方国家和国际金融组织利用亚洲部分国家对贷款的迫切需要,推动了这些国家以美国商法为蓝本对本国的破产法等商法进行修订和改革。尽管移植效果强差人意,美国依此为契机,直接扩展了美国法的国际势力和影响。这些国家的商法体系也获得一次重造的机遇。亚洲的金融危机也整合了香港同中国大陆的经济和金融联系,调整了香港金融市场发展的方向,为两地在21世纪的更高层次和更紧密经济联系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实战的机会。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已经见证了两次规模不等的金融危机。尽管两次危机起源、规模和性质完全不同,但两次危机的共同点是对国际秩序,特别是国际法制度和体系产生了重大影响。21世纪初的阿根廷金融危机彻底改变了国际投资法的面貌,催生了国际投资仲裁判例法体系。在阿根廷金融危机之前,作为国际投资法基础的双边投资协定主要停留在条约制定层面。尽管国家之间订立了许多双边投资协定,这些协定的实际利用率却相当低。外国投资者依据这些双边投资协定为了解决国际投资争议而将东道国政府带到仲裁庭的实际案件数目非常有限。但是,在阿根廷金融危机之后,许多受金融危机影响的跨国公司纷纷以阿根廷为被诉方,将阿根廷诉到了华盛顿中心要求对投资争议进行仲裁。以阿根廷为被诉方的华盛顿中心仲裁案件到目前已达四十余起。这些仲裁案件就管辖权和实体问题的裁决极大地改变了国际投资法的面貌,丰富了国际投资仲裁的实践。以阿根廷为被诉方的仲裁案件为研究国际金融危机中的国家责任问题提供了极好的素材。这些案件对国际法诸多问题提出了挑战:外国投资者在东道国享受的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和公平公正待遇的具体内容、例外、适用和东道国违反这些待遇原则所承担的责任;这些基本待遇与国际法和国际习惯法的关系;国家在金融危机中对外国投资者的投资进行国有化或征收以及征收的补偿标准;经济危机对国家主权的影响;卡尔沃主义的式微;国家在经济危机中可以采取的救济手段,比如紧急情况和公共秩序等例外原则的应用;双边投资协定程序和实体条款的解释和适用;等等。以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破产登记为标志的是次金融危机对金融界和金融业监管的影响正在显现。〔2〕沈伟:《复杂结构金融产品的规制及其改进路径——以香港雷曼兄弟迷你债券事件为切入点》,载《中外法学》2011年第6期。次贷危机随之波及亚洲和欧洲。巴塞尔协定的修订和美国改革华尔街投资银行业的金融法的出台拉开了金融法大变革的序幕。二十国集团已经开始显示出在变革的国际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重构中的重要作用和潜在能量。如同20世纪60年代国际法学界关注国际货币和金融制度的改革那样,2008年开始的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以及之后的欧洲主权债券危机对国际金融体系的重构和欧元区的金融体系的稳定提出了崭新而又迫切的课题。
金融危机暴露的是制度缺陷、结构失衡和体系失调,显现的是从微观到宏观的规制漏洞,归根结底是治理和规制的顽疾没有得到有效治疗。在金融危机渐行渐远的时候,本着拾小遗,察全貌的想法,就金融规制的某些方面深入分析,提出思路和改革路径,是集结本特辑的初始思路。这里汇集的中外学者的文章更突显了后危机时代金融规制所面临的众多课题和无数困难。
《黑暗中的监管》一文的标题就带有浓重的隐喻色彩。即使监管者、实业界和理论界手里有许多研究工具和分析范式,就如何更好更有效地进行监管从而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或扩大仍然是一头雾水。《黑暗中的监管》揭示了危机与监管之间形影不离的关系,以及类似中了魔咒而不能自拔的“危机——后危机——改进监管——危机”的往复循环。金融监管面临的难题是,金融机构在不断变化且相当不确定的环境中运作,以至于即使是在最好状态下颁布的法律也可能存在始料未及的不良效果;同时由于经济和技术环境因素的变化,根据一系列初始条件做出的法律规定也会变得不合时宜。文章在分析了这种内生的监管矛盾性的同时,提出了在危机驱动下的金融立法及其细化规则中回应窘境的最佳方案包括两个关键的程序性机制:一是要求及时地在未来某个时点自动地对后果进行评估并且重新考虑立法性和制度性的决策;二是,在可行的前提下,赋予制度性豁免或者减免的权利,鼓励小规模的有选择的实验并给予行使的灵活性。这两个程序性的设计将使监管机构在更好地了解现况的同时对自身进行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源于危机,并长期伴随着金融立法和规则制定的始料未及的错误。考虑到金融机构、市场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祉的中心地位,对立法者和监管者而言,正确的意图、合理的制度设计以及同所处的政治制度正面的呼应对回应金融危机并且避免加剧危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金融危机暴露的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不仅直接导致了巴塞尔协议三的出台,而且得到二十国集团高层的高度重视,形成了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进行监管的国际共识。由于各国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处置工具与目标以及破产法规则存在极大的差异,所以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跨境处置合作法律框架在整个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处置中、乃至金融危机应对中处于关键地位。但是我国学界对跨境处置合作的关注不足,金融自由化与全球化、金融机构市场化背景下我国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跨境处置将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因为这既涉及国家利益,又涉及机构本身利益,更涉及本国债权人的利益。《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跨境处置合作法律框架研究》一文对这一监管共识和国际努力进行了深入的阶段性分析。跨境处置合作是跨国金融机构的母国与相关东道国之间,基于互惠、平等的原则,通过合意选择法律,并按照一定的程序对问题金融机构进行合作处置的法律制度。如何在系统重要性机构的跨境处置实践中构建合理的合作法律框架,不仅具有国际性,而且具有地方性,应成为我国金融法律制度研究的重要领域,为我国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金融机构提供制度保障。
据估算,2012年以来,影子银行系统的全球规模已增至67万亿美元。影子银行的实质是银行业进行表外业务,以规避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影子银行具有一系列的杀伤力:侵蚀了正规的银行业,形成了监管套利,弱化了银行业监管效果,等等。《监管影子银行系统》比较了影子银行系统和传统银行系统,考察了影子银行系统的效率和风险,并且探究如何监管影子银行系统进而使其效率最大化并使其风险最小化。对影子银行进行深入考察不仅仅是个比较法或域外金融法的问题,这样的讨论对中国也具有非常强的相关性。据估计,在中国,影子银行系统目前达到了20万亿元左右,这一数值大约是银行贷款市场规模的三分之一。中国与美国在影子银行活动的某些细节方面很不相同。与美国影子银行体系相比,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欠缺复杂性,但是正是这个“简单性”增加了监管的复杂性。〔3〕Shen Wei,“Shadow Banking System in China—Origin,Uniqueness and Governmental Responses”,28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anking Law and Regulations 1(2013),20-26;and Shen Wei,“Wealth Management Products in China:Recent Scandals and Regulatory Loopholes”,28Butterworth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anking and Financial Law 5(2013),303-05.本文概括性和普适性的分析总体上能够适用于任何非银行中介融资网络,所以对讨论中国影子银行网络和体系以及相关的监管也具有很强的关联性。
问题银行并购是银行危机处置的重要手段之一,亟需相关的法律制度保障其及时有效的实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金融危机以后加强监管的一个方面就是加强对问题金融机构危机后的处置。《危机处置视角下问题银行并购的法律分析》一文以问题银行并购制度为中心,提出了若干规制思路:以保障和补充流动性为重点、以金融稳定为目标、以存款人利益保护为价值追求,明确界定并购主体范围,有效落实监管促导机制,正确选择并购方式,合理要求信息披露,并建立存款转移、强制担保、并表监管和并购后评估等一系列有针对性的特殊制度。问题银行并购同时还应妥善处理问题银行并购与证券法、反垄断法的衔接与调和。处置问题银行是个宏大的规制课题,这方面的研究仍然可以继续。
《对日本金融监管改革的再检讨》是独树一帜的“国别研究”论文,对读者进一步认识金融规制和改革的复杂性以及地方性极具帮助。最近二十年来,日本推行了金融自由化的政策,并进行了金融监管大改革,核心目标是将一个高度管制的、以银行业为中心的金融体系,转变为一个高度透明并以资本市场为中心的金融体系,并由此为日本经济及其老龄化的社会注入新的增长活力。学界对日本的金融改革的评价为此次改革因日本低迷的经济增长而未能成功。作者却认为,由政府主导的金融自由化与行政体制改革在去除法律与行政体制障碍、构建一个市场化金融体系方面,取得了相当意义上的成功。但是,市场参与者根深蒂固的传统交易习惯以及包括宏观经济增长缓慢、金融市场表现不佳等内在的强大不利因素,都成为了雄心勃勃的金融大改革目标最终实现的障碍。这样一篇“逆势而为”的论文为探究金融规制奥秘的读者给出了这样的提示:通过放松金融管制这一措施所能达到的目标终究有限,而采用结果导向型的评估标准对日本改革的成效进行评价的合理性似乎存有疑问。
信托素来是金融法和金融规制中的核心问题,对培育金融市场和金融市场所必须的市场信任有制度引领作用。许多复杂的金融交易和证券化业务的开展都是以信托为基础的。〔4〕Alastair Hudson,The Law of Finance(London:Sweet &Maxwell,2009).《美国信托法的新方向》为这个特集提供了完美的理论化的脚注。信托制度存在于民事活动和商事活动两个场景之中。这篇论文探讨的主要是民事信托。但是,信托的核心要素在商事信托中具有共通性。此外,考虑到信托在经济发展和财富凝聚之间的依托关系,尽管论文探讨的是美国的信托制度发展,对中国而言也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信托在金融活动中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也需要法学界对信托理论的核心内核和发展走向加以梳理和优化。
尽管特集的论文覆盖了金融规制的许多方面,但没有涵盖后金融危机时代金融规制的某些重要方面。例如,特集没有涵盖国际金融治理体系的改革。目前的国际货币制度和全球金融体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确立的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当代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该组织的核心制度就是加权投票制度。目前,关于建立国际金融和货币新秩序的努力才刚刚开始。国际社会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资源重新分配的呼声很高。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权限和使命在不断地进行调整。这样调整的方向是什么?调整的机制是什么?调整的目标是什么?这些问题学界还没有系统的研究和具有说服力的定论。
再如,发端于1975年的巴塞尔协定被国际银行界称为“神圣公约”。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部分,巴塞尔协定三有了新的变化。巴塞尔协定历来只提出一些指导性的要求,而缺乏有效的国际监管。但是,作为“软法”的巴塞尔协议为从事国际金融业务的银行提供了国际协调标准。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如何增加“软法”的执行效果,增加巴塞尔协议的国际性和有效性,从而建立起更加普世的金融业标准就是一个不得不研究的问题。
此外,全球金融体系治理中的结构性问题也没有得到涉及,特别是二十国集团在金融治理结构中同原有的国际性组织,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衔接和补充没有得到说明。二十国集团的地位和作用是建构新的国际金融秩序的最具有不确定性,同时又最具有可能性的机制和平台。这样的非正式的和松散的结构集团正在竞争取得更多的管理全球化经济的为数甚少的有限权限和资源。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纠缠和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已经在二十国集团的历次会议中展示无疑。美国和法国(代表欧洲的利益)都在利用各自的优势和地位争夺建立国际货币和金融新体系的话语权。金砖五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利用二十国集团的平台争取在重构(如果不是重建)国际货币和金融制度中获得有利的同它们日益上升的经济地位相适应的制度优势。在法国担任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国之际,法国提出把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前提是人民币应当首先可自由兑换。这一提议对中国形成了相当的压力。这些新的提议既向我们提出了制度设计的问题,也提出了话语权的问题。这就需要法学界研究国际金融秩序和体系,以及建立或重构国际金融体系和制度的可能性及路径。
放在更加广阔的全球化的背景下,目前关于国际金融和货币制度的重构是全球制度变迁中的必然要素和组成部分。全球制度变迁讨论的是国家主权的萎缩和商事主体自主性的此消彼长。传统国际法强调的是民族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基础角色和功能。但是全球化加速了市场主体的流动性,使得国家作为主要国际法主体的功能正在萎缩。是次金融危机正在复活一种古典主义意义上的国家主义,这可能是学界始料未及的。同时,全球制度变迁也正在推动一种高水平的全球范围的协商民主。这种民主模式的发展为中国的参与和崛起提供了契机。“新金融体系”恰恰是全球制度变迁中最为基础和最具挑战的要件。
应对后经济危机时代无尽挑战最需要的是指向性和针对性强、路径明晰、具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改革路线图,进而避免整个社会处于后危机时代的混沌、迷茫、束手无策的境地。借用丘吉尔的这句话作为这个“导读”的结束是再恰当不过了:这不是结束。这甚至不是结束的开始。但,这可能是开始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