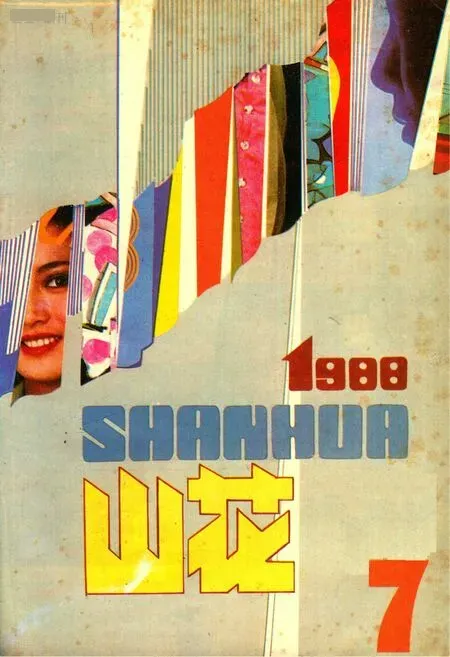卑微的神灵:陈红旗的绘画——兼论乡土绘画的价值再建构
张建建
1997年,印度女作家阿兰达蒂·罗易(Arundhati Roy)写出了后来获得布克奖的小说《卑微的神灵》(The God of Small Things),同时间,中国贵州的画家陈红旗正在画着表现贵州苗族地区岜沙乡村风物的绘画,他已经画了许多年了。罗易写作的背景是全球化资本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化政治对于古老社会的侵蚀,陈红旗绘画的背景也差不多:中国社会几乎每一个角落都开始了浩浩荡荡的商业及其相关价值的建构;罗易用印度式感性且细密的思维描述着诸多发生在文化细节以及微妙人性当中的社会分裂的现场,陈红旗则选择用艺术家个人具有宗教情怀特征的笔触在描述着岜沙苗寨乡民们粗粝质朴的日子以及一个微小族群面对的生存挑战;他们有许多的不同,但是他们亦具有许多共同的思想维度,那就是客观或主观地表达出对于族群文化价值加速崩溃的忧伤,表达出艺术家对历史中某些微小事物的崇敬并且努力再现其人性价值的状态。
这就是我把陈红旗与罗易叠加在一起言说的意义所在:其一,类似陈红旗的一些中国当代艺术家很早就开始了一种对于跨国化艺术语言充斥艺术场域的反思;其二,当代艺术日益加速走向图像化且平面化的语境,由此推促着艺术家重返绘画中叙事价值的期待;其三,经过后现代价值批判的艺术家对于宏大叙事的遗弃促进了艺术家重建族群深处的小历史而带来的历史观念的再认知。它们都体现出艺术家对于现代性侵蚀的当代批判立场。从小说语言与绘画图像具有着共同的表征来看,当代艺术领域正在发生着一种新型的政治行为:为微小的乃至卑微的事物重建其人类心灵的价值而努力。
放在二十年前,我们或许会认为陈红旗的绘画语言,包括其绘画的技法与表现性语言,都是建立在舶来基础上的借用和模仿。其硕大的画幅体现出西方传统风景与历史绘画的宏大构造,其中厚实且强烈的对象体量感或者人物的动态与凝重的表情,那些精确且富有表现力的空间描述,乃至我们还可以发现画家对于史诗般绘画的戏剧化表现的恰当应用,再有其中塑造性极强的笔触肌理乃至色彩的表达以及艺术家感性之泄露,等等,几乎传达出画家是在西方经典画法的呵护之下习得的技法。虽然,这是画家极具专业素养和艺术灵性的展现。但是当我们放眼几十年来中国当代艺术语言发展的系谱之时,我们会发现,以西方语言为典范的艺术表达方式已经从其发源的国度全面弥漫向世界,艺术语言的国际化态势已经是不言而喻地建立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中国的当代艺术家们毫无例外地加入了这个巨大且获益甚丰的俱乐部狂欢当中。简单来说,在当代艺术的场域,语言的创新价值再没有往昔日新月异般的辉煌场面,在艺术商业的压抑之下,当代艺术史构建起来一个巨大的规训法则,艺术家们除了更多反复重现诸种规范化言说之外,就是应用其种种聪明与灵巧在艺术的资本市场里竭尽全力地去分享通过图式认同而带来的巨大红利。在这种语境里面,更加具有传统特征的技法与绘画观念,如写实的技法及其观念,绘画的叙事能力,以及面对现实的图像观念和艺术家的激情表达,等等,皆被当前诸多理论称之为“乡土的”、“写实主义的”乃至更进一步被斥之为“老式的”、“落后的”和“商业的”艺术立场,亦即一种价值卑微的艺术立场。因此可以说,从其艺术风格来看,陈红旗几乎从开始绘制岜沙系列绘画之时,就已经走向了与当代艺术之国际化潮流的反面。那时是上个世纪的90年代,正是中国当代艺术狂热转型的时代。在偏执且时尚的艺术理论看来,陈红旗的转型向更加传统的艺术语言,或许就构成了一种艺术上的政治不正确,也因此,他的作品一直被弃置在批评家们的视野之外,艺术家本人也没有更多机会去获得其应当获得的重视。

陈红旗作品-人像局部6
然而,当语言的国际化潮流翻卷成为巨大的漩涡之时,正是艺术家更有必要根据自己的表达需要去进行睿智的选择之时。这个时候,陈红旗的选择,是返回经典的绘画技法并且在整合经典艺术诸多方法的同时去进行灵性的再发现。无疑,这是一个睿智乃至真诚的艺术家所必要走向的艺术归途。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到,陈红旗的画风里面,或许有着勃鲁盖尔式乡间风情的寓意,也有伦勃朗式强烈的光影表现,亦有着如米勒一般的土地情怀,还具有着更为古老的宗教空间的意境,但是在其强势的风格化里面,这些种种艺术史的遗存,都像是不同历史时期艺术家间的心灵对话,有效且激烈的汇集起来,其画幅当中那些沉着且内敛的人物群像叙写着久远且独立的生命情境,那些跃动着的色彩与笔触亦担当着艺术家疾书时候的情绪叙写,其戏剧性场景的瞬间力量以及人物行动时刻的情境推衍与展开,亦传达出写实绘画所必须具备的历史语境的像喻与连接,尤其是画家在其表达一个微小族群生活场景时所赋予画面的宗教性沉思,尤为体现出艺术家强硬的返回历史深处的精神取向。凝重与忧郁,狂喜与悲怆,这些在美学史里面被充分赋予了宗教寓意和激情表达的表现性概念,在陈红旗岜沙系列绘画里面被凸显起来,由此我们亦可以认为,陈红旗所使用的艺术语言,当其面对岜沙苗族真实粗粝的生活世界的时刻,是一次重要且准确的选择,其强烈而有效的艺术表达,体现出艺术家身处庞大纷繁的当代艺术史而做出完全个人性选择的能力乃至勇气。
面对陈红旗重建写实绘画的勇气,我们或许会强烈意识到,当代绘画已经进入了一个艺术家个人建构其艺术语言的时代,是每一个艺术家个体再次拒斥艺术语言的集体主义狂欢的时代,是艺术家重新回归艺术史而不是更狂热地参与瓜分图像红利的时代。这是因为,从艺术语言的历史价值以及其创建时代的美学思维的功能来说,艺术家肯定承载着一份重要的精神担当。

陈红旗作品-人像局部7
陈红旗的岜沙系列绘画,虽然展开的是一类写实绘画的风格,那些现实场景的再现以及高度戏剧性的人物神情,把写实绘画拟态状物的要求予以了十分准确的表现,不过我们也看到画面中更加富有表现力的那些突显的光影,那些更加强烈的色彩表达以及超现实情境描述,都在为开端的写实场景增加着鲜明的艺术家个人表达的特征。写实的场景写真和超现实的场景表现,类似宗教绘画一样的背景光影的添加,艺术家自己说,是来至对于俄罗斯教堂艺术的倾慕,那么可以说,当艺术家把这些倾慕应用在现实性场景中之时,这些元素无疑也构成了艺术家对于经典写实性绘画的形式突破。重要的是,陈红旗的岜沙绘画更为关注场景的叙事性结构,不论是人物群像,还是双人肖像,乃至多种人物搭配,以及人物内在的生命感受通过这些叙事性言说获得瞬间凝固的力量,强化着这个族群更为深沉的生命品格;喜悦、悲伤以及凝重的场景,得到了敏感且充分的再现;这些再现不仅仅是画面中那些人物的孤独出场,而是与岜沙苗族的生存语境作了广阔的连接,少数族群生存语境在这些充分叙事性场景当中得到了强力的推衍。如果再把艺术家个人性表达的要素置入到叙事结构进行观察,那么我们看到了更加丰富与强烈的叙事表达,那些急速的笔触,动感的肌理,鲜明的光影层次,等等绘画性成分,便成为艺术家与对象间相互关注乃至相互建构的重要手段。鲜明的文学性叙事与鲜明的图像化叙事,共同结构起陈红旗式的写实性表达,艺术家既能够充分表达岜沙苗族深邃的生命言说,也能够充分展开艺术家与对象的富有激情的对话。现实对象与艺术表达的无间相遇,在陈红旗这里亦成为其写实绘画重要的表现特征。
在形式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看来,绘画的叙事性架构应当是纯粹形式化的,是勿容文学染指的,这似乎成为了现代主义的教规。但是陈红旗作品的叙事性结构告诉我们,由于良好的形象塑造与敏感的戏剧性表达,以及艺术家个人情怀的有效融入,文学性价值重返绘画并获得了新生,在当代艺术的语境里面,这样的文学性重建,其实亦是介入性艺术所必须的叙事功能的一种鲜明表达。这也是当代乡土绘画所具有的重要特征。
除了形式主义的艺术原教旨主义对于写实绘画的抑制之外,在当代艺术场域言说乡土绘画也是危险的,如前所说,商业化和国际化的强大规训力量在其本质上是漠视地方以及与地方相关联的乡土的。即使宣扬一种本土性艺术价值,由于其迅速时尚化的机制而使其在展开的同时便迅速丧失本土化的独立美学品格而迅速融入价值平面的文化与商业场域。乡土的异域化、奇异化乃至文化观看的诸多凝视规则对于乡土价值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在此,乡土绘画的重建,除了需要艺术家对于乡土艺术诸多艺术要素的更加积极的再认识之外,亦需要艺术家具有对于乡土价值的更加独立以及更加富有同情理解的勇气和智慧。
面对乡土,就是像贵州岜沙苗寨这样的乡土,艺术家们具有着几乎一致的表现方式,亦即前述形式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的方式,在这种方式中,岜沙苗族的生活场景,原始风貌的空间,服装上那些绚烂的图案以及旅游专家所谓“最后的枪手部落”的风情,在相关的艺术表现里面皆被“遥远的异邦”观念所笼罩,与旅游业对于岜沙苗族的商业化再现一样,风情化、符号化地处理岜沙苗寨的异域情调得到了艺术家的认同。因此我们看到太多似是而非的、花团锦簇的乃至绚烂多彩的苗族符号肆虐在诸多艺术作品里面,古典贵族形象与岜沙概念的图案相得益彰,苗族图像亦被组织进抽象构成的图式里面而形成了当代与现代主义艺术之形式意味。凡此种种,几乎都是在形式主义规制之下的语言再塑,岜沙苗族生存场景中种种挑战与困惑,皆被组织进一种我们称之为“商业的凝视”场域之中而丧失其核心的文化生命价值,并且亦被有效地移入到了商业化艺术之中。这自然是图像红利时代的集体主义狂欢的结果。由此而言,商业化视角浸透进对于岜沙苗族的表达,与福柯所说的“凝视是一种权力”的浸透共同构建起我们时代另外一类权力的表达。
突破这样一类权力化再现,似乎是陈红旗岜沙系列绘画的初衷。20多年的观察与进入,岜沙苗族对画家的生活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自然也对艺术家对于岜沙苗族的艺术再现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由此我们看到,这些作品中的岜沙苗族不再是绚烂多彩的苗族山民,而是喜怒哀乐形溢于色的男女人群,是接亲、送亲、醉酒、葬礼场景中的当事人,是悲哀与狂喜同在的现场,也是宁静和喧嚣并存的山寨空间。作品中的人物也不是遥远异邦中的陌生人群,亦是如所有人群一样处理着生生死死的瞬间。从生到死亡,男人与女人,青年与老人,皆如所有族群一样日夜徜徉在生存的困境。没有特别地去再现其族群的特别符号,亦没有特别去表现艺术家的同情与悲怆。通过这些诸多的场景与人物形象,种种苦涩的、喜悦的,悲凉的和粗粝的生活行为被予以了直观的再现,种种细微的表情与姿态被予以了精心的表达。这是一个微小却整体的族群生境,一个微小却深沉的生命情态,它们一一展开在艺术家笔下,展现在画幅那些涌动的色彩肌理当中,蜿蜒在那些生动的叙事结构之间。与诸多被形式主义规制驯化了的艺术表达不同的是,这些作品几乎是放肆地再现着岜沙苗族的真实生命,包括族群内部的伦理悲剧以及放浪的调情喜剧皆被艺术家予以了直观的再现。
在淼淼人寰之中,岜沙苗族或许只是一个微小的存在,但是这个族群内部的一切生命存在亦是茫茫宇宙间生命存在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没有每一个微小族群的生命存在亦没有宇宙间巨大生命的价值。在充分消费主义乃至宏大无比的物质主义时代,岜沙苗族的生命或许亦是一种卑微的存在,但是其生活场景与所有生命情态也是一样,默默地自我更新与安静的自我生长于天地环宇之间,其生命价值与天地间全部的生命一样都同样具有不可亵渎的庄严。艺术家陈红旗或许有感于这样的认知,因此在直观再现岜沙苗族生命情态的同时,他亦直观地把对于微小族群生命价值的情感予以了神圣化的处理,那些山边的霞云或者郁郁山林当中的篝火光影,将这些微小生命场景呵护起来,亦将这些几乎是卑微的生命情态赋予了神圣的光辉。艺术家将这一份尊重,毫不吝啬的再现于几乎所有的画幅之中。这是陈红旗岜沙系列绘画里面最具震撼力的处理。从其硕大的画幅里面,我们似乎聆听着一声声祈祷的晚钟,正回响在岜沙苗寨的群山林莽之间。全部的忧伤与悲怆,全部的喜悦与狂放,都被艺术家的倾心关切所笼罩。哪怕只是一个微小部族的生命戏剧,却仿佛被艺术家将其放置在了人类的巨大舞台之上而展示出来。
在陈红旗的岜沙系列绘画这里,乡土绘画与世界性的的族群价值再认知的潮流连接起来。面对全球化语境下的族群同化趋势,艺术家们反身回到生活世界的内部,努力去发现诸多微小事物的价值,为这些微小的神灵注入了强大的神性,展现出一种更加富有人性的艺术灵智。而这也是印度小说家罗易与中国画家陈红旗所共同选取的一种价值回归。
乡土绘画的重建,有待于艺术家对于微小生命情态的细致观察,对于微小生活场景的深切关注。更为重要的是,乡土绘画艺术家有必要保持对于微小事物的持续性的尊重。所谓乡土,在此才能够成为艺术家真诚而倾心向往的一片纯灵圣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