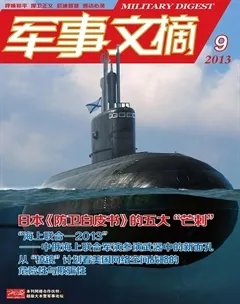『爱国者』和『卖国贼』之间的抢钱之战(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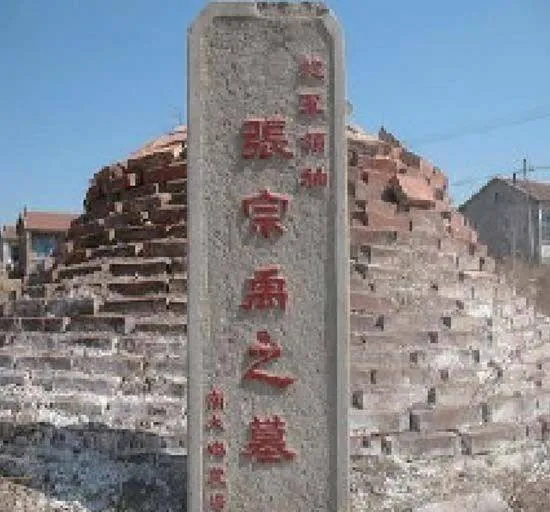




不请自来的过境—左李交恶之源
说起晚清四大中兴名臣,主流观点莫过于“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四人。由于胡林翼英年早逝,未能大展宏图而过早退场;曾国藩垂垂老矣,在剿灭发捻后就决意急流勇退、明哲保身,刻意远离晚清官场的漩涡。所以,真正经历和谱写晚清洋务运动华彩乐章的名臣只有左宗棠和李鸿章。而这两个人,偏偏又是斗争一辈子的政治死对头。在大多数人眼里,左宗棠收复了新疆,是大大的“民族英雄”。而李鸿章却因为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诸多不平等条约而沦为“卖国贼”。所以这两个人于情于理、于公于私,都是势不两立的敌手,没有丝毫回旋余地。可俗语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原本无冤无仇的左宗棠和李鸿章为什么会到水火不容的地步?这还要从围剿太平军时候的一次越界事件说起。
由于以正规经制军队为主体的江北-江南大营已然被太平天国的陈玉成和李秀成联手击灭,清政府在江南的正规军野战主力几乎被一扫而空。因此,围剿太平军的主力就落到了团练武装的头上。当时形形色色的团练武装不在少数,但是既成规模,又有战斗力的武装却只有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和左宗棠的楚军。湘军的攻击方向是由安庆、武昌直指天京(今南京);淮军的攻击方向是从上海出发,由苏州、常州、无锡攻向天京;楚军的攻击方向则是由浙江、福建而至两广,抄太平天国的大后方,收釜底抽薪之效。
按说如此部署完全可以各司其责,但是偏偏出了漏子。李鸿章的淮军为了追缴太平军侍王李世贤残部,当时深入了浙江境内。即便是越界,也是为了剿贼,为了大清的江山社稷,可是左宗棠偏偏就认定李鸿章的越界行为是别有用心,至少是对他本人的无视。左宗棠本人自尊心强而又心胸狭窄也是众所周知的。由于李鸿章和曾国藩之间亲密的师徒关系,原本已经和曾国藩反目成仇的左宗棠恨屋及乌,也记恨上了李鸿章(曾国藩为了将攻克天京的伟业留给曾国荃,令淮军和楚军不得参与攻打天京,以致遭到一心想建功立业的左宗棠的嫉恨)。从此,二人处处较劲,前后持续了20余年。
剿捻引发的羡慕嫉妒恨——左失落李得意
1866年,在福建、两广境内的太平军余部被全数肃清后,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被调任甘陕总督,任务就是围剿活跃于北方的大股捻军。
1864年太平天国主力被剿灭后,尚有大量余部在赖文光、陈得才等人的率领下,和在北方活动的张宗禹、任柱所部的捻军合兵一处继续反抗。他们改步战为马战,以大队骑兵在平原远程机动奔袭,如风卷残云一般来去如飞,绝不拖泥带水,使得前来围剿的以步兵为主的清军一时难以适应,屡屡受挫。特别是1865年5月,捻军在山东曹州(今山东菏泽)高楼寨歼灭清精锐蒙古骑兵,击毙了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一时间声势大振,清廷大为震惊。因此,当肃清闽浙、两广地区太平军余部的左宗棠被北调甘陕的同时,时任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的李鸿章接替剿捻不力的曾国藩为钦差大臣,新募马队北上剿捻。
不料,原本张宗禹所部的一支西捻军被左宗棠剿得走投无路,居然神不知鬼不觉地越过了左宗棠设下的重重封锁线,在左宗棠的眼皮底下渡过了黄河,从陕西越过山西,进入了京畿重地直隶。
捻匪进逼,京师震动,朝廷急令各路军马救援,甚至连恭亲王都赤膊上阵,带上京城八旗神机营出京剿捻,所幸李鸿章率所部淮军及时赶到,在吴桥附近全歼了捻匪,朝野上下才松了一口气。
而直到那时,远在陕西的左宗棠尚不知自己辖境内的捻匪直逼直隶!左宗棠剿捻不但没有将捻军剿灭,居然把捻军剿推进了京畿重地,这个乌龙非同小可,惊动了两宫和圣驾,搞不好是灭九族的大罪。事后,剿灭这股捻匪的李鸿章得到了朝廷的嘉奖,并于1867年高升一步,官拜湖广总督。而放跑这股捻匪的左宗棠满心惶恐地进京述职,两宫皇太后在召见左宗棠时倒也没怎么怪罪,但是慈禧太后却客客气气地对左宗棠给予指示:“……谕以进兵须由东而西,力顾晋防,毋令内窜……”(粗译为:剿匪必须从东向西剿,力保山西,不许再让捻匪内窜。)然后仍令左宗棠回防西北。
左宗棠心坠谷底,剿匪剿了大半辈子,到头来却被两宫皇太后“指点”剿匪必须“自东而西”,自己给自己丢了脸也就罢了,还让李鸿章在朝廷大出风头。以左宗棠的性格,这口气肯定咽不下去,但咽不下去也得咽,谁让捻军是从自己的防区溜走的呢?要说剿贼的能力,左宗棠瞧得上眼的人并不多,而李鸿章恰恰是左宗棠少数能正眼瞧的人中的一个。形势不如人强,不服气不行。
1868年1月,李鸿章的马队(由淮军长江水师集体转制而来,丁汝昌位列其中)在山东剿灭了赖文光、任柱所部的东捻军主力,任柱被杀,赖文光只身逃到扬州被俘。同年8月,西捻军张宗禹部在鲁西北陷入李鸿章的重重包围,全军覆灭,张宗禹渡徒骇河不知所终,一说投河而死。肆虐北方的捻军至此被完全平定。战后论功以淮军居首,李鸿章因此荣升协办大学士。小肚鸡肠的左宗棠显然不想看到李鸿章如此出风头,因此,没事找事地无端怀疑李鸿章所言张宗禹投徒骇河自杀而死的说法,认为张宗禹依然在逃,遂率军四处进行搜捕,结果当然是一无所获。但是左宗棠如此空穴来风、存心挑衅式的举动令之前对其再三容忍的李鸿章也忍无可忍,气愤难平地在写给恩师曾国藩的信中毫不客气地直称左宗棠是“阿瞒本色,于此毕露”。
“台湾事件”的鲜明对比——左冷漠李热心
台湾,虽然早在三国时期就有东吴大将卫温、诸葛直二人率甲士万人登陆,成为有记载的抵达台湾的第一批中原人。清政府在台湾设府置县并向台湾移民,他们只是在台北、基隆和台南等处聚居,大量被称为“化外生番”的高山族原住民部落依旧是台湾岛居民的主体,其中某些原住民民风彪悍而且排外,对一切“非我族类”多持敌视态度。偏偏台湾海域又是台风多发区,经常会有海上失事船只的幸存者被海浪冲到岛上,被原住民部落视为入侵者而被屡屡残忍杀害。1871年,“牡丹社事件”爆发,即琉球遇难船只幸存船民登岸,不料被牡丹社原住民迅速包围,其中54人被杀。原本这仅仅是中国和藩属琉球之间的事件却让日本横插一杠,对琉球觊觎已久的日本以琉球曾向日本萨摩藩进贡而成为日本属国为由,以琉球宗主国的身份插手琉球船民被杀事件,好战的日本军部要求对“残暴”的台湾生番进行讨伐,为琉球船员“报仇”。而外交经验不足的清政府总理衙门大臣、吏部尚书毛昶熙及户部尚书董恂为了推卸责任,给出了“杀人者皆生番,故且置化外。皆不服王化”的荒唐答复,进而让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以“中国派遣特命全权大臣”的身份前来中国交涉此事。期间,日本随员柳原前光捕捉到了借口:“生番害人,贵国舍而不治,我却将问罪岛人。”而此时,糊涂的毛、董二人居然回答:“生番系我化外之民,问罪与否,听凭贵国办理。”终于,日本盼到了梦寐以求且名正言顺的出兵理由。
1874年5月,3600名日本海、陆军在“日本台湾番地事务都督”西乡从道的带领下,携带大炮等军火辎重分乘运输船“明光丸”、“有功丸”、“三邦丸”,在炮舰“日进”、“孟春”的护卫下于当月7日在台湾琅桥海滩登陆。登陆后立即对当地高士佛、牡丹社等原住民部落进行武装进攻。
清政府闻讯后大为震惊,14日,上谕下达:“生番地方本系中国辖境,岂容日本窥伺?”遂下令命李鸿章同日本方面进行交涉,同时任命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组织船政舰队前往台湾与日军抗衡。
接到上谕后的沈葆桢不敢怠慢,立刻召回了调拨在各省的船政军舰,紧急按照舰队编制进行编组操练,计有二等巡洋舰“扬武”,大型炮舰“伏波”、“安澜”、“飞云”,小型炮舰“福星”、“长胜”、“海东云”等。经过短时间的“速成训练”后,舰队便被迅速派往台湾海域和日本舰队对峙,对日舰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中国船政舰队迅速编组完毕,沈葆桢又几经周折,终于从李鸿章处借来了十三营的淮军精锐,由船政舰队载往台湾要口驻扎,与日军登陆部队对峙。
沈葆桢身处福建,请调陆军自然是就近,撇开福建省本身不谈,浙江、江西、广东等福建周边省份是沈葆桢请调陆军的首选,沈葆桢原本以为,凭他和左宗棠曾经的“死党”关系,就算广东和江西的督抚不给面子,有左宗棠大量旧部主持的浙江总该给点面子吧!没想到浙江省也不给沈葆桢一丁点儿面子。吃了好几处闭门羹的沈葆桢向左宗棠求助,可是远在西北的左宗棠一心扑在西北战事上,唯恐一钱银子从自己手里溜掉,又怎么肯为了台湾分出一兵一卒、一钱一饷呢?更何况,此时沈葆桢已经和李鸿章开始有意无意地结成南北奥援,左宗棠自认为是沈葆桢的伯乐,对沈葆桢的举动十分不满,认为是对他赤裸裸的“背叛”。因此,左宗棠有心看沈葆桢的笑话,也算是对沈葆桢“背叛”行为的警告。
与左宗棠的冷漠相比,李鸿章显得非常热心。身为直隶总督的李鸿章虽然受命与日方进行外交谈判,但是既然与福建毗邻的浙江、江西和广东等省的督抚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他又有什么理由去接受沈葆桢的请求呢?
其中的原因说起来也并非不能理解,李鸿章因办洋务在当时的官场上属于“异类”,不容于传统的社会舆论,经常成为众矢之的,举步维艰。而支持李鸿章的人又屈指可数,因此,李鸿章非常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看到沈葆桢的海防思想和自己相似,更何况又是自己丁未年进士科的同年,李鸿章便将沈葆桢纳入到争取的同盟对象当中。
因此,当四处碰壁的沈葆桢试探性地向李鸿章发出借兵申请时,李鸿章便非常热心地给予了回应。很快,在淮军营务处盛宣怀的具体安排下,原驻扎在徐州的铭军唐定奎部十三营精锐从徐州行军到长江边的瓜州渡口,登上船政派来的运输舰“永保”、“琛航”、“大雅”,前往台湾。面对李鸿章的爽快大度,沈葆桢感动莫名,自比“贫儿暴富”,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
左宗棠的冷漠和李鸿章的热心在沈葆桢心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事之后,左宗棠少了一个“死党”,而李鸿章多了一个“知己”。在话语权的争夺上,左宗棠显然又失一招。
大筹议前传——海防大筹议封疆大吏阵容
虽然“台湾事件”最终以日本退兵画上休止符,但因为中方仓促布置,未能对日方形成有效的反制措施,不仅被日本勒索了50万两“抚恤金”不说,还被迫承认了日方出兵台湾是出自“保民义举”。这对以天朝上国自居,视日本为撮尔小邦的大清朝廷来说不吝是当头一棒。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鬼子六”恭亲王痛感海防的重要,于“台湾事件”平息不久就以总理衙门的名义向同治皇帝和掌握实权的两宫皇太后上奏,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6条建议,引起了两宫皇太后的重视,并于1874年11月以同治皇帝的名义下达上谕,要求南北洋大臣、沿海滨江各省督抚将军集思广益,就总理衙门提出的6条建议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细化措施,史称“第一次海防大筹议”。
南北洋大臣、沿海滨江各省督抚将军的具体名单如下:直隶总督李鸿章、钦差办理台湾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沈葆桢、两江总督李宗羲、盛京将军都兴阿、闽浙总督李鹤年、湖广总督李瀚章、两广总督英瀚、广东巡抚张兆栋、漕运总督文彬、山东巡抚丁宝桢、江苏巡
抚吴元炳、安徽巡抚裕禄、浙江巡抚杨昌睿、江西巡抚刘坤一、福建巡抚王凯泰、湖南巡抚王文韶总共16人。另外,起草过《海洋水师章程》的前江苏巡抚丁日昌此时正在广东原籍养病,因此也得到了上奏的权利(奏折由张兆栋转交)。而此时任甘陕总督的左宗棠虽然已不在沿江沿海任职,但是由于其属于洋务派,又是福建船政局的倡导者,所以朝廷也将总理衙门的奏折抄寄一份给他,以征求左宗棠的意见。而恰恰是这一征求,导致了节外生枝……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