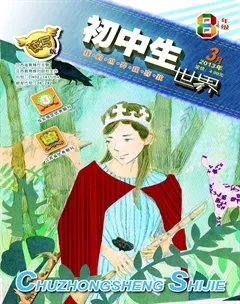风范大国民
在巴黎,我住在塞纳河边一幢十九世纪的老楼里,对法国庭院深深的市井文化有一些切身体会。那些飘散在生活里的细节总是让我无比感动。有一天我下楼去买食物,看见走廊的玻璃门正反面都贴上了精美的信笺,上面工工整整地写了几行字:
亲爱的邻居们:
今天我过生日,偶有噪音,请你们原谅。
感谢你们的理解。
多尼娅
原来我的邻居多尼娅女士今天要过生日,她请了几个朋友来庆贺,因为害怕不小心吵着大家,便写了两张纸条,希望得到大家的理解与宽容。后来我发现,事实上,那天晚上她家没有传出一点喧闹的声音。这只是日常生活中平常的一幕。当晚,我坐在塞纳河边上,很难为情——以中国人的风格情操,多半是要“与民同乐”的。然而,这种“同乐”多半都是建立在扰民的基础之上。别说结婚时的吹吹打打,即使温文尔雅的求爱,也不免会变成高音喇叭里的“安红,我爱你”!
法国的日常生活,留给我印象深刻的事还有很多。比如说,在进出门厅的时候,走在你前面的人会用手挡着门扉等你进,虽然你们并不相识,也可能你们相距有十米的距离。这些细节,让人觉得生活在其中十分温暖。又比如说,在电视里,当主持人出现口误的时候,他会在纠正字词的同时向观众表示歉意。这是一种对观众表示尊重的职业素养。如果你只是急着纠正发音,并不代表你因为你的错误向观众表达了歉意。既然没有这种歉意表达,口误者就会时常想着蒙混过关。在法国,如果播音员在电视里说错了话而不向公众道歉,只会让人觉得他没有教养,而不只是职业道德的问题。在日常生活里,这种“对不起”文化是随处可见的。甚至可以说,许多场合,不经意的歉意表达已经成为西方忏悔文化的一部分。1793年10月16日,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特瓦纳特被判处死刑。走上断头台时,玛丽王后不小心踩到了刽子手的脚,她因此留下了一生中最后也是最让所有法国人至今都脸红心疼的一句话:“先生,我请求您的原谅,我不是有意的。”
十几年前,《泰坦尼克号》中国电影院里掀起了眼泪风暴。最让我感动的镜头,不是爱情,而是生死,是人们怎样有序地上救生艇,是竟然没有一人喊出“让领导同志先走”的口号。在巨轮即将沉没之时,许多人表现出的英雄气概,既是人道主义的,也是出于对秩序的尊重。所以最早知道要沉船、最有条件逃生的船长愿与船同沉;牧师也不忙着逃生,而是为人们朗诵《圣经》;让人感动的还有乐队,在死神逼近的时候,以琴声温暖人心……同样是电影,在没有秩序的年代,我们看到的只是《滚滚红尘》里被拥挤的人群冲散的一双痴男怨女。如果说当时人们不讲秩序是因为战乱,那么现在中国人日常生活里不讲秩序该拿什么当替罪羊?
鸦片战争以降,中国人做梦都想自己国家变得强大。李叔同26岁时曾写《祖国歌》述怀:“上下数千年,一脉延,文明莫与肩。纵横数万里,膏腴地,独享天然利。国是世界最古国,民是亚洲大国民。呜呼,大国民!呜呼,唯我大国民!幸生珍世界,琳琅十倍增声价。我将骑狮越昆仑,驾鹤飞渡太平洋,谁与我仗剑挥刀?呜呼,大国民!谁与我鼓吹庆升平?”字里行间,甚至还有些刀光之气。近年来,伴随着中国国力上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自问如何胜任做大国公民,这是中国人集体理性上升的一个标志。然而,大家所谈多是“不让狂热的民族主义引火烧身”式的警告。笔者以为,除了民族、国家这些大词之外,塑造大国公民,应该从情结走向细节。政治文明之外,更有生活文明。所谓生活文明,可以理解为一种对人尊重、对秩序尊重的文化,它是一切政治文明的摇篮。没有人本主义与秩序文明的根基,幸福会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美丽浪漫却不在我们身边,而自由随时会摇身一变,成为一根驱赶他者生活安宁的鞭子。
(选自《思想国》,熊培云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