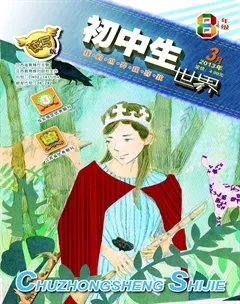有一种声音
曾有一段时间,我们一家都惧怕听到他的声音。
他是一个骑着三轮车的卖米老人,自我幼时起,他就蹬着那辆永远不换的黑三轮车,拖着他那永远不变的诚恳而悲凉的长调,按着永不变更的顺序仰面喊着:“李阿姨,阿要新米?”“张老太,阿要米?” “老头……”厚重的乡音回荡在居民楼间,穿透墙板、水泥、纱窗,于是他的老客户们便推开窗,和他讨价还价。
他一直都是叫我外公“老头”的,在外公刚过世时也是这么喊着。张望着空空的窗口,他并不知道这个“老头”已经不在了,不能再打开窗问“新米怎么卖”。他只是一次次地仰面喊:“老头,老头……”
于是外婆仰面而泣,妈妈的眼眶也红红的,而爸爸却疑惑着,妈妈便缓缓地把手指伸向外公房间的窗,说:“你听。”
大家就都安静下来,只有一股酸涩涌入家人的胸口。外公的“五七”刚过去,丧失亲人的痛苦在鞭炮、香烛和哀乐里剧烈地燃烧过,那些燃烧后留下的、难以挥去的黑色烟尘还在身体里流动,常常呛得我们满脸是泪。而这个声音,又一次牵动了我们的神经,如一截浮木,无意间触及了河岸,轻轻撞击松软的土壤,又随即漂去。我们心头那松脆板结的防线,就这么被击溃了。
没人有勇气打开窗,告诉楼下恳切呼喊着的卖米老人:“别喊了,‘老头’已经不在了……”
于是,在那段日子里,我们都害怕他的声音在一个平静的白日响起,搅起亲人心头的阵阵悲意。
他喊着,我们又何尝不想喊?喊着老伴、爸、外公……也许外公就会在窗边出现。但当卖米老人骑着三轮车喊起“老头”时,我们只能望着窗口的阳光与微尘,或叹息,或啜泣。
这声音,从我们的心灵深处响起,卷来阵阵猛烈的洪流,再让我们自己将其一点点饮尽。
时间一页页地向后翻去。
我们渐渐开始适应没有外公的日子。当我吃着妈妈做的点心,不经意地说出“不如外公做的好吃”时,不会再卡在“外公”二字上久久无声;外婆每天用手绢擦拭外公遗照的相框,当她细心地擦去照片上的灰尘时,也开始擦去自己曾经的泪痕……浓浓的酸苦渐渐被时光冲刷到平淡,慢慢地,只剩下温热。
与此同时,卖米老人的声音仍时时响起。也许他奇怪于这“老头”怎么总不出现,却也每次都来楼下吆喝几声。
我们渐渐不再因这声音的出现而不知所措。
我伏在窗边,看着三轮车上那张熟悉的黝黑的脸,他正张着嘴,用力地喊着“要不要米啊”。我想起外公以前总是应着那声“老头”,打开玻璃窗,向下一望,问卖米老人:“是新米吗?”
“是新米!我自己也是吃这米的,好吃的!”
“是不是啊?那怎么卖啊?”
……
两个老人操着方言你一言,我一语,简单地讨价还价;或是外公毫无意义地问着“好吃吗”,或是卖米老人频频地点头说着“当然好吃”……
我会问外公:“怎么那个爷爷还叫你老头呀,他自己就不老吗?”说罢,自顾自咯咯地笑着……
现在,我在窗口望着老人载着米向一家又一家吆喝,好像外公刚刚也还在楼下跟他买米,正把米搬向楼上。窗口投进温暖的阳光,空气里点点灰尘飘浮。我独自站着,却感到浑身有股暖意,似乎外公就在身边。
我回头望着屋内,妈妈微笑着说道:“好想爸啊,那边也有好吃的米吗?”
我们相视笑了,并不说话。
声音在午后的暖意里氤氲。这声音,大概是一阵风吧,轻轻拂过,将我们心中的湖面晃起碧蓝的波,只有淡淡的思念一圈圈晕开。
这声音也是从心中喊出的,只是时光和爱意磨去了那锋利刺耳的音调,只留下记忆中的温和与柔软。
- 初中生世界·八年级的其它文章
- 运动物体拍摄攻略
- 20年后,我跨进了母校大门
- 爸爸,我想好好和你谈一谈
- 生活的芬芳
- 爱竹
- 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