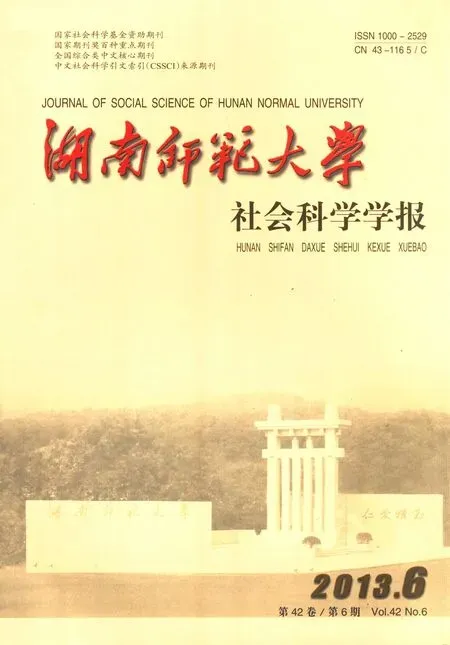网络社会人际关系嬗变对政府行动的影响
——以扩散性动员为视角
朱海龙,彭 鑫
网络社会人际关系嬗变对政府行动的影响
——以扩散性动员为视角
朱海龙,彭 鑫
网络系统地促成了作为国家与社会宏观互动表征的集体行动模式的变迁,尤其是网络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变化相当程度地影响了政府行动:网络社会中人际关系强化了政府行动的社会基础,改变了政府行动性质,促动了政府行动机制的变化,最后,网络社会的人际关系促生了一种全新的政府行动监督机制。从而在某种意义上深刻地促进了扩散性动员,使得网络社会中的集体行动更为广泛地发生,同时对网络社会中的政府行动也是一个全新的考验。
网络社会;人际关系;政府行动;扩散性动员
一、引言
在转型中国,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正在兴起:网络正在重构人们的人际联系,进而重塑了人们的社会关系,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结构模式与特点,一个全新的网络社会正在形成。正是社会模式的深刻变迁促成了政府行动的转换,也一定程度上“从下到上”式地重构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又进一步系统地促成了作为国家与社会宏观互动表征的集体行动模式的变迁。无疑,这种巨大的促进作用是十分复杂和多元的,对于中国社会自身来说,是真正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①,正是因为这种巨大的社会重构,使得中国千年以来形成的既定的政治社会运行轨迹发生巨变。我们无法在这么一篇短短的论文中对其做全面的解构和分析。我们仅仅选择其中的一个方面的关系(即网络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对政府行动的影响)对其探索,以求不断积累,最终达致对这两者相对清晰地了解和分析。对于其他方面研究本人已经或者将逐步著文分析。
二、人际关系、扩散性动员和政府行动
人际关系是指人和人之间的联系状态。动员是指发动人参加某种活动,具有鼓动、宣传、激励等涵义。凡是动员必有对象,动员在本研究中是指政治参与型集体行动的动员,因此根据动员的形式和特征,动员又分为博弈性动员和扩散性动员。扩散性动员不以直接参与集体行动为目标,但能为集体行动的生成和发展创造必要的社会条件。它与博弈性动员既相互区分又遥相呼应。扩散性动员主要发生在事件的爆发期,扩散性动员本身又具有一定的阶段性,它表现在塑造社会舆论、获取社会支持(影响非直接参与者的情绪、态度和行为等)、影响政府行动等方面。动员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人际互动,人际关系的形式和特征对政府行动有着巨大的塑造作用或者结构性限制,没有了人际联系的确立,则动员皆不可能。
在西方当前比较经典的集体行动理论中都非常强调外在资源的价值和意义,或者强调集体行动的政治机会与过程。但作为一个非常尊重个人自由和价值的文化传统的西方社会却很少关注到集体行动参与者个体及其组合的地位和作用,更不用说忽视它的非直接参与者的行动——扩散性动员在事件变化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实质上在网络社会中,它已经成为集体行动的“第二条战线”,其作用事实上已经超越了博弈性动员,然而在所有当前的研究中,似乎都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扩散性动员的地位和作用了,而作为扩散性动员过程之中的关键之关键又是政府行动之变化。
因为政府行动在扩散性动员的链条中处于最后阶段,也是扩散性动员最为关键的阶段,且比较敏感。它构造、定位社会舆论,影响社会支持,并最终可能影响集体行动发展的形态。政府行动是指政府部门及其官员在集体行动过程中的反应,包括内在态度和外在行为。政府行动是网络社会中集体行动的最大外在变量,因此也成为扩散性动员过程中关键的一环。政府行动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是很可能是集体行动博弈性动员和行动的对象;另一方面它又必然与集体行动博弈性动员有着某种内在的一致性,与前者有着某种有意或者无意的协调与配合,否则要么集体行动博弈性动员有可能找不到行动的目标和意义,要么有可能失去存在与发展的可能。政府行动往往是个复杂的概念,既有符合社会期望的角色性的行动,也有角色之外的个体化的行动。既有部门的规范化的行动,也有个体的越轨行动。作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表征之一,政府行动无疑与它的相对方——社会的组合方式与行动方式密切相关。
三、网络社会人际关系嬗变与政府行动转换
首先,网络社会中人际关系强化了政府行动的社会基础
针对某一事件的政府行动必须考虑事件的影响主体。作为一个代表民众利益的政府自然尊重民众的利益诉求,这是政府行动“政治合法性”的根源,也是政府部门及其官员追求的行动目标。即使在某种情形下,这个目标不是实质追求,也是他们行动的表征目标。当社会事件通过扩散性动员形成一个整体性的民众诉求时,更是政府不得不要考虑的情形了。围绕社会事件形成的群体及其组合方式便是政府行动的社会基础。这一点在西方社会,强大的中层社会组织甚至已经形成了可与政府、企业相制衡的第三部门,无论是民主选举还是政策制定、执行,政府部门或者官员都不得不考量他们及其背后群体的诉求。
在当前的中国社会,由于中层社会组织建设的滞后,在通常条件下,民众诉求能够影响政府的行动却必须要有两个基础性要求:一是价值观的广泛认同;二是人际之间的广泛联系。前者是基础,后者是条件,两者缺一不可。价值认同是扩散性动员的第一个基础性条件,没有了共同价值做支撑的众多支持者,则一切皆不可能。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无论在何种社会,对任何一个争议的事件,都会存在相当广泛的持相同意见者,但是只有相互联系与共振才有可能使得条件变成现实。因此只有在共同认可价值观的基础上有效形成广泛的人际联系,才有可能汇聚民意,扩大影响,进而影响到政府行动。全新的网络社会人际关系则一方面促进了广泛认同的价值主体的形成,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它直接突入社会关系的内部,促进了人们之间的广泛联系,从而使得作为公共部门的政府的任何行动都能感知到社会的民意风向标并在不同情形下受其影响。
因此,在传统社会中,人际之间的联系总因为各种自然、社会原因而被阻隔②,因此在一个缺乏社会组织把人们有效群体化的“非团体社会”③,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就是费孝通老人家所说的“差序格局”。这种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④。由于受大多数社会个体“先赋”人际关系的限制,这种社会影响很难达到一定影响或改变政府行动的张力,甚至无法为政府所感知。而且作为一个理想类型的社会关系模型,无疑费老的“差序格局”是从微观个体的视角来思考问题的了,但从宏观整体的角度来说,在传统社会中,我们社会关系的模型又是“封建式”的,如果整个中国社会是一个最大的社会关系圈子,不同的社会关系圈子之间互相封闭,缺乏有效互动,彼此陌生,构造了中国式的“一盘散沙”分割型的“地方性社会”了,这种“地方性社会”又由于中国社会管理集权的传统,由政府官员及其与其结盟的精英所主导,因此弱势的民众之间是非常难以互相响应,互为支持,更难形成集体性的表达影响强势的政府及其行动了。
而网络社会中的人际关系首先突破了“先赋”关系的限制,他们的社会影响力不再局限在“熟人社会”中了,在网络中社会中,由于网络强大的“赋权”功能,任何一个个体都可能是网络中那只扇动翅膀的“蝴蝶”,“六度分割”⑤几乎发挥到极致,网络帮助人们跳出了种种“先赋”关系的限制,同时由于网络陌生人的社会特质,“波纹式”的“特殊性关系”受到监控,而以群体为基础的“团体”式“普遍性关系”开始广泛建立,与他人的关系不再限制在特定的具体范围里,而是处于广泛的、流动的网络空间里了⑥。在传统社会中,只有某种具有“特殊性关系”背景的人才能达到的社会影响力,在网络社会中已经具有了某种普遍性了。任何一个政府行动都必须考量自己在网络空间中可能产生的影响了。同时网络作为完全异质的力量突入中国社会关系的内部,重新塑造了中国的社会关系模型:由“封建式”向“扁平化”迈进。尽管不同的圈子更加广泛地建立了,但是各个圈子之间的封闭性被打破,流动性大为增强,互动不断增加,甚至还可以进行一个“类组织化”的集体行动了。这样大大促进了他们的集体化、组织化的行动,从而也在某种意义上决定性地影响到政府行动了。
其次,网络社会中人际关系改变了政府行动性质
在传统社会中,人们与他人的人际关系有限、封闭、狭窄。这就产生了两种情形:一是由于缺乏中层社会组织的支持,在一个“碎片化”的社会里,个体之间由于缺乏必要的相互支持,不能有效地扩散,且由于信息传递的效率及其低下,从而阻塞了“社会事件”中人际互动向社会互动转变的渠道与可能。因此任何一个事件都只能是“地方性”的和“非社会性”的,都只是一个具体的行政问题,都只涉及到非常有限的个体,或者说“碎片化”的人群。而对更广泛的社会大众来说,他们是旁观者,是无涉者,他们也往往不明所以然,由社会事件引发的社会群体既无组织,更无行动能力。“社会事件”因此无法引起宏观震荡,按照“科层制”的管理原则和方法,政府及其官员也因此为有限涉入,无须整体介入。二是在这样的人际关系中,由于缺乏有效监督的外部社会力量,再加内部制衡机制受到“熟人关系”的稀释,权力向政府及其官员方倾斜,实质是政府一极独大,社会为部分精英所控制。这种社会关系结构异化的极端是官员控制一切:“书记就是党”⑦。
因此一旦社会事件发生,政府及其官员所要做的是防止事件的扩散,防止事件的宏观化,竭力避免事件超出自己社会关系的控制,切实将事件控制在自己能掌控的“地方性社会”中,避免事件的升级变性。尤其是在一个科层化的社会里,要防止其他政府官员,特别是上级领导的涉入,因此也会尽可能将事件控制在一个具体的行政性问题的范围内解决,因为这样只是牵涉到一个“行政问题”,而非“政治问题”,前者仅仅是科学化的“对与错”的问题,而后者则是涉及基本的立场与态度的“是与非”的问题,前者也许是“能力”和“机会”问题,而后者则是“思想认识”问题,两者的性质截然不同:理论上前者是可容忍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因此前者将有更大的弹性和进退的机会,而后者一旦定性,则是具有某种敌对性质的冲突,转寰的余地就非常有限了,因此所面临的压力和结果也将大不相同。
但网络中人际关系的变迁开始大大促成了这种关系的变化,由于网络中的人际关系流动性和浓缩性,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地球村”时代来临,正如著名的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是人体的延伸”,人们通过网络延伸的人体器官(如眼睛、耳朵),实现了在传统社会几乎不可能的“在场”,人们之间的关系既不完全等同于传统的同质的“熟人社会”,也不同于异质的“碎片化”的“陌生人社会”,虽然仍然没有中层社会组织参与,但这种网络社会关系反而具有了某些“团体化社会关系”的性质和特征。因此在网络空间里,任何一个社会事件都会形成一个“社会会议”,而且这样的“社会会议”是不断生成并流动的⑧。
在这样的“社会会议”过程中,一是在网络信息“核爆式”的连环传递下,人际互动高速而具有非凡的效率,人际互动广泛发生,从而使得“社会事件”能在短时间内由微观的“人际互动”向宏观的“社会互动”转换。二是这样的“人际互动”是“脱域”、“去个体”、“符号化”的,至少在形式上是平等的,没有了任何脱离普通参与者的精英,任何人都几乎无法单独控制,一手遮天。因此人际互动经过不断地博弈、聚焦、竞争,交互影响,并经过不断生成和流动的“社会会议”,进而产生宏观意义上的社会互动。一个网络社会事件往往轻易就有数万人,几十万人,甚至就有几百万人参与其中。赵洪祝同志在网上交流,一个访谈的同时在线人数达220万之多⑨。因此一般来说,当今我们国家一个省一般几千万人,一个市几百万人,一个县几十万人。即使一个短暂的访谈就相当于又一个全市范围内的老百姓都参与其中了。无疑这是一个巨大的群体,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这就为行政问题政治化奠定了基础,因此在网络社会中,在一个人数众多的扩散性动员的过程中,政府行动,哪怕就是一个很少的细枝末节,都有可能极具政治性了。
再次,网络社会人际关系促动了政府行动机制的变化
在传统社会中,政府行动机制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自上而下”是政府行动的基本模式,它也是科层官僚体制的基本特征与要求。二是社会问题解决基本都是政府的单方行动,具有强烈的单边色彩,问题的定性、认识与决策基本都是依靠政府及其官员的内审、自我监督。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它是与社会过程是双轨运行,没有互动与交集。
事实上,传统的政府行动机制是依托于正式的、官方的、文本的科层组织关系。传统社会,任何一个集群性的事件一旦发生,无论在何种制度社会中都会受到高度关注与重视。而在高度集权的“总体性社会”,问题的解决基本路径主要依赖于“全能政府”。在传统的非网络社会中,从总体上来说,政府是一个相对“统一体”,在扩散性动员过程中,它是一个集体性概念,而事实上上下级政府及其部门、人员并不是“角色化”运行,他们之间也是有着经常性的互动,并有着日常的情感联络,并且往往具有厉害关系,因此容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这种厉害关联机制和日常化的运行模式中,政府行动往往容易自上而下,单边行动。
同时,在传统的非网络社会中,由于时间和空间等的限制,民众的关系由于时空的特点限制,关系处于一种分散、隔离的状态,彼此没有互动与响应,从而不能产生有效的社会反响,在与政府行动的博弈过程中,基本处于弱势、被动的地位。无论何种民众诉求最终都依赖于政府行动。但民众的诉求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获得政府行动的响应,在“非角色化”运行的地方社会中又取决于形形色色的复杂的人际关系的支持。而作为主要的社会资本形式,民众不仅仅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处于劣势,在社会关系方面更是处于劣势,而相对方政府的行动却处于结构性的优势⑩,因此在一个缺乏中层组织的“碎片化”的社会里,民众之间是孤立的、无交集的,“一体化”的政府往往对民众人际关系具有明显的优势,他们基本能够分割、包围,甚至操纵民众的人际关系的能力(11)。于是在“地方社会”中的民众无法有效表达自身诉求和追求自身利益,而政府行动则有可能非常随意。一旦出现问题,则他们会利用自己在“社会网”中的“单边”优势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样一来,政府行动就容易发生变异:一方面作为社会问题却与社会没有互动,没有社会制衡,更无社会监督,是一种单向行动;另一方面内部监督机制由于受到人际操作,无法有效监控政府行动。
而在网络社会中,人际关系开始发生嬗变、人际关系的高密度,群簇化、多维连接和单一、非正式、弱关系的特性使之形成一个分散的、潜在的无形的“类有机体”,它能够突破传统社会的种种限制,及时地获取广泛的社会支持,从而有效地实现扩散性动员,使得集体行动在无组织的社会状态下能够不断发生、扩展并持续(12)。这样一方面网络形成的非正式的、非组织化的关系由零散分割走向了集结集中,通过紧密的联系获得集体的张力,从而第一次取得了与正式的、官方的、文本的正式的组织关系同等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这种非正式、非科层化的网络关系动摇了正式的、官方的、文本的科层制组织关系,“科层制角色”与“个人心理空间”的矛盾在网络关系中得到释放,“一体化”的政府关系开始消融,堡垒更容易从内部攻破,在众多社会事件中的“深喉”(13)都来自于政府内部人士便是明证。
因此网络社会中政府行动的机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政府行动模式不再完全是科层制式的“自上而下”,在网络社会中,政府与社会的强弱关系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强国家、弱社会”的传统在不经意的过程中有了某种革命性的颠覆,政府单轨式的运行现象有了相当的改观,政府与社会有了更多的交集与互动,政府在行动中更多地考虑到社会的意愿,有时候甚至是主动退避三舍,征求民意。民众与社会不再注定是消极被动的行动者,他们的意志和行为更多地影响到了政府行动,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行动的内省性和自我监督加强,不作为,任意作为和过度作为等都将在一定程度上消减。
最后,网络社会的人际关系促生了一种全新的政府行动监督机制
政府行动的监督体制一般分为两种:一种内部性的监督体制,指依赖党政机关的权力进行的监督体制。一种外部性的监督体制。外部监督主要是指社会监督,尤其是新闻媒体监督。任何政府行动的问题最终必须依靠政府自身的监督来解决,它的优势在于解决问题的刚性,效率、合法性。而外部监督机制的优势则在于其民意的代表,协商的民主性,尤其是其发现问题的能力和灵活性。
但在传统的非网络社会,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各个内外部监督体制之间通常是分割运行,互相交集困难重重,各种监督机制功能很难真正发挥:由于厉害关联机制和日常情感联系,内部监督机制流于形式;由于关系“碎片化”,相互分散、区隔,外部监督机制无从着力;同时更关键的是内外两种监督机制两重世界,两种圈子,信息不通,互为障碍,难于相互响应,事情往往不了了之。事实上,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即使是监督体制的运作都依赖于各种关系基础,没有了关系的传递,则一切皆不可能。在网络社会中,由于人际关系的网络传递,外部监督机制开始强化,内部监督机制开始硬化,更关键的是内部监督机制和外部监督机制开始了“整合化”的趋势,它们遥相呼应,在相互交集的基础上呈现出了一些全新的特征:
第一,外部监督机制强化。网络关系的广泛性,让所有的政府行动都置于阳光之下。网络关系无处不在,尤其是网络中的“拍客”、“深喉”让权力受到监督,而特有的“网络围观”更让人敬畏。无数的网民,包括社会精英,甚至其它官员都会自动加入到对那些敢匿顾民意的官员监督队伍中来,甚至会直接对那些当事官员施加压力或者采取行动。官员也许位高权重,但弱者也有自己的“武器”,可能官员本人就有命脉为其周围并不瞩目的小人物所掌握,而这种飞扬跋扈,敢置民意与职位宗旨公然不顾的官员本身可能就存在种种问题,也总会有其他方面致命的弱点和短处,只是其运用自己的权势得以暂时掩盖,但是一旦引起网络社会的关注,则其被揭发并由网络社会发散的范围远远超出其控制的能力(比如闻名遐迩的人肉搜索让很多无法无天的官员开始有了一种畏惧感),引起更大的社会网的关注与更多的干预,网络使其无处循形。
第二,内部监督机制硬化。政府部门中的厉害关联机制和日常情感联络是千年来的中国分割型的“地方性社会”运行的基本模式,所谓“山高皇帝远”正是政府行动内部监督机制流于形式的重要原因。但在网络中,这种关系构建的时间、空间和社会条件被彻底解构,由某一焦点事件形成的共振网迅速扩大,由于主体关系的庞大与多元,使得它已经超脱于狭窄的厉害关系与情感关联了,再加上网络社会人际传播的便捷,迅速,在很短的时间内即会卷入巨大的社会关系,其影响力在社会网中迅速扩展,这种全新的扩展产生了两个直接的后果:一是这种扩展的效率使得它的覆盖范围远远超出任何个体的控制与掌握,所谓的“民意如山”,不能置之不顾,二是对这种扩展如果反向干预,欲盖弥彰,反而会带来更坏的效果。随之而来,各种内部监督更趋发挥真正作用,受到其他“非正式关系”干预的可能性就越小。
第三,内部监督机制和外部监督机制日趋整合。内部监督机制和外部监督机制本应一体,互相配合,才能真正发挥各自功能与作用。这种关系本来需要正式的社会设置,尤其是制度安排来承担,但在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此类社会设置还远未成熟,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处于分离状态,相互之间的配合主要限于个体化的关系运作,导致的主要问题是内部监督很少能接纳外部监督的反应。但在网络社会中,首先人际关系广泛性与集成性,汇聚了社会力量,改变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性质,极大地促进了内部监督机制对外部监督机制的反应的敏感度和重视度。其次网络社会中关系的普遍性的特质,解构了传统的集体行动的敏感性,进一步突破了政府利益关联体制和日常“潜规则”系统,使得内部监督系统回归“自我”,主动响应社会呼声,履行自身职责。再次就是网络社会关系无处不在,事实上形成了对内部监督系统的再监督,形成了特有的三重关系,在传统媒体失效的地方,自媒体扛起了舆论监督的旗帜。
可以说在网络社会中已经不再有“山高皇帝远”,甚至有人说“网络是到在中南海最近的距离”。即使最基层的社会,任何人想“一手遮天”的时代已经过去,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官员竟然也成了网络社会中的“弱者”。一些官员如果处于传统和本能,看不到网络社会发展的趋势、力量的现实,那就会与这种新的监督机制撞车,结果可想而知。正是针对网络中广泛产生的民意,2009年中央进一步加大了对严重违背民意、招惹民怨的官员问责力度。6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在问责的6种情形中,包括“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的”情形。2009年中在网上网下造成恶劣影响的王帅案、邓玉娇案、石首骚乱、开胸验肺案、“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事件、重庆高考加分作弊案等事件发生后,当事官员先后被问责。
结论
总之,网络社会中人际关系在变化,从相当深刻的意义上改变了黑格尔所说的“市民社会”的存在形式与性质,进一步深刻影响到“政治国家”之代表—政府的行动,从而在某种意义上深刻地促进了扩散性动员,使得网络社会中的集体行动更为广泛地发生了。无疑政府行动在扩散性动员链条中微妙而关键,到了政府直接面对扩散性动员的社会诉求以及来自不同方向压力做出反应性行动的时候,扩散性动员的动员无疑已经到了一个顶峰和转折点了,政府行动决定扩散性动员的形态、性质、意义和结果。合适的态度和行为将成为执政者和社会公众双方面的重大考验,处理得当,则可以化危机为转机,促进社会民主协商,提高民众的参政水平和政府执政能力,并进一步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良性互动的政府与社会关系,扩大执政基础,推动社会和谐、科学发展,从而真正地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否则,则会使得社会危机不断以“负资产”的形式不断聚集,将整个社会逐渐地造就成一个不断充气的气球,直到最后总的爆炸,这无疑是深刻的社会解体和失范,是各方都不能承受之重,是博弈论中共同的负面选择。总之,这种新型社会扩散性动员的处理模式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我们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变量。
注 释:
①梁启超:《李鸿章传》,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前言。
②朱海龙:《网络社会人际关系与社会舆论》《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4期。
③④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6页。
⑤有一个数学领域的猜想,名为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中文翻译包括以下几种:六度空间理论或小世界理论等。理论指出:你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六个,也就是说,最多通过六个人你就能够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
⑦《河南省卢氏县原县委书记杜保干大干“形象工程”实录》,载于《工人日报》2001年8月10日第1版。
⑨《一场访谈220万人同时在线,动动鼠标按按键盘就能跟“老赵”聊天》,载于《浙江日报》2008年12月15日第2版。
⑩著名学者于建嵘曾经调研指出在上访的维权农民中绝大多数民众的亲戚朋友没有一个科级干部。
(11)在众多的社会事件中,政府都使用浑身的解数控制当事人的各种关系,包括“株连”法,利用当事人的亲友关系牵制当事人,否则会受到扣除奖金、降级甚至开除公职等处罚。
(12)朱海龙:《网络社会人际关系与社会支持:以扩散性动员为视角》,《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13)深喉,即“DEEP THROAT”——在水门事件中为记者提供重要资料的人。1972年,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依据线人“深喉”的消息,捅开“水门事件”的内幕,导致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辞职下台。事后,这两名记者一直拒绝透露当时线人的身份,但是《华盛顿邮报》的总编辑西蒙斯引用了当时一部知名色情电影《深喉》的片名,作为告密者的化名。后来人们通常恭称那些为了公众利益而秘密地提供重要资料的人为“深喉”。“深喉”尤指哪些掌握重要信息源的政府人士。
The Network Society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Government Action:A Diffusion Mobilization Perspective
ZHU Hai-long,PENG Xin
Network systematically contributes to the changes of collective action model as macroscopic characterization of interaction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especially changes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the Internet Society considerably affect the government action:interpersonal relations in the network society strengthen the social basis of government action,alter the character of action,and promote the change of government action mechanism.Finally,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in network society produce a new government action supervision mechanism.Thus,in some sense,it deeply promote the diffusion of mobilization,the network society’s collective action is more widely occurred,and it is a test for government action.
Network of social;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government action;diffusion mobilization
朱海龙,湖南师范大学副编审,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北京 100732)彭 鑫,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湖南 长沙 410081)
(责任编校:文 泉)
湖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学术骨干培养计划项目“网络群体性事件应急管理研究”(12XGG15);中国博士后基金课题“网络群体性事件应急管理研究”(2013M541128);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网络社会中政治参与集体行为的动员和生成研究”(2010YBA166);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网络社会中政治参与集体行动的动员和生成”(1011238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