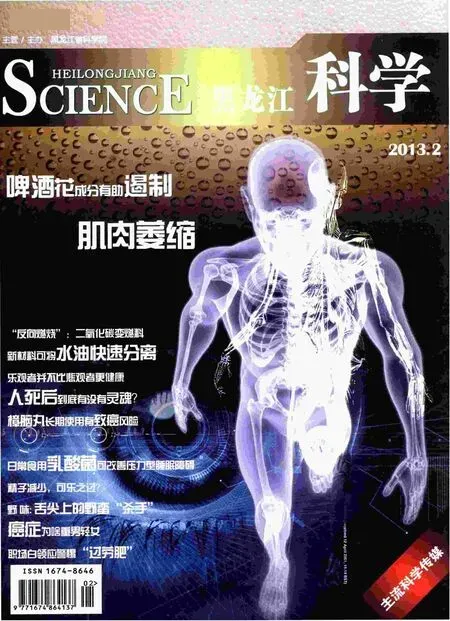商业银行破产的理论逻辑初探
邹德刚
(吉林大学法学院, 长春 130012)
始于2007年的金融危机强化了人们对于银行失败对经济产生强大破坏力的认识。可以说,至今世界经济还远未破解金融风暴的猛烈打击,各国、各界、各种力量与资源都被调集起来以消解这次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强大负作用,一个使世界经济安全着陆的构想急迫地拷问着有关商业银行破产及相关的制度。
成千上万人的破产给了我们一个教训:我们急切需要更加有效率、更加有系统性的监管规则。此外,对于当前审慎与监管的发展,就意味着我们需要赋予“相关力量(或为职能者)”以识别及将风险消解于早发阶段的“权利”。否则,一旦特定的风险脱离了早期的这种甄别与控制,无疑将产生巨大的、系统性的破坏作用,诚如此次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一样。而这样的“赋权”实质上属于商业银行破产法律的内容,它已经越过国界,成为了具有国际属性的一项诉求。这些诉求迫使银行破产形成独特的法律规则,用以应对实践中陷入困境的商业银行。利用有效的重组或关闭,限制其困境带来的冲击,以保护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解决巨大的金融危机或者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如若缺乏这种统一的法律步调,各国金融监管部门的干预就呈现一种无序状态,要么被迫提供巨大的流动性支撑金融机构,要么对其提供上万亿的资产担保。
商业银行破产的法律制度源于普通公司破产法律构造,但又有重大区别。因此,我们需要回顾普通公司破产的法律制度,同时对于商业银行的特性也需要重点探讨。只有通过基础破产的研究,我们才能推导出一个比较优化的商业银行破产框架。
由于银行的特殊性及其与法律制度的关联[1],公众的信任对于银行业而言是生死攸关的,一旦信任失去,银行将面临挤兑。更为可怕的是,这种挤兑造成极大的恐慌在银行业蔓延出去,甚至传导至整个经济层面。例如,大批银行的倒闭将直接中断支付体系的正常运作、停止了必要的信用供给,从而引发货币危机,代价更是无法估量的。
普通的破产规则对于商业银行而言是不适合的,因为它过于强调银行债权人的利益最大化,从而无视整个银行业的系统稳定性。雷曼兄弟的倒闭就是这个金融系统悲剧的极端表现。公众基金也不是银行失败的万能药方。对破产银行进行丰厚公共支援,将引导它们在正常的金融职能中为了利润追逐更高的风险,形成事前的道德风险激励。无条件的支助无疑会加重政府预算的成本。更为重要的是,它必须给予银行监管权威一种崭新的权能,使其能够逐步关闭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失败银行,从而彻底销毁破产银行的“系统性”底牌,否则,“大而不能倒”和“系统性风险”将成为银行破产制度永久的噩梦。
2007年的金融危机使得银行审慎监管的希望幻灭了,它既无法阻止商业银行的破产,也无力应付这些破产所联合产生的消极的外部效应。例如,存款保险以及隐而不显的政府保障实质上是商业银行风险喜好的刺激源,它们经常使银行落入自己构建的风险陷阱之中,然而,有趣的是,这样的刺激却来自审慎监管的举措。一个全新的银行破产理念不仅要包含审慎监管的措施,更多的应该是诉诸市场竞争法则,以降低商业银行风险喜好的刺激。事前减少存款保险、而事后将破产银行的负担尽可能地转移到并不享有保险资格的银行债权人身上,这种审慎监管与市场法则的结合正是我们商业银行破产规则所追求的目标。
通过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一个基本的逻辑框架展现在研究者面前,我们不能削足适履,简单地移植普通公司破产的相关制度,必须提请监管威权充分考虑商业银行的特性,以便能制定适合的破产规则。换而言之,既不能简单套用“原理式”破解方式[2],也不能无谓地放弃市场机制的理论。市场与监管分处权力的两极,我们需要谋划出一条路径,告诫市场“破产并不是目的,而仅是一种手段”,同时提醒监管权威“应该考虑更多的市场法则”。如此,研究必然从如下路径展开:(1)事前最优的规则;(2)监管力量及时地介入;(3)事后困境银行的解决方案;(4)国际性协作的需求及解决困境银行规则的统一性。
首先,事前的规则意味着规制银行独特规则的建立。这就需要特别注意银行困境日益增长的可能性以及事前具有激励效应的道德风险问题。解决之道最重要的在于引入“周期性资本比率”这样的经济概念,这就要求商业银行在经济景气时期增持资本,通过经济上升期减少风险资产在资产负债表中的比重,以降低经济下行时给银行带来困境的可能性,同时商业银行可以通过此种累积式的缓冲平稳地开展业务,从而顺利渡过困难期。
其次,“及时”,对于监管力量强制介入至关重要,这意味着要将银行破产的影响降至最低的诉求。“前破产”阶段的干预应该能够较为从容地应对萌芽中的金融脆弱性。强制性的“干预”通过要求银行增加新资本、限制一定的银行活动等方式来达到目的,因为这种干预是监管者发现特定问题之后的举措。为了保障这种“前破产的干预举措”的成功,就必须要赶在银行真实失败或已经长期处于流动性困境之前完成,这需要通过明晰的启动机制来达到此目标。
再次,事后规则强调在商业银行破产与普通公司破产的解决方法上的显著不同。普通公司破产着眼于破产企业的价值最大化,而商业银行破产还必须考虑到银行破产所带来的负外部性。因此,商业银行破产就必须考虑固定化的模式,包括出卖银行资产,可以全部也可以分开转让,或者转让给特定的实体作为新的继受者,也可以进行临时的公共式的控制。当然,资本的输入可能会成为最常见的事后解决途径。
最后,对于跨国银行的问题急需国际性的协议。国家风险、汇率风险、系统风险等基础概念已然进入了法律研究者的视野,并更大强化了法律与经济跨学科对相应商业银行破产问题研究的力度[3]。虽然这样的国家间合作是一个挑战而且仍需时日,但是,这样的国际性框架一旦建立不仅能够在应对商业银行破产方面提供统一的规则,而且对于减少分歧发挥巨大的作用。只有这样,世界各国才能放下国内保护及诸多主权因素,在银行破产问题上真实面对问题、适当解决问题。这种协力是平等的起点,无论商业银行地处何方,也不论其债权人遍及世界各地,他们都将在权利义务上实现真正的对等,损失的共享、监管的合作等等。全新的商业银行破产理念将孕育这种责任共担的公平精神,从而在破产相关程序中实现政策目标与利益的平衡[4]。
一个健全的商业银行破产法律制度,应该给监管者和银行管理者建立一个可以操作的机制,借此恢复中断的金融系统、减少破产的损失以及破产所带来的社会代价。这样的机制还意味着关注利益最大化目标之外的其他福祉,系统的康复、市场的完善以及降低道德风险。
[1]艾娃·胡普凯斯.比较视野中的银行破产法律制度[M].上海:中国法律出版社,2006.
[2]韦恩·莫里森.法律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1.
[3]张继红.银行破产法律制度研究[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9:209-211.
[4]丁文联.破产程序中的政策目标与利益平衡[M].上海:中国法律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