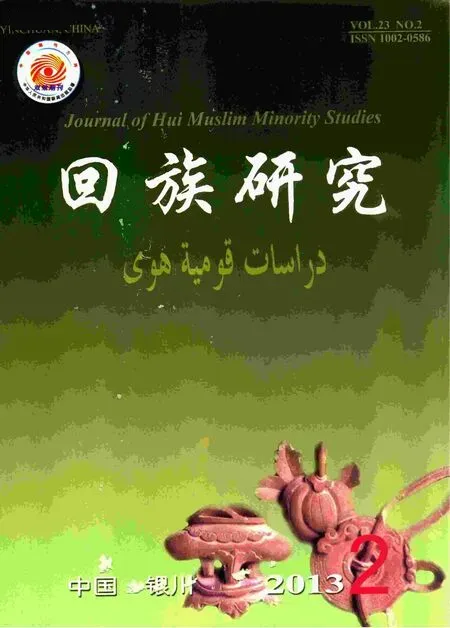试论伊斯兰经济系统的人文驱动力
周立人
(上海理工大学 管理学院,上海200093)
一
经济系统的人文驱动力主要体现在信仰(信念)、伦理规范以及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对自己经济行为的审度和驾驭诸方面。它体现的是一种内外一致性,即内在的信仰(信念)、伦理规范与外在的经济行为的辨证统一。
众所周知,信仰不仅是一个人的内在力量,也是一个民族和一个社会的内在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信仰的人是没有灵魂的人,没有信仰的民族是没有灵魂的民族,没有信仰的社会是没有灵魂的社会。正如泰戈尔在《一个艺术家的宗教观》中指出的,信仰体现的是有关人生意义的真理,“它的完美就是我们生命的完美。我们须得使这一生命的一切表现成为我们的诗篇;它一定能充分显示我们无限的灵魂,而不仅仅显示自身并无意义的所有物”[1](P717)。伦理规范则是调节人与人(包括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群体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人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公认的行为准则,但它的维系需要借助于信仰的支撑。只有在以信仰为牢固基础的伦理规范的约束下,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才能实现对自己经济行为的准确判断和控制,进而让群体和整个社会朝着理想的目标运行。因此,伊斯兰经济始终强调这样一种理念,即如果要让经济的发展能够真正给人类带来物质和精神上的进步,解决诸如公正、效率及社会福利等问题,单单靠一般意义上的道德情感和经济行为的结合是不够的,还要依赖由信仰所唤醒的道德上的自觉意识,因为这种道德上的自觉意识能够有效地主导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的经济行为,使之不至于背离伦理规范。
诚然,一般意义上的经济伦理学也认为,经济与伦理乃是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两大方面,前者主要解决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物质需求而进行的生产、消费、分配和交换等问题,后者则关注什么样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分配方式以及交换方式才算符合人类的道德需求这些精神层面的问题。然而,伊斯兰的经济伦理学则更强调信仰对于实现道德需求的意义,更强调经济主体的道德自觉性对经济系统的影响力。
这里所说的“道德自觉性”,当然离不开信仰者的情感世界。当代宗教心理学之所以将宗教信仰者丰富多彩的情感世界当做自己研究的重点,就是因为它真真切切地看到了信仰者内在的心理活动对现实生活的影响力,看到了他们的宗教激情事实上构成了宗教型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源泉之一。威廉·詹姆斯在《宗教经验之种种》一书中指出,信仰者的情感世界是宗教信仰中最具活力的元素,它表现在信仰者与“神圣的对象保持关系所发生的感情、行为和经验”[2](P30)。他认为:宗教观念只有借助于信仰者的丰富的情感世界才能形成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如果离开了信仰者的情感世界,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形态,就无法正常地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能。
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伊斯兰始终不渝地坚持伦理规范与经济活动相统一的原则,反对将两者割裂开来或者将两者对立起来。伊斯兰认为,借助信仰而得以维系的伦理规范永远不可能只局限于抽象的、形而上学的范畴,它应当对现实社会的各个层面实施积极有效的干预,尤其是要干预很容易使人朝着物质主义沉沦的经济活动。正如艾哈迈德指出的,伊斯兰经济的最主要特征之一,在于使人们的经济生活不仅具有鲜明的“目的性”(purposive),而且受制于“价值方面的引导作用“(value-oriented),这样便能推动整个穆斯林共同体的进步[3](P174)。穆斯林在各种经济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高尚的伦理意识,说到底即是一种在价值导向的作用下追求自我完美、自我尊严的人文意识。这种以信仰为基础的人文意识不仅能够有效地调控个人的经济行为,而且还可以强化社会的自我整合力和凝聚力。
鉴于上述的认识,伊斯兰宗教型社会积极引导穆斯林在从事生产、消费、分配和交换等经济活动时都自觉地遵循与经济运行各个环节相契合的伦理规范。
在生产方面,伊斯兰倡导人们通过自己诚实的劳动去创造物质财富。《古兰经》说,“我以白昼供谋生”(78∶11)。①“我确已使你们在大地上安居,并为你们在大地上设生活所需。”(7∶10)“当礼拜完毕的时候,你们当散布在地方上,寻求真主的恩惠,你们应当多多地记念真主,以便你们成功。”(62∶10)这里的“散布在地方上,寻求真主的恩惠”,即是指用自己诚实的劳动去创造物质财富。阿布德拉蒂在《伊斯兰精义》中说:对穆斯林来讲,“通过正当的劳动来谋取生计不仅是一项义务,而且也是一种值得赞美的德行。有些人明明有能力参加劳动,但却游手好闲,依赖他人生活,这类人在伊斯兰教看来是有罪的”[4](P126)。先知穆罕默德曾指出:“一个人手拿绳索,然后负薪去卖,胜于去向一个富人乞讨——无论得到东西或被拒绝。”“最合法的食物便是自食其力。”“谁为自己打开了一扇乞讨之门,安拉就为谁打开七十扇贫穷之门。”[5](P252)就组织化、规模化的劳动——生产而言,伊斯兰认为,生产只是一种手段,它必须服务于伊斯兰的崇高目标。正如阿布德拉蒂指出的:“伊斯兰的经济体制不是单单用生产数字与生产能力来描绘的。它同时还需要在道德上与原则上用一种包容性的价值体系来加以理解。”[4](P127)用现代人的话说,就是不能光用GDP 来衡量一个社会的进步。
在消费方面,伊斯兰主张坚守既不吝啬也不浪费的中正之道,因为吝啬会降低合理的消费水平,削弱对生产和供给的刺激,使社会经济停滞不前,而浪费不仅会导致生活无所节制等道德问题,而且还会导致自然资源的闲置,使其得不到应有的开发和利用。《古兰经》说:“真主已准许你们享受的佳美食物,你们不要把它当作禁物,你们不要过分。真主的确不喜爱过分的人。”(5∶87)“挥霍者确是恶魔的朋友,恶魔原是辜负主恩的。”(17∶27)“他们用钱的时候,既不挥霍,又不吝啬,谨守中道。”(25∶67)这里所说的“中道”,不仅仅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意义,更具有伦理学本体论上的意义。为了处罚浪费行为,伊斯兰经济法规定:凡将土地荒置三年之久,该土地即不复占有者所有;如果他既不耕种又不建屋或作其他用途,这块土地三年后就应作“空地”处理;如有他人使用该土地,不可诉之于法,政府也无权将该土地交还给原先的所有者。此外,伊斯兰还将那些有碍于人们身心健康的消费品(如烈酒、毒品、自死物、奢侈品、淫秽品等)归入禁忌之列。
在分配方面,伊斯兰强调劳动者应当充分享有其劳动成果,反对剥削和对他人财产的非法占有。《古兰经》说:“你们不要借诈术而侵蚀别人的财产,惟借双方同意的交易而获得的除外。”(4∶29)在有组织的生产机构,雇主与雇员是平等的,他们在共同承担风险的同时也分享着生产带来的成果。而对于整个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伊斯兰主张通过天课、施舍和遗产分配等手段来调节贫富之间的差别。根据伊斯兰教义,有五种东西必须交纳天课:即金银、贸易品、农产品、牲畜和矿产品。天课的收入主要用于救济“贫穷者、赤贫者、管理赈务者、心被团结者、无力赎身者、不能还债者、为主道工作者、途中穷困者”(9∶60)。伊斯兰经济学家卡哈夫指出:“天课制度被认为是伊斯兰社会经济结构的组成部分之一。天课是依据伊斯兰教律来征收和分配的。天课基金会(Zakat Fund)隶属于政府机构下的一个部门”[6](P26)。关于施舍,《古兰经》说:“你们当分舍你们的财产。”(2∶254)“如果你们公开地施舍,这是很好的;如果你们秘密地施济贫民,这对于你们是更好的。”(2∶271)这里所说的“秘密地施舍”,是指摆脱了任何功利主义动机的德行。正如康德所说的:“德行之所以有那样大的价值,只是因为它招徕那么大的牺牲,不是因为它带来任何利益”[7](P47—48)。关于遗产分配,《古兰经》说:“男子得享受父母和至亲所遗财产的一部分,女子也得享受父母和至亲所遗财产的一部分,无论他们所遗财产多寡,各人应得法定的部分。析产的时候,如有亲戚、孤儿、贫民在场,你们当以一部分遗产周济他们,并对他们说温和的言语。”(4∶7—8)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伊斯兰不仅充分肯定妇女和儿童继承遗产的权利,而且还主张用遗产来济贫。
在交换方面,伊斯兰强调买卖公平,反对欺诈行为。《古兰经》说:“伤哉!称量不公的人们。当他们从别人称量进来的时候,他们称量得很充足;当他们量给别人或称给别人的时候,他们不称足不量足。”(83∶1—3)“你们应当秉公地谨守衡度,你们不要使所称之物分量不足。”(55∶9)除此之外,伊斯兰教法规定:出售物品时,明知物品有缺陷而故意隐瞒,那么成交属非法;与卖主共谋,引诱买者上钩的行为也属非法。还有为了确保买卖双方的利益,伊斯兰提倡商品必须在进入市场之后才能进行交易,这样做能防止买卖双方都可能因还没有获悉市场行情而蒙受不必要的损失[8](P260)。至于在金融交易方面的高利贷等盘剥行为,伊斯兰对之是深恶痛绝,严厉禁止:“吃重利的人,要像中了魔的人一样,疯疯癫癫地站起来。这是因为他们说:‘买卖恰像重利。’真主准许买卖,而禁止重利。”(2∶275)卡哈夫指出:在伊斯兰经济体内部是绝对禁止利息的,“这就是说借贷的利率永远是个零数,不管是消费者的信贷还是生产者的信贷”[6](P26)。这主要是为了防止某些人凭借贷而不劳而获。另外,伊斯兰还反对市场垄断、囤积居奇、投机赌博、买卖假冒伪劣商品、出售难以确定交货的商品等,最大限度地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总之,伊斯兰认为,伦理法则不仅高于经济法则,为经济系统的运行起导航的作用,而且应当成为经济活动主体自觉遵守的契约。由于伦理规范有了宗教信仰体系的支撑,因而伊斯兰伦理规范有别于世俗的伦理规范具有神圣性的特点。它能将宗教信仰和务实精神完美地统一起来。
二
诚然,中国的儒家也提倡伦理精神和务实精神。例如,孔子主张人们应该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论语·宪问》)的积极态度投身于改造大自然的活动,并且批评那些弃世绝尘的人“清洁其身,而乱大伦。”(《论语·宪问》)然而,他的“先富后教”(《论语·子路》)思想却将经济发展置于伦理道德规范之前。孟子、管仲和韩愈都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例如,孟子说:“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意思是:开明的国君让老百姓从事生产活动,这样就一定能使他们上足以赡养父母,下足以抚养妻子儿女;遇到了好年成则丰衣足食,遇到了坏年成也不至于饿死;在此之后再促使他们讲究善心和德行,这样他们也就很容易服从他的统治了。管仲也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管子·治国》)意思是:治理好国家的前提是让百姓过上富裕的生活,百姓富裕了就容易统治和管理了。韩愈说:“人之仰而生者谷帛,谷帛丰,无饥寒之患,然后可以行之于仁义之途,措之于平安之地,此愚智所同识也。”(《进士策问》)意思是:五谷和丝帛是百姓赖以生存的物质保障,这些东西富足了,自然也就没有饥寒的忧患,然后便可以使他们走上仁义的道路,将他们安置在平和安定的环境里;关于这一点,愚者和智者的看法是相同的。
显然,这种将经济发展置于伦理规范之前的做法,其本身就违背了伦理精神(且不谈它在伦理的目标导向上强调“民之从之”)。它不但会让伦理规范处在一种期待和缺位的状态,从而导致对经济行为道德失范的默认,而且还会在“民富”的理想达到后,削弱伦理规范对经济活动应有的调控力度。更何况,事实上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物丰则欲省”,而是随着温饱等问题的解决又会生发出许多新的需求和新的社会问题。这些新需求和新问题非但不能使伦理规范的推行变得容易,反而向伦理规范提出了新的挑战,加大了伦理规范对社会调控的难度。
在孔子看来,西周领主制封建宗法社会是人类最合理的社会。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他认为,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从事生产劳动并且创造物质财富的应该是被统治阶级,而占有和享用物质财富的应该是统治阶级。也就是后来孟子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这不仅贬低了生产劳动行为本身和从事生产的广大黎民百姓,同时也进一步确定并强化了当时上尊下卑的宗法制度。孔子年少时曾因家境贫寒而不得不参加一些体力劳动,对此他十分感慨地对子贡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他对生产劳动的轻蔑态度溢于言表。正如匡亚明在《论孔子的经济思想》中指出的,“这种把促进社会发展的崇高的创造物质财富的生产劳动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生产技术连同劳动人民一道加以轻视和贬低的思想,是阶级社会少数人剥削和掠夺多数人劳动成果的极不公平的怪现象所产生的怪思想。正是这一怪思想影响了往后长达二千余年的中国社会”[9](P57—62)。
中国传统伦理的世俗性质决定了它很难将主客体完美无缺地统一起来,很难将经世致用性与超功利的真理性结合起来。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在中国,“道德的时代性和历史继承性”诸特点决定了伦理规范“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会阻碍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10](P89—95)“道德至上的形式化等特点使人们的道德行为具有不得不为之的他律性,而不具有‘我自己想做’的主体性。统治者本想全力促成普遍的道德至上心态,迫使社会成员在巨大的道德舆论压力下俯首帖耳,结果却压出了人们对道德的玩世不恭……这也许就是国人长期在精神生活中缺乏‘为精神而精神、为道德而道德’的纯粹精神的原因吧;没有个人利益支撑的精神信念很难在中国传统人中树立起来”[11](P13—17)。
在经济意识与伦理意识的关系上,伊斯兰始终认为,伦理意识应当以一种超越于个人利益之上的姿态控制经济意识。因为作为经济意识之内核的实际上是市场意识,它总是要受到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等一般经济规律的制约,总是要体现“利益最大化”的规则。因此,由私欲带来的谋利的冲动往往会使市场表现出自发性和盲目性的特点。作为伦理意识之内核的是价值意识,它体现的是信仰、信念、公正、正义等,是遏止私欲和市场恶性竞争的有效手段。当然,伊斯兰在强调伦理意识的时候,并不反对一般意义上的经济活动。在伊斯兰看来,作为谋生和获得财富之手段的经济活动是人类的基本活动。阿布德拉蒂在《伊斯兰精义》中说:“真主鼓励每个穆斯林自食其力,不要养成对他人的依赖性。伊斯兰尊重所有为了谋生而从事的工作,只要这些工作是正当的。”[4](P126)先知穆罕默德有句名言:“为今世而工作,好像你永远会活下去;为后世而工作,好像你明天就会死去。”[12](P86)他还说:“靠自己劳动挣来的食物最好。真主的使者达伍德就是靠自己的劳动而生活的。”[13](P63)但经济活动只解决了一个谋生和获得财富的问题,而没有解决人之所以成为人的价值问题。后者的解决需要伦理法则的干预。恰如希迪奇指出的,伊斯兰经济伦理学的任务之一是研究如何让人们的“精神需求”(spiritual needs)和“物质需求”(material needs)同时达到满足[14](P202)。他所说的“精神需求”,即是“后世的报酬”(人之所以成为人的价值所在)。正如《古兰经概述》指出的:“财富只是人生的点缀,并不是人生的目的,只有后世的报酬才是更美好的,更值得追求的。”[15](P102)换句话说,发展经济主要是为了解决人们的生存问题而并不构成人的全部目的或最高目的,同满足生活需求相比,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则是更为重要的。如果把发展经济当作人的全部目的或最高目的,甚至认为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所有问题都能够通过经济系统的“过滤”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其结果必然是人的主体价值的丧失。
伊斯兰还主张借助利他主义的伦理意识来克服经济活动中的一己之私,从而净化人们的灵魂与财产。《古兰经》说:“迷惑世人的,是令人爱好的事物,如妻子、儿女、金银、宝藏、骏马、牲畜、禾稼等。这些是今世生活的享受;而真主那里,却有优美的归宿。”(3∶14)这里提到的“优美的归宿”,即是指通过利他主义来克服人的私欲,进而净化自己的心灵,取悦于真主。《古兰经》说:“你要从他们的财产中征收赈款,你借赈款使他们干净,并使他们纯洁。”(9∶103)“施舍财产,以求真主的喜悦并确定自身信仰的人,譬如高原上的园圃,它得大雨,便加倍结实。如果不得大雨,小雨也足以滋润。”(2∶265)先知穆罕默德说:“谁若施舍正当职业所挣来的财物,即使是一粒蜜枣(真主只接受用正当手段挣来之物),真主定会以右手接它。然后就像你们精心喂养自己马驹一样地培育它。对施舍者来说,其回赐就会像大山一样。”[13](P55—56)这就是说,伊斯兰主张在穆斯林的经济活动中必须牢固地确立起利他主义的伦理意识,即为了他人和社会集体的利益可以牺牲个人的利益,为了整个社会的长远利益可以牺牲个人的眼前利益。这种利他主义精神,由于被赋予了宗教情怀,因而更能衍射出价值的力量和人性的活力。利他主义者在作出牺牲的时候获得的是超越个人利益之上的道德价值,而且由于他的牺牲,社会发展更加有序化、合理化,社会发展的人文环境也得以提升和张扬。由此带来的社会效益最终还是能够让利他主义者得到分享。
三
从历史上看,一些发达国家在经历了经济上的高速扩张之后,深藏在经济表层底下的各种矛盾逐渐显现,有的甚至积重难返,从而造成经济持续发展的后劲不足。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缺乏一种像伊斯兰一样的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利他主义精神。
西方经济学通常将从事经济活动的人视为见钱眼开、唯利是图的“经济动物”,从而剥夺了人的尊严;其次,由于利己主义的动机被确认为最基本、最原始的动机,因此调动、激发和满足这一动机便具备了一定的合法性,成了催生经济发展的唯一激发机制。其结果无疑会带来人的异化问题,即人丧失了主体的地位,沦为被物欲所摆布、所控制的对象。
西方经济学的“自利”原则,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近代伦理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西方近代伦理学家对人类自私的本性大都采取肯定的态度,有的甚至把它视作等同于道德的天经地义的东西。例如,霍布斯等人将人的各种欲望的满足看成是一种“善”,爱尔维修把利己主义当作人类行为的最高出发点,曼得威尔尽管看到了人类自私的本性必然产生竞争意识并由此带来一些负面的效应,但他断言:“人生来就是自私的、难以驾驭的动物。”“世界上被称为劣行的东西,才是我们成为社会造物主的伟大原则,才是无所不包的各种贸易和职业的牢固基础。”[16](P209)这些论断为后来西方主流经济学“经济人”假说提供了人性论方面的一大依据。向来提倡道德主义之精神的康德也认为,具有“社会化”需求的人同时也具有“独立化”的倾向,当这种倾向碰到来自外部的约束力时,便激发了“自然本性”的潜力,“因此,让我们感谢大自然之有这种不合群性,有这种竞相猜忌的虚荣心,有这种贪得无厌的占有欲吧!没有这些东西,人道之中的全部优越的自然本性就会永远沉睡而得不到发展”[17](P8)。穆勒的功用主义(即功利主义)伦理学虽然将“道德情感”和理性主义植入他对人性的定义中,但他继承了经验论哲学的传统,首先,把以“趋乐避苦”为原则的经济动机界定为“善”;其次,把公共利益(即所谓“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看成是依附于个人利益的“合成体”,把满足个人利益的经济效率看成是一种体现公道的“正义”。正如赵修义指出的,“功用主义过分地强调经济动机的作用,有一种把道德问题缩小成经济问题的倾向,即把快乐或愉悦作为一切行为的目标,于是伦理学被缩小成了‘最大快乐之目的对资源所进行的最佳的分配’。其结果是‘伦理学被经济学所取代’”[18](P58—64)。
阿马蒂亚·森似乎察觉到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中伦理规范的缺失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他在《经济行为与道德情感》一文中指出:早在古希腊时代,提倡“集体先于个人”原则的亚里士多德在《尼可马克伦理学》和《政治学》中对经济与伦理的关系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注,而且后来的经济学家都对这一命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但随着经济学的不断发展,伦理对经济学的指导意义渐渐被人们所淡化、所忽略;而以“实证经济学”为主导的现代经济学,其“性质已经受到经济与伦理学之间所产生的疏远的极大损害”[19](P66—70)。他还指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势必排斥伦理规范在实际经济决策中的作用。他批评乔治·斯蒂格勒等人把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定义为“自身利益的经济人”,把“自利”原则看得高于伦理价值。他说:“的确,如果自利在我们的选择中根本就没有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正常的经济交易就会崩溃。但真正的问题是,究竟是否存在一种以上的动机,或曰究竟自利是否是驱策人类的唯一动机……如果人们以一种全然自利的方式行事,那么他们会实现某种规定的成功标准(如某种效率)吗?”[19](P66—70)
把“自利”原则看得高于伦理价值,势必引发一系列的问题。首先,人很容易由主体蜕变为对象,由目的沦落为工具,人对经济活动的驾驭以及价值观对经济活动的导航作用会让位于经济规律的“霸权”统治。换句话说,人们会让经济必然性来控制自己的自主性,会将经济利益的满足误认为主体价值的最终兑现。其次,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物质生活的不断改善,人的欲望也由此恶性膨胀,不少人会将原来不属于自己的奢侈消费(包括违背伦理道德的有害消费)当做“合理消费”来加以肯定并且刻意追求,从而造成人性的堕落;即自利的无限性与经济发展的无限性会相互刺激,使整个社会成为一个由物欲主宰的世界。再者,“自利”原则会导致经济的盲目扩张,进而造成生态和环境的破坏。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论及当代西方经济社会时说:“人类的力量影响到环境,已经达到了会导致人类自我灭亡的程度……要对付力量所带来的邪恶结果,需要的不是智力行为,而是伦理行为。”[20](P38)
面对诸多经济系统内部和外部的问题,现代西方自由主义学派极力否定包括宗教在内的道德权威的力量,而强调所谓“秩序”的自发性作用。例如,哈耶克说,市场经济无论是从它的起源和运行还是从它的性质和价值来看,始终是一种“自发秩序”和由这种“自发秩序”形成的“制度”。“竞争市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优点在于,在这样的市场上,每个人仅需意识到影响他个人的事情,而从个人行为中产生出来的‘制度’是未经设计而产生的社会制度的典范”[21](101)。他在主张个人自由竞争的同时,甚至反对社会平等和分配正义,因为在他看来,不平等是社会进步的必要前提和根本动力,分配正义必然妨碍自由的实现。显然,哈耶克的观点是源于亚当·斯密等人的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亚当·斯密曾经说过,当每个人以“自利”的方式自由地追求自身利益时,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借助法律化解经济人与经济人之间以及经济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冲突,从而形成一种能使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都得到实现的“自然秩序”。也就是说,主观追求自身利益的经济人会在客观上有利于他人和社会,因此,社会应当鼓励人们尽可能地去追求自身利益的满足,以此来实现整个国家的富裕。
由此可见,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也罢,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学也罢,都忽略了经济发展所必须承载的道德价值,而将市场和法律当做社会“秩序”的主要来源和支柱。其实,市场也好,法律也好,就其本质而言,是属于一种外部的力量,仅仅依赖它们是远远不够的。正如库特卜指出的,人类社会的进步“单单靠经济规则的订立是不够的,还要有一套道德的规范与精神的价值”[22](77)。
伊斯兰经济作为一种有价值负荷的经济,其哲学前提是工具价值和目的价值的统一,是将经济活动的主体看作信仰与务实的统一体。伊斯兰认为,尽管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甚至偶尔也会形成一定的秩序),但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不能只从经济运行机制(包括市场机制)的内部去寻找,因为人作为驾驭经济活动的主体,其人文精神对于经济活动的目的具有价值上的导向作用。因此,在伊斯兰看来,经济活动的规律性(自在性)和驾驭经济活动的人的主体性(自觉性)应该构成经济系统健康运行的双重性。况且,在穆斯林的经济生活中,集体主义、利他主义始终是高亢的主旋律。伊斯兰社会始终倡导把以宗教信仰为依托的人文精神同自然经济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人们的经济行为不仅具有物质上的动力源泉,同时也具有精神上的动力源泉。伊斯兰有关经济行为的伦理规范是宗教信仰和现实生活相结合的典范,它赋予伊斯兰经济巨大的生命力。这种以宗教伦理为人文动力的经济文化能够促使人们在从事各种经济活动时自觉地摆脱“自利”原则的束缚,从而推动个人与社会的共同进步。
简而言之,在伊斯兰经济发展模式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经济系统作为社会发展大系统里的一个子系统,始终接受着宗教伦理观念的导航、监督和调控,从而形成了一个经济活动和宗教伦理相契合的二元结构。宗教信仰、宗教伦理和宗教情感等事实上构成了伊斯兰经济系统的内驱力,它们能有效地作用于经济系统而不被经济系统所分化、所侵蚀。伊斯兰认为,只有坚守以正信为基础的伦理规范,伊斯兰经济才能得到健康、有序的发展,才能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协调,才能更好地体现人的价值和尊严。
注释:
①以下经文均引自马坚译《古兰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1]梁适.中外名言分类大辞典[K].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
[2][美]威廉·詹姆斯.宗教经验之种种[M].唐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47.
[3]Ahmad K.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n Islamic Framework[M].Khurshid Ahmad(ed)Studies in Islamic Economics.The Islamic Foundation,Leicester,U.K.,1980.
[4]Abdulati H.Islam in Focus[M].International Islamic Federation of Student Organizations,kuwait,1990.
[5][阿拉伯]安萨里·圣学复苏精义[M].马玉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6]Kahf M.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Consumer Behaviour in an Islamic Society[M].Khurshid Ahmad(ed)Studies in Islamic Economics.The Islamic Foundation,Leicester,U.K.,1980.
[7][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8]Qaradawi Y.The Lawful and the Prohibited in Islam[M].The Holy Koran Publishing House,Beirut,Lebanon,1984.
[9]匡亚明.论孔子的经济思想[J].江海学刊,1990(1).
[10]刘光明.经济活动伦理研究[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1).
[11]肖群忠.论“道德功利主义”:中国主导性传统伦理的内在运行机制[J].哲学研究,1998(1).
[12]Hathout H.Reading the Muslin Mind[M].New York:American Trust Publications,1995.
[13][埃及]穆斯塔发·本·穆罕默德艾玛热.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M].宝文安,买买提·赛来,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14]Siddiqi M N.Muslim Economic Thinking:A Survey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s[M].Khurshid Ahmad(ed)Studies in Islamic Economics.The Islamic Foundation,Leicester,U.K.,1980.
[15]宁夏回族自治区伊斯兰教协会.古兰经概述[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
[16]晏智杰.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17][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18]赵修义.经济伦理的研究对象和主要课题[J].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1).
[19][美]阿马蒂亚·森.经济行为与道德情感[J].聂元昆,译.经济学动态,1996(8).
[20]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M].北京: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1985.
[21][英]J.R.沙克尔顿,G.洛克斯利.当代十二位经济学家[M].陶海粟,潘幕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2]Qutb M.Islam:the Misunderstood Religion[M].Al-Faisal Printing Co.,kuwait,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