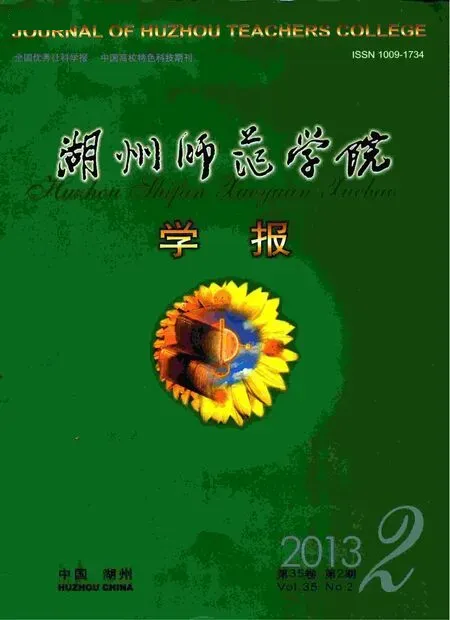论沈从文种族与女性性别叙述中的“生活”与“生命”*——以《月下小景》和《主妇》为个案
罗克凌
(赣南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西 赣州341000)
关于沈从文“生活”与“生命”的主题研究,沈从文研究专家凌宇在其《沈从文的生命观与西方现代心理学》中有十分详透的阐释,凌宇认为:“下意识心理描写是沈从文创作中常见的节目。弗洛伊德心理学对沈从文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然而,在以生命观为核心的人生观及其创作的主体走向上,沈从文没有走向弗洛伊德主义。他对生活与生命的诠释以及对乡村各种生命形式的探寻与发现,显示出他对人生的心理学观察角度,并与20世纪50年代兴起于西方的心理学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取同一立场”[1](P30),“生活”和“生命”在沈从文的话语系统中有特定内涵,与“生活”是“人类的全部活动”而“生命”是“人作为生物存在的所有特征”[1](P33)的一般理解不同,沈从文的“生活”是非神性的存活,而“生命”却是具有神性色彩的对人类远景的凝眸。本文拟以小说《月下小景》和《主妇》为例,从沈从文在现实生存境地中遭遇的心理纠结出发,去同态观照其小说中种族与女性性别叙述中“生活”与“生命”的命运纠葛,从而更好地去理解沈从文复杂的创作情怀。
一、沈从文“生活”与“生命”的现实变奏
沈从文生于僻远自足的湘西世界,可谓“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澜”。当“五四”狂飙的余波尾焰点触这座边城蛮地时,沈从文还是一个土兵,过着近乎“人类童年期”的原始心态生活。看杀头,也不格外觳觫地惊惧,甚至伴着一种耍戏样孩童的天真,猛踢“尸头”三五脚,从中寻求一种并非“生活”残酷印象的乐趣,直至凭着乡下人固拗的精神勇气走入北京,“开始进到一个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永远学不尽的人生”时,他才知性地发现以往生活贫简、荒陋的全部血腥之处,也才懵懂地开始做起一个要求“生命”精粹圆全的梦来。初到北京的他,以一种“生命”尊严的顽强气性,要度“生活”四面楚歌的“寒冬”。一个连新式标点都不知晓的“愣小子”,一个想上大学却在应考中对国学“一问三不知”的“傻小子”,一个住在储煤间(沈从文自嘲“窄而霉斋”)、冬天以单棉衣作被的“穷小子”,要开始阅读、“熟习”社会这本大书了,要“把自己跌进一个陌生世界里去明白一切”[2](P6),并且雄纠纠、气昂昂向往以一种朴素单纯的“生命”态度来成就一个呆头呆脑“乡下人”“专业作家”的伟梦了,揆诸其本真的心志:为的却是年青人明天庄严、合理的“生活”。“我既然预备从事写作,就抓住手中的笔,不问个人成败得失,来作下去吧”[3](P2)。最促迫棘手的事当然是“应付生活”,虽然本可以向居住在北京的表亲和远亲请以援手,但“乡下人”内在“生命”蛮勇的顽韧气分拒绝了这种“嗟来之食”不体面的诱惑,就算有一顿没一顿,就算赶场朋友熟人中作不速的食客,也在“生活教育”中自得其乐,赢得了最本在“生命”圆实吁求的怿悦。
在自学苦读的磨砺中沈从文有了第一篇稚拙“习题”的“尖兵”问世,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对于创作“生活”,“乡下人”宁愿在章法外失败,也不愿在章法内成功,这种逼心不挠的理念正是其对艺术“生命”天然崇奉的守执。经过为教学而粗率“标新立异”一大堆东西的小说“习题试验”,沈从文从最亲魂的本土沅水流域获得了艺术极致的灵心妙感,《边城》便是以“生命”生花之笔素绘湘西自然人情“生活”式样最美丽、最成功的崭获。命运女神的眷顾并没有戛然休止,当教授了,成作家了,名誉如日中天,爱情也喜获丰收,“生活”对沈从文迟到的爱激发了他文学“生命”最粹美的潜能,《湘行散记》在向“黑俏”新妇灵魂甜语的真与梦的编织中散发出一种对一草一木具像“生活”无比温情、温暖的感动,这就是“美丽得令人忧愁”的“生活”与“生命”水乳交融的诗。经逢革命与抗战社会生活大背景的转捩,思想有些“顽固保守”的沈从文“似乎当真变成了一个自办补习学校中永远不毕业的留级生”[3](P4),他看到了真实的凄惨、悲壮的死亡与牺牲,却永远不明白记住了“时代”却忘了“艺术”的“差不多”、“平均数”的文学作品与这种时代“生活”精神的伟烈到底是否完全一体化“生命”天然的和谐,虽然在《湘西》中也在为“生命”圆美的梦作着堂吉诃德式的道德努力,虽然在《长河》中也在为“生命”圆美的梦作着对“新生活运动”无情嘲弄的抨击,然而一旦政治“红色”闪电把他并不宽容地拘勒暴挞,他的“生活”即刻病瘁,他的“生命”也跟着委顿,一个寄注“野”与“梦”的诗意传奇溘然徂逝,只有等到埋醉于《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精神春天代偿气候时,沈从文的“生活”庶几重获灵动,因了永不灭熄、“跛者不忘履”的内在诗情,沈从文曲线救“心”,将“生命”沧桑擎起,“可以说,他的前半生的文学创作和后半生的文物研究,都是源于他的艺术个性,源于他的经历,实属同一个艺术家生命流程中的两条支流。他用自己的生命,或用文字去创建一个艺术世界,或去研究那颜色、丝线、青铜、泥土、木石所组成的物质文化世界、物质艺术世界”[4](P188),虽然大概只不过是灵魂上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
几乎像所有艺术家一样,沈从文过着一种内在的双重生活,“所谓艺术家的双重生活,就是指他们过的一种双重身份、两种人物的生活。他们生活于现实世界,又生存于自己构想的艺术世界”。[4](P11-12)“现实”是“生活”的,而“艺术”是“生命”的,沈从文穷力于“用人心人事作曲”,矻矻孜孜为“生活”、“生命”疲癃鏖战,仿佛永远在灵魄上“训练自己达到将来更完全”。当我们忆起沈老晚年对自己一生怀忆返顾的话语:“我生命中虽还充满了一种童心幻念,在某些方面,还近于婴儿情绪状态,事实上人却快八十岁了。近三十年我的写作生命,等于一张白纸,什么也没留下。事实上却并不白白过去”[3](P6),我们总会为这个创作了如许“孤独的纪念碑式”作品的善良老人“相当长,相当寂寞,相当苦辛”、在“生活”与“生命”之间离奇故事一般坚卓营求的一世唏嘘不已。
二、种族中“人”的“生活”与“生命”
由于有两种少数民族的血液在沈从文身上流淌(沈从文的亲祖母为苗族,其母亲为土家族,他身上混合着汉族和少数民族的血液),沈从文对于势卑位弱的少数民族种族(主要指苗族)之文学呈现便有了格外复杂的历史生命记忆、文化心理意识悲悯的倾心。朱光潜分析其《边城》时说到它“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忧隐痛”[5](P27),《月下小景》就是这种表现的鲜明一例。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道德文化博弈在沈从文的创作中同时也便有了精神指向上“是丹非素”的情感用武场。从某种正确的立场而言,“沈从文家乡的边区居民和部族人民能够引来典型的青春和活力,引来超越西方文化和中国旧知识阶级的僭越的文明力量”[6](P5),这在其小说《媚金、豹子与那羊》中体现得尤为分明:
地方的习惯是消灭了,民族的热情下降了,女人也慢慢的像汉族女人,把爱情移到金银虚名虚事上来了,爱情的地位显然已经堕落,美的歌声与美的身体同样被其他物质战胜成为无用的东西。[3](P58)
作者将“女人也慢慢的像汉族女人”作为褒贬意指近乎奚落式的诅咒,将少数种族纯真、圣洁的自足德性崇尚为至高无上精神图腾般的“社会集体想象物”来抵制汉文明任何方际自尊上的污渎。这种种族群上的二元对立态度自然也涵盖于作者另一对重要的精神范畴之中:“生活”与“生命”。从某种意义而言,在沈从文的文学世界里,汉族便是追尚“生活”的代表,而少数种族却是追求“生命”的典范,“生活”里尽是卑猥的物欲利害计算,而“生命”却可以铸造高贵的多方品格。有了这种人性文化的两相参照,作者的冰炭爱憎情怀便如白雪一样了然。诚如我们所知,湘西是一座“历史”从来“不动心”问津的“边城”,而“边城”里的少数民族聚落更是不开化“边城”的“边地”,就像《月下小景》中所描述:“傍了××省边境由南而北的横断山脉长岭脚下,有一些为人类所疏忽、历史所遗忘的残余种族聚集的山寨。他们用另一种言语,用另一种习惯,用另一种梦,生活到这个世界一隅,已经有了许多年”[3](P396)。虽然文化原始落后,然而这个残余的种族却有一个本族“英雄人”追赶日月的传说,英雄为了本族人未来的辽长幸福突然有一个伟大的愿心冲动——意欲征服主管日月运行的神,“勒迫它们在有爱情和幸福的人方面,把日子去得慢一点,在失去了爱,心子为忧愁失望所啮蚀的人方面,把日子又无能为力得快一点”,最后“人虽追上了日头,却被日头的热所烤炙,在西方大泽中就渴死了”,在这种近乎悲壮的神话义举中兆示了这个少数种族一种雄强伟岸的生命力梦想。有了“英雄”的神上祖先,便自然会有“英雄”的人间后代,在“无盗贼,也缺少这个名词”的本地土人中就有这么一对“人性与自然契合”的痴情美丽好儿女——寨主独生子傩佑和他的少女恋人。在温柔清莹的一派月光底下两情人喁喁蜜语,正享受着“生命”纯然绽放的幸福与感动。这种爱情“生命”的绽放是通过“走马路”恋媒的唱歌完成的,就像作者在其另一小说《龙朱》中所诠释的那样:
一个男子不能唱歌他是种羞辱;一个女子不能唱歌她不会得到好丈夫。抓出自己的心,放在自己爱人的面前,方法不是钱,不是貌,不是门阀也不是假装的一切,只有真实热情的歌。……一个多情的鸟绝不是哑鸟。[3](P45)
这与汉族人的实用理性势利情欲迥乎不同,女孩唱道“身体要用极强健的臂膀搂抱,灵魂要有极温柔的歌声搂抱”,“他们的口除了亲嘴就是唱赞美情欲与自然的歌,不像其余的中国人还要拿来说谎”[3](P75),这便是××族最“健康放荡”、波希米亚式的爱情宣言。然而少数种族也有少数种族原始落后的戕残人性“生命”的习俗,即按照“××族人的习气,女人同第一个男子恋爱,却只许同第二个男子结婚”,“第一个男子因此可以得到女人的贞洁,就不能够永远得到她的爱情”,××族人以一种宗教般“信托”的虔诚、虔敬、恪守着这个“野蛮”的规矩,却似乎并无情绪上的任何违心挣扎。他们对以汉族为标志的现代文明有一种强烈本能的敌视疏离感,仿佛文明的入侵就意味着他们“生命”的毁灭,所以“他们愿意自己自由平等的生活下来,宁可使主宰的为无识无知的神,也不要官。因为神永远是公正的,官总不大可靠”[3](P72)。他们愚忠地驯从于他们自己的“神”——一个未被现代文明扭曲的充满“生命”自由活力的原始神,即使要付出“生活”上吓人的代价也毫不恤惜,于是爱情悲剧便无可避免地悄然而至。小说中写道,“两人的年龄都还只适宜于生活在夏娃亚当所住的乐园里,不应当到这‘必需思索明天’的世界中安顿”,夏娃亚当的乐园是个全息“生命”的世界,而当这个世界“必需思索明天”时,便俨然转化为一个“生活”的世界,“但两人业已到了向所生长的一个地方、一个种族的习惯负责时节了”,表明这个来自“集体无意识”中的种族“魔鬼”规约对每一个忠实于“生活”的适时种族男女都铁律地适用,而每一个××族的儿女也同样无所怨悔地接受着,这是他们的文化基因、文化胎记、文化烙印,也是他们的文化“生命”,一旦悖离便会失却其叶根相属的种族文化身分认同。即便如此,××族人同样无法拒绝“人”非种族层面上的个体主我“生命”意识悸动的萌孽,女孩子说“这世界只许结婚不许恋爱”,“应当还有一个世界让我们去生存,我们远远的走,向日头出处远远的走”,男孩子说“有了你我什么也不要了。你是一切:是光,是热,是泉水,是果子,是宇宙的万有”,这便是一种企图撇离、否弃形式“生活”(结婚)的纯“生命”(恋爱)询唤,可是这个世界容不得两颗无辜“原罪”受毁的心。向哪走成了一个问题,“非汉少数种族”似乎总有一种吉普赛人“非家幻觉”的“文化离散”心灵流浪感,“南方有汉人的大国,汉人见了他们就当生番杀戮,他不敢向南方走”,表明了汉族凌戮逼压少数种族这种“记忆伤害”一直盘桓在作者的灵魂内久久不散。西有虎豹,北亦同族,剩下的一条便是他们的“英雄”祖先走的东方惨烈“蹈死”之路。“××人有一首历史极久的歌,那首歌把求生的人所不可少的欲望、真的生存意义却结束在死亡里,都以为若贪婪这‘生’,只有‘死’才能得到。战胜命运只有死亡,克服一切惟死亡可以办到”,“又野蛮、又妩媚”的死亡便是××族人爱情“生活”与“生命”的“合题”,冲突在此消弭,畸衡得以圆融,于是一场爱情“生活”与“生命”的生死较量便在男女双双服毒赴死的悲剧性收场中拉下了帷幕,他们“把一个诗人呕心沥血写不成的一段诗景,表演来却恰恰合式,使人惊讶”[7](P91),诚如作者结尾所暗示“月儿隐在云里去了”,“爱能使人喑哑——一种语言歌呼之死亡”[2](P295),爱与死果真艺术毗邻,“爱”之月隐在“死”之云里去了,信哉斯言!
三、女性性别中“人”的“生活”与“生命”
沈从文作品中具有“贾宝玉情结”的对象女性都是纯净璞素的,萧萧、夭夭、三三、翠翠,似乎都带有实际生活中“主妇”(沈从文的妻子张兆和)“黑中俏”的美质姿影,除了夭夭比较活泛机敏,四个少女似乎都是作者一怀湛蓝天际邈洁流云诗思的化衍,对爱情懵懂、蒙昧得可谓天然愚痴,却也倍添了不少美丽得让人心碎的忧愁,清新的朦胧,幽净的惆怅,“生活”与“生命”一样地单粹,演绎场场近乎无事的悲剧。这些女主人公性格都透心的明亮,仿佛不含任何渣滓的玲珑水晶,因了“生活”某些不可测的人事嬗变,水晶被打破了,碎出一地依然粹美的珍珠,虽是不成圆全的支离,却更加勾起读者十二分惜弱的悯恋与爱怜。如果说她们是作者作为一个诗人的幻梦童话杰作,那么《主妇》则是作者作为一个散文写手创作的一个更为接近真切现实“生活”的、超离天真善良的女性体味现实主义思考报告。远远告别幻想的激情,以近旁刚刚新婚不久的妻子作模特,去记录沈从文对其最亲近女性最本真的悲欢照察。想象与现实的冲击,诗情与冷思的冲撞,外在实“生活”与内在梦“生命”的冲突,将沈从文对女性生存的认识与理解导入到一个更为复杂渊深的视域阀限,从而将其“生命”女性观并不“隔”地在文本中形塑,颇为耐人寻味。
《主妇》写了一对年青夫妇结婚三周年纪念日一天里的所行所为,所思所想,小说以男主人公为视角叙述者,字里行间弥漫着一股微带蜜灰色忧愁的怀旧“伤寒”味,是轻恋,更是凝忧,即使两夫妇末终依旧琴瑟相谐,却也免不了鲁迅《伤逝》里子君怪怨涓生大男子主义的悲哀和曹禺《北京人》里曾文清、愫芳精神隔阂孤独的怆伤。“主妇”的“生活”是单薄的,“她想起她的生活,也正仿佛是一个不可把握的幻影,时刻在那里变化。……她很快乐。想起今天是个希奇古怪的日子,她笑了”[7](P59);“主妇”的“生命”是被动的,“三年前同样一个日子里,她和一个生活全不相同性格也似乎有点古怪的男子结了婚”。单薄的快乐仅因为一个三周年结婚纪念日,她想起了一些单薄的愉快往事,便“关不住青春生命秘密悦乐的微笑”[7](P296);被动的接受仅因为她是一个宿命里就应该被别人追求的“守心”对象,她觉得“一切都是偶然的,彼一时此一时。想碰头太不容易,要逃避也枉费心机”,她扮起一个新娘子,“心甘情愿给一个男子作小主妇”,也就完结了一个女性应当如此“生活”才最“生活”的使命。她不去追问为什么,也倦于去盘缚“一切若不是命定的,至少好像是非人为的”那些抽象无谓的无稽思考。日子过去了,生儿育女了,她有时也对“她是不是也随着这川流不息的日子,变成另外一个人呢”生发些许芒昧的怅然自失感,“因为孩子,她忘了昨天,也不甚思索明天。母性情绪的扩张,使她显得更实际了一点”,叙述者显然有些令人气闷的“朦胧”怨怼情绪。“主妇”恋爱时,也不过借各样男子的情信催给自己“一点秘密快乐,帮助她推进某种幻想”,一切都是被别人精神“催眠”的,偶尔主动时,也不过想用什么法子使男子那点能让一个女子的心保持鲜、新、醉、敏、灵的痴处保留下来,成为她生命中一种装饰,据说“一个女人在青春时,是需要这个装饰的”,“生活”永远是男子的天,女性自己的爱愿充其量好比青蛙死呆的珠眼,只有男子的“跳”才会引起自己并不热络的“灰情”关注。“主妇”因了男子全盘格外的对己“惊异”美的迷狂(久持幼稚的狂热),便决心开始学做家庭与社会双料的“模范主妇”。她尽力去适应男子的生活习惯,却没有对男子性灵深处成熟“理解”的体心,“她才二十六岁,还不到能够冷静的分析自己的年龄。也为了爱他,退而从容忍中求协妥,对他行为不图了解但求容忍”,她希望男子生活样式“长处保留,弱点去掉”,却也不能够了然“一个人的性格,在某一方面是长处,于另一方面恰好就是短处”的“生活”哲学之双律背反。听完男子的心声吁求,主妇便有了“一种属于独占情绪与纯理性相互冲突的矛盾”,她没法驾驭男子精神幻想高飞的内意倾向,便不去理解那些深度的“生命”根柢情愫,而是在力求简单的现实“生活”追求中找寻最“化零为整”的慰安。“她承认现实,现实不至于过分委屈她时,她照例是愉快而活泼,充满了生气过日子的”。三年的结婚生活让她意识到很多引起轻微惆怅与惊讶的变迁,然而唯有一事让她“觉得希奇(似乎希奇)”——自己一种好像毫不改变的东西(青春美丽的常驻),她为自己经年不逝的美貌与美德尚能给予一些熟悉的陌生人一点烦恼抑或幸福而感到由衷的快乐,女人“生命”的全部价值意义或许仅仅在此。她害羞地想起一个诗人所说的“日子如长流水逝去,带走了这世界一切,却不曾带走爱情的幻影,童年的梦,和可爱的人的笑与颦”,女人“生活”的全部快乐积储或许也仅仅寄存于这种诗意的想象之上,然后“主妇”对男子天然叫一声“你不知道我如何爱你”这一其唯一安身立命之精神维系口号,男子却伴着“一缕新生忧愁侵入他的情绪里”,“他觉得她太年青了,精神方面比年龄尤其年青。因此她当前不大懂他,此后也不大会懂他”。这便是易于满足渺小愉快的“主妇”悲剧之所在,也是沈从文成熟期对真实女性的一种文学思考观察,女人似乎永远逃不脱一生被拴在男子裤腰带上的命运(女人的话题一生都是男子,谈他、爱他、怨他、希望他“完全属于她”……,永无终了),而我们的男子却在思想:作为“生活”插曲之一的女人,其琐屑轻薄的“生活”“边角料”悲剧性地缠缚了几乎所有男子心心念念欲求内在“生命”圆、粹、美、全升造伟大梦想的一生可能性光荣。
沈从文穷其一生,在“生活”与“生命”的爱、憎纠结中打滚,一方面羁轭于“生活”“实然”的形而下困境,另一方面却憧憬于“生命”“应然”的形而上寄栖,在现实生存境遇中如此,在其文学世界的营构中亦如此,小说《月下小景》与《主妇》便是沈从文在关于种族与女性性别叙述中“生活”与“生命”不得谐和的例证,这种不谐和是隐含作者在其潜文本中的无意微妙呈露,却反映了作者最内在、最深在、最本在的精神生态。
[1]凌宇.沈从文的生命观与西方现代心理学[A].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2002(2).
[2]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十一卷文论)[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3]沈从文.沈从文小说选(上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4]贺兴安.楚天凤凰不死鸟——沈从文评论[M].四川:成都出版社,1992.
[5]朱光潜.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J].花城,1980(5).
[6]金介甫.沈从文传[M].符家钦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
[7]沈从文.阿黑小史[M]//沈从文小说选(下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