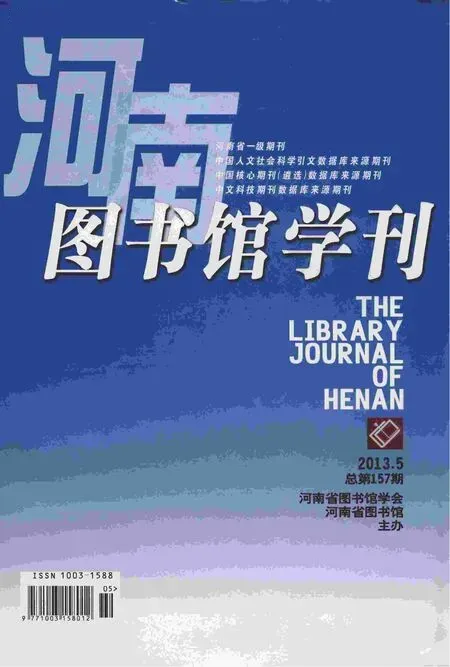“太上研究院”走出的国学大师——蔡尚思和图书馆
刘 娟
(南京图书馆,江苏 南京 210002)
“在我漫长的治学道路上,我受益最多的,莫过于图书馆。因此,我对图书馆怀有深厚的感情和崇高的敬意。”这是我国著名思想家、哲学家,百岁老人蔡尚思先生在其文章中的肺腑之言。确实,在蔡尚思漫长而崎岖的治学道路上,图书馆这位默默无闻的“朋友”如影随形,相依相伴,是他学术上的“知己”,跋涉中的“驿站”,给了他莫大的帮助和供给,和他结下了不解之缘。
1 蔡尚思和图书馆的一生之缘
蔡尚思生于1905年,学术生涯长达80余年。早年,他走南闯北,艰辛求学,晚年依然著书立说,孜孜不倦。回顾他的治学之道,“首要的在于多读书”、“须臾离不开图书馆”。正如他自己所言:“哪里有大图书馆,哪里就有我的足迹。”
1921年2月~1925年6月,蔡尚思到离家乡一百多里外的永春县福建省立第十二中学读书,校长是前清举人、诗人兼藏书家郑翘松。他藏书颇丰,为闽南一带最富。蔡尚思除了在课堂上向老师请教外,经常向他借书来读。四年多时间里,蔡尚思渉猎了诸子哲学、司马迁、班固的史学、唐宋八大家的文学,为以后的学术生涯打下了较坚实的基础。
1925年~1928年,蔡尚思不为父强迫结婚所阻止,也不顾乡人的劝告,坚决独自冒险北上求学,于弱冠之年考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孔教大学研究科为研究生,并师从清华研究院王国维、梁启超等教授。在得到诸多名师教益的同时,他又一头钻进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第一个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中国现代第一个国立图书馆)刻苦攻读,学业大进。梁启超在看了他的《论各家思想》一稿后曾勉励他:“大稿略读,具见精思,更加覃究,当可成一家言。勉旃!勉旃!”
1931年9月~1934年8月,蔡尚思到武昌的华中大学教书,经常向文华公书林、湖北省立图书馆程方馆长借读,同时也向兼做图书生意的汉口藏书家徐恕借书来读。他先后偷读了马列主义理论著作几十种,明白了许多新道理。这段时间是蔡尚思思想大转变时期。
1934年~1935年,因华中大学校长言而无信,蔡尚思与之失和,愤而辞职,来到南京,入住号称藏书为“江南之冠”的南京国学图书馆,发愤埋头读书。这是蔡尚思最难以忘却的一段生活,是他生平最值得纪念的一件事,是他一生读书的“黄金岁月”。国学图书馆独特的“住读”制度和丰富的馆藏以及柳诒徵馆长的关照,给了蔡尚思饱读诗书的大好机遇。他“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短短一年,以“日夜不休”的苦读、快读,读完了历代除了诗赋词曲一类以外的文集数万卷,搜集中国思想史等资料几百万字,成为名副其实的“读书破万卷”,从而奠定了他中国思想史、哲学史、文化史、历史的深厚学识,为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基础。这段闭门“住读”生活是蔡尚思学术生涯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时期,“是我治学上最满意的一个时期”、“读书之多,学问增长之快,在我一生之中都没有超过这个时期的”。
1935年~1941年,蔡尚思到上海沪江大学任特种教席,教授历代文选、中国通史、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课。其间,沪江大学图书馆、顾廷龙主持的合众图书馆是其常年借读的场所。其中1935年9月至1937年间,只要是寒暑假,他都要特地从上海去南京国学图书馆补充查阅搜集资料,坚持不懈。
1949年以后,蔡尚思先后担任沪江大学副校长、代校长,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副校长、顾问等多种职务。虽然教学和教务繁忙,但他还是经常去沪江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看书,从而著述不辍,完成了多种学术著作。
1984年~1985年,蔡尚思的家乡福建德化建立图书馆,蔡尚思闻讯甚是欣慰,因为他少时在德化饱受无书可读之苦。他解囊相助,两次把自己一生几经损失的宝贵图书捐出赠送给德化县图书馆。
1988年~1989年,蔡尚思为了编著《中国礼教思想史》一书,每天都到复旦大学图书馆看书补充资料。这是他五十多年后又一次在图书馆的读书生活,蔡尚思自认“比之青年时期也许还要难得而可贵些!”“是亦一大幸福也”。
1990年,蔡尚思在写《周易思想要论》一书时,因为复旦大学图书馆的参考资料不够全面,85岁高龄的老人还挤公共汽车去上海图书馆查阅有关著作数十种,早出晚归,坚持数月,而且还自豪地告诉别人自己是挤公共汽车来的。
1992年2月,蔡尚思又把自己的珍贵藏书装了九大箱,第三次捐赠给德化县图书馆,以支持家乡的图书馆事业。
2 蔡尚思对图书馆的独到见解
和图书馆一路走来,蔡尚思功成名就,硕果累累。他深知图书馆的地位和作用,每每感慨“我能够得到一些学问,要多归功于图书馆”“尤其是大图书馆的藏书”“我的治学,以文学为入门,以思想史为中心,以文化史为外围,以通史为基础,以其它有关学科为常识。治学范围较广,须臾离不开图书馆”。不仅如此,他更是经常撰文或在著述中专门论述图书馆,结合亲身经历,以独特的见地阐释图书馆的重要性,呼吁人们重视图书馆,利用图书馆,可以说,他是宣传图书馆最得力的优秀读者。
早在青年时代入住南京国学图书馆之际,蔡尚思就在《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年刊》上发表过《学问家与图书馆》一文,专门探讨图书馆的作用问题。文章开宗明义:“学问多出于书籍,书籍多聚于图书馆,无图书馆即不能产生大学问家。”洋洋洒洒,论之颇详。这是蔡尚思最早论述图书馆的一篇文章。其后,他在《中国历史新研究法》一书中,又以“研究与图书馆”为标题专章阐述了这个问题。章节末尾总结道:“我们有两个老师:一个是活老师,即教员与学问家,一切都是有限的;一个是死老师,即图书或图书馆,一切都是无穷的。所以死老师远胜于活老师,上课室不如上图书馆。如往图书馆勤读一年书,便胜在大学校虚坐四年毕业,甚至比入任何研究院都要好。大图书馆直可叫做‘太上研究院。’我便是一个入研究院与常游‘太上研究院’的过来人。”
晚年,蔡尚思经常撰文回忆自己的治学生涯,只要谈及治学经验,他总会说道:“我从前只知大学研究所是最高的研究机构;到了三十年代,入住南京国学图书馆,多读些书以后,我才晓得大图书馆是‘太上研究院’与‘太上导师’”。“太上研究院”一直是蔡尚思对图书馆的尊称,足见其对图书馆的崇敬。他曾以“图书馆是太上研究院”为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进一步阐明自己对图书馆的认识:“学生,顾名思义,就是要向老师学习。但大凡学生,都有两种老师:一是活老师,即学校里的师长;与活老师相对,图书馆及其藏书可称得上是‘死老师’……但是,在人生求知的道路上,自学的时间却远远超过学校教育的时间。所以,对于一个人的学识的贡献,可以说,‘死老师’远远超过了活老师……”。
3 蔡尚思和柳诒徵的莫逆之交
在蔡尚思成功的道路上,南京国学图书馆功不可没,而其中国学图书馆馆长、著名学者柳诒徵更是居功至伟。“如果没有柳先生给我多读书的大好机会,就连今天这样的我也不可能。”“这个长辈给我的教益,超过了我的所有老师,是我学术上的最大恩人。”柳诒徵是为蔡尚思提供读书机会最多的长者,是为蔡尚思讲述历史故事最多的长者,是对蔡尚思鼓励最多的长者,是给蔡尚思教益最多的长者。他们虽然一个贵为国学大师、鼎鼎有名的大图书馆馆长,一个只是默默无闻的普通读者,却一见如故,志趣相投,以真挚的友情,演绎了一段为世人津津乐道的佳话。
不妨用蔡尚思自己的几段回忆来重温这段“忘年之交”。
“我得以在国学图书馆中大借书大阅读,应当归功于柳馆长特别给我的权力,他先告诉阅览室的馆员,必须尽量给我自由借阅图书,每次五册、十册以至数十册,都不限制。如果不是如此,我是无法完成略阅赶阅馆藏别集的预定计划的。他是我在治学上最大的一个恩人,他最大量地供应我研究的图书之外,还经常对我讲文化掌故等等,等于为我这个后辈补课,使我得到书本上所得不到的许多知识。……我起初以为,我与柳先生在孔子思想上,在政治思想上,至少也会有对立情绪;哪知他一点也没有这样要求我,相反,在纪念孔子诞辰时,请我为馆员讲孔子思想。他真是我的一位好老师。”
“我生平最念念不忘的就是这个大图书馆和柳馆长。我离开该馆时向柳馆长辞行,他特写‘开拓万古心胸,推倒一时豪杰’横幅,作为临别赠言。又说:‘自有此图书馆以来,所阅图书之多,无一超过蔡先生者,请作一文以为纪念。’我为作《学问家与图书馆》一长文交给发表,我感谢他给我多搬图书的特别权利,他感谢我把图书蠹鱼赶走的特别功劳。”
“柳先生又是最使我感动的长辈,我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逃难住在复兴中路,柳先生当时住在海防路,二地相去很远。有一次他步履维艰地走来看我,他先说:‘您是最多读南京国学图书馆藏书的一个人,自您离馆以后,我经常想念您,所以特来拜访。’接着表示:‘我视图书馆重于自己的家,重视馆藏图书甚于自己的家产,爱护无微不至。抗战前夕,我把馆藏书籍搬运迁藏,但至今已损失了一部分。我对祖国文化未克尽全责。’说着不觉流泪。这非常感动我,我也泪珠欲滴了!”
2005年,南京图书馆为制作一部馆史资料片,特地去采访了蔡尚思。时年,蔡老已届百岁高龄,记忆力大不如前,所以,当他按照工作人员准备好的稿子念到“我是1934年至1935年在南京国学图书馆住馆读书的”时,停了下来,否认道:“我去过的地方很多,我记不清是什么时候在国学图书馆住读的了。”然而,当念到“柳诒徵是我的恩师”一句时,他笑了:“这句话是对的,他就是我的恩师,他的确是我的恩师。”可见,柳诒徵是蔡尚思心中永远铭记的恩人。
4 蔡尚思利用图书馆的谆谆教导
善于利用图书和图书馆,是一切人才成功的重要因素。蔡尚思一生书海遨游,孜孜不倦,以柳诒徵夸奖的“前既无古人,后也恐怕难有来者”的“蜜蜂采花”式、“工人开矿”式、“竭泽而渔”式的“苦读”,遍览各大图书馆的藏书,不仅为世人留下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读书方法和经验。
1990年,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汇集了40多篇国内知名学者文章的《著名学者谈利用图书馆》一书,其中蔡尚思的《图书馆是太上研究院》一文置于首篇。对于利用图书馆的体会和心得,蔡尚思娓娓道来,语重心长,总结了六个要点。
4.1 进了图书馆,不能见书不见人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往往被人们忽视的问题。有的读者一踏进图书馆的大门,就摆出一副大学生、研究生、专家、学者的架势,目中无人,不肯下问。殊不知图书馆里有许多学有专长的学者和专家,他们能在目录、版本、信息等方面给你以很多帮助,使你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实际上优秀的图书馆工作者都是培育英才的良师益友。
4.2 要学点目录学
目录索引是读书治学的门径,是打开图书馆大门的钥匙。清代学者王鸣盛认为,书目是“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有人更把目录索引比作学海的灯塔、航手和指南,“使人人知某书当读,某书不当读,则为易学而成功且速矣”。因此,学点目录学,掌握查阅文献资料和最新信息的方法,可说是在图书馆读书的一条捷径。“我入住南京国学图书馆,第一件事就是买一部该馆出版的集部目录,正是这个道理。”
4.3 正确处理专攻一门与博览群书的辩证关系
进图书馆读书,自然要有明确的目的。对于自己所攻的专业与研究的某一课题,要求掌握全面、系统、完整的知识,应该千方百计捕捉与此相关的信息,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但是,如果孤立地专攻一门,把自己的知识面搞得很窄,其结果就会连一门也攻不通。
4.4 能入能出,书而不呆
到图书馆来,就是为了读书。爱读书,迷于读书,确是好事。拜书为师,尚友古人,结交当代作者,乃是学问家必由之路。但是,不能入而不出,食古不化,成为书本和古人的奴隶。读什么书就爱什么书,研究谁就迷信谁,以为把研究对象抬得越高,其学术价值就越大,就不对了。
4.5 学无止境,永远向前
图书馆不仅是读书的地方,也是修身养性的地方。在图书馆里,可以看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可以看到宏观和微观的大千世界,可以看到无边无际的知识宝藏。置身其间,古今同时,中外同地,心胸开阔。要向前进,不要倒退。学术无禁区,真理无顶峰。如果进了图书馆,仍旧目光如豆,宥于一孔之见,那就等于还在图书馆的门外了。
4.6 乐从苦中来
人们常说读书乐,这是对的。但是,如果不肯苦读,又何来其乐陶陶?“我少时穷苦,思想才得以前进。我失业在南京苦读,每天十七、八小时,不可谓不苦矣!然而,职业上的失业,却是学问上的得业,一载苦读,终身受用。凡事都有两面性,学若不下苦功夫,单纯追求读书乐,我看,这种乐趣在图书馆里是找不到的。”
蔡尚思生平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再度入住南京国学图书馆,可惜一直未能如愿,因此,他深盼后世有人能像他一样,选住一个大图书馆读书和搜集资料。“比我从容不迫,更扩大其范围,也更仔细认真地去通读一下:研究中国文学史的应当遍阅集部图书,其中有连我也没有翻过的诗、词、曲……”这既是一位前辈对莘莘学子的殷切期望,也是一位读者对图书馆的热忱与期待。“小水出小鱼,大水出大鱼”,愿更多的蔡尚思在图书馆这样的“大水”里脱颖而出。
[1] 庄焕先.著名学者谈利用图书馆[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
[2] 蔡尚思.蔡尚思学术自传[M].成都:巴蜀书社,1993.
[3] 包中协.图书馆是太上研究院——访复旦大学蔡尚思教授[J].江苏图书馆学报,1987(6):78-79.
[4] 蔡尚思.中国历史新研究法[M].北京:中华书局,1940.
[5] 蔡尚思.中国文化史要论[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0.
[6] 镇江市文史资料研委会.柳翼谋先生纪念文集[M].镇江:镇江市文史资料研委会,1986.
[7] 蔡尚思.蔡尚思自传[M].成都:巴蜀书社,1993.
[8] 岳峰.蔡尚思教授访问记[J].史学史研究,1992(2):55.
[9] 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记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0] 蔡尚思.中国思想研究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