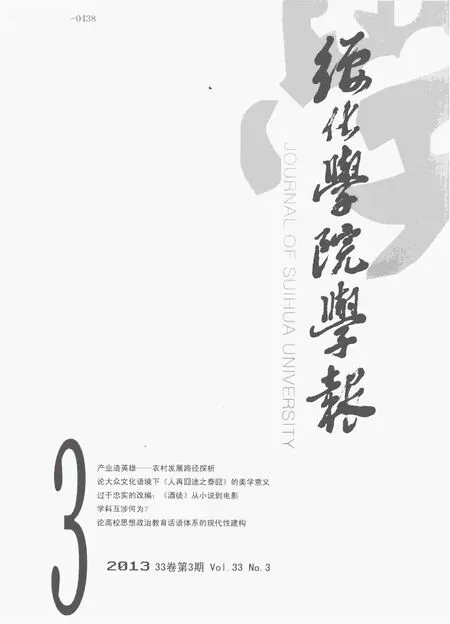论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的文化重建
高 杨
(中国传媒大学 北京 100024)
二十世纪的经典社会学理论强调社会结构的“现代化”和“非传统化”[1],这表示社会结构在进化论意义上的演进方向。但是,社会结构的调整既决定于现代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社会变化,又受社会固有的能够代表本民族精神的传统文化所影响。而后者在为社会结构赋予精神价值和摆脱阶段性的审美疲劳所带来的异化感方面意义深远。
一、社会结构的动态演进
在欧美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中,社会结构是指独立于主体性的人并对人有制约作用的整体外部环境。之所以使用这样一个概念,是因为它的抽象程度最高,相对剔除掉了所有意义和价值成分,这就为代表意义价值的文化概念有效进入提供了空隙。
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上层建筑受经济基础制约,但是我们发现在经济基础附近,一直徘徊着另一个要素,它是和人的理性一样驻扎在人的精神领域,影响着人的日常行为及对外在世界的理解和判断。这种带有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式的精神状态就是人的文化积习,它顽固地束缚着人的思考,将人的思考和想象局限在本族先民划定的领域,我们几千年来只是在一个划定的精神圈层内游戏,只是在不同时代他们玩的玩具或有不同。
对于马克思的社会学理论,关于社会结构的三元模式是“经济——政治——文化”。这势必会造成这样的认识,文化是在经济和政治双重制约下形成的。但是,处在历史中的社会事实却与此存在很大的差异,尤其是在有新思想进入的社会转型时期。这种模式应相对复杂地表征为“旧文化——经济——政治——新文化”。这样,在形成新的社会结构过程中,需要新旧文化间的彼此对译和新旧文化同时阐释这个社会结构以求其合法性就有了合理的解释。
社会结构的现实存在有着天然的合理性,它是经过不间断的社会斗争而选择出来的特有形式。因此它能保证整个社会的理性运行并推动人类社会朝着理想世界方向演进。像韦伯曾经描述的那样:“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不曾像近代西方如此深刻地体会到,整个国家生活的生存,它的政治、技术和经济都绝对地、完全地依赖于这样一个经过特殊训练的组织系统。社会日常生活之中最重要的一些功能都已经逐渐被那些在技术上、商业上以及在法律上受过训练的政府行政人员所操控。”[2]虽然韦伯的论断不免带有一定的理想化色彩,但这也是由于学术抽象所带来的,而不是他可以将其所观察和分析的社会结构理想化。任何一个社会结构的构成实际上也都依赖于这种“经过特殊训练的组织系统”,因为它保证了我们生活的环境是在一个相对系统化和理性化的层面运转。
但是,社会结构的不合理性也由这种系统化和理性化而凸现出来。社会结构的现实转化所面对的不是一个机器世界,而是一个充满血肉生气的人类社会,一个充满多元精神的独特群体。社会结构的自身属性要求其按部就班地运转,这就会在社会结构本身的整体性固化和人类精神的动态演进中失衡,使其职能从服务转变为异化人的存在。社会结构的这种整体性“是互不相容的事物之间的一个张力。对于我们来说,它并不是一个客体,而是位于遥远而朦胧的地平线上;他是作为独立的实存者的人们的寓所,是这些实存之创生的可见形态,是感性中的超感性者的清晰化——但所有这一切都在此沉没到非实存的深渊去了。”[3]雅斯贝斯所提出来的“感性中的超感性者的清晰化”正是在社会结构成为人的异化存在时所产生的独特效果。
社会结构所面对的这些深层问题要求它进行阶段性调整,而这种调整不仅仅是部门的增减,更应该是基于对功能的要求而对社会结构进行的文化阐释。传统文化对社会结构的合理赋值,一方面能够增强社会结构的活性;另一方面能够刺激社会主体的精神。这样势必会带来一个国家文化形象的彰显,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发挥提供必要的前期准备。但是,这种赋值需要理性而深入的论证。在以适配性为主要原则下,文化提炼出自身的恒久价值并与社会结构的静态属性相融合。
二、社会结构与文化价值匹配
文化是一个深刻的精神命题,它必须在经过历史的无数次的淘洗始终停留在人的身上的东西,这不能简单地通过人类社会的精神脸谱化来解决。而文化的碰撞就是摩擦或者战争,当今很多政治事件都和文化冲突相关。当我们进一步分析文化冲突的后果,我们发现结论似乎与我们曾经的设想存在很大的差异。张典教授在评析韦伯的理论时曾经引用过尼采对文化的论述:“尼采认为每种文化精神合而不同、相互激发,希腊本土的精神在这种激发中提升了自身的境界,综合不是互相成为一体,而是在外面刺激,每一种文化精神从外面吸收营养促使自身生长。那么,从尼采的德意志的思维方式出发,资本主义是一种理性的异化物化行为,在希腊精神的内部就潜藏着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就是希腊精神的现代性形态。”[4]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引申,社会结构的样态和社会精神的状况并非完全是外力作用的结构,而很大程度上是本民族文化精神的顺势选择。
任何一个民族都会自觉保持本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尤其是在两种异质文化直接对抗时,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就极易被凸显出来。即便在大国文化温和输出的和平年代,文化也很难被轻松取代;相反,文化的自我保护机制会适时地将“输入文化”中的合理成分吸纳转化为与其适配的一部分。荆学民教授也认为,“人类文化精神的独有特质是,它不仅随着经济政治的变化而变化,而且相对独立的自身运作发展的过程会成为一种强力地作用于整个社会的文化力量。”[5]但是,这并不意谓着我们可以坐视甚至放任文化间的博弈,放心地等待文化的自我保护机制自动发挥作用。因为,文化的自我保护机制是建立在本民族对其的自觉和自信的基础上的,而这种自觉和自信来源于文化价值的自检。在合理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后,儒家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和道家的“逍遥”思想对于打造外勤内乐的新型人格君子社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构建新的社会形态的科学思想。但是,在具体实践的过程中要根据具体国家的国情,这就要求我们把本国的文化进行现代化转型,以辅助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的构造的基本要素是人,所以对于人的培养和素质的打造甚为重要,而这就不单单只依赖马克思主义思想就能完成的,还需要本土的固有文化软性地改造,这一方面可以与我们国民的习俗相配合,另一方面也不违背民众的基本情感。
卡尔·亚斯贝斯在《时代的精神状况》一书中论及文化和个体的关系:
人不仅是生物遗传的产物,更主要的是传统的作品。教育是在每一个体身上重演的过程,个人在其中成长的实际的历史世界所发生的作用,连同双亲和学校对他施加的有目的的教育,以及社会生活的各种风俗习惯的影响,最后,还有他所有的见闻与经历给予他的影响——这一切都使他获得了所谓的他的文化。他以自己的存在的活动使这个文化完善,而这个文化对于他,可以说,是他的第二天性。[6]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化是个体的固有标志,文化对个体的影响举足轻重。因此,文化不可以泛化为普通的行动与需要,但是它与人的日常行为关系密切。文化是从人的本性出发,形成的对人类生存有利的价值观念。这就要排除单纯对个人欲望的满足,由此形成的社会构型就可以与历史层面的文化相贯通。而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够形成稳定而持续的社会局面。
对于社会结构的静态分析,我们要从时代的背景出发梳理基本的社会关系,尤其是带有本源性的“劳动”和“社会分工”,以及由此形成的按劳分配的原则。这就把传统的“义利之争”与“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放到了一个讨论平台。我们仍然需要承认“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因其是现有的生产模式的最优选择。可见,传统文化与社会结构并不矛盾,但是将二者流畅地结合尚待时日。
三、文化对社会结构重建
文化的作用不是颠覆现有的社会结构,而是对其进行合理化地补充和完善,中国的传统文化更是不懈地坚持这样一个原则。“儒学的本旨在于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它虽然诞生于农业社会,但是其社会构型的设计,却不是基于农业社会的特殊情况,而是基于对人的肯定和天然的血缘亲情,因此儒学对于社会构型的基本设想,井不限于农业社会,而是有其普遍的价值。同时儒学的精神,乃是即现实即超越的精神,它对社会构型的基本设计即它的社会目标、设计起点及实行手段都是现实可行的。”[7]文化的这种“即现实即超越的”的功能使其能够肩负起与社会结构密切配合推进社会演进的使命。
中国的文化的主要样态是儒道二元,儒家要求仁,而道家讲求道。二者对待自然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儒家认为上天是仁慈的,因为生;而道家认为天地是不仁慈的,因为他让人受苦。这样儒家就要求人顺应天道,而道家追求的是内在个人的幸福。这两家对待人的本性中的欲望却是相同的,儒家采用的是社会化的方式,用礼节情;道家则从观念层面要求禁欲,追求朴真。儒家最痛心的就是礼坏乐崩,道家痛苦的是人心不古。
这两种文化样态对于中国的社会结构影响很大,我们可以从《尚书·伊训》中看到当时对统治者的要求:“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敢有殉于货色、恒于游畋,时谓淫风;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惟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8]这是在礼乐尚未建立起来的时代,政治上对人的欲望的处置策略。建国者提炼出来十种丧家亡国的错误。这对于中国历代的政治都有深远的影响,社会批评朝政所依据的基本原则也是这个要求所划定的。
传统文化与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关系密切,但是人民群众并不一定都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清晰地认识,这就需要舆论的宣传和思想的引导。而传统文化的构建可以弥补法制建设的缺口。荆学民教授认为,“文化精神牵导着时代的前进,构筑着人的生存模式和样态。”[9]社会结构转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形成的过程中文化精神的作用不可低估,这也和历史文化传统所遗留的政治模式密切相关。
社会结构的文化精神化需要一个基本原则,这个原则应该是在对社会结构进行深入地分析和理解的基础上,分析和判定现实社会的未来走向。对于社会结构的分析和文化价值的定位,其实“都蕴涵着对于现实和未来的价值判定和政治诉求。”[10]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是这一原则的基本准绳。
社会结构的文化精神化在个体层面是要把“经济人”转变成“文化经济人”。在经济话语成为主流的当下,人在社会上主要是经济人的角色,这势必会把人的主要思考模式转向利益的最大化,这是人在现代社会的经济旨归。但是人的精神需要安顿,人有创造理想世界的需求,人还有文化旨归,因为“文化不再像传统的那样与政治、经济等相并列,而是将政治、经济内蕴于自身。”[11]社会结构的精神化的实现也依赖于文化与政治、经济的结合程度。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对其内部合理精神的现在转化必然能够强化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哈贝马斯认为,以语言为媒介的互动对于社会再生产和进化就如劳动一样是至关重要的。[12]中国精神的现代化也是一种以语言为媒介的互动。这种互动的成功一定能为中国的文化建设提供有力的精神支持。我们应该学会用文化精神要求我们当下的行为,包括我们的日常行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结构层面真正精神化,才能整体形成中国的文化标志,中国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都有赖于此。
[1]帕特里克·贝尔特.二十世纪的社会理论[M].瞿铁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00.
[2]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陈平,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6.
[3]卡尔·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M].王德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86.
[4]张典.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关系分析 [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8):457.
[5]荆学民.信仰在社会结构及其转型中的地位和作用[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8(3):64.
[6]卡尔·亚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M].王德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77.
[7]黄守红.儒学社会作用方式的演变及现代转型[J].求索,2005(4):117.
[8]吴树平等点校.十三经[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36.
[9]荆学民.文化哲学的三形态检讨[J].求是学刊,2000(4):13.
[10]吴波.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内在逻辑的当代解读 [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2):5.
[11]荆学民.文化哲学的三形态检讨[J].求是学刊,2000(4):13.
[12]帕特里克·贝尔特.二十世纪的社会理论[M].瞿铁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