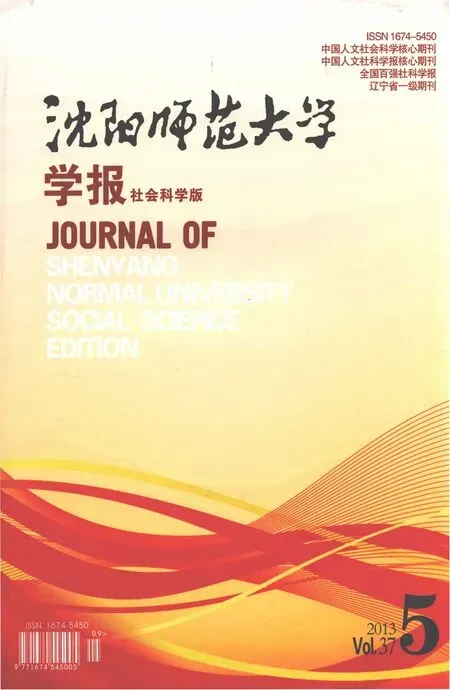马克思关于社会交往与人自主意识的建构
姜爱华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科部,辽宁 沈阳 110036)
社会交往是人们之间的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所展开的社会关系的统一,人的自主意识是人自主决定自身生命活动的意识。由于人的活动并非是纯粹的活动,而是一开始就处于与他人交往的一定境遇中,受一定社会交往形式的制约。因而,在一定的社会交往形式中,个人为了实现自主活动就会产生现存实践的意识,即自主意识。
在马克思的理论生涯中,交往关系与人的自主活动的关系一直是其关注和思考的核心问题,在他看来,交往关系本是人类绝对自主性的体现,并且是人自主活动的产物,却反过来成为外在的、独立的力量,限制自我意识的自由,成为人自主活动的阻碍,因而要超越交往关系的限制和阻碍,就要建构以交往关系的扬弃为中介的积极的自主意识。这是使异己的力量转化为个人占有的力量,实现人的自主活动的积极环节。
一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曾试图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研究揭示人的自主意识与人本身的生命活动相分离的根源。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指出,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而同自己的生命活动直接同一,不同于动物,人作为有意识的存在物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就是说,他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对他是对象,因而他的生命活动才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可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工人)的劳动这种生命活动却是被迫的强制性劳动而不是自主的劳动,人在劳动之中感到不自在,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自主性存在,觉得自己是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就是说,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人的自主意识与人本身的生命活动相分离,这就是劳动的异化,亦即自我异化。而在马克思看来,“如果人的活动对他本身来说是一种痛苦,那么这种活动就必然给另一个人带来享受和欢乐。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只有人本身才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1]56。就是说,人之所以把自身的活动看作一种不自由的活动,正是由于他把这种活动看作替他人服务的、受他人支配的、处于他人的强迫和压制之下的活动。很明显,人的自主意识与人本身生命活动的分离,即人的自我异化离不开交往关系的异化。
马克思因而逻辑地得出,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从而异己力量转化为个人占有的力量,人的自主意识的重塑,要通过人的经济关系,即通过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来完成。在他看来,“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及社会的存在的复归”[1]78。我们看到,尽管受费尔巴哈的影响,马克思关于劳动异化是以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为核心内容的,因而还没有摆脱抽象表达问题的方式,但他以劳动的异化揭示交往关系的异化已隐含了交往的经济内容与实践基础。这表明,人自主意识的建构不是凭空的而是由一定的社会交往关系,尤其是基于劳动的社会物质联系所限制和决定的。因而,建构人的自主意识就要批判地考察人所处的一定的社会关系。
但一直以来,人们总是在对自身的抽象理解的基础上,考察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关系,交往不过是从“人的本质”或“人的特性”,即“人”中引申出来的一个抽象概念。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通过批判布·鲍威尔一伙对人的社会关系,“只是提供了一幅毫无内容的漫画,这幅漫画只是满足于从某种精神产物中或从现实的关系和运动中截取一种规定性,把这种规定性变为想象的规定性,变为范畴,并把这个范畴充作产物、关系或运动的观点”,指出这种唯心主义的思辨伎俩就在于“把现实的人变成了抽象的观点”[2]。因而,马克思认为,有必要抛弃“抽象的人”,而从“现实的人”出发来考察现实的人类关系和运动。这就为切实地扬弃人的交往关系而非交往关系的某种想象的规定性,建构人的自主意识找到了现实的感性的出发点。而对于现实、感性,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认为,既不能像唯心主义那样将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也不能像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那样,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是要把他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这表明,人的自主意识与现实的人、感性的人的活动是内在统一的,人自主意识的建构既不能依托于某种精神产物或某种想象的规定性,抽象地发展其能动的方面,也不能依托于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而是要依托于感性的人的活动,依托于实践。人的自主意识并不是脱离实践之外的独立存在,而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内在环节,是人受动和能动的辩证体现。所以人的本质,尽管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但并不是永恒不变的。人不仅自然地存在着而且自为地存在着,从而展开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自我产生活动即历史。费尔巴哈没有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因此他不得不撇开历史的进程。而马克思在对人的本质作肯定理解的同时包含否定的理解,即看到现存社会关系的肯定方面又看到其否定方面,这是符合人的自主意识建构的能动诉求。我们看到,关于人自主意识的建构,马克思不仅指向人的社会关系而且指向社会关系所存在的否定方面,同时找到了扬弃的途径和力量即实践,尽管仅仅是以提纲的形式表达的。
二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则把先前以提纲的形式表达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展开。马克思开篇就强调指出:“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3]72-73意识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人的自主意识的建构亦应当从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个人所发生的交往关系(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出发,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
而交往所承载的个人之间的社会历史联系,决定了个人不仅同活人交往而且还要同死人交往,不仅受活人的制约而且还受死人的遏制。如马克思所说:“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他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4]100-101所以,对马克思来说,不是劳动对象的一定性质而是劳动对象性的性质本身即一定的交往形式,对个人需要的满足来说,成为一种障碍和异化。不过正是这样一种障碍和异化引发了人的激情和自主意识,成为目前为止推动个人由被迫劳动向自主劳动转变的主要力量。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历史地产生的交往形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就会由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式转而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即由个人自主活动的条件转而成为个人自主活动的障碍,成为“自主活动的否定形式”。而正是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亦即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矛盾引发了人的激情和需要,激发了人的自主意识。这是意识到历史运动的局限性并有了超越历史运动的觉悟,是现存的实践的意识。这时,采取行动来打破这种陈旧过时的交往形式的社会实践就会来临,由是“已成为桎梏的旧的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为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变成桎梏,然后又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3]124。他们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一个有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人的自主意识亦在矛盾的冲突和解决中,不断发展和成熟。同时,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个人的活动日益受到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就是说,各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然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最初形式,本是由人们的相互作用产生的,却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不堪忍受的力量,因而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自主意识必然会发展成为实行彻底革命的共产主义意识。
而伴随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分工也发展起来,尤其是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不仅使意识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而且从此,意识可以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就是说,“意识可以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3]82。这显然是意识自主性的极端表现。但在马克思看来,即便是现实地自主想象的意识,也能在现存关系中找到它的影子。如他举例说:“‘怪影’、‘枷锁’、‘最高存在物’、‘概念’、‘疑虑’显然只是孤立的个人的一种唯心的、思辨的、精神的表现,只是他的观念,即关于真正经验的束缚和界限的观念。”[3]83
所以,如果这种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和现存的社会交往关系发生矛盾,那么仅仅是因为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可见,人自主意识的建构只有立足于生活的生产方式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交往形式,才具有现实的实践的意义,否则只能在想象中具有想象的力量。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意识就是由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彻底激化,从而在被压迫阶级中产生的彻底革命的意识,而且为了使共产主义意识普遍产生,就必须在实际运动中而非想象中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
三
从《哲学的贫困》到《资本论》及其手稿,随着交往理论的具体深化,马克思关于人的自主意识建构的实践取向更加具体而彻底。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批判蒲鲁东指出,产品的分配关系并不是任意决定的,而是由生产资料尤其是生产工具的分配关系所决定的,只要生产资料还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产品的分配就不可能平等,从而将考察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由以产品分配为基础进一步深入到以生产资料的分配为基础。由此,我们可以逻辑地推出,要扬弃束缚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建构人的自主意识,就要具体深入到由生产资料的分配所确立的生产关系层面才具有彻底性。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就直接以生产关系对应生产力,来阐述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他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他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2]32-33显然,马克思已然要求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去解释”时代的变革,从而具体而深入地敞开人自主意识建构的实践取向。
所以,当马克思选择以资本主义经济为研究对象,则不仅揭示出资本的本质乃是在物的外壳掩盖下的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即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社会生产关系,而且为研究古代经济等提供了钥匙,从而为敞开人的自主性发展史提供了现实依据。马克思正是依据生产关系的状况及其扬弃,揭示出人的自主性发展经历了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基础上的个人独立和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三个阶段。这表明,随着异己力量不断转化为个人占有的力量,人的自主能力的增强,人的自主意识必然在不断扩大的自主活动中得到充实和发展。
我们看到,马克思关于人自主意识的建构并不是停留于思辨领域的所谓大而全的永恒体系,而是在对交往关系的领悟及实践批判中发展和完成的。在马克思看来,并不是经济状况自动发生作用,像某些人所设想的那样,而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我们必须把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一定交往关系中人自身生命活动的局限性和目的,并有了超越历史局限性的觉悟这一点看作是现实的进步。因为它使人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即能够超越现实的确定性而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从而使人达到自由的境地。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246.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