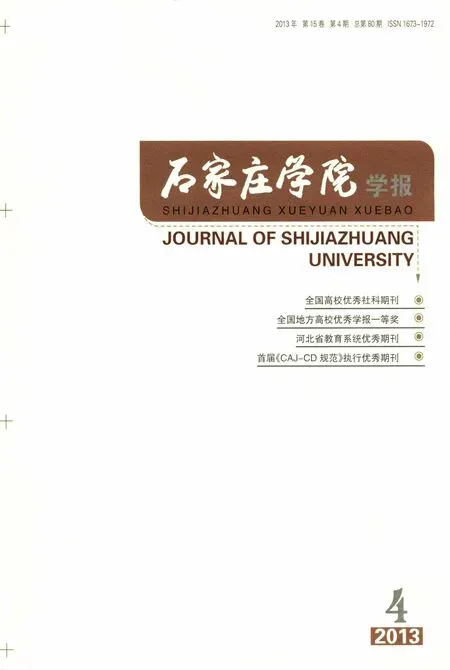关于历史真实的别一种书写——刘建东《一座塔》阅读印象
杨红莉
(石家庄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35)
刘建东的《一座塔》①《一座塔》刘建东著,重庆出版社2012年出版。文中未标注之文献均出于此。是一部家族小说,却隐喻着中华民族在特定时代风云跌宕的历史;这是一部有关英雄的传奇,却同时呈现了他们“双面人”的真相;这是一部历史小说,却寄寓着作者对于复杂人性的阐释;这是关于一座塔的故事,但却隐藏着关系民族文化生命的密码。
小说主要讲述张姓家族在20世纪40年代的起伏人生。分居A城和东清湾的老兄弟两个及其各自的儿女们,由于日军的到来并毁灭了张家的祠堂而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居于A城的哥哥张洪庭试图在家中建一座最高的塔以供奉祖先、显示荣耀,守在东清湾的弟弟张洪儒却将自己封闭在石屋之中表达着他的愤怒、愧疚;张洪庭的儿子们投靠日军和亲日政府,分别做着高升的梦想,张洪儒的儿女们却走向了反抗侵略的道路。
张洪庭和张洪儒兄弟,同样是为了张氏家族,可是,前者着眼于权力和富贵的荣耀而导致迅速覆灭,后者则放眼于民族的兴亡终至成为英雄的父亲。张氏家族的子弟们或者成为了被纪念的英雄,或者成为了被唾弃的败类。张氏,是汉族姓氏中最为庞大的姓氏,张氏家族的兴衰隐含着民族兴衰的大义。但是,具有哲学头脑的刘建东并没有将一个家族故事讲述为老套的正义战胜邪恶的故事,而是赋予小说以复杂的内蕴,尤其是对“真相”——人性真相、生活真相、历史真相的形象呈现和哲学追问,使之成为一部神秘与形而上气息都非常浓烈的现代小说。
一、两面书写与真实观
小说讲述了一段特定时代的历史,但是,在对这段特定历史中的人物、事件的书写上,刘建东却往往给予矛盾的两面书写。
在刘建东笔下,主要的人物都具有两面性。比如,对于张武备这个形象,作者就用了两种笔法。张武备是张洪儒的儿子,是小说的主人公之一。他的父亲张洪儒试图以谈判的方式要求日方返还强占的土地,必然的失败摧毁了倡导儒家仁爱文化的张洪儒,于是,张洪儒筑石屋而反思和蓄积,再不肯轻易出屋;强大的父亲隐居后,张武备逃出家乡,成为一个自发反抗日伪军的民间英雄。对张武备这个形象,小说一方面从叙述人的视角进行正面描述,另一方面则从其他人物尤其是对手的视角进行侧面描述。如小说中这样正面描述张武备:“但是在龙队长 (张武备)的内心,有一个无法攻克的秘密始终折磨着他,羞涩。羞涩就是他的内心,就是他的外衣,就是他对世界的认知。……羞涩在他身体里如同蓬勃的春天,一天天壮大。”在这样富有客观色彩的深入描述中,那个一直在父亲羽翼下生活、刚刚拿起枪来的张武备作为普通人的柔弱、怯懦让读者一览无余;然而,在他的对手——时时在搜捕他的堂兄张武厉看来,张武备却是另一种形象:“骑在马背上的张武备,在传言中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像一个从古代战场上归来的武士。”在张武厉眼里,张武备是无比强大和神武的。
对张武厉的塑造同样如此。在别人眼中,张武厉是一个“一身戎装”“高高在上的家伙”,是一个“杀人恶魔”;然而,在内视角的叙述下,我们看到,当夜晚来临,这个白天无比强大的人却无比可怜,他每天半夜赤裸着身体梦游,模仿开枪杀人的动作其实只是象征性地杀一只小鸡。他人眼中的强大和内心真实的孱弱同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更具两面性的是少女张如烟或杨小雪。正如她所拥有的这两个气质不同的名字,这个少女白天是那么诡异和乖戾,而到了夜晚却又那么善良和博爱。“白天和夜晚,张如烟和杨小雪身份如此鲜明地交替着。白昼,痛苦与厌恶包围着她;夜晚,同情,可怜,与年龄不相仿的爱牢牢地控制着那个瘦小的身体和充满幻想的头脑。”
小说中,对事件也往往采用这样对立式的叙写。比如,张武备潜入A城刺杀张武厉未遂,随即落荒而逃。叙述人说:“一路之上张武备他们都如几只惊弓之鸟。”但是,这种“失败的滋味”只有他们几个人感觉到了,在传说中,却完全是另外一幅样子:“龙队长亲自枪杀了一名汉奸走狗,给A城的敌人以沉重的打击。”
这种对同一个对象的两面甚至相反书写,在小说中处处可见。刘建东为什么选择这样的方式?这种前后否定式的叙写意图是什么?笔者以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叙写固然一方面互相补充,构成了完整的、立体的人物,从而避免了人物的扁平化;而从另一个层面看,还体现着刘建东对于真实的认知。在文本中,作者曾借叙述人这样表达他对人的真实的看法。他说,人有“一个人的真实”,也有“大多数人的真实”,也就是既有“自我”的真实,也有“他我”的真实,这两个真实,有可能截然相反。但是,这两个可能截然相反的真实又共同构成了这个人的总体真实。对于历史的真实,刘建东同样持此看法。文本中叙述人说:“我相信历史会在某个时期分杈的,有时候它会与真实接近,而更多的时候,真实会成为一个虚幻的影子。历史就是在若隐若现的真实和虚幻的转换中完成了它自己角色的扮演,被动的接受,不能破解的谜团,证明历史本身是无辜的。”这段关于历史的阐释,笔者以为是刘建东对于历史真实的理解。历史是什么?历史是说者所说,亦是听者所听。但说者所说,未必一定是听者所听,并且,说者所说,抑或听者所听,也未必就是真相本身。所以,刘建东对一个对象的两面叙述,其目的正是为了告诉我们历史真实的复杂性、矛盾性、偶然性抑或不确定性。或者还可以说,刘建东的小说告诉我们:多种相互矛盾的真实才是真实的真实。
二、三重叙述与历史观
在叙述视角的选择和使用上,刘建东一方面颇费心思,另一方面又极其灵活。说他颇费心思,是因为他在《一座塔》里精心营构了三重叙述,而每一重叙述又各有用意;说他极其灵活,是因为他在进入人物内心世界的时候,从来不会囿于固有视角的限制,而追求叙述上的最大自由。
刘建东精心营构的三重叙述视角,从外到内分别是:第一重,美联社记者美国人碧昂斯的视角;第二重,“我”——张氏家族的后人的视角;第三重,故事内部更加自由的第三人称叙述视角。从主次程度上看,第二重视角是主视角,另外两个视角是辅助视角;但是,从重要程度上看,第一重视角才是最重要的,代表着叙述人或者说作者本人的历史观。
我们先说第三重视角。第三重叙述视角的设置和选择比较容易理解:这种灵活的叙述方法使得文本在进入人物内心方面更具灵活性和深刻性,从而,使小说在向人物内心开掘方面达到了理想的高度。
我们接着看第二重视角,即张氏家族的后人“我”的叙述视角。这个视角贯穿文本,“我”讲述着姥爷、舅舅、小姨们的故事。这种家族讲述一方面加重了故事本身已有的血缘浓度,另一方面更加重了故事背后的真意:历史的残酷和血腥与血缘亲情是背道而驰的。显然,这样的叙述视角比纯粹的客观化叙述多了情感,多了意味,多了残酷历史的质感。还有一点,就是尽管我们看到小说是“我”在讲述,但仍然能感觉到,“我”的讲述背后隐藏的是“我母亲”,或者说,“我”的视角其实是与“我母亲”的视角合二为一的。而在小说故事中,“我母亲”一方面是家族故事的旁观者,因此便于客观地叙述家族内部的斗争;另一方面,只有借助“我母亲”,冲动的进步青年黄永年以及其背后的共产党人老杨才能进入小说,才能将那个独特历史阶段“声音”的丰富、嘈杂完整地呈现出来。所以,这种合二为一的家族叙述视角增添了小说的容量。
我们需要着重分析的是第一重叙述视角,即美国记者碧昂斯的视角介入文本的用意。刘建东为什么要设置这个视角?这个人物既没有和某个人物发生密切的关联,也没有影响故事的进展,似乎和小说没有什么必然关系,那么,作家设置这个叙述视角的用意是什么呢?
笔者以为,恰恰是这个西方外来者的视角在代替刘建东表达着他的历史观。那么,外来者眼中的历史是什么呢?碧昂斯的《平原勇士》这样阐释张武厉和张武备两兄弟对不同道路的选择:
所处的环境,所受的教育,以及对于社会、道德、政治的认知程度,对于他们的人生之路产生了无比巨大的影响。他们就像是河流的两个分支,他们的发源地是一致的,而当他们在政治的在某一时,某一处,或是某一个外力的影响下,开始决裂,开始向不同的方向流淌时,便开始产生了猜疑,矛盾,仇恨,敌视,杀戮。这就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景象。
张武备,张武厉,他们各自鲜明的生活轨迹,其实并不能掩盖他们内心的挣扎。他们是两条河流中的两个孤独而忧郁的持桨者。他们都很努力,奋力地向前划,却不明方向。
在碧昂斯看来,张武备、张武厉兄弟两个人都是“平原勇士”,没有正义或非正义的区别,因而都是她那本《平原勇士》著作的男主角;在碧昂斯看来,历史不是政治层面上的是或非,也不是道德层面上的善或恶,而是基于种种因素导致的不同的人生之路。人的历史,内心的历史,他们在自己所选择的人生道路上的“奋力地向前划”,才是历史。窃以为,这其实正是刘建东的历史观,是作家本人对于历史的认知和判断标准。总之,借一个外来视角阐释他对历史的认知和判断标准,这就是刘建东设置第一重视角的根本原因。
三、象征与诗学观
《一座塔》并不是一个可以轻松阅读的文本,甚至也不是一个可以在阅读中获得愉快体验的文本。相反,这部小说充满着阅读的障碍,既需要读者有足够的阅读耐心,还需要有对这些障碍不断破解的智力。阅读刘建东的这部小说,就如同走进了一片无边无际而又茂密潮湿的原始森林,需要你全身心地去感受和探索。当然,你的收获也将如冒险成功一样非同寻常。
这片茂密的森林里生长着象征的枝叶。何谓象征?黑格尔说:“象征首先是一种符号……这里的表现,即感性事物或形象,很少让人只就它本身来看,而更多地使人想起一种本来外在于它的内容意义。 ”[1]10象征何用? 布斯(Wayne Clayson Booth)说:“现代小说中用来代替议论的许多象征,其实和最直接的议论一样,是充分的介入的。”[2]219也就是说,象征义隐藏着作家的真实意图。
“塔”是小说中一个贯穿始终的意象,也是结构小说的中心线索。但是,小说中却有一显一隐两座塔。表象的塔是张洪庭建造的安魂塔。张洪庭建造安魂塔的过程,同时也是张氏兄弟姐妹们各自人生道路向着相反方向展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兄弟间的相互残杀发生在塔里,兄妹之间的乱伦也发生在塔里,这座意在安顿祖先灵魂、彰显张氏家族荣耀的宝塔成了耻辱的象征和代名词,张洪庭建塔的意义完全被颠覆了。最后,梦想破灭的张洪庭死在塔中。这座充满了讽刺意义的玲珑塔也终于在解放后被炸毁。隐含着的塔则是自筑石屋的张洪儒所建筑的一座精神之塔:试图用和平的方式与侵略者谈判失败后,他就怀揣着《论语》在自我封闭中反思并积蓄着能量,等待着机会,并终于在小女儿遇难后破门而出,用传统文化的力量唤醒了失语的张氏族人,带领族人走上了为死于抗日的子弟们招魂的漫漫征途。
一显一隐的两座塔,回答的深层问题是:究竟什么才是安顿祖先灵魂、重新彰显家族力量的方式?是仅仅靠砖瓦建起来的塔,还是凝聚在内心永远不倒的精神宝塔?《一座塔》用象征的手法揭示出一个民族延续的秘密。
东清湾的失语更是一种象征。东清湾的乡亲们在张氏祠堂被炸掉后突然不再说话了,张洪儒的三女儿张彩虹更是连听的能力都丧失了。用张洪儒的大女儿张彩妮的话说,“他们和彩虹一样,魂都丢了”。唯有张彩妮,却如同富有特异功能般听得见石屋中父亲的声音,听得见乡亲们隐密在心底的语言。她是传统文化和现实境遇的桥梁和中介。但是,失语的东清湾人却在重新走出石屋的张洪儒老人的带领下齐声诵读《礼记》,他们在自己文化的感召下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并循着这种声音为亲人们招魂。失语与重新找回话语,隐含的是文化的自信和力量。
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声音”,同样富有深刻的隐喻意义,并彰显出刘建东的哲学深度。对于人生价值、政治主张、生活选择所产生的嘈杂、喧哗,刘建东用“声音”予以概括。在作品中,“我姥姥”房间里各种嘈杂的声响是物理意义上的声音。但是,动荡社会中不同的观点和主张所产生的“声音”则是一种隐喻,暗示着政治上的各方力量。“这一年,在中国,我母亲的时代,会听到不同的声音,在重庆、南京、北平,还有延安,有的声音浸透着鲜血,有的伴随着怒骂,有的激愤,有的故作姿态,有的令人作呕,有的沮丧,有的自鸣得意……这些声音此起彼伏,嘈杂而不辨真伪。声音在广袤的土地上失去了方向,与真实和真相擦肩而过。”选择不同政治和人生方向的张家兄弟们其实是在追寻着不同的声音,“声音”由此具有了哲学的意味,指向文化、立场、观念等意义。
当然,叙述一个复杂的家族故事也许并不鲜见,同时,在这个故事中渗透进对于历史、政治、英雄等命题的形而上思考也许同样并不鲜见,但是,刘建东却用两面性书写、多重叙述视角以及象征的手法,让《一座塔》成为中华民族在特定时期的一部形象化历史,具有了民族史诗的品质。
[1][德]黑格尔.美学:第 2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2][美]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