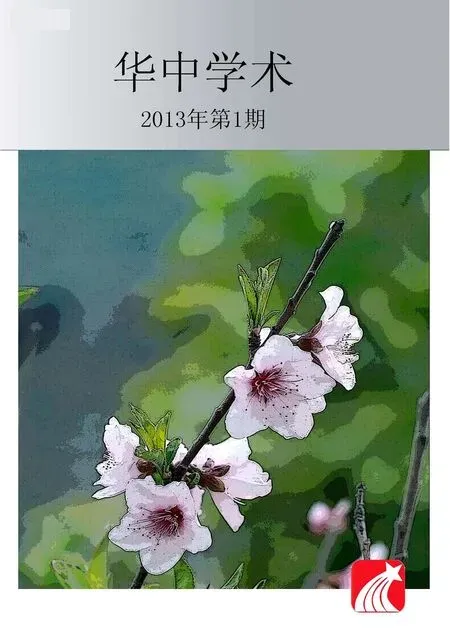东风化雨昙华林
——我的导师石声淮教授
傅道彬
(黑龙江省文联,黑龙江哈尔滨,150040)
东风化雨昙华林
——我的导师石声淮教授
傅道彬
(黑龙江省文联,黑龙江哈尔滨,150040)
1982年9月,我考入武汉华中师范学院(现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研究生,跟随著名学者石声淮教授学习先秦文学。9月,东北长白山区的家乡已经是秋风萧瑟,枫叶如火;而华师的桂子山上却是满目葱绿,桂子飘香。
当时先生并不住在华师校内,而住在武昌昙华林华中村14号的一座砖木结构的二层小楼里。踏着木制楼梯特有的节奏,拾阶而上,便是先生的书房。小楼原是先生岳丈钱基博先生的旧居,房前屋后,梧桐掩映,绿荫如盖。钱基博先生去世后,先生一直住在这里,守着先生的旧居,也守着钱老先生未尽的学术事业。
第一次去见先生的时候,是一个午后,先生的桌前散放着一堆竹签,午后的阳光装满书房,先生身材瘦高,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先生生于1913年,那一年他69岁。先生招了我们三位研究生,大师兄谭思健来自江西,二师兄万平来自四川,我来自吉林。一周两次课,从桂子山下来,坐车到大东门,然后徒步到昙华林,车挤人多,路途辛苦,但是每次去先生家我们都异常兴奋,因为昙华林里住着先生,先生的书房便是我们的课堂。春风细雨,润物无声,我们在昙华林度过了三年的读书时光。
经历了“文革”的十年动乱,和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先生劫后余生,他本已退休,却又被重新召唤回来指导研究生,老树新枝,桑榆晚晴,先生似乎有着使不完的力量。先生刚刚入了党,还写了一首词发表在华中师范学院的校报上,整首词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其中有一句“老子犹堪绝大漠”。这句诗出自陆游《夜泊水村》:“老子犹堪绝大漠,诸君何至泣新亭。”先生引诗入词,抒发自己虽至暮年而壮心不已横绝大漠的豪迈情怀。先生乐呵呵地说“这里的‘老子’,可不是‘老子天下第一’的‘老子’,而是一个老人哦”。
在先秦典籍中,先生最喜欢的著作就是《周易》。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周游列国,竹简盈箱,一直随身携带着《周易》,到了“居则在席,行则在囊”的地步。而我看到先生的书桌上经常翻摊着线装的《周易》,旁边是演《易》的竹签。我们的第一课也是从《周易》开始的,先生以象说《易》,以为阴阳源于男女,抽象的卦象有着具体的生活原型。他说:“《颐》卦卦辞谓:‘观颐,自求口实。’颐是自求口实,你看《颐》卦的卦象作,下震上艮,上下实,而中间虚,上下是唇吻,中间就是牙齿啊。再看《噬嗑》卦作,卦象是下震上离,《彖》曰‘颐中有物曰噬嗑’,与《颐》之卦象中间全虚不同,《噬嗑》卦象中间有一实物,不正是颐中有物吗?”抽象的卦象经过先生的解释生动具体,多年过去了,仍然能够想起先生讲课时的情形,仍然记得他的主张和观点。他解释《鼎》卦,下巽上离,下为木,上为火,正是炊馔烹饪之象,鼎便是最早的食器。再把《鼎》卦翻过来看便是《家人》卦,上木下火,有木有火,炊烟飘飘,才是一家人吗。《晋》卦,下坤上离,坤为地,离为日,是日出大地之象,固有晋升之意。而把晋的卦象倒过来作,就是《明夷》,“明入地中”,描绘的是太阳落山的景象。先生徐徐道来,玄远高深的《周易》在先生的娓娓讲述中变得朴素而亲切,《周易》并不神秘,抽象的《周易》是从具体的生活出发的。
在给我们讲述《周易》的日子里,先生先后发表了《说〈彖传〉》(上)(《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说〈彖传〉》(中)(《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说〈彖传〉》(下)(《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3期)、《说〈杂卦〉》(《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说〈损〉〈益〉》(《湖南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等一系列学术论文。《说〈彖传〉》,分上、中、下三篇,连续在《华中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那时候还没有所谓国家级刊物之类的说法,著名学者的论文大都刊发在自己学校的学报上,这是先生最长的学术论文,也是最见功力的文章。先生认为《彖传》解释卦形的结构,一是用内外卦,内卦是卦的下体,外卦是卦的上体;二是用中爻,所谓“中爻”是指第二爻和第五爻,是内卦即刚柔的位,中或失中、当位或不当位、应或不应;三是用卦变的原理。从《彖传》对《周易》的卦形结构出发,先生揭示了其蕴含的思想原理:
第一,世界是充满矛盾的,矛盾源于不同事物的对抗。“《彖传》认为这种排斥、冲突、对抗、‘不同行’、‘不相得’构成了世界。它解释《睽》卦:‘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天和地是统一体‘天地’的矛盾的双方,男和女是统一体‘人类’的矛盾的双方,一切事物是统一体‘万物’的矛盾的无数方。正因为它们是矛盾的,所以能够‘同’、能够‘通’、能够‘类’。只有天而没有地(或者只有地而没有天),只有男而没有女(或者只有女而没有男),只有一物而没有万物,就不成为世界。”
第二,事物是运动的,在运动中矛盾是可以转化的,达到平衡的。先生认为,《彖传》说“交”、“感”、“应”是变化,是运动;说“通”、“化生”、“兴”也是变化、运动。此外《彖传》还说“上”、“下”,“动”、“静”,“行”、“止”,“来”、“往”,“进”、“退”等一些空间或时间的移动、数量或质量的变化等,表示运动、变化的观念。先生特别注意到《彖传》对“消息”的阐释,“消息”是矛盾,更是矛盾之间的转化,“消”是衰退,趋向灭亡,“息”是滋长,趋向昌盛。阳和阴是矛盾的双方,阳消则阴息,阴消则阳息。
先生以联系、贯通的观点考察周易之间的关系,描绘出整个《周易》相互转化相互作用的运动形态,揭示出《周易》蕴含的运动逻辑和历史循环的哲学思想。
第三,事物的运动是有时间因素的。中国古代思想家特别强调时间与时机的重要意义,比起空间的转移,《彖传》的作者更注意时间的作用,《周易》多次提到“时之义大矣哉”,强调的就是时间的意义。先生指出,《大有》和《艮》两卦《彖传》说得很明白:《大有》卦《彖传》说:“应乎天而时行”,《艮》卦《彖传》说:“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就是要符合自然规律(“应乎天”)而议“时”行动,动(“行”)和静(“止”)不违失“时”;和《系辞传(上)》“变通者,趣(同‘趋’)时者也”是一致的。《彖传》还说到“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释《乾》)、“二簋应有时,损刚益柔有时”(释《损》)。“时”在《彖传》中的意义不可忽视。
先生经常把最新的学术成果带到课堂上来,让我们的课堂充满了新鲜感,有着浓厚的讨论和研究氛围。先生曾经发表过《关于“有亡荒阅”》的学术论文,认为周文王“有亡荒阅”的法令,是指在当时的国际间,如果有奴仆逃亡,要大事搜查,不许别国藏匿他国的逃亡人士。“亡”,逋逃的人;“荒”,大;“阅”,搜索。这一法令的制定给奴隶们逋逃制造了困难,从而保障了殷周时代各个邦国统治集团的利益,保持了一时的社会稳定,因此得到了贵族势力的拥护。而商纣王恰恰是违背了这一共同的国际公约,《尚书·牧誓》记周武王率领军队攻打到商王城郊的牧野,讨伐商纣王的罪状之一是:“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显然违反国际间的“有亡荒阅”的法令,引起了国际愤怒,这是商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先生特地将这一题目在课堂上讲述,并让我们也谈谈自己对“有亡荒阅”的理解。我当时写了“自将磨洗认前朝——从‘有亡荒阅’谈殷商亡国的原因”的作业,虽然以一个小材料谈历史的大问题,材料不够充分,论据也显薄弱,但还是得到了先生的鼓励,这不是因为观点的正确,先生真实的用意是引导我们的学术创新意识。
先生学术上实事求是,不尚虚言,不率意为文,不追求时尚,一生仅发表了十几篇论文,而这十几篇论文却篇篇精彩,堪为学术的经典论作。其论作通常是一个引证接着一个引证,一个材料接着一个材料,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让观点在史实的叙述中呈现,而叙述中蕴含着深刻的哲学精神。《尚书·无逸》记载周公告诫周成王应该学习殷王中宗(太戊)、高宗(武丁)、祖甲(帝甲)及周文王的榜样,要勤勉发奋,不应贪图安逸。其中说到周文王“无逸”具体表现之一,是“卑服即康工田工”。所谓“卑服”是从事统治阶级以为的低贱的体力劳动,“田工”自然是田野劳作,而康工之“康”,郭沫若《周易之制作时代》里认为是“糠工”,即从事舂米的劳作。不过郭沫若先生认为周文王是“一位半开化民族的酋长”,生产和生活条件都十分恶劣,是简陋寒碜的,因此周文王要亲身从事艰苦的耕田和舂米的体力劳动。照郭沫若的说法,不仅周文王要亲身从事稼穑,而且不可能创作《周易》这样伟大的思想著作。对此,石先生在《周文王“卑服即康工田工”辨》一文中,征引各种历史材料和考古成果,论证文王时代周朝已经具有高度发达的文明,文王的“康工田工”,是礼乐仪式,是表演性的象征性的,文王时代完全能够完成《周易》这样的文化经典。先生的论述是朴素的,而其观点现在读来,仍然有振聋发聩令人耳目一新之感。一篇《说〈损〉〈益〉》,不足八千字,却从《周易》的《损》、《益》二卦入手,沿波讨源,探索“损益”在周代思想中的原始哲学意味;然后延伸到《论语》、《老子》对这一思想的不同阐释,分析儒、道两家对“损益”的观念的不同理解;进而顺流而下,征引《荀子》、《淮南子》、《说苑》、《孔子家语》等历史文献,考察损益思想的衍生流变,通过一个普通的语词的解读,阐发中国思想史的演进变化,先生的学术目光是远大的,而其论证的方法却是细微的。
一次闲谈中先生说到“敬惜字纸”,先生谓“敬惜字纸有两个含义,一个是说纸,就是节约纸张;另一个是说字,就是珍重文字,不率意为文”。先生布衣蔬食,自奉甚俭,通信的信封总是用旧信封翻过来用,是爱护纸张;而珍重文字,不率意为文,不强作解人,则是先生对文字对学术的尊重。这或许可以解释先生留存文字不多的原因,而这恰恰体现了先生的一种学术敬畏,一种学术操守,一种学术神圣。总体来说,先生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在先生的世界中,为我们的民族和国家保住一点守住一点什么似乎是当下最为重要的任务。在古典文化传统消失殆尽的时代里,传承比发明更为急切,讲述比创新更有力量。人们常说“守正出新”,如果暂时不能“出新”,还不如先来“守正”。
先生在学术上是深受钱基博先生影响的。1938年先生考入湖南国立师范学院,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因家庭贫苦无力交纳学费而提出退学申请。钱老先生知道后,让其以学生的身份担任助教,不仅让先生完成了学业,还能将长沙乡下的母亲接来赡养。后来钱老先生还将女儿许配于先生,钱老先生看重先生的不仅是才学,更是品格,是担当和责任。
关于先生与师母的相识,坊间多有不实记述。1985年5月,我陪先生去湖北天门参加“竟陵派文学研讨会”,晚饭后陪先生散步,先生深情地讲述过在蓝田的那段往事。师母暑期来探望在蓝田任教的父亲,在钱老先生的书房里第一次见到了娴雅端庄富有书卷气的师母,先生说,那一刻我竟说不出话来。回到家里,先生与自己的母亲说起钱老先生的女儿,母亲怂恿先生说:“那你赶快向老先生求婚啊。”当先生红着脸向钱基博老先生求婚的时候,钱老先生沉吟良久说:“我并无准备,容我想想。三天以后告诉你。”三天以后,老先生说:“我同意了。”先生说,他老人家对我是大恩德啊。上课的时候,先生每每引用钱基博先生的观点,总是称呼“他老人家说”,言语之间饱含深情。先生早期教授的几位本科学生曾经回忆石先生:
1957年“大鸣大放”时,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钱基博老先生作为一名政协委员,给湖北省领导写了一封洋洋洒洒的万言书。当时钱基博老先生年事已高,身患重病,交付石声淮教授寄出。朋友建议不寄为好。石声淮教授拖延多日未寄。钱老先生一再催促,声淮教授终于寄出去了。后来,钱基博老先生为此被错划为“右派”。当时,钱基博老先生病重,华中师范学院领导出于“人道”,未将“右派”结论告诉他本人。但是,“右派”必须接受批判,就将钱基博老先生女婿石声淮教授找去代替接受批判。钱基博老先生本人,至死不知道自己是“右派”。
1957年12月3日(周二),石声淮教授在三号楼一楼阶梯教室,给我们1956级讲“课”,其内容是:
我的岳父钱基博老先生,于1957年11月30日(周六)逝世。钱基博老先生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石声淮教授潸然泪下,全体学子屏气凝神(文见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1956级彭慧敏、刘百燕、左兵《怀念声淮教授》)。
从湖南蓝田李园到湖北武汉的昙华林,先生追随钱基博先生二十余年,先生像一个传灯人一样,将钱基博先生的文明之火传承下来。传承钱基博先生的学术,是石先生晚年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钱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就是先生与师母整理重印的。1991年我在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接受了编辑《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集》的任务,得到了先生许多指点和帮助。
先生讲授先秦文学,以经学为纲,以文献学为基础,以形象教学为基本方法。先生以为六经为先秦文学之根,经学包含着文学意蕴,先生的文学史观体现出一种以历史和哲学、经学与文学相融合的开阔的理论目光。先生不仅关注《诗经》、《左传》、《国语》和诸子散文以及《楚辞》等传统的文学篇章,更注意对《尚书》、《周易》等经典的文学解读。先生很早启发我们关注“三礼”,不仅关注其中的典章制度,更应注意其包含的篇章结构和文学思想。先生曾布置过一篇作业,就是比较《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与《淮南子·时则》,二十多年后我发表了《〈月令〉与中国文学的“四时结构”》的长篇论文,如果没有先生的启发引导还是很难注意这样的问题的。先生讲经学,从《汉书·艺文志》入手,提纲挈领,纲举目张,是经学史、是文学史也是文献学史。先生善于图画,课堂上常常是寥寥几笔,就生动勾画出人物的表情和典章器物的形貌,“总角”、“熨斗”、“缙绅”、“绶印”、“崇牙”等先生几笔勾出,跃然纸上。在讲到《触龙言说赵太后》的时候,先生画了三个表情,描绘出赵太后从“明谓左右”的愤怒到“色少解”的温和再到“恣君之所使”的喜悦的表情与心理变化,十分传神。而先生更是歌者,他乐于歌唱,他的古诗歌唱更富有感染力。
先生沉浸在古典文化的世界里,每日捧读经典,朝诵夕吟,从无暇日。先生不仅对《十三经》等文献可以背诵,对经典的注疏也了熟于心,唐诗先生也能背诵几千首。先生歌唱《诗经》给我们留下了最深的记忆。《诗》三百零五篇先生皆能歌唱,先生的歌唱不是私塾先生的摇头晃脑式单调乏味的吟诵,而是悠扬婉转跌宕起伏情感真切的艺术歌唱。《黍离》的悲凉无奈、《蒹葭》的忧伤抑郁、《硕鼠》的急切冷峻、《七月》的凝重苦涩,在先生的歌唱中艺术地展现出来。诗的意蕴是潜藏在诗的音乐里的,上古诗歌不求格律,不讲平仄,原因是它是音乐的艺术。那一刻,许多语词的训诂变得没有必要,音乐的境界更能传达出诗的艺术蕴涵。不唯《诗经》,楚辞以及李白、杜甫的诗篇,先生也能歌唱。
先生歌唱《离骚》,最具风味。先生以四句一节,把握《离骚》结构脉络,情感随着结构的变化而起伏跌宕,把屈原缱绻抑郁、无奈彷徨的心境表现得淋漓尽致。那天,窗外东风骀荡,阳光和煦,在先生深情的歌声里,泽畔行吟的屈灵均形象变得清晰起来。三十年过去了,当时情形,宛在目前。先生有歌唱的习惯,我们去昙华林拜访先生,常常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他哼唱着一首首古诗,曲调悠扬,意味深长,环绕于梁间树上。听到先生歌声的人,都被诗的音乐所感染。1982年初冬先生去黄冈参加“苏轼学术研讨会”,会上特地安排先生歌唱诗骚,代表们侧耳倾听,会场安静极了,听者无不被先生的歌声所征服。事后,来自齐齐哈尔师范学院的何凤奇老师,专门给我寄来了磁带,让我为先生的歌唱录音。我认真地给他录制了磁带,自己却没有录制,总以为和先生在一起的时间还长着呢。先生逝世后,我找人向何老师问起过录制的磁带情况,何先生说因为反复播放,磁带已经破碎。广陵散尽,先生的歌诗,遂成绝唱。
先生教书是颇为认真的。每讲一部经典,先生都要求我们写出心得;每一节课后,必有大量作业。这里记录一次讲课后先生布置的作业:
1.将《尚书·无逸》分段。2.比较《乐记》与《诗大序》,谈“情动于中”的含义。3.关于《生民》,毛传与郑笺理解有何不同。4.读《论语》,结合孔子论诗,谈《诗经》与音乐的关系。5.背诵《诗大序》。6.背诵《系辞》。
先生对我们的要求也十分严格,写错一个字,重写二十遍。看到其他专业的研究生们纷纷发表论文,我们三位每天写讲稿、记笔记、写作业,不免私下里抱怨,以为耽误了论文的写作和发表,现在想来实在悔愧难当。当时研究生的专业考试,通常是开卷,导师布置个题目,隔段时间学生交上去即可。而先生的考试却是闭卷,在先生家里,先生念题,我们记录,限定时间,当场交卷。别的专业研究生考试成绩都是八九十分,而我们都还不到七十五分。而学校规定,专业课不到七十五分不能答辩,我们只好向先生求情,先生才给我们每人提了五分,算是勉强过关。有一次先生布置作业,我写了一篇关于社树崇拜的笔记,通过社树祭祀风俗的考察,提出了人类历史上存在“木器时代”的观点。先生觉得立意不错,让我将其写成一篇论文。受到先生肯定,我十分高兴。谁知道这篇论文,先生竟让我改了八次,论文上密密麻麻布满了先生批改的笔迹。后来这篇论文与先生联合署名,以《木的祭祀与木的崇拜》为题,发表在《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上,并被《光明日报》、《文摘报》、《中国史研究动态》等介绍,这是我最早的一篇关于古典文学研究的学术论文,那一年我还不到二十五岁,正是先生的鼓励和扶持,将我带入了学术研究的道路。
先生以学术为生命,不为潮流所动,坚守自由独立的学术品格,有着不可动摇的学术原则。某学者要从副教授评为教授,将成果寄给先生作鉴定,先生谓“这个人的学术成果连中等水平的讲师都不够,怎么能够评教授呢?”惹得人家老大不高兴。一位外地的学者想联合几位学者成立一个所谓学术研究会,写信给先生,请求先生让钱钟书出面帮助说项,并让先生“奔走呼号”。先生看不惯那些热热闹闹的学会之类和一些人的表演,回信道:“我已老迈,故不能奔走;我声音嘶哑,故不能呼号。”先生为人谦和淡泊,话语舒缓,不事张扬,但绝不是无原则的乡愿。
在一些怀念先生的文章里,石先生经常被描写成一位木讷古板的学究形象。先生确实有他不谙世事老派知识分子的一面,1949年后他还穿着长衫,戴瓜皮帽。先生学富五车,在华师有“活字典”之称,但有段时间他不肯认简化字,将“贯彻”写成“头彻”,因为繁体“實”字下面的“贯”改成了“头”,他误以为“贯”字简化成了“头”。从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上看,其实这是一种文化立场和古典精神的坚守。事实上,先生的兴趣是广泛的,他的生活是富有情趣、富有诗意的。他会弹钢琴,通晓英语和德语,先生的讲稿我们都看不懂,因为是用英语写的。一次先生带着师母从武汉乘船去无锡探亲,船上有两个德国人,先生便用德语和他们谈话,临别时德国人说:“你再到德国,请与我们联系啊。”还留了通讯地址、电话。先生说:“我哪里去过德国啊,不过是自学的土德语啊。”说起这些,先生一面笑着,一面还颇有些自我欣赏。1983年4月至5月间,先生去湘潭大学讲学,带我们几位研究生同行。那时我二十几岁,没大没小,有时还与先生开玩笑,先生笑着,并不介意。一次我让先生猜谜语,谜面是“闭着嘴笑”,谜底是“哈”。先生起初没猜出来,不过先生想了一下说,“哈”字的谜面应该是“接吻”啊。惹得我们几位大笑不止,觉得还是先生的谜面更贴切,更耐人寻味。先生在湘潭讲学的日子,每天晚上我们都陪先生读书至深夜,入夜,先生怕我们饿,还将别人送给他的点心和白天剩的馒头、面包之类送给我们。有时点心不够,先生就让我们划拳决定胜负,先生在一旁看着,大笑不已。
1984年我们进京访学,想去拜访钱钟书先生。不过我们有些担心,有“文化昆仑”之称的钱钟书,不见记者,不访名流,能见我们三个外省研究生吗?还是先生写了信引荐,行前先生特地将一套《谭献日记》手稿托我们带给钱钟书先生。谭献是晚清著名学者,是章太炎的老师,手稿是钱基博先生从谭献后人处购得,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钱基博先生去世后,一直保存在石先生手里。先生说:“带给默存先生吧,放在他那里比放在我这里有意义。”当我们将《谭献日记》手稿带给钱先生的时候,钱先生显得特别高兴,大声招呼杨绛先生来欣赏。那天钱先生谈话的兴致很高,讲起话来手舞足蹈,神采飞扬,一派诗人的天真本色。而通过这件事情,看出先生对学生的关心体贴和做事的周到细致。
毕业后我执意离开了华师,离开了先生,来到哈尔滨师范大学任教。行前先生殷殷嘱托,并特地写了一封信向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吴忠匡先生(曾任钱基博先生助教)推荐我,并请吴先生对我帮助关照。1996年中秋节前,我路过武汉,华师历史系的马良怀师兄陪同我一起去拜访先生,先生已经离开了昙华林,住在桂子山上儿子石定柔师兄的家里。晚年的石先生有些健忘,定柔师兄怕其走失,上班时便将先生锁在家里,隔着栅栏,我叫先生,先生叫着我的名字,并问我东北是否下雪了,那一刻我热泪盈眶,一时间说不出话来。第二年春天,就传来了先生逝世的消息。听说先生住过的昙华林旧居,现在已经改造成了“钱基博故居”,不知参观的人们是否知道那里不仅居住过一代国学大师钱基博先生,也住过我的导师——儒雅仁厚、博学多识的石声淮教授?东风细雨,杏坛教化,先生在那里住了四十多年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