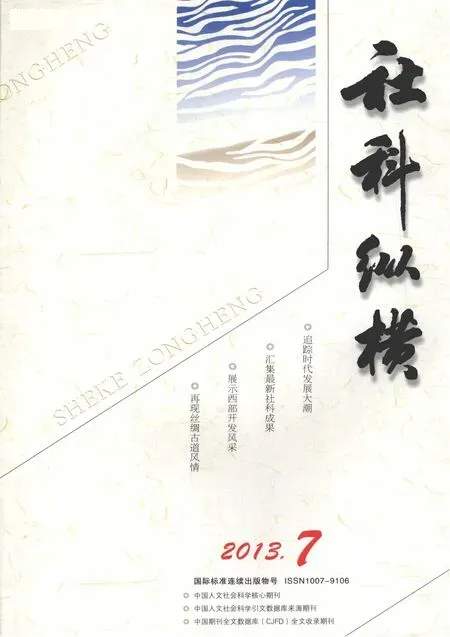精神分析影响下的女性主义电影观众理论
李东晓
(平顶山学院文学院 河南 平顶山 467000)
20世纪70年代初期,在西方妇女解放运动影响下,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研究也开始兴起。声势浩大的妇女解放运动在实践领域里的目的就是揭露父权社会中女性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并为妇女争取与男性平等的经济、政治等权利而斗争。受此影响,早期研究电影的女性主义者主要使用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方法来审视电影对女性形象的歪曲。70年代中期,受符号学、意识形态理论、精神分析以及后结构主义等理论影响,对女性观众主体特征的探讨成为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女性主义者从性别视角探讨了与电影观众相关的诸多方面,诸如:影片是如何再现女性的?这些再现与作为电影制作者的导演、摄影师以及社会文化背景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性别权力关系?观众与电影影像之间是如何互动的?如何建构女性观众的主体性?……总的来说,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以弗洛伊德和拉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理论为基本的理论工具,女性主义者围绕着“凝视”过程中的性别权力关系以及女性观影主体位置特性等方面不断探索,推动了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的发展。精神分析影响下女性电影观众主体位置理论主要有以下形态:
一、银幕之外没有女性观众
英国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家劳拉·穆尔维(Laura Mulvey)在1975年发表的《视觉快感和叙事性电影》一文奠定了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的基础。穆尔维借助于符号学、意识形态分析和精神分析批评的理论方法,以好莱坞电影为研究对象,把电影看作意义生产的过程,重视文本分析,揭示观众观看行为过程中存在的性别权力关系。穆尔维探讨了引起观众心理快感的两种机制,以此来揭示观影过程中女性被客体化的过程。第一种引起快感的机制是窥隐癖。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窥隐既是人的本能,也是快感的源泉,这种快感是观看主体把客体当成性刺激物观看时所产生的心理快感,它通过对被窥视的对象的贬值、惩罚、控制带来乐趣,其本质上是带有威胁性、挑衅性的。电影的内容以及观看环境都给观众提供了一个便于窥隐的空间,促进观众形成窥隐的幻觉。在观影的过程中男性的力比多得到释放,欲望得到替代性满足,从而获得视觉快感。而女人始终总是处于被凝视的客体地位,是银幕故事中人物的色情对象,也是观众厅内观众的色情对象,观众从女性形象那里获得窥隐的快感,产生控制或支配女人所带来的乐趣。另一个引起视觉快感的心理机制是“认同”,它通过自恋和自我发展而来,在这个过程中,观众的自我与银幕上类似他的人(“理想的自我”)认同。鉴于父权制的社会结构,穆尔维认为电影中的男性人物不能承担性的对象化的负荷,男人在叙事进程中的功能是造成事件并推动故事向前发展,这就决定了“理想的自我”是由男性明星来充当的。因此,男性始终呈现出主动性的特征,主流银幕上的男性形象并不是通过他们的外表形体或性感获得魅力,而是为观众提供一个理想的自我。观众看到的男主人公的形象远比镜像中的自我完美,因而完全忘记了现实中的自我,与影片中的男主人公形成自恋式认同并获得视觉快感。穆尔维认为主流好莱坞电影把色情编码到电影文本中制造观影快感,看的快感分裂为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这种快感具有的不平等关系反过来又强化了社会现实中的主客体间的不平等关系。穆尔维强调“必须打破这些电影编码及其与造形外部结构的关系,才能对主流电影和它所提供的快感提出挑战。”[1]
单从揭示观影过程中男性观看女性被看这种二元对立关系来看,穆尔维的理论的确没有什么新意,因为在漫长的女性主义运动过程中,伍尔芙、波伏娃、米利特等女性主义者对于传媒中女性形象的非真实表现早有论述。穆尔维的理论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她关注的实际上只是男性观众对女性身体的窥隐癖幻想和男性心理认同,忽视了女性观众的观影位置和欲望。穆尔维提及了男性同性恋快感的问题,顾及到了因身份差异而造成的观影感受的差异,但没有深入探讨,其它身份对认同作用的影响也没有提及。但是,穆尔维的贡献是巨大的,穆尔维对于银幕内人物的观看也作了简要分析,启发了女性主义者对观看过程中的性别权力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在方法方面,电影机制与意识形态相结合的分析方法成为一种非常有效的女性主义电影理论方法,穆尔维对精神分析理论的经典借用为以后的女性主义者指引了方向。穆尔维的成就及缺陷都促进了女性主义者对女性观影主体性进行不断深入探讨,推动了女性主义电影理论不断向纵深发展。
二、在两性之间摇摆的女性观众
穆尔维的理论把男性观众始终安置于主体的位置,对于女性观众的忽视引起了众多女性主义者的批评。在《追思〈视觉快感和叙事电影〉——金·维多《太阳浴血记》的启示》(1981)中,穆尔维也试图纠正《视觉快感和叙事性电影》中自己对女性观影位置的忽视,但穆尔维依然坚持,女性观众的主动欲望需要暂时进入男性立场才能获得,这样,女性观众通过换装(transvestism)完成性别认同。比如《太阳浴血记》中的珍珠一方面想保持被动的女性气质嫁给受人尊敬的大哥杰西,另一方面又渴望拥有男性生活和欲望从而与路特产生了假小子的恋情,两位男性角色代表着珍珠不同的欲望。“珍珠的主动位置和女性观众的位置相似,她通过对自己主动阶段的回忆而暂时接受男性化,珍珠的故事没有表现出对男性认同的成功,却表现出其悲哀。她假小子式的快感,她的性欲不能得到路特的完全接受,除非自己走向死亡。同样,女性观众的女性化幻想也没有得到接受,这一幻想与男性化自身相互矛盾,在异装癖的外衣下烦躁不安。”[2]
作为对穆尔维两篇文章的回应,玛丽·安·多恩(Mary Ann Doane)在《电影与装扮——一种关于女性观众的理论》(1981)中引用电影理论家麦茨、拉康以及法国女性主义学者的理论探讨女性观众位置的问题。按照麦茨等人的说法,艺术都基于一定的距离感,观看者必须维持他与图像之间适当的距离。多恩认为电影提供了众多的可供观看的东西,但这些值得看的东西往往是缺席的、不在场的。作为主体的观众的一切欲望都依赖于对缺席客体的无休止追求,而缺席本身就是一种存在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绝对的、不可填补的距离。男性观众可以和外界甚至于自己的身体保持适当的距离并建立一种主客体关系,从而保持知识和信仰的平衡,因而其注定是一个恋物癖者。女性观众要采纳恋物癖者的位置,如果说不是不可能,也必定会感到极端的困难,对女性观众而言,就是存在着图像的一种过度在场(over-p resence)——她本人即是图像。“在电影的符码中,要超越对于男性位置的单纯接受,女性观众被给予了两种选择:过度认同的受虐,或者,接受成为自己欲望客体的自恋,并以最激进的方式占用那个图像。”[3]多恩强调妇女可以通过“装扮”(masquerade)也就是通过一种过于夸张的女性气质的表演使得妇女与自己身体的建立一种距离,这种距离使妇女有可能逃离身体,成为知识的主体而不是凝视的客体。
多恩和穆尔维的共同点是两人都强调了女性观影位置的流动性,其差别在于穆尔维的异装癖女性观众是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男人以便与对象之间建立一定距离从而获得观影快感。多恩认为女性特质本身就是权力关系网络中的一个位置,装扮对女性气质的过度表演本身就是对女性特质的重构,这在某种程度上为改变现存的社会权力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撑。穆尔维和多恩的理论揭示了女性观众的位置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游离变动的事实,但二人在精神分析的理论框架下分析女性观众的位置,其理论仍然没有跳出二元对立思维的误区。
三、变动不居的女性观影主体位置
20世纪80年代,与精神分析理论相关的幻想理论受到了一些女性主义者的关注,幻想理论认为幻想过程中的主体位置是多重而游移变动的,幻想过程中的性别认同也具有机动性,以此为基础,女性主义者认为,电影也可以为观众提供多重的主体位置。在《幻想》(1984)等文章中,伊丽莎白·考威(Elizabeth Cowie)把电影本身当作幻想来思考,强调幻想的重要性,反对传统的精神分析电影理论仅把妇女限制在受虐认同的结构里,反对把妇女的认同点固定在虚构的被动受虐的女性主人公身上。事实上,幻想中的主体陷入了一连串的意象之中,幻想的存在使主体可以跨越多重的主体位置。作为虚构的电影,它能够激发观众的幻想,促使观众把现实中相关的情景纳入幻想之中,因此,女性观众可以跨越性别的限制,采取多个主体立场,发生多重认同,并不是像穆尔维所说的男性作为施虐的凝视主体和女性作为奇观的客体的简单的二元对立。
幻想理论强调观影主体没有一个固定的位置,没有哪一个位置能够成为中心在其中起主导作用,将观众带入一个更加多元的境地,是对穆尔维的男性是凝视主体女性是凝视客体这种二元对立理论的解构,但是从女性主义的目标看,“去中心化”的结果也可能会使妇女失去承认女性受压迫的经验,从而无法为女性提供抵抗社会现实的动力,女性主义鲜明的政治性也无形之中弱化了,该理论还忽视了幻想主体的文化语境及身份对观影的影响,不可能揭示女性凝视的真实状态。
四、女性作为抗拒性观众
女性主义者在论及女性电影观众的时候涉及到了三种不同的观众:文本内隐含的观众、坐在电影院中的有着不同身份的现实观众以及作为女性主义批评家的观众。穆尔维、多恩、考威等人所阐述的观众是一个文本预设的位置,这种文本中隐含的观众与坐在电影院里的现实的经验观众之间存在着距离,这种理论很难为现实的观众提供反抗的机会。塔尼亚·莫德莱斯基(Tania Modleski)在精神分析理论框架内思考女性主义批评家的位置,提出“抗拒性观众”的概念。她指出传统电影叙事强化了男性的俄狄浦斯危机,并力求通过压抑女性的欲望和声音来摆脱这种危机,但那些具有性别歧视的电影文本对女性的声音的压制未必就是完全彻底的。女性声音表达了对父权制社会秩序的不满与反抗,女性主义批评家的任务就是正确理解并确定这些被压抑的声音,以便在现实中为女性反抗的提供机会。“女性主义批评家必须拒绝屈服于电影令人恐怖的力量,而是应该肯定这些‘诱惑性’文本戏剧性、阴险性的方面——文本中比作者知道更多的部分,那些……女性拒绝向男性权利和男性策划投降的时刻。”[4]在进行文本解读时,女性主义批评家应该占据不同于男性批评家的解读位置,坚持一个文本对女性的特殊意义,把阐释政治化。莫德莱斯基力求摆脱精神分析理论的束缚,主张对文本进行抗拒性解读,她以女性主义批评家身份维护了女性主义的政治立场,表现出强烈的现实性。
结语
西方女性主义者借助于精神分析等理论对女性观众主体特征的探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极大地丰富了女性电影观众理论,但以精神分析为基础的观众理论探讨的是电影文本中隐含的观众,忽视了具有多种身份的现实观众。文化研究的兴起为女性主义电影观众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女性主义者将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年龄等属性和观看效果联系起来,将文本分析、人种学、福柯的权力理论等多种方法综合起来,力求突破以精神分析理论的二元对立思维的限制,促进了女性主义电影观众理论不断向纵深发展。当然,精神分析的女性主义观众理论并没有退出舞台,穆尔维所侧重的文本分析等方法一直是女性观众研究离不开的理论基础。
[1]劳拉·穆尔维.视觉快感和叙事性电影.李恒基,杨远婴.外国电影理论文选[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652.
[2]Thornham,Sue.Feminist Film Theory:A Reader[C].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9:129.
[3]玛丽·安·多恩.电影与装扮——一种关于女性观众的理论.李恒基,杨远婴.外国电影理论文选[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679.
[4]转引自休·索海姆.激情的疏离: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导论[M].艾晓明等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