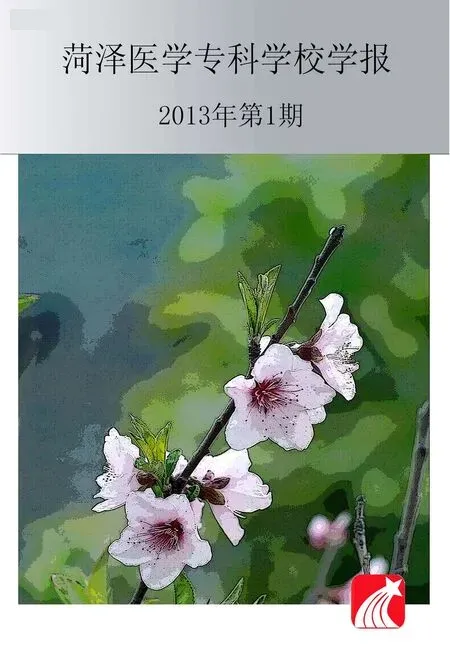胸腰椎爆裂性骨折治疗的研究进展
常锐,王德春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脊柱外科,山东青岛266071)
胸腰椎爆裂性骨折治疗的研究进展
常锐,王德春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脊柱外科,山东青岛266071)
胸腰椎;爆裂性骨折/治疗;胸腰椎爆裂性骨折/发展趋势
胸腰椎爆裂性骨折的治疗不管从理论上还是从临床上都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其研究方向也从原来的宏观领域发展到了微观领域,但手术入路还有很多争议,内固定系统从原来的AO理论发展到BO理论。随着对脊柱生物力学的研究,CO理论在指导内固定系统的发展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同时也将指导爆裂性骨折的新的分类、治疗和护理,从而使胸腰椎爆裂性骨折患者的治疗有一个前瞻性的理想效果。现将近年来的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1胸腰椎爆裂性骨折定义及分类
脊椎爆裂性骨折是椎体压缩骨折的一种特殊类型,是随CT在临床中的应用而逐渐了解的,约占脊椎骨折的20%。由Holdsworth[1]于1963年首先提出,它是指轴向压力加上不同程度的屈曲或旋转力作用于脊椎,使椎间盘的髓核疝入椎体,导致椎体内压急骤升高而引起椎体自内向外的骨折,即椎体粉碎骨折。脊椎爆裂性骨折最显著的特点是脊柱中柱受损。伤椎前柱与中柱均崩溃,椎体后壁高度降低并向四周分散,两侧椎弓根距离增大,椎体后壁骨折片连同椎间盘组织膨出或突入椎管,常致硬膜囊受压,后纵韧带可以完整。该类损伤最常见于胸腰段,仅第1腰椎即可占脊柱爆裂性骨折的50%以上,原因可能是此区无胸廓保护,并且胸椎小关节在此由冠状方向转为矢状方向。胸腰段脊柱(T10~L2)处于两个生理幅度的交汇处,活动度又大,是应力集中之处,因此该处骨折十分常见。1983年Denis[2]提出三柱理论,并根据损伤部位不同分5型,其中爆裂性骨折被划分为第二型。Bǎhler[3]将脊椎爆裂性骨折分为5个主要类型,国内的学者如张光铂[4]、金大地[5]、池永龙[6]、饶书城[7]等从不同的角度对爆裂性骨折的分类有所研究。
2胸腰椎爆裂性骨折损伤的机理
爆裂性骨折最早阐述:当暴力作用于脊柱上时,椎体的一个终板发生骨折,椎间盘中的髓核被挤入爆裂的椎体。Roaf在对脊柱压缩实验中发现骨髓等物质从被压缩的椎体内向外流出,同时椎间盘内压力增大,终板向椎体侧膨隆,最后开裂,使髓核物质进入椎体,增加了椎体内的压力,使之爆裂。爆裂性骨折发生于髓核进入椎体的速度大于椎体内骨髓、脂肪等物质流出速度之时。由于加载速率是控制椎体内部液体流出的一个主要因素,Tran[8]在牛胸腰椎标本上用相同能量不同加载速率的轴向因素载荷撞击标本,定量地给出了撞击载荷率与骨折类型的关系。
3胸腰椎爆裂性骨折损伤的生物力学研究
杨欣建[9]用低中高3种能量研究爆裂性骨折发生过程表明,开始是终板破裂,接着是椎体骨折,接下来是骨折块移位和后柱损伤,说明后柱损伤是爆裂性骨折严重性的表现。神经损伤发生在受伤即刻,而与事后影像学上骨折块位置无关。这一观点认为,脊髓神经损伤程度主要取决于损伤瞬间的严重性,椎管瞬间狭窄程度远远大于伤后狭窄程度,损伤后的弹性复位及搬运活动使得就诊时的影像学表现仅代表致压物伤后静止的位置,而不能反映致伤的过程和程度。Panjabi等[10]的实验表明,椎管动态侵犯率比静态下测量值高85%,提示脊髓神经在瞬间损伤远远大于静止状态下的压迫伤。de Klerk等[11]对42例患者随访研究发现,平均椎管正中矢状径由原来正常的50%增至75%,原来椎管越是狭窄,椎管正中矢状径增加越甚,狭窄的椎管有自发性塑型和重建现象,即椎管内骨块可随时间延长而部分吸收。Mohanty等[12]对45例胸腰椎爆裂性骨折的分析表明,椎管重塑与神经损伤及恢复之间无相关性。
从以上的生物力学研究中可得出以下结论:1)椎间盘纤维环及后纵韧带在椎管内骨块复位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2)后纵韧带在骨块复位的早期起主要作用,纤维环在此期起次要作用。3)椎间盘纤维环在骨折块的后复位期起主要作用。4)在整个复位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叠加作用。5)当后纵韧带或纤维环损伤时,只要其中之一保持完整,充分的纵向拉伸力仍可使椎管内骨折块获得较好的复位。
4胸腰椎爆裂性骨折的非手术治疗
对于胸腰椎爆裂性骨折,笔者认为首先应重视体位复位与功能锻炼,目前多使用体位复位的是骨盆牵引与脊柱外固定支架,牵引重量多在10 kg,使前纵韧带紧张,使骨折在肌肉和韧带的紧张下完成复位的第一步,功能锻炼常用仰卧位锻炼法和俯卧位锻炼法。
5胸腰椎爆裂性骨折的手术治疗方法
胸腰椎爆裂性骨折手术治疗前主要步骤:一是复位,进一步恢复压缩椎体的高度和脊柱正常序列;二是充分有效的椎管减压,为脊髓或神经的恢复创造条件;三是固定,即重建脊柱的稳定性;四是融合。
5.1后路入路后路手术的指征包括:1)伤椎前缘高度丢失不超过原椎体高度的50%。2)椎管占位在T12及以上<35%,L1~3<45%,L4及以下<55%。3)外伤距手术时间1 d以上。4)骨折伴脱位或多节段相邻椎体骨折。
5.2椎体侧前方入路从损伤较重的一侧入路,在横突根部与小关节外侧缘交界处切除椎弓根和椎体后外侧骨质,从侧后方显露出硬脊膜,用神经剥离子探查椎管内硬脊膜前方受压的情况。如果是较小的骨片或碎裂间盘组织,用钳子夹出,较大的骨折块则用弧形凿切除,深度达椎管对侧,使硬脊膜充分减压,椎间取髋骨或肋骨植骨,从后路行鲁克棒内固定[15]。一般认为侧前方入路手术指征为:1)脊髓损伤后有前脊髓综合征者。2)有骨片游离至椎管前方的严重爆裂性骨折或陈旧性爆裂性骨折伴不全瘫者。3)后路手术后前方致压缩未解除者。4)前方致压的迟发性不全瘫者。总之,不存在一种能适合所有爆裂性骨折的定式手术,脊柱后路手术开展较早,技术较为成熟;而前路手术因解剖结构复杂,创伤较大,开展相对较晚。一般认为,胸腰椎爆裂性骨折手术人路的选择取决于骨折的类型、骨折部位、骨折后时间及术者对入路的熟悉程度。
6胸腰椎爆裂性骨折的临床分析
现代胸腰椎爆裂性骨折的治疗,往往根据DENIS三柱理论,并以CT、三维重建和MR等影像检查来指导临床。胸腰椎爆裂性骨折,根据损伤程度可以分为稳定和不稳定型两种,Altas[13]将不稳定脊椎爆裂性骨折CT表现概括为:1)椎管移位。2)椎体压缩高度超过50%。3)附件骨折。4)椎弓根间距增宽。Been[14]把下述小关节变化定为不稳定:1)椎体半脱位伴小关节前绞锁。2)椎体侧脱位伴小关节外侧脱位。3)急性脊椎后凸畸型伴椎体轻度半脱位及小关节脱位。Willen[15]等分析了8例椎体爆裂骨折的尸体标本,根据尸检病理表现对照相应的X线征象,在Denis分类的基础上判断其稳定程度:Denis A、Denis B型属稳定性;Denis D伴有小关节移位的Denis B属不稳定型,并经病理得到了证实。对于不稳定型爆裂性骨折治疗的主要目的是稳定脊柱,预防畸形的发展,消除疼痛,并防止神经系统的并发症。对于有神经损伤的爆裂性骨折一般需行后路减压,复位植骨融合术。对于稳定型损伤的患者是否需要手术治疗,目前意见乃不一致。对于有神经损伤的患者提倡手术治疗,有行侧前路,后路两种方式。以后路首选,如果只是行椎弓根螺钉固定,只是恢复了后柱的稳定性,其前屈压缩刚度乃较正常标本减少41.9%,说明其前中柱仍然存在力学缺陷,随着椎体成形术(PV)技术的发展,聚乙烯咔唑(PVP)和聚乙烯吡咯烷酮(PVK)技术表明聚甲基丙烯酸甲酯骨水泥(PMMA)和磷酸钙骨水泥(CPC)模仿VP可以恢复椎体强度,同时CPC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生物活性和骨传导能力,是继PMMA后恢复椎体高度的理想材料,林宏[16]等研究认为对于胸腰椎爆裂性骨折利用KP经后路撑开骨折锥体,恢复锥体高度后加以固定并经椎弓根向锥体内注入CPC,临床治疗20例胸腰椎爆裂性骨折,术后都有良好恢复,后凸cobb角平均恢复11度。
胸腰椎爆裂性骨折的治疗不管从理论上还是从临床上都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其研究方向也从原来的宏观领域发展到了微观领域,手术入路还有很多争议。内固定系统也从原来的AO理论发展到BO理论,随着对脊柱生物力学的研究,CO理论在指导内固定系统的发展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同时也将指导爆裂性骨折的新的分类、治疗和护理,从而还胸腰椎爆裂性骨折患者一个崭新的明天。
[1]Holdsworth FW.Fracture,dislocations and fracture dislocations of the spine[J].Bone JointSurg,1963,46(1):6-15.
[2]DENIS F.Spinal instability as defined by the three column spine concept in acute spinaltrauma[J].Clin Orthop Relat Res,1984,(189):265-276.
[3]BǎHLER L.Die techniek deknochen bruch behandlung imgrieden und imkreigen in German[J].Verlag von W ilhelm Maudrich,1930.
[4]张光铂,李子荣,张雪哲.胸腰椎损伤的综合分类与治疗[J].中华外科杂志,1989,27(2):71-74.
[5]金大地,杨守铭,于娜沙.胸腰椎骨折分类及病理形态特点[J].中华外科杂志,2000,38(11):811-814.
[6]池永龙,毛方敏,林焱.胸腰椎骨折分类及病理形态特点[J].中国脊柱脊髓杂志,1999,9(5):253-255.
[7]饶书城.脊柱外科手术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3:202-206.
[8]Tran N T,Watson N A,Tencer A,etal.Mechanism of burst fracture in the thora-columbar spine[J].The effect loading Rate Spine,1995,20:1984-1988.
[9]杨欣建,王正国,朱佩芳.胸腰段脊柱爆裂骨折瞬态损伤机制及节段稳定性研究[J].中华创伤杂志,1999,15(2):103-106.
[10]Pan jabiM,Kifune M,Wel L,et al.Dynamic canal encorachment during thora-columbar burst fracture[J].JSpinal Discord,1995,8(1):39-48.
[11]De klerk LW,FontijneW P,Stijnen T,etal.Spontaneous remodeling of the spinal canal after conservativemanagement of thoracolumbar burst fractures[J].Spine(Phila Pa 1976),1998,23(9): 1057-1060.
[12]Mohanty SP,Venkatram N.Does neurological recovery in thoracolumbarand lumbar burst fractures depend on the extent of canal comprom ise[J].SpinalCord,2002,40(6):295-299.
[13]Atlas SW,Regenbogen V,Rogers L F,et al.The radiographic characterization of burst fracturesof the spine[J].AJR Am JRoentgenol,1986,147(3):575-582.
[14]Been H D.Anterior decompression and stabilization of thoracolumbar burst fracture by use of the slotzielke device[J].Spine,1991,16(1):70-77.
[15]W illen JA,Gaekward U K,KakulasRA.Acutebuste fractures:a compar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a modern fracture classification and pathologic finding[J].Clin Othop,1992,276(8):169-178.
[16]林宏,李子泉,秦方先,等.胸腰段脊柱爆裂性骨折[J].川北医学院学报,2002,17(2):45-47.
R683.2
:A
:1008-4118(2013)01-0085-03
10.3969/j.issn.1008-4118.2013.01.44
2012-12-05
常锐(1977-),男,汉,山东巨野县人,巨野县人民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青岛大学医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创伤骨科、脊柱外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