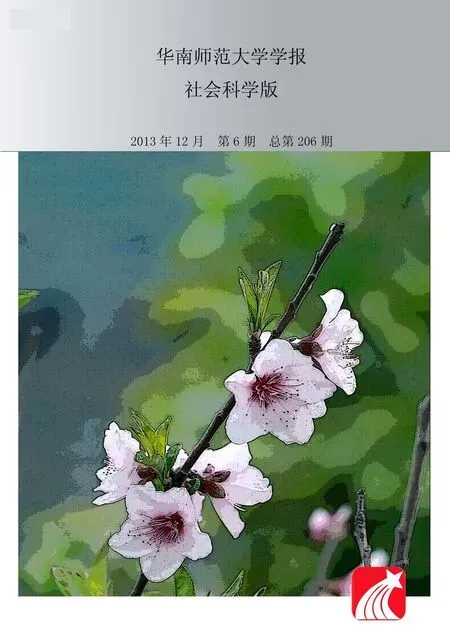视觉的气质——中西方艺术思想的共通与其影响下的绘画艺术
徐 强
(厦门大学 艺术学院,福建 厦门361005)
中西方的艺术对于精神无限自由超脱之“气”的追求和宇宙有限物质真实之“质”的探究在精神上是一致的。从大的方面看,都是对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的揭示和表现。艺术应该是有血有肉的,它本身就是一种生命,一种由大自然和人共同创造的、像大自然和人一样有着丰富多彩的精神内涵的生命。形式是载体,艺术精神才是重要的、本质性的。正如黄宾虹所说:“画之形貌有中西,画之精神无分乎中西也。”①黄宾虹:《虹庐画谈》,第65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年版。
一、气质概念的引入
中国古代人透过“气”来理解世界,气是遍布宇宙天地的客观存在,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是万物的本源,万物是气的不同存在方式,万物又因为气的属性而归于同一。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二章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在老子那里道即是气,是万物的基始。庄子《知北游》中曰“通天下一气耳”。气是一切处于运动中的原动力。体现在气中的宇宙观对中国艺术产生了巨大影响,艺术家以天地之气运,人身之气血,两气相求为根基,融合对自然宇宙、人生感悟、时间意义、永恒之觉悟,超脱于外象,进入天人合一、物我两忘之艺术境界。在潜然默化中把不可言传之“悟”,借可视形象表现出来,重要的并不在具体的某事某物、某情某景,而在于以此表现出的精神和生命脉动,这是中国美学的基础。离开了对“气”的理解和运用,就无法把握中国艺术精神的实质。
在中国古代,对“质”的理解是由“气”衍生出来的,统一在气的笼罩和贯通中,是有形的、具体的、可以被视觉直接看到的客观存在的气的凝结。在《易纬·乾凿度》中阐述了形质的生成与气的关系:“夫有形者生于无形,则乾坤安从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未相离,故曰浑沦。”气和而成质,质是万物的基始,个体是“气和之质”。
其实,西方古代思想史上也出现过与中国“气质”观念相通的理解,在很早就提出以一种基始物质作为万物之本的原思想。在古希腊,阿那克西曼德提出万物始于没有边缘、无定形、无定状的“无限”。这一混沌的设想与中国的“气”在内涵上很相似,不过“气”的概念更感性,更生动,更容易被理解。还有,伊奥尼亚学派的泰利士把“水”看作是万物的基始,郝拉克利特认为“火”是万物的基始。这些原始朴素的思想使我们看到,在思想的开端上对宇宙和世界的看法是多么相近。不过在理性精神的指引下,西方的宇宙观发生了转向,转向了深邃的理念世界;直到19世纪末非理性思潮的崛起,才又开始向中国的“气质”观靠拢。
二、视觉真实的理解
人类天生就具有对事物穷根究底的本性,西方理性精神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更证明了这一点。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再到古典主义,西方绘画总体特征是以逼真的、惟妙惟肖的立体写实为追求的目标。这是由西方人对视觉真实的含义理解所决定的。西方传统上把认知对象放在认识者之外进行,作为观察者的人对“视觉”的理解只是确定其为感知外界的功能而已,这种理解被机械地固定下来后,剩下的是对视觉真实向纵深方向探究。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黑格尔在其《美学演讲录》中阐述了他对视觉真实的理解:“艺术的功用就在使现象的真实意蕴从这虚幻世界的外形和幻相之中解脱出来,使现象具有更高的由心灵产生的实在。”①[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第12页,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西方艺术一直以来把“真实”放在第一位,认为“真实”是靠眼睛的器官功能像照相机镜头那样把外界的事物即所谓的现象挪入我们的认知当中去。这种把主客观割裂的认识与中国主客一体的一气以贯之的思想有很大的不同。西方艺术发展到塞尚,开始对视觉的真实提出质疑。塞尚说:“我确实感到,前辈大师们过去所画的户外景物都被表现得含糊不清,它们给我的感觉是不真实的,首先,是不具备大自然所提供的原来面貌。”②[美]奇普:《艺术家通信——塞尚、梵高、高更通信录》,第7页,吕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塞尚对视觉的质疑是革命性的,震动了整个欧洲,席卷了整个世界,成为现代主义的开端。
在中国“气质”观的引领下,中国人对“视觉”的理解要宽泛得多,“视觉”在汉语造字时就有“心见之觉悟”的含义。中国艺术精神的特征是内外统一的、物我合一的。这表现为通过眼睛把外在的事物和内在的我合而为一,甚至是进入忘我的虚己以待物的艺术之境。这种对视觉的理解在中国人看来是很自然的,并不需要理性的论证和逻辑的思辨。清初画家石涛在他的《苦瓜和尚画语录》中对视觉真实作出了具有他个人语言色彩的论述,他认为视觉真实是一种“受”,是大“受”,而眼见的只是“识”。在《画语录》第四章中写道:“受与识,先受而后识也,识然后受,非受也。古今至明之士,借其识而发其所受,知其受而发其所识,不过一事之能,其小受也,未能识一画之权而大之也。……如天之造生,地之造成,此其所受也。”在这里,石涛贬斥的“小受”,可以认为是指西方传统艺术中摹仿和再现性的以描摹外部真实为特征的艺术。他所说的“如天之造生,地之造成,此其所受也”与塞尚的“让自然在自己身上说话,自己完成”③焦小健:《塞尚晚年绘画研究》,载《新美术》2007年第3期。相互印证。
三、视觉的气质
绘画是种视觉艺术形式。视觉的真实在气与质的聚散、绵延和隐显中得以呈现在自由自在的艺术生命之中。
(一)视觉气质的聚散与形神兼备
在绘画的艺术处理上,如何在气与质之间架起一座往来自如的桥梁呢?
“形”是质的外显形式,是气聚的结果;“神”是自由飘逸之气的本来面目,是气散的方式存在。气聚、气散是一种同时的存在,归于一气。中国古代绘画理论很早就指出“形神兼备”这一艺术处理方法和要求,即形质与神气的统一;而形是可见的、可以被感知的,神是不可见的、不容易被把握的,但是是可以通过心见之觉悟去靠近。所以,东晋顾恺之提出了“以形写神”、“传神写照”。这里,形质是手段,神气是目的,以形质来体现神气的聚散与合离。
“形神兼备”是一种辩证的统一,揭示出中国视觉艺术中气质观的深刻影响。在绘画艺术中形离不开神,神也离不开形,应该是以形写神,神藏于形。首先,形是神的外在面貌,气聚而成万物是气运动的客观必然,如果轻视形、取消形,神就无所依托,就不能够创造出传神的艺术作品;其次,神是形的内在追求,忽略了绘画中神气的表达,一味追求形似,就会创作出毫无生机的匠气之作。
“形神兼备”的最终效果即艺术之“真”,这也是视觉气质的聚散在绘画中的必然结果。五代画家荆浩在《笔法记》中说:“似者得其形而遗其气,真者气质具盛。”在视觉气质的滋养下,绘画以其视觉的方式追求着无限的自由和最终的真实。正如萨特所说:“总而言之,我看到的是蜂拥般的内聚,骚动般的弥散,就让画家去描绘吧!”①[法]萨特:《萨特论艺术》,第71页,欧阳友权、冯黎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二)视觉气质的绵延与气韵生动
中国艺术的精妙之处就在于“气”的轻松弥漫、鼓荡纷呈、诗意的永恒流动中。这种流动在西方哲学家柏格森那里被称为“绵延”。这种“绵延”致使艺术世界充满生气,于鲜活的感觉中体会到意味弥远。这种超越时空的生命节奏感成了中国艺术精神的生命特质。
视觉气质的本质就在于绵延的“动”之中。动是生命的特征,也是艺术的精神核心,是时空一体的气与质的没有清晰界限的相互融合、相互渗透。艺术起源于生命之“动”。中国传统艺术把外在的如山岳、水流、云雾等的生命节奏与人生和生命深刻体验之脉动合而为一,是内外合一的“动”,一切都处于绵延之“动”中;视觉气质在气息绵延的引导下,表现为空间的“动”。这就使空间呈现开放,无从封闭;这种开放又是连续的,不可分割、没有停顿,这种空间是时间性的空间。宗白华说:“我们的空间意识的象征不是埃及的直线甬道,不是希腊的立体雕像,也不是欧洲近代的无限空间,而是潆洄委曲,绸缪往返,遥望着一个目标的行程(道)!我们的宇宙是时间率领着空间,因而成就了节奏化、音乐化的时空合一体。”②宗白华:《美从何处寻》,第102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视觉气质的绵延又体现在“游”之中,这是富有灵性和诗意的中国传统智慧在创作和审美中的运用,解决了时间与空间、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矛盾,是化时空、主客为一体,没有分别,没有间隔的“游”。中国古代的文人画家以悠游的心态澄怀观道,徜徉于时空之河的绵延之中。视觉气质之游无挂无碍、自由自在、物我两忘地穿梭往返于心内像外、时间空间之中,这是俯仰自得、游心太会、目即往还、心亦吐纳的艺术之境。如此精神获得了无尽的自由和超脱,并展示出宇宙世界的本来面貌。南朝谢赫提出绘画六法,又把“气韵生动”置于六法之首,从此“气韵生动”成为中国绘画艺术的最高标准和最终追求。“气韵生动”在视觉艺术的范畴内我们理解为时空一体的视觉气质的绵延之动,这符合中国独特的宇宙观和生命情趣,也可见气质观影响下中国艺术对气的生命节奏的追求。“气韵”是指宇宙生命的生命节奏,“生动”是指生生不息的视觉气质的绵延之动,“气”“质”的相辅相成造就了气韵生动的艺术效果。恽寿平在《瓯香馆画跋》中云:“气韵藏于笔墨,笔墨都成气韵。”好的绘画艺术作品是视觉气质的自然流溢。
总之,生命之“动”是宇宙的真相,生命本体创造不已,流动不息,悠游于万物中的“气”引领着这绵延之动,是生生不息的视觉气质的表现形式。
(三)视觉气质的隐显和虚实相生
西方早在古希腊时期,原子论者就认为在“实”即“有”和显现的存在之外,尚还有“空”即“无”和非显现的存在,它同样是构成万物的主体。在古代西方思想中对于实在客观的显现的思索用力很多,而对于“虚”“无”的非显现存在的认识只是偶尔闪亮的思想火花,所以西方古代到近代的艺术面貌是质实而不虚的再现性艺术。
中国艺术精神对气的理解,反映在对虚的重视上。《庄子·人世间》中说:“气也者,虚以待物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庄子所谓“虚”,是要人们摒情去智,洞忘物我,其目的是积极地虚怀纳物,以应无穷。在中国艺术思想中,不是一味求隐蔽的“虚”,还同时兼顾显现的“实”,这也是由视觉气质的内涵所决定的。对于这视觉气质的隐显以“虚实相生”作为认识的手段和创作的方法,视觉气质的存在形式是虚以隐、实以显的共同存在,虚实相互转化、相互包容,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中有实在于以万物之有的实来对虚的隐蔽效果进行深入描绘,目的是“虚”;而实中有虚就在于“实”有对“虚”的心理暗示能力,因为人的直觉想象具有时空的穿透力,表现为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艺术效果,表现出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虚实相生”的重点在虚,中国绘画艺术是以重虚为特征的,“虚以涵实”是中国艺术的精髓,以虚运实,有中生无。中国古人用智慧洞悉了模糊、混沌的理解要比明晰的概念更富有表现力。这种模糊只能通过意会来体验,“虚”也就成为最活泼的生命之源。
通过近代西方绘画艺术的发展,我们也看到西方绘画艺术由实向虚转变。如果用中国“虚实相生”的道境来体察,莫奈、塞尚、贾科梅蒂等许多绘画大师的画面无不体现了这虚实相生之道。如莫奈晚年的《睡莲》系列作品,是直面自然的写生,画出了飘渺的互隐互现的朦胧诗意;而氤氲的气机交错是塞尚晚年众多的《圣维克多山》写生作品的突出特点,在他的画中,物质的实有消解为本然的空灵状态,化入浑然一体的视觉直观的混沌之中。
四、视觉气质在绘画艺术中的实践意义
视觉气质的艺术实践意义,在于他的感性特征和其巨大的包裹性。
首先,视觉的气质是感性的。艺术的真实靠的是视觉的本质直观,这个直观在20世纪影响最大的哲学流派——现象学看来即回到事物本身,回到原初实在的直接性,并以此为严格的出发点去介入实在,投入到归于一气的生命本体的艺术创造之中。中国的艺术气质观在视觉的心之妙悟的前提之下,气与质在艺术创造与审美的过程中“神会”和“迹化”,艺术家在瞬间的顿悟中进入“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悠游的澄明境界。这种“神会”是“气”“质”交融的至高境界,必将产生“迹化”,创作出可遇而不可求的“逸品”和“神品”的绘画作品。在视觉艺术中“气”与“质”是视觉直观活动中最活跃的、最基本的因素。塞尚晚年时说:“我想让你明白的是一些更为神秘的东西,它更为错综复杂地盘绕在生命的根源之中,聚合在不可捉摸的各种感觉的源头。不过我认为就是它,这神秘之物,构成‘气质’。也正是这最本源的力量,即‘气质’,能够引领一个人朝着他的奋斗目标前进。”①许江、焦小健编:《具象表现绘画文选》,第10页,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其次,视觉的气质具有最大的包裹性。“气质”无所不在,无所不包,贯通一切。视觉的“气质”既是精神的,又是物质的;既是主体的,又是客体的;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既是空间的,又是时间的。表现为既是凝聚的,又是弥散的;既是运动的,又是静止的;既是显现的,又是隐蔽的。中国艺术精神在绘画这一视觉艺术领域里也体现于“形神兼备”、“气韵生动”、“虚实相生”之中。
从当今来看,中国和西方的绘画都在寻找出路。西方当代绘画在塞尚的现代主义启蒙之后,经历了抽象主义的两个极端,即对“气”的盲目狂乱的使用的抽象绘画和完全忽略“质”的、纯主观的理性神秘主义的抽象绘画。前者的典型是以波洛克和德库宁为代表的抽象表现主义绘画;后者的典型以罗斯科和纽曼为代表的极简主义绘画。抽象艺术在走了几十年后,就无法再走下去了,因为其在传统的再现性艺术之后,对视觉真实不愿作深入的理解,以致走向纯粹个人的情绪宣泄或理性游戏,后来被缺乏真情实感、故弄玄虚、病态的歇斯底里的后现代主义所取代。这些都不符合视觉气质的本质含义,走向忽略视觉真实的极端,也背离了生生不息的生命本质意义。当然,西方当代也有一些了解了视觉气质本质含义的画家,并对艺术的发展作出贡献,如贾科梅蒂、莫兰迪、阿利卡、巴尔蒂斯、弗洛伊德等画家。虽然他们都有各自的艺术主张,但他们在坚持具象的视觉真实的前提下,进一步追求那自由超脱的无限,他们在视觉气质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必然会留存于绘画史上。而中国绘画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学习西方后,在领略了西方传统艺术对视觉真实的“质”的探究及现代艺术和后现代艺术的冲击后,对视觉气质的意义在实践领域中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和领悟,同时也更意识到中国艺术精神的丰厚营养需要我们去挖掘和发扬。
我们应该综合中西方艺术精神的精粹,以中国人的中庸智慧去理解视觉气质的本质含义,在抽象和具象之间、物质和精神之间、人与自然之间找到自己绘画实践的根据地,使绘画作为视觉艺术的形式的精华在当代人类精神生活中做尽可能大的承担,成为人精神上的栖息地,并开创一条生生不息的道路,启示人们去领悟和接近生命意义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