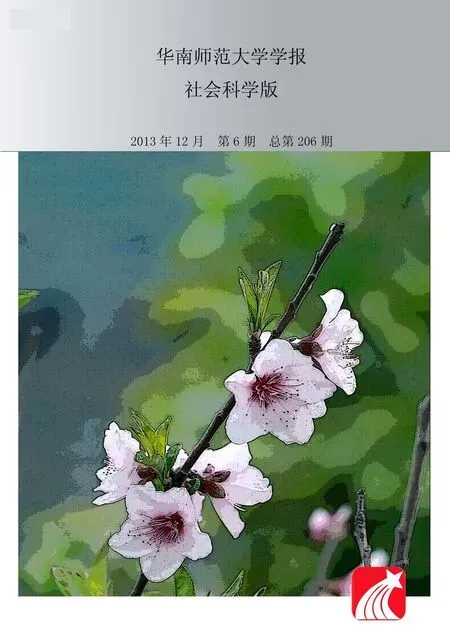现代艺术的孤独
种 海 燕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现代艺术是孤独的。孤独既是现代艺术作品的普遍主题,也是现代艺术家及艺术品的存在状态。
一、从显赫走向孤独
艺术曾经是亲和的、显赫的、神圣的。在前现代社会,艺术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首先,艺术是无可替代的历史记录者。诗歌、绘画等传统艺术形式既是自然与生活的记录者,也是时代风云的记录者。人们通过史诗记录民族的历史,通过诗和画定格英雄和盛会。德国画家阿尔布雷希特·丢勒1502年所画的水彩画《野兔》是那个时代令人叹为观止的杰出画作,画家惟妙惟肖地记录了野兔的每一个细节。直到19世纪,绘画还一直担当着历史事件记录者的不二角色。“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四世从未怀疑过,当他的军队取得一场辉煌的胜利时,他的宫廷画家委拉斯开兹是纪念这一胜利的最好人选。当马拉于1793年在浴室里被谋杀时,几乎应普遍的要求,雅克-路易·大卫不失时机地画出了《马拉之死》这幅画。1834年,伦敦的议会大厦被烧塌后,艺术给我们描绘了最令人难忘的场面,透纳用艺术形式描绘了现场直冲夜空的熊熊大火。艺术在这样的场合是无可匹敌的,它给我们提供了别处无法得到的感受。”[注][美]约翰·拉塞尔:《现代艺术的意义(上)》,第3页,常宁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其次,艺术与艺术家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具有极为广泛的影响力。一篇优秀的文学作品问世,人们竞相传抄,一时洛阳纸贵。孔子收集民歌以了解民风;新乐府借“惟歌生民病”的诗歌达到讽喻君王的目的;李白以诗名直接得以进入仕途;宋高祖因担心李后主后期词作的影响而起杀心;柏拉图要把诗人从理想国中驱逐;卢梭和达朗贝尔为日内瓦是否该建立剧院激烈论证……所有这些事件或者现象都有一个潜在的前提,即艺术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人们喜爱艺术,理解艺术,崇拜艺术,因此艺术家才显得如此重要,艺术才会对社会产生直接的、深刻的、长远的、正面或者负面的影响。
最后,艺术具有崇高的地位。柏拉图认为诗非人力所能为,是诗人借助神灵凭附的神力所创造的。帕斯卡尔坚信上帝是美的根源。李白被称为“谪仙”,有文采的作家被看作是文曲星下凡。
然而在现代艺术中,艺术的上述特征都消失了。艺术不再是社会的中流砥柱,它退出了普通人的生活,那些曾使艺术居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与特质,如记录、讽喻、揭示真理等,都几乎消失殆尽了。艺术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弱。这是一个诗人无名的时代。纵使屈原复活,也很难想象,今天的人们会为一位诗人的离去而举国悲痛,并把这种悲痛世代传承。孔子说:“不读诗,无以言。”然而今天还有多少人读诗呢?诗人、读者以及诗歌的魂魄已经乘着田园时代的牛车和牧笛远去了。这是一个艺术退出普通民众的生活与生命的时代。优美也罢,崇高也罢,荒诞也罢,艺术作品的美的韵味总是需要人们的停留和细细品味。然而,这种驻足、停留在“时间就是金钱”的今天变得奢侈,人们普遍没有时间放慢生存的匆匆脚步,更不用说审美的、无功利的虚静心态了。艺术,越来越像一个美好但却虚幻的梦,远远地游离在不可触摸的远方。传统艺术形式是这样,现代艺术形式同样如此。而且,现代艺术形式上的晦涩难懂、理念上的荒诞艰深,使很多受众知难而退或难以认同,艺术的受众范围越来越小。从杜尚起,现成的生活用品、工业制品被变成了所谓的“装置艺术”,小便池堂而皇之地变身为艺术,艺术被日常生活化,彻底“从被人顶礼膜拜的神圣殿堂和墙壁上走下来并融入世俗生活”[注][美]金·莱文:《后现代的转型——西方当代艺术批评》,第18页,常宁生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艺术的神圣、崇高消失殆尽。
二、现代艺术孤独意识的成因
现代艺术为什么会走向孤独?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被动的,源于现代技术的冲击、消解。比如,现代社会以技术的新闻影像取代了传统艺术的记录功能。现代人已经无法体会16世纪的人们面对丢勒的《野兔》所感受到的震撼,以及对画家辛勤劳动所产生的敬意。因为今天,人们可以按下快门,轻易地在瞬间做到同样的毫发毕现。在重大的历史场合,艺术无可匹敌的地位也被取代,报纸等纸质大众传播媒介以及新兴的电子影像具有更逼真的复现效果、更快捷广泛的传播效应。
另一方面,这也是现代艺术的自我选择。贡布里希在《艺术的故事》的卷首写道:“实际上没有艺术这种东西,只有艺术家而已。”那么,现代艺术家为什么要选择孤独呢?
毋庸置疑,现代艺术家常常是孤独的。他们总是落落寡合:有些人离群索居,艺术成就在生前得不到承认;有些人漠然于外界的评判与喧嚣,备受褒扬却自觉抑郁、孤立无援,所以现代艺术家中自杀和患有精神疾病的比例非常高。现代社会早期的浪漫主义首开这种孤独之风。卢梭、华兹华斯都隐居乡间,反对现代都市文明,质疑理性和进步,自称 “一个孤独的散步者”、“一朵孤独的云”。现代绘画早期的印象派画家中,塞尚近四十年的艺术生涯始终伴随着偏见、嘲笑与攻击;高更与家庭和社会决裂,孤身前往南太平洋中的马提尼岛过原始生活,在贫困中终其一生。现代艺术家的这种孤独,最初可能是生活所逼,而他们后期孤寂的生命状态,则主要是自我选择的结果。为什么要做这种痛苦的选择?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孤独有助于艺术家进入沉思的创作状态
华兹华斯喜欢用‘Solitude’一词来表达孤独带给他的令人愉悦的感受,因为“在退隐生活中,想像力最自由也最富有创造性;回到孤独的人物——他的环境的观察者,因为他周围没有人能够使他分心”[注][英]安德鲁·桑德斯:《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下)》,第46页,谷启楠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卡夫卡说:“为了我的写作我需要孤独,不是‘像一个隐居者’,仅仅这样是不够的,而是像一个死人。写作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更酣的睡眠,即死亡,正如人们不会也不能够把死人从坟墓中拉出来一样,也不可能在夜里把我从写字台边拉开。”海明威更是把孤独状态与作品的永恒内涵联系起来,他在《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的书面发言》中谈道:“写作,在最成功的时候,是一种最孤寂的生涯。作家的组织固然可以排遣他们的孤独,但是我怀疑他们未必能够促进作家的创作。一个在稠人广众之中成长起来的作家,自然可以免除孤苦寂寥之虑,但他的作品往往流于平庸。而一个在岑寂中独立工作的作家,假若他确实不同凡响,就必须天天面对永恒的东西,或者面对缺乏永恒的状况。”但是,如果独处和沉思只是为了有利于艺术创作的话,为何现代艺术家普遍在创作状态之外,仍然坚持甚至沉湎于孤独状态呢?为何孤独意识独独在现代艺术家群体中表现得格外突出? 显然,还有更深刻的原因。
(二)个体意识的觉醒
在前现代文化中,人的个体地位往往会被忽视。雅各布·布克哈特指出:“在中世纪,人类意识的两方面——内心自省和外界观察都一样——一直是在一层共同的纱幕之下,处于睡眠或者半醒状态。这层纱幕是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织成的,透过它向外看,世界和历史都罩上了一层奇怪的色彩。人类只是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党派、家族或社团的一员——只是通过某些一般的范畴,而意识到自己。”[注][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125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运动消除了这层迷雾,使“承认人的个性具有天然合法性”这一现代性思想深入人心,个体意识建立起来。“假如我们忽略那些先驱者,那么,对17和18世纪古典派的反抗就是始于卢梭。人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一种个人主义的复兴,同时也可以看到浪漫派的肇始,因为,个人主义是浪漫的起点和它首要的定义要素。”[注]刘小枫:《诗化哲学》,第24页,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被称为“浪漫主义运动之父”的卢梭对于现代艺术个体意识的确立的确功不可没。卢梭的作品大都带有自传特点,其文学创作中的男主人公身上都带有卢梭自己的影子。他和他作品中的主人公(限于男性主人公)几乎都有自我中心、自我崇拜和自我赞扬的倾向。在卢梭的笔下,他们纯洁、真诚的品格使他们总是与周围的社会环境处于敌对的状态。因而,这些作品的中心任务就是表现“自我”与整个周围环境的冲突,表现他们如何在这种对立中去追求自由、平等和自我的尊严。卢梭很自负地声称,自己虽然并不比别人好多少,但一定是与所有人都不同的一个。这种对于独特性的承认和肯定给他的思想和作品定下了基调,也给后来的浪漫主义定下了基调,影响了后来的浪漫主义乃至整个现代艺术。
现代艺术这种凸显自我的特点一方面是历史的进步和必然;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它的两个问题。一是像白璧德批评的那样,过于强调个体独特性,成为浪漫主义的一个不良特征。二是沉迷于自我的心灵体验,走向自我封闭的小圈子。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言:“传统的现代主义试图以审美对生活的证明来代替宗教或道德;不仅创造艺术,还要真正成为艺术——仅仅这一点即为人超越自我的努力提供了意义。但是回到艺术本身来看,就像尼采明显表露的那样,这种寻找自我根源的努力使现代主义的追求脱离了艺术,走向心理:即不是为了作品而是为了作者,放弃了客体而注重心态。”[注][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98页,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
(三)现代艺术反叛思想和批判精神的需要
现代艺术具有浓重的叛逆思想和批判精神。贡布里希认为创新是西方艺术的传统,因此“西方艺术的故事就是无休止的实验的故事,就是追求前所未见的新颖和独创效果的故事”[注][意]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第8页,范景中译,广西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这种追求创新的传统在西方现代艺术中发展到极致。现代艺术质疑一切权威和规则,反形式,反理性,反文明。文明、城市以及现行的生存方式都是现代艺术家所不能接受的,都成为他们的批判对象。一个游离于社会边缘的他者显然更能看清社会和人生,批判现实和历史。因此,现代艺术家主动选择远离主流世界,冷眼观望,大胆质疑。艺术家与同时代的人们发生激烈的冲突,在他们看来,当代社会是黑色的、冷漠的、荒谬的,既然“他人即地狱”,独处聊胜于群居。卢梭说:“当一个人不愿成为奴隶时,他就必然要求离群索居,独来独往。”[注][法]卢梭:《卢梭自传》,第159页,刘阳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他在1762年写给马勒赛尔伯的信里写道:“我在世上活了四十年,对自己和别人都感到不满。”“我蔑视我的时代和我的同代人,并且感到我在他们之间根本找不到一种能宽慰我的心的境遇,渐渐地,我的心与人们的社交活动疏远了。”[注][法]卢梭:《致德·马勒塞尔伯先生的信(1762年1月12日)》,见《卢梭自选书信集》,第63页,刘阳译,译林出版社1997年版。因此,他通过远离都市、远离权力中心、远离主流思想的自我放逐,使自己成为“他者”,从而使自己具有和同时代其他思想家不同的、更为自由的视角和更为彻底的批判性。
因此,真正伟大的现代艺术家总是处于孤寂当中,这是因为他们为了保持独立性和自由的批评立场而把自己主动放逐到社会边缘。因此,他们必然是所在社会主流政治力量和文化力量的“圈外人”、“边缘人”和异端分子,是永远的流亡者。“对于受到迁就适应、唯唯诺诺、安然定居的奖赏所诱惑甚至围困、压制的知识分子而言,流亡是一种模式。即使不是真正的移民或放逐,移民或放逐者的思维方式,面对阻碍却依然去想象、探索,总是能离开中央集权的权威,走向边缘——在边缘你可以看到一些事物,而这些是足迹从未越过传统与舒适范围的心灵通常所失去的。”[注][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第57页,单德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作为知识分子的现代艺术家们正是以这种“走向边缘”的途径获得新的视角和理论高度,获得独立与自由的空间。
现代艺术家的孤独状态同样也体现在现代艺术作品中。孤独是现代艺术作品的普遍主题,与它萦绕在一起的还有忧郁、绝望、幻灭、虚无。1898年高更在自杀被人救起后创作完成了他最重要的作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这个独特的标题也是所有现代艺术的共同追问。然而只有问号,没有答案。在这幅画的画面后景部分站立着一位“偶像”,这是高更心目中的“超现”(beyond),象征着人类灵性的追求。高更在一封写给评论家丰泰纳的信里说道:“画里面的偶像不是一种具体的表白,而是一个雕刻,但不像野兽那么冰冷,也不很凶暴。在我的梦中,它与我茅屋前的整个大自然融为一体,主导着我们原始的心灵。就我们的起源和那神秘的未来而言,它包含着模糊的和不可理解的因素。它对我们的痛苦是种假想的安慰。”是的,它只是一种假想的安慰,一如浪漫主义者和自然主义者笔下的“自然”、贝克特戏剧中的“戈多”、席勒的“完整的人”、波伊斯的“上帝”,只是能够提供短暂的麻醉和镇痛效果的安慰剂。
三、自我封闭的救赎悖论
在神学退去了神圣光环之后,艺术曾被寄予厚望,人们希望它能够担负起救赎的使命。席勒试图通过美和游戏弥合人性的分裂,接近神性的目标。他认为只有游戏,才能使人达到完美并同时发展人的双重天性;审美是沟通感性和理性的唯一途径,要使感性的人成为理性的人,必须首先使他成为审美的人;艺术和审美能够培养感性和理性的整体达到尽可能的和谐。韦伯更是直言艺术具有“世俗的救赎”功能:“在生命的理智化和合理化发展条件下,……艺术变成了一个越来越具有独立价值的世界,它有自己存在的权利,无论怎样来解释,艺术都承担了这一世俗的拯救功能,即它提供了一种从日常生活的刻板,尤其是从理论的和实践的理性主义的压力中解脱出来的拯救。”[注]H.H.Gerth,W.Mills (eds.). From Max Weber: Essay in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342.然而,时至今日,艺术和审美并没有带领迷茫的人们进入“诗意的栖居”。世俗的喧嚣、金钱的狂热、末日的绝望、存在的荒诞,艺术表现、批判、追问这些现代社会的顽疾,但却只能随波而转,徒劳叹息,在孤独和迷茫中继续探寻。
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把“孤独的个体”作为其哲学的本体和研究对象,他说:“人是精神。但是精神是什么呢?精神就是自我。自我又是什么呢?自我是一个与它本身发生关系的关系,也就是说,在它所处的这个关系中,它与它自己发生了关系;因而自我不是关系,而在于一个关系把它和它自身关系起来了这一事实。”[注][丹麦]克尔凯郭尔:《一个诱惑者的日记——克尔凯郭尔文选》,第340页,徐信华、余灵灵译,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在克尔凯郭尔看来,每个个体都是孤独的。这种个体性不是由外部施加的,而是由其自身所决定的。个体的存在就在于其孤独性。因此,每个个体的存在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每个生存个体都必须凭借自我意志自己作出选择。克尔凯郭尔认为,绝望是美学境界的顶峰,也是个体必然遭遇的生存状态。选择绝望是成为精神的必然前提,同时,选择绝望体现了个体的自我意志,也就意味着选择了自己并由此而成为一个伦理的人格。生存个体通过选择自己,选择绝望,从而选择了永恒。这也是现代艺术和艺术家的存在状态。
在这个过程中,现代艺术走向了一个自我封闭的系统。一方面,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艺术家越来越重视个体的心灵体验,走向与现实世界的疏离、走向自我选择的孤独、自闭;另一方面,艺术为了体现实现自身的创新,凸显自己的独特性,艺术内部各门类走向更加细微的分化。格林伯格发现,现代主义艺术作为一场运动有两个分化:一是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区分;二是各门艺术之间的区分。他注意到,每门艺术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边界和特性,“每门艺术都不得不通过自己特有的东西来确定非它莫属的效果。显然,这样做就缩小了该艺术的涵盖范围,但同时也更安全地占据了这一领域”[注]周宪:《视觉文化:从传统到现代》,载《文学评论》2003年第6期。。这进一步割裂了艺术与日常现实及大众的联系。艺术与普通人民的关系越发疏离,丧失了公众的关注。现代艺术的孤独导致救赎使命走向一个无法实现的悖论。自我意识的觉醒使艺术强调独处与沉思,强调个体的心灵体验,追求个性的张扬与卓尔不群;然而,“个体意义的取得必须基于一种大众意识的认同”[注][加]查尔斯·泰勒:《现代性之隐忧》,第59页,程炼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艺术仍须依赖大众的首肯和参与。
孤独是现代艺术的必由之路,曾经给艺术带来创新和力量。同时,孤独也是现代艺术的顽疾,只有当它不再孤独的时候,现代艺术才能发生新的蜕变,开启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