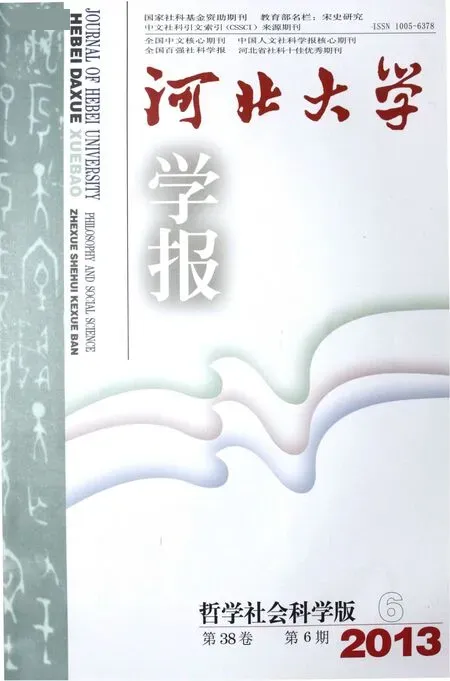从杜威的质疑看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几个问题
张 宛,张 丽
(1.河北大学 教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2.河北大学 管理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现代美国教育家杜威在其著作《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曾对柏拉图《理想国》中反映的治国与教育思想提出质疑。首先,在杜威看来,柏拉图笔下的“理想国”完全是一幅静止的城邦图景,杜绝改变成为维持“理想”的要务。杜威认为,“虽然柏拉图的教育哲学是革命的,但它仍然受他的静止的理想所束缚。……虽然他想根本改变当时的社会状况,他的目的却是建立一个不容变革的国家”[1]101。这无疑使抱持进步主义信念的杜威感到困惑。其次,杜威对于柏拉图将公民依据他们原本的能力分成“有限而鲜明”的阶级不以为然。在他看来,柏拉图尚缺乏对个人的独特性与个性的认识,因而“没有认识到个人和社会群体的活动的无限的多元性。因此,他的观点就局限于几种天赋能力和社会安排”[1]98,结果只能是将个人与个性置于社会安排的从属地位。再次,令杜威感到费解的是,即便在理想国中“生活的最终目的是固定的”,并要根据这一目的来组织并管理国家,可为什么即使是对于城邦中音乐曲调这样“很小的细节”都要进行严格的监管呢?这些疑惑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杜威对柏拉图教育思想的正确理解。
倘若对柏拉图生活时代的特征、流行的历史观以及柏拉图构建“理想国”的基础——“理念论”有所把握,并能从和谐与对立并存、正义与幸福相关联的角度去认识理想城邦与公民的关系,能看到作为“理念之物”的音乐在理想城邦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则杜威的疑惑可一一解开。从而有助于更加客观公正地理解《理想国》中所蕴含的治国理念与教育思想。
一、静态城邦图景的由来
杜威发现,在“理想国”中“真正的现实是不可改变的”[1]101“变革”被视为“非法动荡的证明”,在那里“生活的最终目的是固定的”[1]101。这令持有进步主义信念的杜威感到不解。想要探究这幅静态城邦图景的由来,就需认识柏拉图生活时代的特征、倒退与循环史观及“理念论”在当时的重要影响。
1.时代的特征。要理解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于城邦蓝图的静态设计,首先需了解他所生活的时代之特征。正如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中所谈到的:“希腊人对永恒的追求是极其热烈的追求,正因为希腊人本身对于非永恒具有一种非凡的鲜明感受。他们生活在一个历史以特别的速度运动着的时代里,生活在一个地震和侵蚀以在其他地方罕见的暴力改变着大地面貌的国度里。他们看到的整个自然就是一场不断变化的场面,而人类生活又比任何其它事物都变化得更为激烈。”[2]53柏拉图生活的年代,正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的动荡时期,战争激化了雅典城邦乃至整个希腊奴隶制内部的矛盾,使希腊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因社会的两极分化、频繁的党派斗争、政权更迭和城邦间的对抗而呈现乱世景况。战争使得全希腊的政治秩序、精神生活与道德价值陷入极大的混乱与危机中。正因深刻体会着这些危机,又亲历了恩师苏格拉底被雅典重建的民主政体判处死刑的事实,柏拉图必然渴望建立一种理想的政治秩序,并护卫它,使它在各种剧变的动荡中保持恒久。
2.倒退与循环史观。在杜威看来,柏拉图哲学是存在缺陷的,他认为“柏拉图哲学的失败,……就是他不信任教育的逐步改进能造成更好的社会,然后这种更好的社会又能改进教育,如此循环进步以至无穷”[1]101。
而在这里,杜威无疑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古代与现代历史观的差异十分明显。如果说身处20世纪的杜威眼中的世界是“进步”的,那么,生活在古希腊时代的柏拉图的世界恰恰是“循环倒退”的。就西方史学而言,进步史观是在近代以后才逐渐发展并颇为昌盛的,而在这以前循环观、倒退观占据着主导地位,古希腊、罗马时代就是如此①参见张井梅.16、17世纪历史进步观与西方史学[J].历史教学问题,2008(2).文章指出,这并不是说,古希腊就没有进步观,只是学者对这个问题持有不同观点。古希腊时期,历史观念较为模糊,并未形成后世系统性、有条理的概念,倒退观、循环观、进步观并存,但以前两者为主。另可参阅:祝宏俊.古代希腊进步史观的产生[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古希腊人赫西俄德即是倒退史观的典型代表。他认为,截至他生活的时代,人类历史经历了五个时期——“黄金时代”“白银时代”“紫铜时代”“英雄时代”“黑铁时代”,认为历史是一个逐渐衰微、堕落的过程,从“无忧无虑、尽享天年”[3]70的黄金时代退行至“日间辛苦劳作,夜间受尽侵害”的黑铁时代。在他以后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至亚里士多德都承袭了历史退化的观念,并辅以循环观,勾画历史的演变。“如果可以承认存在某种相对的进步,那么希腊哲学家所持有的普遍观点则是:他们生活的时代必然是退步和衰落的——其必然性在于这一阶段是由宇宙的本质预先设定的”[4]46。这种悲观和退化的历史观,称得上是古希腊历史观的一大特征。
3.“理念论”的阐释。柏拉图是在他“理念论”的基础上描画“理想国”的蓝图的。从理念论出发,柏拉图将世界划分为可见世界与可知世界,可见世界是流变的,可知世界则是永恒不变的理念的世界。作为精神实体的“理念”是柏拉图构建理想国的基石,这座理想城邦中公正和谐、秩序井然的政治生活,正是源自“善”的理念的指引。在柏拉图看来,“善”是万物的本源,是神布置一切时所根据的原则,是一切事物的原因,也是一切事物追求的目的[5]242。“至善”是最高的理念,在这一终极目标的引导下,理想国实现着正义的分工,人们各司其职,各安其位。城邦仿佛一个巨人,具有理性、激情和欲望组成的灵魂,与此三层次对应的便是以智慧、勇敢和节制为特征的三个阶层——哲学王、军人和农工商阶层。各阶层间分工明确,互不僭越,体现着“正义”的要求。其中,哲学王是理性与智慧的代表,是与“善”的理念最为接近的人,自然成为理想国的统治者。依据柏拉图的布划,既然“理想国”已是城邦中的至善,它还能向何处去呢?这无疑也是柏拉图力求保持其“静止”,杜绝其变化的缘由之一。
二、理想城邦与公民的关系
然而在这个以“至善”为旨的理想城邦之中,城邦与它的公民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据杜威分析,“由于柏拉图缺乏对每一个人的独特性和个人与众不同的特性的认识”,使得他主张“有限的能力和有限的阶级的理论”“最后的结果就归结为个性处于从属地位的思想”[1]100-101,而个体对城邦的从属关系必然导致个性被压制和个体与城邦之间对立冲突的出现。在一个以“正义”和“整体幸福”为要义的城邦当中,个体的幸福会被关照吗?这是杜威对《理想国》的质疑之二。而实际上,只需对理想国中个体与城邦关系的本质、正义与幸福的关系稍作剖析,杜威的疑惑便可迎刃而解。
1.和谐,还是对立?在哲学王“贤人治政”的体制下,理想国中形成严格的社会分工,城邦人依据其天赋(金质、银质或铜铁质)而受到适当的教育,最终被安置在“最适合其天性”的行业里为城邦工作。在杜威看来,这样的社会安排恰恰遮蔽了个人的独特性与个性,使其只能被动、服从于社会的需要。
的确,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处心积虑地建造着一个理想的城邦(也即一个正义的城邦)。在这个城邦里,城邦利益至高无上。公民从属于城邦,为城邦利益而死生。例如,在《理想国》第三卷中,对于染病者的处置方式就有如下表述:“苏格拉底:……我们可以说,阿斯克勒比斯是早已知道这个道理了:对于那些体质好、生活健康,仅只有些局部疾病的人,他教给了医疗方法,用药物或外科手术将病治好,然后吩咐他们照常生活,不妨碍个人尽公民的义务。至于内部有严重全身疾病的人,他不想用规定饮食以及用逐渐抽出或注入的方法来给他们以医疗,让他痛苦地继续活下去,让他再产生同样糟糕的后代。对于体质不合一般标准的病人,他则认为不值得去医治他,因为这种人对自己、对国家都没有什么用处。”[6]117
城邦中染病较轻者能够得到及时、积极的治疗,以保证其尽快恢复健康,不妨碍完成公民之责;而对于染病较重者,则要从城邦的利益和大局考虑,不会不惜耗费资源去做无用(于城邦)之功。这是因为理想城邦的目标并不是为了谋求某个个人或阶层的福利的最大化,而是为了整个城邦和全体公民的整体幸福。而这种“整体幸福”的实现,对于某个个体而言,则可能意味着牺牲。这一原则同样体现在针对作为统治阶层的护国者的规定当中。例如,《理想国》第四卷中有这样的言论:
阿得曼托斯:假如有人反对你的主张,说你这是要使我们的护卫者成为完全没有任何幸福的人,使他们自己成为自己不幸的原因:虽然城邦确乎是他们的,但他们从城邦得不到任何好处,他们不能像平常人那样获得土地,建造华丽的住宅,置办各种奢侈的家具,用自己的东西献祭神明,款待宾客,以争取神和人的欢心,他们也不能有你刚才提到的金和银以及凡希望幸福的人们常有的一切……对这种指责你怎么答复呢?
苏格拉底:……我们的护卫者过着刚才所描述的这种生活而被说成是最幸福的,这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我们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单独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当前我认为我们的首要任务乃是铸造出一个幸福国家的模型来,但不是支离破碎地铸造一个为了少数人幸福的国家,而是铸造一个整体的幸福国家。[6]132-133
这样看来,理想国显然与杜威心目中理想的民主主义国家相去甚远,它是一个贤人治政的专制国家。护国者也是为城邦而存在的,他们肩负着立法、护国的重任,因而受到更加严格的约束,他们无法为自己所在的阶层谋取利益,而要为城邦的整体幸福辛勤工作。
实际上,希腊语中的“Πολιτεiα”①“理想国”一词便是译自希腊语“Πολιτεiα”一词,又译“共和国”,后一译法更接近其本意。一词原意是指“对人的研究”或“人学”,由于古希腊人认为人总是以他们的共同体的形式(即城邦)而存在的,便把对人与其共同体的研究称作“关于城邦的学问”[7]19。城邦是由个体的人组成的,人的聚集是城邦最原始的内涵和前提。就古希腊时代而言,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个人的生存需仰赖城邦,形成了一种个人依赖于城邦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个人与城邦的存在是一致而和谐的。然而亦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文明发展水平和文化特征相适应的是,即使是在理想城邦中,城邦关注的只可能是整个城邦和全体公民的福祉,而对于单个公民或某一阶层的幸福却无暇一一顾及。城邦的意志与全体公民的福祉相和谐,而落到单个公民身上,却不免出现对立。在此种对立之下,个体的性命未必能够保全,更难奢谈杜威所谓的“个性与独特性”了。
2.幸福与正义的关联。以追求“整体幸福”为旨的理想国就无法关照个体的幸福吗?在《理想国》中我们不难发现关于“幸福”的讨论是与“正义”联系在一起的。而“正义”的内涵是理想国的中心问题之一。柏拉图将正义分为“大的正义”和“小的正义”,并“提出了一种崭新的观点:大的正义即城邦国家体制赖以建立的伦理根据,而小的正义则是个人的心灵美德与道德行为,二者是相通相关的。前者属于城邦国家的体制伦理,而后者则属于个人道德的范畴”[8]8。
就城邦内部安排而言,“大的正义”是指每个人单搞一门手艺,各司其职,各安其位,相互不僭越,整个国家就会和谐繁荣。就对外布置而言,理想国拥有军队建制不是为侵略别国,而是为了抵御外侮(对内也可压制奴隶的反抗)。一个健康、正义的城邦是不追求物质的奢华的,也就没有膨胀的私欲怂恿它去觊觎别国的资源。这是城邦正义的另一重要方面。理想的城邦教育人克制内心非法的欲念,因而它的公民就不会产生侵掠别国的冲动。可见,“大的正义”是以“小的正义”为前提的,而“小的正义”要靠“大的正义”引导、教育才得以形成。因此教育在理想城邦的形成中就成为关键的一环。柏拉图坚持“理想国”的图景要通过教育去实现。在城邦的教育之下,个人心灵的美德积聚为城邦的美德。“灵魂的秩序不过是城邦的秩序内在于个人的体现,而城邦的秩序不过是灵魂的秩序在社会生活层面的反映,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9]35。
美德(智慧、勇敢、节制、正义)滋养下的正义城邦是幸福的城邦。而个人幸福的获得,同样依靠正义的指引。在正义引导之下,向“善”的追求,向“善”的理念无限的靠近,这就是柏拉图所认识的人的终极幸福。这种“幸福”与阿得曼托斯所言的庸俗的幸福有着天壤之别。
由于人的灵魂由理智、激情和欲望三部分构成,如同在正义的城邦中三个阶层各司其职、互不僭越一般,在灵魂的层面上,“当人的这三个部分彼此友好和谐,理智起领导作用,激情和欲望一致赞成由它领导而不反叛”[6]170,这样的人就是具有节制和正义美德的人,是幸福的人。而“不正义、不节制、怯懦、无知,总之一切的邪恶,正是三者的混淆与迷失”[6]173,它们给人带来不幸。那么,理想国中最幸福的是哪部分人呢?在柏拉图看来,天生具有最佳资质、接受了最完备的教育、对于真理怀有无限好奇和渴望、永不懈怠地接近着“善”的人,自然是最幸福的。他们是城邦中的“爱智者”,即哲学家。
总之,“理想国”虽然无法关照到每个个体独特的生存状态,但在构建理想城邦的同时,却已通过教育将通往幸福的“正义”的钥匙交到了每个公民手中。
三、“理念之物”之于理想城邦
在建造理想国的过程之中,教育被柏拉图赋予了重要的位置。在这项为城邦公民打开“正义”“幸福”之门的重要工作中,没有可以忽略的细节。这也是对杜威第三个疑问的解答。在“理想国”的静态图景当中,杜威特别提到那些令他费解的不容变更的“很小的细节”。在杜威看来,根据一个固定的目的“组织国家,即使很小的细节都不应改变”“虽然这些细节本身无关重要,但是如果容许改变,就会使人们的心理习惯于变革的观念,因而有破坏作用,发生无政府主义现象”[1]101。
杜威所谓的那些“无关重要”的微小细节,主要是指理想国中对音乐的监管问题。例如,《理想国》第四卷中,柏拉图在谈及人的培养和教育时,多次要求对音乐的曲调进行严格监视,以防止音乐的翻新影响到公民的性格、习惯,最终影响到立法,而为害国家。
苏格拉底:我国的领袖们必须坚持注视着这一点,不让国家在不知不觉中败坏了。他们必须始终守护着它,不让体育和音乐翻新,违犯了固有的秩序。他们必须竭力守护着。……因为音乐的任何翻新对整个国家是充满危险的,应该预先防止。
……
苏格拉底:因此,我们的护卫者看来必须就在这里——在音乐里——布防设哨。
……
阿得曼托斯:别的害处是没有,只是它一点点地渗透,悄悄地流入人的性格和习惯,再以渐大的力量由此流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再由人与人的关系肆无忌惮地流向法律和政治制度,苏格拉底呀,它终于破坏了公私方面的一切。[6]139
音乐在“理想国”的城邦生活与教育中,果真如杜威所说是无关重要的细节吗?在当今生活中看似无伤大雅的音乐曲调的变化在“理想国”中却被柏拉图反复警告,无疑表明着符合城邦精神的音乐在构建理想城邦中的重要作用。柏拉图坚持理想国的政治主张须依靠教育来实现,音乐便毫无悬念地成为其教育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无小事,音乐也必然被细心选择、时常检视。
音乐何以如此重要?这是因为在理想国中,音乐不仅关乎教育,更关乎“理念”。或许受到毕达哥拉斯学派①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观点:数乃万物的本源。的影响,柏拉图认为音乐具有“数与比例”这一理性特征,因而是接近万物本源的“理念之物”,恰与理想国的“理念”诉求相契合。在《斐利布斯篇》中柏拉图也谈到,“有些声音柔和而清楚,产生一种单整的纯粹的音调,它们的美就不是相对的,是从它们的本质来的,它们所产生的快感也是它们所特有的”[10]298。这里的本质是指音符之间数与比例的关系,这种快感指的是因数的比例的关系在心灵里产生的和谐感。柏拉图认为音乐的本质即音乐的理性,不增不减,不生不灭,永恒不变[11]87。也正因如此,音乐特别能够深入人的心灵,而且不会磨灭。音乐能够使灵魂因为接近理性,而更加优美。
那么何种乐曲才是“理想国”所需要的呢?当然是符合城邦精神能够滋养美德的乐曲。“与毫无畏惧地奔赴战场或遭遇不幸而和命运进行艰苦搏斗的勇士们的行动相称的乐曲,以及与他们在和平幸福环境中的心情相适应的乐曲”应当被保留下来,而“一切带有女人气的并且使人陶醉之类的乐曲则必须排除”[11]88,因为这样的乐曲含混了音乐的本质,使性情和欲望的成分压倒了理性,所以会对听者的性格发生消极的影响。对于筛选出来的好的曲调要进行严密监视,以杜绝其变化;因为好的曲调一旦变坏,则会“激励和培育心灵中低贱的部分去毁坏理性的部分”[6]404,不仅无法使人的心性得到完善,还会通过毁坏人的理性影响立法和政治制度,以致危及“理想国”的存在。
[1]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2]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M].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3]王勤榕.西方史学中的历史循环论与历史进步观[J].北京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6):70-78.
[4]张井梅.16、17世纪历史进步观与西方史学[J].历史教学问题,2008(2):46-50.
[5]滕大春.外国教育通史(第一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
[6]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7]贺小梅.柏拉图《理想国》中的不理想之处及其启示[J].学理论,2009(4):19-20.
[8]姚介厚.柏拉图的城邦文明论和“理想国”设计[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3-12.
[9]聂敏里.《理想国》中柏拉图论大字的正义和小字的正义的一致性[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30-43.
[10]柏拉图.文艺对话录[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11]王绍灿.试述古希腊时期柏拉图的音乐教育思想[J].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01(6):87-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