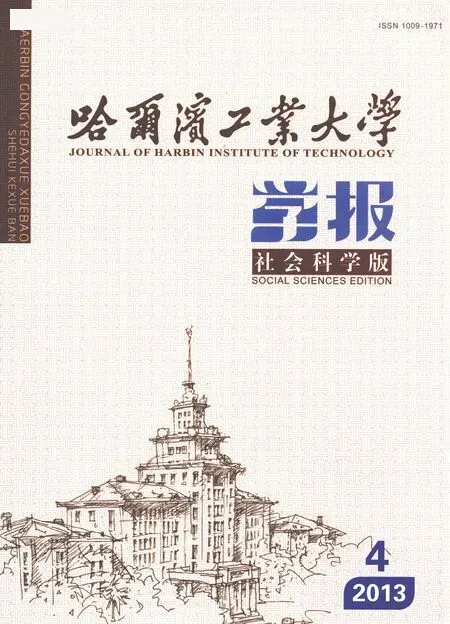市场、社会与社会建设*
曹锦清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200237)
·社会理论与社会建设·
市场、社会与社会建设*
曹锦清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200237)
社会建设的概念在我国很晚才被提出来,这意味着社会被重新发现和理解。明确社会在哪里,这是社会建设的首要问题。伴随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社会问题和矛盾大量涌现,这为社会建设提供了一种理解思路。社会建设何以可能,不仅要以公平为原则,建立广覆盖、适度保障、可持续的社会保障网络,更应当重建以家庭、职业、社区为单位,形成“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社会共同体。
市场经济;社会;社会建设
一、重新发现“社会”
在马克思之前,社会被认为是受人的动机、欲望、情绪和意志等支配的,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这些因素在其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冲突。马克思第一次把对社会的研究从唯心史观中解放出来,不从欲望、情绪中寻找社会发展的原因,从而创立了科学的唯物史观。
毛泽东在标志着他的思想开始成熟的重要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什么是社会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在《新民主主义论》第二部分,他讲道:“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毛泽东指出,“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1]毛泽东还分别在第五、第六和第十一部分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此,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社会同样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位一体。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邓小平原来也认为公有制和市场是兼容的。当时,国内很多人认为,随着市场化的推进,资产阶级必然出现,两极分化不可避免。针对国内出现的这一言论,邓小平在1987年、1988年和1989年就反复强调,只要我们坚持两个主体(所有制上的公有制和分配上的按劳分配)不动摇,就不会出现两极分化,也不会出现资产阶级。如果出现这种局面,就说明社会主义走到了邪路上。一旦出现这一局面,区域、民族、阶级、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都会出现。尽管有这种担忧,邓小平“南巡”之后,进一步强调改革开放。在1992年,我国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当然,邓小平也一直没有放弃对市场经济可能带来的社会分化的关注。1987年,邓小平就强调,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能搞资本主义。在1992年,他又说:“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2]1356-1357。“如果仅仅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2]1256-13571993年在同弟弟邓恳谈话时,邓小平又进一步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问题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从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2]1356-1357
二、“社会”在哪里?
社会在哪里?这是社会建设的首要问题。问题被提出来以后,官方和学术界都力图来破这个迷局。
人口高流动、财富高分化、社会问题严重,这让原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显得力不从心。正是由于原来的“三位一体建设”不够,官方文件将之称为社会,但是政府的各个部门和学术界对于什么是社会则众说纷纭。
政法治安部门认为管理是上位概念,而建设是下位概念。他们把社会建设的核心定位于如何管理一个陌生的高流动社会。近年来,社会矛盾和犯罪案件增加,而警力相对不足,大量的协警开始出现。这一方面是由于警力增加的名额有限;另一方面也解释了不占用编制、成本相对低廉的协警这一群体出现的原因。由于人口的高流动,原有的以户籍所在地为核心的管理制度已经很难实现其预期目标,只能转向以居住地为核心的管理。与此同时,对社会的管理寄希望于安装摄像头等技术手段,现在很多案件的破获都依赖于遍布大街小巷的摄像头。
民政部门把如何能对由于财富高度的分化而筛选下来的底层民众提供一张社会安全网作为社会建设的重点。问题是,这个网多大、多厚才够安全。欧美等高福利国家,一般依靠高税收来为它的福利制度提供财力支持。然而,经济运行不会永远一帆风顺。当经济出现通胀或通缩时,财政收入出现问题,必然导致赤字,以至出现政府无钱可用的现象。然而,在一个选举政治的制度下,福利支出是一个刚性的支出。时间长了以后,就会产生主权债务危机、失业率居高不下、游行示威等一系列问题。所以说,我国要从国情出发,建立一个广覆盖、保障适度、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可持续性取决于经济在未来的运行情况,保障力度可以在财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逐步提高。
不同于政法部门和民政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则把社会建设的重心放在促进稳定就业和对失业群体的保障问题上。在他们看来,解决城市下岗职工、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和每年数百万的新增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是重中之重。
从整体而言,学术界对社会建设的认识比较激进,目前在经济学、法学和社会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首先是公民社会派。从西方传入的“civil society”一词,在中国有多个翻译:公民社会、市民社会、民间社会和草根社会等等。总之,这一派认为,在政府结构之外,由公民自己组成的各种各样的组织,都叫作社会组织。当然,目前在我国这些组织还要到民政部门进行登记。很多学者将这些社会组织称为公民社会,认为可以纠正政府和市场的失灵。这是他们的理论和价值期待。
第二种是社会结构派。这一派把社会理解为由不同的阶层构成,社会建设的重点是把围绕分配形成的金字塔社会转化为菱形或橄榄形社会。该派关注的焦点是分配问题,要求解决贫富过度分化带来的问题。有些学者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的分化很严重,基尼系数很高,已经和南美很接近,进而得出中国社会已经很危险的结论。这些学者以陆学艺等为代表,认为要把金字塔社会压得扁平一些。他们主张把最低工资要提高一些,转移支付要大一些。
第三种是民生派。这一派认为社会建设主要是医疗、教育等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目前,我国面临一个尖锐的问题——住房保障问题。住房能不能脱离市场,从商品转化为公共产品。如果一个生活中的中产阶级也买不起房子,那么会出现什么后果。这些人大多受过高等教育,他们的抵触情绪就会表达出来。因为有知识,他们可能会形成一种舆论,甚至对社会的意识形态提出挑战。
总之,我们感知到了社会问题的存在,但要完整地表述,还有待进一步探索。问题已经呈现出来了,答案还需要继续地寻找。
三、市场经济与社会问题
在中国政治话语中,现代化通常被理解为五化: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和全球化,其核心是市场化。改革开放由市场化、由资本带动,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大家都感受到了经济发展带来的益处,蛋糕不断地被做大,财富积累很迅速,但市场经济的动力有问题。建国以后,我国多次强调反私、防私和批私,同时号召每个人都为国家、为集体服务和奉献。总之,宣扬多做贡献、少拿报酬,同时心里还要很高兴。邓小平在1978年就说这种为人民服务的大公无私精神,对少部分人是可以的,对大部分人则不可以;在短时间内可行,长时期则不可行。因而,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个动机一旦被市场激发,个体就会为了提高个人收入、改善自我生活水平而努力奋斗。
早在18世纪,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提出了“看不见的手”这一重要命题,这个理念一直被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接受和宣扬。他们认为,参与市场运作的是一个个的个体,这些个体在主观上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通过市场进行各种各样的交换,市场交换行为在客观上会形成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中,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可以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实现自发的调和,这也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观点。对于这一观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到或感受到它的存在,有一定的经验支撑。但是,如果要把这些日常经验抽象化和普遍化,作为一个普遍的判断来说是错误的,在市场中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冲突和矛盾。
周期性地通胀或通缩带来的波动是市场经济面临的首要问题。对于工业化之后的资本主义社会来说,生产力大幅提高,生产本身已经不是问题,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将生产出来的产品卖出去。在19世纪初期,西方遭遇了第一次以生产过剩为标志的经济危机。经济周期性地出现波动,无论是通货紧缩还是通货膨胀都会带来问题,如何应对经济的这一周期性循环波动就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大问题。在经济学家所开出的诸多药方中,凯恩斯主义被认为是一个成功的典范,在不同的时期被人们广泛接受。
劳动者所面临的第二个风险是劳动过程和失业的风险。不同于农业生产中低风险,在工业生产中,劳动者的安全如高污染、高温、职业病等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此外,相对于农业生产中的不完全就业或“隐性失业”,在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中,劳动者面临着失去工作的巨大风险。同时,失业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和政治经济学问题,如果出现大规模的失业并应对不当,极易出现社会动荡,影响我们社会稳定和发展。
工业化会带来工厂向同一个物理空间集中,随着工业化而来的城市化带来了人口的大量集聚。大量的人口集中在有限的狭小空间,会带来卫生防疫及随人口高流动带来的道德解体和犯罪问题。要解决这些人的居住,还带来了住房问题。对于这一系列问题,在西方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也同样存在,恩格斯在其所著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有详细的论述。
贫富分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已经成为一个客观事实。由于公有制和市场不兼容,公有制基础上的按劳分配就会解体,进而共同富裕的预期被肢解,整个分配格局发生变化。在新的分配格局中,资本得到利润,管理者拿到年薪,普通劳动者获得工资,技术工人凭借其技能领取高于普通工人的收入。近些年来,工资性收入占GDP的比重在不断下降,贫富分化和资本的地位不断上升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同时,对于原来属于地主的地租应该由谁来收取,我国没有进行明确的界定。土地增值的利益如何分配,土地是谁的,土地的所有者有没有得到合理报偿,土地出让金应该如何分配才更加体现公平原则,这些问题都还没有解决。
在市场竞争中,个体由于其先天和后天的各种资源及禀赋、能力等差异,会天然地出现阶层分化。对于这一现象,国内的诸多学者已经进行了深入研究,在此就不再赘述。东西部之间的矛盾我们这些年也开始感受到。应该说,这些年来,中西部地区为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和能源。但是,他们的劳动力得到的只是工资,通过提供煤、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得到的补偿远不足以补偿其所为之付出的经济和环境代价。所以,目前新增了资源税,通过这一举措增加中西部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
城市和乡村的差距更是一个长久存在而改善缓慢的现象,中央一直在采取各种措施,“千方百计”提高农民收入。应该说,从目前来看,有一定成效,但是进展不是很大。自2004年开始,中央就明确提出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是,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仍然在不断加大,只是加大的速度有所下降。在2008年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更是进一步强调要重点解决这一问题。会议提出,自2008年至2020年,要使农民的收入增加一倍。这意味着在未来的12年内,农民纯收入的年均增长至少要达到6%的水平,对于国内许多落后地区来说,实现这一增长目标是十分艰巨的。从中可以看出,中央对城乡不断加大的收入差距的忧虑在加大。为了拓宽收入来源的渠道,我国将林地也进行改革,承包权被规定为70年,并且规定林地可以被抵押。问题是很多山是荒山,很多山也只能种树,能够被用来种植经济作物如竹子等山地很少。由此可见,通过林地改革大幅提高农民收入是很难的。
市场竞争既是资源配置的手段,又是自由的、普遍的、强大的清洗和简化机器,具有简化人类复杂而富有情感的各种动机的功能。人类的复杂动机被市场简化为一种动机,即最大限度获取货币化的利益。人与人之间的所有直接关系都被简化为间接的关系,以现金为纽带,简化为冷冰冰的现金交易。各种非货币化的情感,无论其有多么高尚,市场一概不予承认。多种动机被简化为一点,利己成为人们在市场竞争中最为重要的动机。更为可怕的是,这一动机还侵入了人类最古老、最稳定的共产主义的最基本单位——家庭。
毋庸置疑,市场化和私有化已经侵入了家庭——这一最基本的微观单位。2011年新出台的与婚姻法有关的司法解释就是对这一变化的一个回应和写照。按照这一趋势发展下去,我国原来由两个家庭结合所建立的婚姻关系,其基础就会转化为仅仅是两个个人的结合。这一切是否从某种程度上说都是在为离婚作准备;在市场经济中人到哪里去寻找温暖的归宿;家庭的私有化是否能够避免。如果答案是否定的,爱情与婚姻将成为一种买卖,那么婚姻和家庭还有什么意义。每一个人都成为孤魂野鬼,形同行尸走肉,在哪里游荡而茫然不知所措。
四、社会建设何以可能
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保障网,目前学术界有多种主张。有人主张建立一个城乡、区域等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现在来看有难度。欧美等一些高福利国家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对于我国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警醒。高福利需要高税收来支撑,也就是要有经济的稳定增长来提供保障。同时,高福利还带来一些问题,比如安全性过高就会使一些人失去劳动的动力。希腊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目前面临的主权债务危机就和它的经济发展、福利制度及选举政治有关。它的人口有1000多万,经济主要依赖工业、旅游业和农业。近年来,它的工业遭到德国等国家的强烈冲击,旅游业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也很不景气。加入欧盟以后,希腊建立了高福利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政治上实行民主选举的形式,而选票政治带来的一个明显弊端就是政客的短期效应。一旦经济出现波动并持续较长时间,财政收入下降,而高福利所构成的刚性支出受制于政府体制而无法削减,就必然会出现一系列问题。
邓小平就特别敏锐地注意到高福利社会可能出现的问题,他在1992年就曾说过,“都搞集体性质的福利会带来社会问题,比如养老问题,可以让家庭消化。欧洲建设福利社会,由国家、社会承担,现在走不通了。老人多了,人口老化,国家承担不起,社会承担不起,问题就会越来越大。全国有多少老人,都是靠一家一户养活的。中国文化从孔夫子起,就提倡赡养老人。”
所以说,我国要建立起一个广覆盖、适度保障、可持续的社会保障网络。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保障力度可以在财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逐步提高。比如在教育领域,中央政府已经提倡有条件的地方在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普及十二年义务教育,也就是高中教育也由财政来承担。
西方社会在19世纪到20世纪也在讨论这些问题。面对社会转型出现的社会失范问题,涂尔干提出要重建社会秩序,而重建社会秩序的前提是大家有道德共识,他将希望寄托于行业协会和职业道德。对于我国而言,在快速的市场化过程中,随着单位制的解体,个体获得了空前的选择自由并在物理空间和社会经济地位上高速流动,可这些自由的个体被货币连接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重建大大小小的共同体?或者说,在一个分化了的社会,共同体建设何以可能?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家庭是否还能够作为共同体存在。中华民族的根在家,以家为本位,家是构成社会的最重要的基础。随着工业社会的来临,家庭的职能不断被分离出去,生产和消费开始分开,现在就连最为基本的生育功能也出现动摇,不生育或通过其他方式养育下一代的现象越来越多。总之,核心家庭不断增多,家庭的职能也在不断萎缩。美国是一个以个人为本位的国家,它在家庭这一问题上也经历了多次反复。20世纪60年代,在弗洛伊德理论和反战思潮的影响下,美国的年轻人开始尝试各种婚姻关系,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些人开始重新思考家庭和宗教在生活中的作用。这一点,也反映在美国政府立场的转变上,里根政府总体上来说奉行保守主义,到了克林顿时期趋向自由主义,到了小布什政府又重新回到保守主义立场。如果说婚姻高度不稳定,爱情成为一种买卖,那么,从婚姻退回到同居呢?目前,同居在法律上已经不被追究责任,社会习俗也不再对之进行道德谴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人与人之间将只剩下猜疑、相互提防和算计,这一切最终带来的只能是无休止的孤独和焦虑。所以说,当代中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家庭的问题。
此外,以宗教为例,各种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宗教建设也应该进入我国的社会建设之中。市场经济只提供经济利益,不供给人生的意义。但是,人活着又必须要找到意义,总要为某种信仰而不是个人而活。目前,很多人没有信仰,不知道为什么而活,所以要有宗教。在一个失去信仰的年代和社会里,由于有了需求,宗教建设必然要加强。另外,还有一些社会组织,比如说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维权组织、志愿服务等,对于这些大大小小的社会组织也要适当引导和扶持,相关的研究要加强和深入。
[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09.
[2]邓小平年谱: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M arket,Society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CAO Jin-qing
(School of Social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nghai200237,China)
The concept of social construction in our country is only proposed lately,whichmeans that society is to be rediscovered and understood.Where the society lies is the first issue of social construction.A-long with the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t planned economy to socialistmarket economy,large amount of social problems and contradictions have emerged,which provides a line of thought to understanding the ideas of social construction.Social construction is possible,only when it should not only setup a sustainable social security network with wide coverage and moderate security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but also reconstruct a community of"out-in friends,help one another in defense work"taking family,occupation and community as unit.
market economy;society;social construction
C916
A
1009-1971(2013)04-0001-05
[责任编辑:唐魁玉]
*感谢杨君在本文写作和文稿整理过程中给予的帮助及建议。
2013-04-08
曹锦清(1949—),男,浙江兰溪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城乡发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