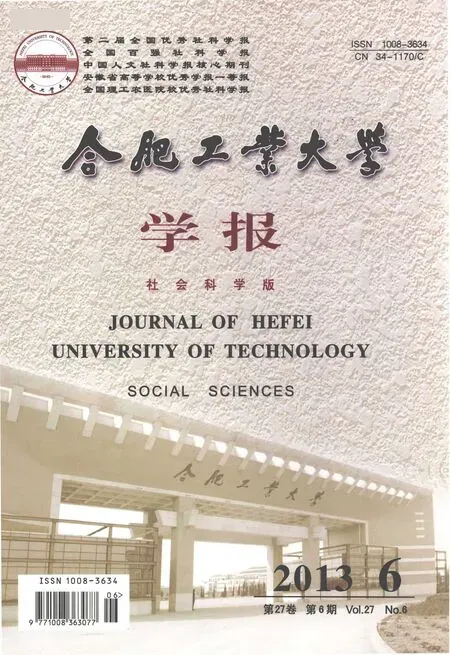记忆·旅行·追寻——论莫里森《宠儿》中的历史、文化和自我意识
许庆红,王 巧
(安徽大学 外语学院,合肥 230601)
一、引 言
《宠儿》(Beloved,1987)是美国当代著名黑人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1931-)的长篇代表作。莫里森的崛起和成名使她成为20世纪后三十年世界文坛中一颗璀璨的明星。作为在白人文化为主体的社会中一名非裔美国作家,莫里森一方面接受美国的传统思想教育,受到以白人文化为中心的环境影响,“但另一方面她又在只占美国人口少数的黑人群体中,受到了独特的黑人文化、黑人理念、黑人历史的熏陶,这一点恰恰是激发托妮·莫里森深刻思考和创作激情的原动力”[1]2-3。莫里森得益于拉尔夫·埃利森和詹姆斯·鲍德温等黑人作家开创的黑人文学传统,以敏锐的目光观察美国黑人生活,“努力致力于护持和弘扬黑人文化,她的作品也始终以表现和探索黑人的历史、命运和精神世界为主题,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在一起”[2]25。而与其他黑人作家有所不同的是,莫里森具有浓厚的历史感、文化意识和自我意识,这些在其文学创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宠儿》便是基于美国历史上著名的玛格丽特·加纳弑婴案所进行的文学创作,是其将历史与文学艺术相互杂糅的成功典范。
《宠儿》自问世以来,因其特殊的故事内容、独特的写作手法一直受到国内外文学评论界的广泛关注。迄今为止,众多评论家已经从后殖民、女性主义、叙事学、魔幻现实主义等理论视角对这部作品的思想主题、人物形象和艺术形式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和研究。但是,将历史记忆、文化旅行和自我追寻三个维度融为一体对该作进行三位一体的解读并不多见。该小说真实地再现了美国内战之前非裔美国人在奴隶制和种族歧视双重迫害下的悲惨生活。通过对往事的回忆,莫里森将最真实的黑人历史和文化揭示给当代美国社会,呼吁非裔美国人勇敢地面对历史记忆,找到属于自己的历史,在文化旅行中找寻自己的民族文化之根,治疗文化缺失症,并最终实现黑人民族的自我追寻。本文从非裔美国人的历史记忆、文化旅行和自我追寻三方面分析莫里森如何唤起黑人民族内心的历史文化感,走出阴霾,在新的社会文化中实现真正的自我追寻。
二、非裔美国人的历史记忆
美国的蓄奴制是“黑暗的制造者”,美国内战结束之后,“黑奴制意识[并]未烟消云散,它依然在啮噬黑人的心灵,影响黑人的思维与认识”[3]163。对此,许多非裔美国作家都曾以优秀的作品进行控诉和声讨。可是,随着年代已远,对于这一百多年前的历史,美国黑人或白人因回忆的痛苦或直面的尴尬正在有意识地逐渐将其忘却。然而,作为非裔美国文学第三次高潮中的杰出作家,莫里森却敏锐地转向历史记忆,通过她的力作《宠儿》艺术再现历史的真实与残酷,在记忆中反思和质询种族问题。
《宠儿》的创作取材于美国内战前一名叫作玛格丽特·加纳的女奴的真实生活惨况:她带着孩子一路逃亡,可是,奴隶主追踪而至。为了让自己的孩子不再落入奴隶主之手,她采用了极其血腥的方式杀死婴儿。至于加纳这样做的原因,用她自己的话说:“与其让他们重被带回奴隶制,一点点地被折磨死,那还不如现在就结束他们的苦难。”[4]157这是一位奴隶母亲走投无路时的无奈之举,不惜用生命和鲜血捍卫其孩子和自我作为人的尊严。几个世纪以来,该故事一直是画师们呈现不尽的一个庄严题材,也是作家们不厌书写的一个主题[5]78。莫里森对之进行了艺术的再创作:被杀的婴孩成了时时作祟的冤魂,并在十八年后还魂重返人间,进行复仇,索取母爱,折磨母亲。莫里森将这样一个血泪交融的凄惨故事缓缓地诉诸笔端,艺术再现历史记忆当中黑人奴隶的受难经历以及由此孕育出来的浓郁的爱,而读者往往难免深陷其中,体悟人物痛苦的心路历程。
《宠儿》集中鞭笞了奴隶制的罪恶,塞丝的杀婴记忆就是“黑人群族苦难历史的记忆”[6]74。小说扉页上题写的“献给六千万甚至更多”,既是对被贩卖黑奴的屈死冤魂的深沉告慰,又是对惨绝人寰的蓄奴制的悲愤控诉。作为奴隶的黑人母亲塞丝,她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包括爱自己孩子的权利。为了使自己的女儿免遭奴隶的悲惨命运而在另一个世界重获自由之身,她选择了亲手杀死女儿这种极端的方式。这是一段谁都希望尽快遗忘的记忆,但往事的印记却不容人们遗忘和抹杀。因此,宠儿变成了鬼魂,她的重返使每个人又不得不回到了那充满罪恶的时代。莫里森通过《宠儿》揭示的不仅仅是个残酷的杀婴故事,而更多的是这个故事发生的社会历史语境及其产生的罪恶影响——美国内战之前的蓄奴制和种族主义对非裔美国人的精神摧残。蒙受羞辱与折磨的黑人群体很难勇敢面对过去、忘却过去的身体和精神创伤,也缺少重新构建未来的希望,仿佛“重建生活就是一种对永远抹不去的过去以及对那些死去的,或饱受折磨的人的一种背叛”[7]200,深沉的历史记忆构成了他们内心挥之不去的巨大阴影。莫里森将黑人的个人身世、群体的遭遇乃至整个的非裔种族命运相融,赋予作品难以替代的社会历史文化价值,牵引着世界范围内的读者关注美国黑人民族的历史记忆,了解他们的心路历程和内心创伤。
在接受丹尼尔·泰勒·加斯里的采访时,莫里森坦言,她对这部鞭挞奴隶制的小说并没有太大的自信:“它可能是我写的书中最没人愿意读的,因为那里面的东西,是书中人物不想去回忆,我自己不想回忆,黑人不想回忆以及白人也不想回忆的。我指一种国家健忘症。”[8]257从《宠儿》中塞丝对其母亲的回忆中读者可以感受到奴隶制的残酷与冷血,从而理解作者为何会有此感慨。奴隶制下人性扭曲的奴隶主往往把女奴当成泄欲的工具,任其肆意揉捻。塞丝是她母亲唯一留下的孩子,“其他许多跟白人生的她也都扔了。只有你,她给起了那个黑人的名字”[9]74。尽管存活下来,塞丝却丝毫没有母亲哺育她、为她梳头的记忆,“我记得她甚至总不跟我在同一间屋子里过夜”[9]72。塞丝是靠着母亲胸下的黑奴烙印来辨认她。年幼的她还天真地想要同样的烙痕。成年后她才明白那是奴隶主财产的象征,是自由与尊严被剥夺的标识。尽管没有人愿意重拾如此沉重苦难的记忆,但随着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的兴起,非裔美国人开始对主流白人社会产生抵触。重现过去奴隶制的惨痛历史记忆、反思历史并找到黑人赖以重建自我身份的历史文化根基,是当代非裔美国人最终实现自我身份的必由之路。对莫里森而言,历史是黑人无法割断的纽带,蕴涵着民族的集体记忆,只有重返历史才能洞悉黑人的灵魂。她正是通过多重叙事技巧再现故事发生地“124号”的生活场景、人物和事件,从塞丝的过往生活里挖掘出片断进行拼接,将深藏在记忆里的故事重新复原完整,将对蓄奴时代的回忆、忘却、压抑、挖掘、拒绝、重新回忆到再遗忘这一迂回曲折的过程充分展示出来。
小说《宠儿》中,十八年前的弑婴案让塞丝登上了报纸,但那时如果你在报上刚看见一张黑人的脸,恐惧的鞭笞就会掠过你的心房,“因为那张脸上报,……它必须是件离奇的事情——白人会感兴趣的事情,确实非同凡响,值得他们回味几分钟,起码够倒吸一口凉气的。而找到一则值得辛辛那提的白人公民屏息咋舌的有关黑人的新闻,肯定非常困难”[9]186。那个时候在白人眼里,黑人绝无话语权可言,他们只配得上“动物属性”。十八年后,白人种族主义的立场仍矗立不倒。鲍德温在去接丹芙的路上回忆曾经救塞丝的情景时竟这样感叹:“教区设法让弑婴案和关于野蛮的叫嚷声转了向,从而为废除奴隶制进一步奠定了基础。多好的年月啊,充满了唾弃和判决。”[9]304黑奴们曾遭受的血和泪竟成为白人讴歌的典范。更讽刺的是,他家“后门旁边的架子上摆着一个嘴里塞满钱的黑小子。……他跪在一个底座上,上面漆着‘听您使唤’的字样”[9]304。通过对这个“比奴隶更恨奴隶制”的鲍德温的塑造,莫里森揭露了废奴主义者的虚伪以及废奴之路的艰辛。
从惨无人道的蓄奴制,到奴隶制推翻后仍然广泛存在的种族隔离与种族歧视政策,都是美国历史记忆中的阴暗面,共同折射出在此历史背景下非裔美国人走出压抑和控制、寻求自己文化身份的艰难旅程。《宠儿》的锋芒直逼历史的惨痛记忆及其给黑人造成的心灵创伤,充分展示了莫里森自觉的历史意识和高尚的人文情怀。
三、非裔美国人的文化旅行
从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60年代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非裔美国人的命运经历了从奴隶到解放、从黑人自由民到北方城市的中产阶级、从白人主流社会的排斥到寻找黑人民族之根的文化苦旅的变迁过程。
欧洲白人文化的政治和经济强权一度遮蔽了非裔美国群体的声音。被迫踏上命运之旅的非洲族裔人不仅遭受着被欧洲白人贩卖到美洲充当奴隶的“肉体奴役”,而且遭受着黑人文化传统被白人强势文化压制的“精神奴役”。群散居于美洲新世界的非裔美国人便徘徊在陌生与隔绝的文化身份失落的空间里。正因为如此,在莫里森的创作中,她始终将文化问题置于重要位置,着重展现白人文化入侵黑人文化的总格局,以及这种格局对黑人心态的影响。在她看来,“非洲民族主义(Africanism)之所以能成为文学的想象并对其有所影响就是兴趣所致,因为人们只消仔细研究一下文学的黑人性(blackness),就会发现文学的白人性(whiteness)的本质,甚至根源”[10]1006-1008。莫里森关注黑人文化的传承和黑人身份的建立,尤其是黑人女性的命运,这些都是整个黑人族裔得以发展和延续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在莫里森看来,非裔美国文化长期以来一直处于美国白人主流文化的排斥与忽视之下,但是,随着非裔美国人自我意识的提高,他们认识到自身文化的边缘化地位以及不同文化的差异性。“我们生活的美国是一个过去总是被抹去、将来总是清白无辜的地方……过去要么不在场,要么就被浪漫化了。现存的文化不提倡对过去真相的追寻,更不会接受关于过去的真相。与三十年前相比,现在,记忆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11]11于是,莫里森的小说世界竭力呈现非裔美国人的文化之旅,他们试图从文化“旅行”中通过差异性挖掘非洲民族文化传统,寻找自己的文化言说方式,并最终重构自己的文化身份。
《宠儿》中的人物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即种族记忆所困”[3]167,他们都生活在往事当中而难以自拔。莫里森借助黑人家族姓氏和神话传说,揭示非裔美国黑人的文化身份现实。例如,黑人会飞的传说表达了蓄奴时代身陷奴隶制的南方黑奴追寻独立与自由身份的内心愿望。自从被贩卖到美洲后,处于他者化地位的黑人奴隶便一直幻想着能够飞回非洲,但由于被割断了根脉,他们的愿望也只能是一种奢望,只能用超越时空的“飞翔”来予以表达。莫里森曾就此说过:“那永远是我生活中的民间传说的一部分;飞翔是我们的一种天赋。我不在乎它看上去有多愚蠢。它到处存在——人们曾经谈论它,它存在于黑人的圣歌和福音音乐中。它也许是异想天开——逃离、死亡等等。但假定它不是。它会是什么呢?”[12]26《宠儿》中,在追捕塞丝的“学校老师”面前,塞丝是一位惊慌失措的母亲,她“飞翔起来,像长翅的老鹰一样提起自己的孩子。她脸上长出了喙,双手变成了劲爪,调动全身,将儿女四个全部带在身上;肩上一个、腑下一个、手上一个、另一个则一路哭着被带进了遍洒阳光和木屑的木棚里”[9]188。塞丝当时的念头就是以飞翔的方式逃离。“不,不,不不不。很简单。她飞起来。攒起她所创造的每一个生命,她所有宝贵、优秀和美丽的部分,拉着、推着、拽着他们穿过幔帐,出去,走开,到没人能伤害他们的地方去,到那里去。远离这个地方,去那个他们能获得安全的地方。”[9]195自由飞翔的鸟类这一隐喻性的表达方式既反映了黑人个体对自由的向往,同时也指向黑人群体以及整个非裔美国民族意识在白人强势文化的掌控下的觉醒,他们憧憬着在文化的旅行中探索民族的出路。这也表明了莫里森的文学成就,她并没有囿于对非洲传统文化的简单运用,而是赋予其以崭新的含义,与非裔美国文化的寻根意识产生联系。
在传统的非洲文化里,名字对于非洲人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既标明着个体的自我身份,又是祖先的纽带,恰当的名字能够影响被命名者一生的命运。莫里森曾在接受托马斯·勒克莱尔访问时(Thomas Leclair)说过:“如果你来自非洲,你的名字就消逝了。这尤其成为问题,因为那不仅仅是你的名字,而是你的家庭,你的部落。”[12]28作为家族历史文化烙印的姓氏,是区分家族或族群的重要标志,而真实姓名的缺失恰恰表明黑人被贩卖到美洲成为奴隶后,被迫割裂了与自身家族历史文化的联系。作为能指符号的姓名,是代表黑人个体和族群文化身份的不可替代之物。比如,小说中塞丝的婆婆获得自由后,一直坚持自己的名字是“贝比·萨格斯”:“萨格斯是我的姓,先生。随我丈夫。他不叫我珍妮。”[9]169-170“贝比·萨格斯”是她的所谓“丈夫”留下来的一切。现在,如果她用某个卖身标签上的名字称呼自己,他就无法找到她了。莫里森藉此说明,非裔美国人对自己非洲家庭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坚守,是最终寻求真实自我身份的必经之道。
与此同时,从更深的意义上看,莫里森认为,只有坚守族群本土文化与历史传统,主动抗拒文化殖民,非裔美国黑人才能在历史记忆和文化旅行中传递真正属于自己的民族精神内涵。以布鲁斯和爵士乐为主要特色的美国黑人音乐,浸透着非洲文化历史的沉浮和变迁,承载了非洲民族文化之根,描述了非裔群体颠沛流离的旅行,抚慰着他们的精神和灵魂,成为他们彰显其独特文化身份的主旋律。音乐对于黑人民族的重要性在《宠儿》描写的保罗·D 的故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当保罗·D 和其他四十六个黑人奴隶在佐治亚州做苦力时,被白人用一根长长的铁链锁在一起,他们住在陷入地下的木匣子里,吃不饱、穿不暖,并时时受到白人的侮辱和戏弄。此时,音乐便是他们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动力。“在‘嗨师傅’的带领下,男人们手抡长柄大铁锤,苦熬过来。他们唱出心中块垒,再砸碎它;窜改歌词,好不让别人听懂;玩文字游戏,好让音节生出别的意思。他们唱着与他们相识的女人,唱着他们曾经是过的孩子;唱着他们自己驯养或者看见别人驯养的动物。他们唱着工头、主人和小姐;唱着骡子、狗和生活的无耻。他们深情地唱着坟墓和去了很久的姐妹。唱林中的猪肉;唱锅里的饭菜;唱钓丝上的鱼儿;唱甘蔗、雨水和摇椅。”[9]130纵然白人可以限制黑人的自由,忽视他们的人格,但无法阻止他们唱歌。在歌声中黑人们彼此交流、彼此鼓励、彼此热爱。非洲黑人民族与音乐有着无法割舍的情缘,被噤声的他们正是以其独有的方式在布鲁斯与爵士乐中弘扬着美丽的黑色生命之魂。
四、非裔美国人的自我追寻
自我的追寻是莫里森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莫里森认为,过往的黑人民族历史和文化是黑人族群意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他们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正视、继承和弘扬自己历史和文化中的精髓,是重新建构真实身份的必经之路,也是重新发挥非裔美国黑人主体性的体现。历史记忆与文化旅行,并不是单纯为了修正白人所记录的关于黑人的历史和文化,而是为了发现过去影响现在的根源,也是为了反抗浊化黑奴过程的一部分,找回自尊自爱的一部分[13]214。对于非裔美国人来说,与本民族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有意割裂以及对白人文化和价值观的曲意迎合,会导致他们自我主体性的缺失和自我认同的混乱,以至于不能够很好地融入社会、体现自我价值。因此,对此有着敏锐感触的莫里森,势必要尝试带领“整个离散的黑人群体”去“寻找自己的身份,寻找自己的起源以便能理解自己”[14]97,从而走出这场自我主体的迷雾。
《宠儿》中,莫里森通过刻画三代黑人的自我追寻,表达了黑人群体逐渐走出过去的阴影,通过自己的努力,慢慢融入到新的文化当中,更好地把握现在和未来。作为小说的女主角,塞丝在自我追寻的道路上几经坎坷。首先,与婆婆贝比·萨格斯相比,塞丝所代表的新一代黑奴具有更强的反抗性。然而,残酷的奴隶制仍然给她带来了无比的恐惧。塞丝在“甜蜜之家”偶然听到学校老师在给学生讲她的动物属性时心理自我发生了巨大变化,她不再任劳任怨,决心冒死逃出“甜蜜之家”。其次,为了维护做人的尊严,不再被当作动物,她毅然在“学校老师”面前杀死了自己的女儿。可是,杀婴事件使塞丝陷入了身份危机,对死去女儿的愧疚感使她无法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再次,“甜蜜之家”的同伴保罗·D 来到了她家,唤起了塞丝对尘封往事的记忆。正当塞丝决定与保罗·D 重新开始时,十八年前被她杀死的女儿借尸还魂归来追讨爱债,塞丝又迷失了自我。最后,历经了痛苦的折磨后,在小女儿丹芙和黑人社区的帮助下,塞丝终于摆脱过去,迈向新的生活。
莫里森刻画的黑人奴隶中保罗·D 是最先意识到社会自我的代表。逃离阿尔弗雷德砸石场后,保罗·D 便把“佐治亚的阿尔弗雷德、西克索、‘学校老师’、黑尔、他的哥哥们、塞丝、‘先生’、铁嚼子的滋味、牛油的情景、胡桃的气味、笔记本的纸,一个个地锁进他胸前的烟草罐里”[9]136。对于保罗·D 而言,他不能理解塞丝因为对孩子的爱过于浓烈而离开了他,这与他最初的人生理念相悖。可是,故事的后来,随着他对塞丝越来越了解,他改变了自己,接受了事实,并勇敢地承担起男子汉的责任。
塞丝的小女儿丹芙则是黑人勇敢寻找社会自我的典型代表,象征着年轻的黑人一代。丹芙从对“124号”受小鬼困扰习以为常、到对宠儿的依恋、再到勇敢走出“124号”,成为承担起养活母亲和自己的坚强女孩,她的社会自我变化过程正是莫里森对新一代黑人的希望。虽然奴隶制早已不复存在,但是,黑人们必须走出过去的阴霾,全身心融入新的社会,从中找到真正的自我,并做真正的自我。小说的最后,保罗·D 告诉塞丝,她自己才是最宝贵的,从而唤醒了塞丝的自我意识。与此同时,他也唤起了他自己的自我。“但莫里森更想主张的是黑人要像丹芙那样学习知识,主动为自己创造良好的社会情境,保持社会自我中的自尊,担当积极的社会角色。”[15]243
不管是故交还是陌路,只要拥有共同的黑皮肤,他们的默契就是互帮互助。这种黑人群体意识不仅代表了黑人的社会文化价值观,而且可以用来对抗强大的白人社会文化。非裔美国人的历史文化因黑奴制和种族主义而遭到破坏,黑人对自己历史的记忆如碎片般零散,甚至是遗弃了记忆。黑人群体价值观构成了寻找黑人历史的线索,同时也为他们反抗压迫提供了力量源泉。《宠儿》中贝比·萨格斯的悲剧、塞丝和丹芙的走出阴霾并获重生都体现了融入黑人群体力量的重要性。血泪的奴隶史给黑人民族带来了巨大的心灵创伤,过去使他们不堪回首,因此,他们企图用暂时的记忆缺失来缓减伤痛,但是忘却过去不等于过去没有发生,不能正确、勇敢地面对过去就无法更好地把握现在和未来。“莫里森要向人传达的信息不仅是要记住历史,还要为了民族和团体的未来忘却历史,要在记忆中忘却。”[16]71因此,如何正确构建自我的历史文化身份是黑人能否确立自我意识的关键。
五、结束语
当代美国社会中,种族问题仍然存在,部分白人始终不能把非裔美国人当作平等的个体来尊重。而对于非裔美国人自己而言,自从他们被强行带至北美大陆以来,他们的历史被忽视、被否定,历史的断层导致文化的缺失。当代的美国黑人群体仍然很难真正融入美国的主流历史文化,部分人也不太情愿在非洲的历史文化中寻找归属感,因此,他们很难明确自己的身份,作为边缘群体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正如沃克在《寻找我们母亲的花园》中所作的阐述:“任何主体的真相,只有在故事的方方面面被聚合到一起,所有不同的意义形成一个新意义时,才能被呈现出来。”[17]49莫里森致力于用艺术手段还原最真实的历史,反思和质询最真实的美国奴隶制,还原那个制度下黑人的真实的生存状态,并借由这种回忆,帮助当代非裔美国人了解自己的过去,面对历史记忆,踏上文化旅行,找寻自己的文化之根,塑造自己的文化身份并合力推进非裔美国文化的发展。毋庸置疑,这便是黑人女作家的文学努力所具备的非同寻常的意义。
[1]毛信德.美国黑人文学的巨星——托妮·莫里森小说创作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2-3.
[2]王守仁,吴新云.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与二十世纪美国黑人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5.
[3]胡全生.难以走出的阴影——试评托妮·莫里森《心爱的人》的主题[J].当代外国文学,1994,(4):163-167.
[4]Singh A,Skerrett Jr J T,Hogan R E.Memory and Cultural Politics[M].Boston:Northeastern UP,1996:157.
[5]McKay N Y,Earle K.Approaches to Teaching the Novels of Toni Morrison[M].New York: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1997:78.
[6]董俊峰.六千万黑人冤魂的投诉——《娇女》主题初探[J].外国文学研究,1994,(4):73-77.
[7]Capra D L.Representing the Holocaust:History,Theory,Trauma[M].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4:200.
[8]Taylor-Guthrie D.Conversations with Toni Morrison[M].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4:257.
[9]托尼·莫里森.宠儿[M].潘 岳,雷 格,译.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130-195.
[10]Morrison T.Playing in the Dark[C]//Literary Theory:An Anthology.Julie Rivkin,Michael Ryan,eds.Macaden,MA:Blackwell Publishing,2004:1006-1008.
[11]Morrison T.Living Memory:Toni Morrison Talks to Paul Gilroy[J].City Limits,1988,(13):10-11.
[12]托马斯·勒克莱尔.“语言不能流汗”:托妮·莫里森访谈录[J].少 况,译.外国文学,1994,(1):24-28.
[13]Middleton D L.Toni Morrison's Fiction:Contemporary Criticism[M].New York &London:Garland Publishing,Inc.,2000:214.
[14]Wilson M.The African American Historian:David Bradley's The Chaneysville Incident[J].African American Review,1995,29(1):97-107.
[15]金艳丽.托妮·莫里森《宠儿》中黑人民族对自我的追寻[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4):241-244.
[16]王湘云.为了忘却的记忆——论《至爱》对黑人“二次解放”的呼唤[J].外国文学评论,2003,(4):71.
[17]Walker A.In Search of Our Mothers'Gardens[M].San Diego:Harcourt,1983: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