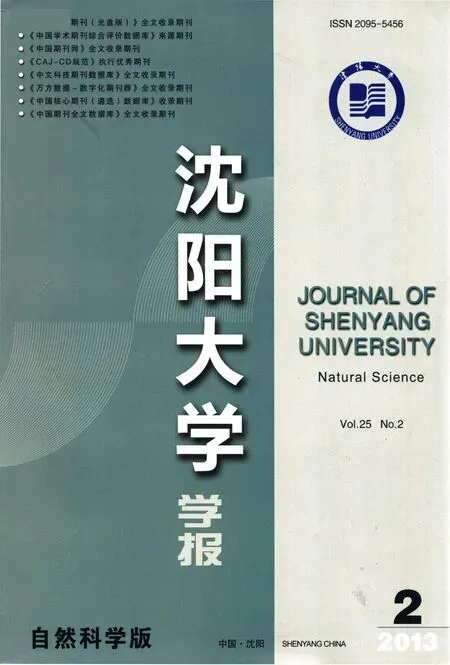市场份额责任模式之选择——从与共同危险责任的区别角度
林 耕 宇
(福建师范大学 法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8)
近年来,我国大规模产品侵权案件频有发生。从早年的“龙胆泻肝丸”案,到2008年的“问题牛奶”系列案件①在"龙胆泻肝丸"案中法院判决被告因无法满足侵权法对因果关系的要求而败诉,"问题牛奶"案是通过行政手段才得以较为妥善解决的。。,再到近年的饮料塑化剂及“毒胶囊”等事件,司法实践的事实表明,我国现有的侵权法体系在应对因果关系不明的大规模产品侵权案件时已显得力不从心。有不少学者呼吁通过借鉴美国侵权法中的市场份额责任制度来填补我国侵权法制度在这个方面规制的空白。市场份额责任制度始于20世纪80年代,但是经过了30年的发展并未形成一个得到统一认可的制度体系,而是在众多法院对其的司法实践过程中发展出了多种理论与制度模式。因此,我国在借鉴市场份额责任制度之前首先对这些理论制度作出厘清是十分重要的。共同危险行为责任与市场份额责任制度具有一定的渊源,在制度设计上也有相当的相似性。本文拟通过对比市场份额责任与共同危险责任的关联与差别来对两种代表性市场份额责任模式——加州模式与纽约模式的理论与制度作出分析,探讨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的市场份额责任模式。
一、市场份额责任之阐释
在美国,市场份额责任理论是在乙烯雌酚(DES)系列案中运用并得以发展的一种理论。“DES案件”发生于美国1980年前后。DES是一种人工合成的雌性激素,用来避免孕妇流产,是一种防止流产的通用且无商标的药品。在1970年前后,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指出这种药物会导致乳腺癌,也正式确认了含有DES药品的致害性和风险性,服用过此类药物的妇女生育的女性后代在成年后可能因此患癌症。随着含有DES成分药物的缺陷被美国FDA 公布,全美出现了许多消费者因DES的副作用而起诉制造商过失的诉讼。然而,在所有“DES 案”中的受害人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尽管能证明损害源自DES,但因年代久远,销售记录灭失、产品具有同一性等原因,在客观上造成了受害人普遍不能证明到底是哪个厂家的产品导致了损害,因而达不到传统的举证要求。如果法院坚持传统的举证规则,那么只能判决原告败诉,这将使得无辜的受害人得不到救济,有违实质公平。为了实现对DES药品受害人的救济,市场份额责任理论应运而生,并且在不同的法院司法实践中发展出了不同的模式,其中以辛德尔案为代表的加州模式与以海默茨案为代表的纽约模式最具代表性①市场份额责任的模式不仅限于这两种,美国许多州法院都通过判例确立了各具特色的市场份额责任模式,出于篇幅限制,文中无法对所有模式作出介绍。。
1.加州模式
1980年加利福尼亚高院的辛德尔案(Sindell V.Abbott),是市场份额责任的第一次司法实践。加利福尼亚高院在审理辛德尔案时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工业化的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了具有可替代性的商品,这些商品有可能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却无法被追踪到任何特定的生产者,面对这种进步,法院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执着于传统的理论学说,要么跟上时代的步伐,满足时代变迁的需要,而在DES案中,相比有过错的生产商,无辜的被害人更值得保护。加利福尼亚高院通过在之前的选择责任判例(等同于大陆法的共同危险责任)中寻求突破,创造性地提出了市场份额责任的概念②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在“辛德尔案”中的判决就是沿用自同是加州判例的“萨默斯枪击案”。在“萨默斯枪击案”中,原告与两位被告同属于某一打猎协会的成员。外出打猎之时,两位被告因过失同时向原告所在方向射出了一颗子弹,其中一颗子弹击中了原告的眼睛。原告无法证明究竟是其中哪一位被告的子弹击中了其眼睛,但是能够证明两位被告都因过失而发射了子弹。[1]。根据加州模式的市场份额责任,原告只需做到以下三点就可以主张被告的责任:①证明自己受到DES 药物侵害的事实;②每个被告都生产了此类DES产品;③起诉的被告占有足够市场份额比例(法院并未说明何为足够比例,该案中原告起诉5 家当时占有市场份额最大的企业,共占有90%的市场份额)。只要条件得到满足,被告就必须依据其各自的市场份额承担责任,但是法院还赋予被告自证免责的权利,被告可以通过证明其产品不可能造成原告的损害来对抗原告的诉求。在辛德尔案中法院没有说明被告承当的是按份责任还是连带责任,但在之后的Brown V Superior Court案中,加利福尼亚高院明确指出了连带责任有违市场份额责任初衷,被告承担的应当是按份责任。
2.纽约模式
1989 年的海默茨案(Hymowitz V.Eli Lilly),是继辛德尔案之后的另一个市场份额责任的重要判例。有学者这么评价:“海默茨模式是继辛德尔模式之后唯一能称得上模式的市场份额责任类型,而不仅仅是辛德尔模式的变种。纽约模式将对产品责任体系有着与辛德尔案不相上下的影响力”[2]。纽约州上诉法院在审理海默茨案时将市场份额责任的基础认定为是生产商的产品宏观上造成的社会公众的损害,而不是个别案件中的事实因果关系,认为“分配责任时应当使各个被告的责任与其宏观上(overall)的过错相一致,这种过错的大小是通过每个被告的行为对广大公众(public-at-large)造成危险量来衡量的”[1]。在制度的设计上,纽约模式与之前的加州模式存在较大的区别。在纽约模式中,被告即使能够证明自己并未造成原告损害也必须承担责任,唯一的免责方式是证明自己从未生产供孕妇使用的DES药品,在市场份额数据的选择上,纽约模式采用了更加稳定准确的全国市场份额数据作为判决的依据,另外,纽约模式出于避免被告承担过重责任以致影响产业的发展的考虑,认为被告承担的责任份额应当严格限定在其所占有的市场份额比例内,因此,如果原告无法起诉足够的被告将无法获得相对足额的赔偿。
二、市场份额责任与共同危险责任之比较
共同危险行为责任是我国侵权法制度中现有的一种适用于侵权人不明情况下的侵权责任规则制度,《侵权责任法》第10条规定:“二人以上实施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其中一人或者数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能够确定具体侵权人的,由侵权人承担责任;不能确定具体侵权人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共同危险责任指的是数人实施的危险行为都有造成他人损害的可能,其中一人造成了他人损害,但不知数人中何人造成实际损害[3]。通过对比共同危险责任制度与市场份额责任制度可以发现,二者在适用情形上存在着相当大的相似性。首先,二者都涉及了多数的加害主体,在共同危险行为责任中存在数个实施了危险行为的行为人,这些行为人的行为均有可能造成被害人的损害,而在市场份额责任中则涉及到了市场中所有的生产同质性产品的产商,这些产商的产品均投入了市场并且被消费者购买。其次,无论是共同危险责任还是市场份额责任,受害人均由于加害行为或者缺陷产品性质的原因无法证明具体的加害人,两种责任形式都存在因果关系证明的客观不能性[4]。
共同危险行为责任与市场份额责任存在的上述相似性使得人们很容易对这两种责任产生混淆和误解,以致二者常常被混为一谈。即使是一些主张市场份额责任与共同危险责任存在区别的学者,在谈二者的区别时也通常仅仅论及在共同危险责任中原告可以起诉所有的危险行为人,而市场份额责任中受害人出于客观原因限制无法找到所有的危险行为人以及在责任承担上存在按份责任与连带责任之差[5]。事实上,市场份额责任与共同危险责任存在着更为本质的区别。
其一,市场份额责任与共同危险责任在制度设计上的适用案件类型上存在区别。共同危险责任适用于一般的侵权案件,虽然存在多个危险行为人,但是一般仅涉及一个受害人和一个损害结果,且案件独立存在并不与其他案件相关。而市场份额责任是设计用来应对大规模侵权案件的。大规模侵权产生于工业化大生产背景下,指的是基于同一个侵权行为或者多个具有同质性的侵权行为,给为数众多的受害者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具有因果关系复杂,受害人分散等特点[6]。在这样的大规模侵权中,不仅存在多个致害产商,还涉及众多的受害人和损害结果,因此,一次大规模侵权事件有可能引发许多互相关联的个体诉讼。
其二,市场份额责任与共同危险责任在责任承担的基础上存在着区别。在共同危险案件中,虽然存在多个侵害行为,但是通常只有一个侵害行为造成了实际损害,也就是说,假设一个共同危险案中的加害关系可以通过证据证明得清晰明了,则只有造成实际损害行为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其余行为人可因其行为并未造成实际损害而无需承担责任。共同危险行为人承担责任的基础是各个行为人参与对他人人身财产安全构成危险的行为本身,证明了他们主观上具有疏于注意的共同过失,这种共同过失把共同危险行为人联结成一个共同的行为主体,主观上的可责难性与行为危险的共同性,使得所有危险行为人共同为受害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7]。而有所不同的是,在适用市场份额责任的DES案中,各个药品产商所生产的每件计入市场份额数据的DES药品,均通过市场进入社会并被消费,也就是说,虽然无法确定具体的受害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各个产商的行为都造成了损害后果(虽然不一定是造成了原告的损害,但是一定造成了其他消费者的损害)[8]。诺假设案件的加害关系可以被证明,则每个产商的加害行为都将与一定的损害后果相联系。而每个产商所占有的市场份额比例的大小,大致上代表该产商所造成的损害总量的份额(不少人认为市场份额责任中的市场份额数据代表的是原告使用某产商产品的可能性,比如一家占有20%市场份额的产商,消费者在货架上选取其产品的概率就是20%,这其实是一种误解)[9]。至此,可以看出市场份额责任与共同危险责任的一个重要区别:市场份额责任各加害行为均造成了实际损害,而共同危险责任一般只有一个加害行为实际致损;市场份额责任的案件中,每一个被告厂商的行为都必定会造成损害的后果,因此,在市场份额案件中承担责任的基础并非是行为的危险性,而是造成实际的损害。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虽然市场份额责任与共同危险责任存在一定的相同点,但是本质上二者是两种不同的责任制度。市场份额责任最初发展自共同危险责任制度,并不意味着市场份额责任属于共同危险责任范畴,或者说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共同危险责任,市场份额责任应当被视为是与共同危险责任并列的一种制度,同属于侵权法在因果关系不明时的责任分担制度体系。
三、我国市场份额责任模式之抉择
1.加州模式与纽约模式在制度取向上的区别
市场份额责任和共同危险责任都属于侵害因果关系不明情况下的责任模式,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这些责任模式都不是人们在解决侵权纠纷中首选的责任形式,只有在因果关系的证明存在客观上的困难,适用一般的侵权责任规则无法发挥侵权法应用的救济功能的情况下,市场份额责任与共同危险责任才有适用的空间。作为一种替补性、第二性的责任形式,市场份额责任在其制度设计上,应当尽可能使案件的结果与因果关系明确的情况下采用传统侵权法规则得出的结果相当。能否较好地做到这一点是衡量市场份额责任制度设计合理性的重要标准。加州模式和纽约模式体现了市场份额责任在追求这个目标上的两种不同的制度取向。加州模式鼓励被告通过举证证明自己的产品不可能造成原告损害或者造成的损害比例较小,以缩小可能的致害人范围,在市场份额数据的选择上采用尽可能细化的地方性市场份额数据作为责任分担的依据。可见加州模式市场份额责任倾向于追求个案的精确性,力图使个别案件判决更加精确地反映该案真实的情况。而纽约模式将市场份额责任的基础认定为是生产商的产品宏观上造成的社会公众的损害,而不是个别案件中的事实因果关系,限制被告的自证免责,并且在市场份额数据的选择上采用全国性市场份额数据作为责任分摊依据,可见纽约模式注重的是宏观上责任分担的公平,力图使各个厂商最终承担的责任总量与其造成的损害相当。
2.市场份额责任模式选择之分析
辛德尔案作为最早的市场份额责任案件,加州高院在其审理过程中参照之前的共同危险责任案件,提出了最初的市场份额责任概念,因此,加州模式的市场份额责任一定程度上受到共同危险责任制度框架的局限,这种局限性的一个集中体现就是二者在制度取向上都倾向于追求个案的精确性。上文已分析了市场份额责任与共同危险责任的区别,共同危险责任案件通常就是以个案的形式存在,仅存在一个实际致害人和一个受害人,因此共同危险责任制度追求个案精确性没有任何问题,如果因果关系能够得到证明,根据一般侵权法规则,案件的结果将是实际致害人承担受害人的所有损害赔偿的责任,没有造成损害的共同危险行为人不承担责任,尽可能缩小致害人的范围可以使案件的结果更为接近因果关系明确时的结果。而市场份额责任是适用于大规模侵权案件的制度,在市场份额责任案件中往往涉及众多被告产商和数量巨大的受害人,致害行为与受害人损害之间的因果对应关系也远远比共同危险案件复杂。一次大规模侵权往往会引发许多大大小小的相互关联的个体诉讼,案件之间的关联性意味着在对这些诉讼作出考量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当前的案件,而更应当注重于考量各个厂商最终承担责任总额是否恰当。
在市场份额责任案件中产品具有同质性,相同单位的产品造成的损害是相同的,因此,有理由相信如果市场份额责任案件中的因果关系能够得到明确,每个产商最终承担的责任总额是与其所占有的市场份额相当的。一种合理的市场份额责任制度设计,应当使得各个厂商最终承担的责任总额趋近于其所占有的市场份额。加州模式的市场份额责任虽然可以使个案中的责任承担趋近于该案的真实情况,但是一味地追求个案的精确性并不能有助于各个致害厂商最终承担的责任总额更加接近于实际情况。事实上,在市场份额责任案件中,厂商能够自证免责往往并不是因为其比其他厂商尽到更多的注意义务或者是生产的产品更加安全,而仅仅是因为恰巧没有在特定的时间或者地点投放产品或者是没有生产具有某种特定特点的产品,这种免责具有随机偶然性.正如一些学者评价的,对于厂商来说,这就相当于一笔“意外之财”(windfall)[10],而对于整个侵权案件的结果来说,这种免责是一种无谓的变量,使得厂商最终责任的分配偏离其市场份额。而反观纽约模式市场份额责任,否定了被告主张自己并未造成原告损害而逃避责任的免责制度,对于将致害产品投入市场的被告严格按照其市场份额课以责任,这样的制度设计从整体上保证了每个被告承担的责任总额的比例与其市场份额相当,这保证了案件的最终结果与因果关系明确的情况下能得出的结果总体一致。有质疑观点认为,纽约模式市场份额责任要求未造成原告损害的无辜被告人为他人的行为承担了责任,是将侵权责任建立在纯粹风险的基础上,违背了侵权法传统中的结果责任与自己责任的原则。此观点其实是混淆了市场份额责任与共同危险责任的情形,上文已经论述了二者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市场份额责任中各个产商都实际造成了消费者的损害,所谓的“无辜的被告人”并不存在,各个被告是根据各自造成的实际损害承担责任的,所以纽约模式并未违背侵权法的传统规则。
此外,纽约模式市场份额责任在美国司法实践中最大的障碍在于美国实行的双轨制的立法司法体制。由于美国各个州都有各自的法律,各州的法院对案件的审判也不受联邦和其他州的制约,故若无法说服所有州的法院都接受海默茨案审判的理念,则纽约模式力图在宏观层面使各个厂商最终承担的责任总量与其造成的损害相当的目的是难以实现的。但在我国并不存在这一问题,我国属单一制法律体制,全国范围内适用同一部侵权法,而且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具有指导作用,因此,在我国法律体制下推行纽约模式市场份额责任的困难要小得多。
四、结 论
科技与社会的进步总会带来新的侵权行为类型,我国工业化大生产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大规模侵权事件的发生,通过借鉴美国市场份额责任制度使我国侵权法体系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实属必要。加州最高院在辛德尔案中通过借鉴共同危险责任判例创造性地提出了市场份额责任的概念,但是作为最初的市场份额责任形式,加州模式的市场份额责任难免局限于原共同危险责任制度的框架。纽约模式市场份额责任在辛德尔案的基础上对市场份额责任制度有了进一步发展,摆脱了共同危险责任专注于个案的制度取向的影响。注重整体上责任分担公平的纽约模式市场份额责任,更为契合DES 案这样的大规模侵权案件。因此,相对于加州模式市场份额责任,纽约模式的市场份额责任制度对于我国更具有实际的借鉴价值。
[1] WF EBKE.Market Share Liability[J].J.S.Afr.L,1999(4):665-683.
[2] Andrew B.Nace,Market Share Liability:A Current Assessment of A Decade-old Doctrine[J].Vanderbilt L.Rev,1991(44):395-407.
[3] 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研究:上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546.
[4] 马新彦,孙大伟.我国未来侵权法市场份额规则的立法证成——以美国侵权法研究为路径而展开[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1):93-101.
[5] 怀宇.市场份额责任理论刍议[J].人民司法,2006(6):84-86.
[6] 杨立新.《侵权责任法》应对大规模侵权的举措[J].法学家,2011(4):65-76.
[7] 杨立新.侵权法论[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546.
[8] 阿瑟.利普斯坦,本杰明.兹普斯蒂.产品质量侵权时代的矫正正义[M]∥格瑞尔德.J.波斯特马.哲学与侵权行为法.陈敏,云建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95.
[9] 谢远扬.论侵害人不明的大规模产品侵权责任:以市场份额责任为中心[J].法律科学,2010(1):98-106.
[10] Deborah L.Pagan,Products Liability-Hymowitz V.Eli Lilly &Co.:The Purist's Form of Market Share Liability Applied to DES Cases[J].Memph.St.U.L.Rev,1990(20):667-6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