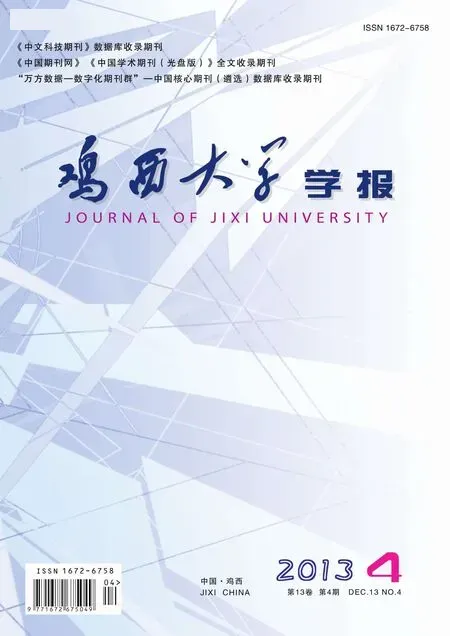语用学视角下的语用意义与语境
钟福连
(福州大学 阳光学院,福建 福州 350015)
语用学视角下的语用意义与语境
钟福连
(福州大学 阳光学院,福建 福州 350015)
语用学的发展具有先慢后快的趋势和明显的阶段性,对语用学的研究离不开对语用意义和语境的研究。当前语用学著作似乎对语用意义或语境的讨论远远不够,这与两者在学科内的核心地位极不相称。本研究认为,语用意义并不是一种具体意义,语境意义、非自然意义、施为用意和特殊含意实指语用意义,语境研究包括研究其生成条件或构成要素两条路径,而动态的认知语境观利用关联这个常量来分析语境,因此能够恰当地代表语用学学科的语境。
语用学;语用意义;语境
回顾语用学这一学科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它具有先慢后快的趋势和明显的阶段性。19世纪30年代末期,Pierce、Morris及Carnap等将语用学并入符号学的哲学研究领域。[1]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末,Austin、Searle及Grice等语言哲学家对言语行为和会话含意理论的研究尽管造诣颇深,但仍停留于哲学研究领域。20世纪70年代,《语用学杂志》(Journal of Pragmatics)的出版发行,[2]意味着语用学已成为一门新兴学科。20世纪80年代以来,语用学更是快速发展,1986年成立的国际语用学会(IPrA),使得语用学的研究迈上了新台阶。如今,语用学的学科独立性和良好发展前景日益显现,再也没人怀疑它的学科地位。
研究语用学,很难绕开语用意义和语境。《新编语用学概要》把语用意义和语境定为语用学研究的两个基本概念,但不可否认的是,语用学研究的意义很宽泛,包括语用学的意义、语用意义和其它意义等;对语境的研究也在语用学、语言学和社会学等不同学科视角下进行着。国内语用学对语用意义与语境的研究,可谓众说纷纭,却又语焉不详。有人认为,语境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既明确又模糊。语用意义亦是如此。
1923年,Malinowski提出了“语境”的概念。1983年,Leech将“语用意义”和“语境”列为语用学研究的两个核心概念。[3]如果说语用学是一门研究在特定语境下言语(说话人意义)如何生成和理解的学科,那么,语用意义和语境作为语用学的核心概念便迎刃而解。但遗憾的是,当前虽然许多语用学著作字里行间提及了语用意义或语境,但是并未独辟章节来专门讨论语用意义或语境。笔者认为,这显然与语用意义和语境的核心地位极不相称。
一 语用意义
语用学研究意义,具体来讲,研究说话者在使用或交际中的语言符号如何生成意义,它的几个传统课题,如“指示语”、“含意”、“前提”等,均以意义为目标。语用学研究在特定交际环境下的语言运用、理解与交际,因此它要研究意义。关于语用学研究的在特定环境中生成和理解的“意义”应界定为何种意义,就不得而知了,有学者认为它是语用意义,外延广至语境中使用语言所传达的一切内容。但是,国内语用学著作并未讨论意义之“意义”——语用意义,只是提到了各种名称的“意义”。
1.抽象意义与语境意义。
一些语用学者认为,语用学与语义学均研究意义,但前者研究具体(实际使用中)意义,后者研究抽象意义。抽象意义,就是语言形式自身的意义,它与语境之外的意义是迥然不同的,Thomas认为,它包括非语境意义、词汇意义、语义意义或语言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说,抽象意义与语境意义是一组相对意义。然而,也有学者表示,语义学研究抽象意义而语用学研究语境意义,但两者并非完全独立于所属学科——在言语交际中,听话人能否从抽象意义的层面过渡到语境意义的层面,取决于词义、指称意义和结构意义是否明晰。也就是说,听话人要推导出说话人意欲表达的含意(语境意义之一),必须先琢磨清楚其话语语言形式表达的抽象意义。因此,抽象意义和语境意义是语用推理过程中两个层面的意义。倘若语用意义包含语境中使用语言所传达的全部内容,则“语境意义”似乎可以理解为语用意义,而“抽象意义”并不是语用意义。
2.自然意义及非自然意义。
Grice认为,语用意义可划分为自然意义及非自然意义。[4]前者自然地映射事物的内部特征,不需人为修饰;后者则指交际者在具体交际场合下表达的意义,包含一定的人为因素。语用学研究非自然意义——揭示非自然意义如何得以表达和理解。按语用学的研究性质,此“非自然意义”即为语用意义。
3.话语意义与施为用意。
话语意义,是说话人在特定话语中阐释的字面意义,直白易懂;施为用意,相当于会话含意理论中的含意,指说话人的特定话语所表达的真正用意,它需要透过字面层面来理解,这就表明它也是语用意义。施为用意似乎也可理解为语用意义。
4.一般含意与特殊含意。
某些学者认为,一般含意和特殊含意是会话含意的组成部分,但两者的产生时机并不一致。前者是在说话人遵守合作原则中某项准则时产生的;后者则是在说话人明显或故意违反合作原则的某项准则时产生,甚至在遵守合作原则的某项准则时也可能产生。[5]两者的依赖机制也不一样,前者不需要依赖特定语境;但后者则倚重于特定语境。语用意义离不开言语交际的具体语境,无论是语言单位还是非语言单位,均可能产生语用意义。语言单位产生的语用意义,表现形式多样,有语义变异、语义辑合和语义分解;而非语言单位产生的语用意义,主要依靠话语结构和非语言手段来体现。语言单位的语义改变涉及语境因素,属于语义学和语用学关注的共同问题,而非语言单位的语用意义仅是语用学关注的问题。看来,特殊含意的达成必须借助语境的辅助,因此可以把它归为语用意义。Marmaridou认为,语用意义产生在认知的基础上,由此她提出了语用意义的认知假设。
上述研究表明,语用意义指的是说话人在实际言语交际中意欲表达的意义,或是听话者根据交际目的成功地推断出的说话人意义。语用学所涉及的意义十分广泛。笔者因而尝试地得出,语用意义不是一种具体意义,语境意义、非自然意义、施为用意和特殊含意实际上指的都是语用意义,名称不同而已。而对语用意义的判断理应成为研究语用学性质的重要依据。
二 语境
语用学研究在特定语境条件下的话语生成和话语理解,因此语境作为语用学的核心概念就迎刃而解了。但是,对于什么是语境,可谓说法不一。在Malinowski认为语境包括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的基础上,Firth提出了语言语境或言内语境;[6]Halliday 和 Hasan则将对语境的研究向纵深推进,提出了语域理论,对情景语境进行了分析,阐明它的构成要素有语场(field)、语旨(tenor)和语式(mode)。[7]胡范筹和樊小玲从对语境的认知模式出发,认为语境的解释包括常识性的解释和分析性的解释。现代语用学指出,语境不仅包括言语的上下文,而且也包括语言活动所处的客观条件和社会背景。Versehueren语境观认为,语境划分为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是在交际双方使用语言过程中生成的,且不会一成不变,将伴随着交际过程的发展而变更。[8]笔者以为,语境分析有研究其生成条件和构成要素两条路径可以选择。胡范筹和樊小玲的研究属于前者,Malinowski、Firth、Halliday和Hasan及现代语用学的研究属于后者,而Versehueren的研究则综合了以上两条路径。Grice语境观,Sperber和Wilson语境观在语用学领域内的代表性堪称首屈一指。如今,人们往往通俗地把前者称为传统语境观,而把后者称为现代语境观。其实,这两者都研究了语境的生成,但区别却很明显:它们分别将语境归属为静态和动态,前者认为交际双方是被动的,后者认为语境是听话人对世界的一种假设。
1.Grice语境观。
说话人依照合作原则进行交际;听话人依托语境,根据说话人对合作原则的践行情况,判断其表达的会话含意。Grice语境观的基本假设是,说话人总体上遵守了合作原则,听话人据此并结合其它相关语境因素,从说话人违反准则的依据推断其表达话语的会话含意。Grice的语境观虽未解释语境的含义和构成,但推出了一个观点,即语境是合作原则推理过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笔者认为,Grice语境观对交际中的语境假设尚有较大发展空间,还有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亟待探究。
2.Sperber和Wilson语境观。
在传统语境观看来,语境早在会话之前就已存在。人们总体认为,传统语境中各种要素对于实现语用推理非常关键,但类似语境观并不能清楚地剖析语用推理的实际过程,也不能真实地反映不同交际主体的认知心理。与此相反,Sperber和Wilson将语境概括为一种心理建构体,称它为一系列假设,存在于听话人的大脑中,影响着话语解释。[9]Sperber和Wilson语境观的核心内容在于:其一,语境是一个变量,它并非事先给定,而于交际中产生。其二,侧重话语的“明说”意义和“暗含”信息。[10]“明说”作为说话人清楚的表述,一目了然;而“暗含”则是说话人为了增进话语的关联,需要听话人加以推理。其三,构建语境要以寻找最佳关联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交际这个认知过程中,听话人和说话人能否默契配合,取决于关联性这个最佳的认识因子。关联原则使听话人不但懂得说话人明说了什么,而且明白说话人暗指了什么。其四,“互明”这一认知环境由交际双方共享,其重要性不容置疑。Sperber和Wilson的语境观围绕着听话人,视关联为制肘交际过程的基本因素,是个常量;语境是个心理建构体,是个变量。从语境的研究路径来看,Grice语境观与Sperber和Wilson语境观都是分析语境的生成,但是后者的研究似乎更为深入成功。此外,语用学领域内,Brown、Levinson和Leech等人对语境在话语中扮演的角色也作了重要的研究;Leech认为,语境是交际有关主体都具有的知识储备,能促进听话人理解说话人的话语。
三 结语
Marmaridou基于语用意义的理论角度,指明了语用学研究的三个视角:哲学、认知和社会,这一道明语用学与认知语言学交叉研究的理论构建模式,实际上与Sperber和Wilson的认知语用学一脉相承。语用学研究具体交际中的语言,离不开语用意义和语境。具体交际中的语言(言语)所生成的意义即为语用意义。
理解语用学学科首先必须牢牢把握学科关键点,尤其是语用意义和语境这两个核心概念。关于意义的研究,一些学者强调应避免语义、语用二分法和一刀切的模式。离开了具体的语境谈论语用意义,就无法正确领会说话人的表达意图。深入讨论语用意义和语境会使我们有效地领会谈话人的表达意图,使交际有序有效。另外,语用学近三十年发展迅猛,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相关论文和专著不断问世,语用学者只有紧紧把握学科发展脉搏才有可能驾驭学科。
[1]赵虹.论语用学的哲学渊源[J].科技信息,2008(30):190.
[2]涂嵘.语际语用学与大学英语文化教学[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116.
[3]陈海威.从合作原则、礼貌原则和身份原则看王熙凤的语用策略[D].杭州:浙江大学,2006.
[4]张树筠.会话含意与听力教学[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85.
[5]崔建立.含意阶段性特征的语用视角阐释[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157.
[6]胡霞.语境研究的嬗变[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105.
[7]董育宁.新闻评论语篇的语言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07.
[8]胡霞.认知语境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05.
[9]蓝岚.国外语言学界语境研究概述[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136.
[10]马崴.关联理论对合作原则的几点修正[J].襄樊学院学报,2008(6):62.
ClassNo.:H03DocumentMark:A
(责任编辑:郑英玲)
Pragmatics:PragmaticMeaningandContext
Zhong Fulian
(Sunshine College of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15,China)
The pragmatics discipline, with two core concepts of “pragmatic meaning” and “context” has undergone the developing stages of “first slow later fast”. Up to now ,the academic discussion of these two concepts, even in the pragmatics works published, is far from satisfactory. What are the pragmatic meaning and context in this discipline?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former does not refer to one specific meaning; instead, it is named in other names but means the same thing. Furthermore, the study of the latter is that of either the generation factors or the component parts. Based on relevance, Sperber and Wilson’s dynamic context theory could properly explain the context in the pragmatics discipline.
Pragmatics; pragmatic meaning; context
钟福连,硕士,讲师,福州大学。
1672-6758(2013)04-0130-2
H03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