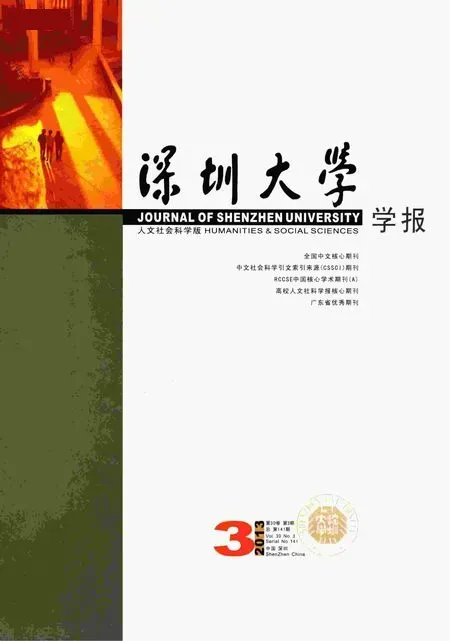论网络环境下人格权侵权的惩罚性赔偿
陈年冰,李 乾
(1. 山东大学法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2.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我国已经是全球网民数量最多的国家。 依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3 年发布的报告, 截至2012 年底,我国的网民数量已达到5.64 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到4.2 亿, 微博个人用户达3.09 亿[1]。随着网络社会的强势崛起,社交网站正逐步成为人们表达自我观念、参与公共讨论的平台。 《时代》总编查德·斯坦格尔指出,Web2.0 的迅猛发展使得网民的原创性内容呈现爆炸性地增长, 影响力与日俱增[2]。 在大众网络时代,个体之间的互动性普遍增强,但同时也导致人肉搜索,个人信息泄漏,侮辱、诽谤他人等侵犯人格权益的事件频发, 这意味着在网络环境下,自然人的人格权比现实社会更容易受到侵害,且后果更加严重。 人格权本质上是一种精神性权利,主要体现的是精神性利益。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更由于网络传媒业的发展,人格权越来越多地体现出财产权的特征,人格权的商业化将成为一种趋势,王利明教授认为,“除了生命、健康、自由等权利之外, 几乎其他所有的人格权都可以商品化”[3](P23)。 借助于网络的传播功能,名人的姓名权、肖像权等进行商业化利用的价值越来越大,并且人格权的商业化利用已不再是名人的 “专利”,“任何人都有将自己的人格利益进行商业化利用的可能。 ”[4]权利人通过对具有财产价值的人格权进行商业化利用或者通过合同允许他人进行商业化利用,并获取报酬。 当这些人格权受到侵害后,允许权利人通过财产损害的方式进行救济也就成为必然。笔者试图通过本文说明, 在复杂的网络环境下人格权侵权仅适用补偿性赔偿已难以实现救济上的衡平性以及正义性, 应当积极探索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建立。
一、补偿性赔偿已不能完全适应现实的需要
当前,网络环境下人格权侵权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侵权内容的动态性。 网络信息瞬息万变,新发布的内容短时间内就可能变成历史记载。 侵权行为人运用免费的网络资源,通过建立自己的博客、微博,大量散播侵权内容,再由无数网民的跟帖、传播,侵权内容如同滚雪球一般,具有规模性且处于动态扩张状态。 另一方面,侵权内容可以制作成BT 文件,永久性地保存在互联网空间,也可以脱离互联网储存在电脑终端。 这些侵权内容犹如一颗不定时的炸弹,随时都会在网上重现。 一言以蔽之,一旦人格权在网络环境下受到侵犯,侵权内容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第二,侵权行为的隐蔽性。网民在网络上的身份是虚拟存在的,在非实名制网络的环境下,每个网络用户的身份都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例如,在任何一个有网络的地方, 侵权人都可以匿名地发帖散布侵犯他人隐私、名誉的信息。
第三,传播范围的广泛性。网络社会高速的传递性和远程的流通性导致人格权被侵害后, 传播时空范围的不可测性。网络是一个开放的平台,一旦信息进入网络领域,个人信息遭到泄漏以后,我们难以估测出会有多少人,以及什么样的人会获取该信息,获取信息之后的用途也难以预测。 这种不可测性对主体的人格利益及财产或将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全球各地的网络用户可以随时在服务器上浏览、 下载侵权内容。《淮南子·说山训》中提到的“众议成林,无翼而飞,三人成市虎,一里能挠椎”只是对现实世界谣言蛊惑后果的描述, 而在网络环境中借助于现代的信息传播手段, 网络侵权的损害后果呈现全球化的趋势。
第四,损害后果的多样性。在现实空间的精神性人格权的损害主要涉及的是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而网络环境下侵害人格权所导致的损失则不仅涉及精神损害,还会更多地涉及财产损失。侵权行为涉及侵犯隐私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等。 在网络环境下,企业普遍存在“信息饥渴症”,侵权行为应运而生,据新闻报道,我国有近2 亿条公民个人信息被非法买卖, 多名持卡人被盗刷信用卡累计达200 余万元[5]。 据《2011-2012 中国互联网安全研究报告》,我国有84.8%的网民遇到过网络信息安全事件困扰,总人数达4.56 亿。 这些事件包括个人资料泄露、网购支付不安全等,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94 亿元,人均损失553.1 元[6-9]。 涉及侵犯其他人格权的案件也比比皆是。Google 侵犯隐私权案是一个典型的案件。与传统的人格权侵权相比, 受害人受到的物质损失更为严重,且难以防范。网络环境下的人格权侵权的物质损失既包括直接损失也包括间接损失。
第五,损害后果的严重性。侵权文件一旦被发布在网络上,将会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害,受害人的损失通常难以计算、弥补,且铸就的伤害具有不可挽回性。我国的“人肉搜索第一案”王菲案就是典型代表。2007 年,北京女白领姜岩因不堪忍受丈夫王菲的婚外情,在博客上记录了自己生命的最后2 个月,最终跳楼自杀身亡。
网络环境下人格权侵权特点的存在, 凸显出我国现有的人格权侵害中财产损失以补偿性赔偿为责任形式的救济模式的诸多缺陷:
首先,救济力度不够。网络环境下侵犯人格权的案件,侵权人会基于违法收益与成本的考量,通过违法而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微博第一案”就是典型代表①。补偿性赔偿在网络环境下难以实现实质正义。
其次,预防功能不足。补偿性赔偿规则旨在受害人个人的权益回复,填补个案的损失。侵权人尤其是网络服务商在网络侵权时通常会为了获取巨额的财产利益而铤而走险, 侵权的冲动往往抵消了对侵权后果承担损害赔偿的恐惧,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侵权人或继续实施侵权行为, 导致网络环境下侵犯个人权益的现象愈演愈烈。此外,补偿性赔偿无法对潜在侵权人起到威慑作用。
最后,维权成本高昂。 在网络社会下,网络用户的身份都具有一定的隐蔽性, 这种隐蔽性给了侵权人一道“防火墙”,在侵权行为发生后,受害人难以找到最初的侵权现场, 也不能准确地判断侵权时间和确定参与侵权的人数。鉴于证据收集的困难,受害人仅能证明部分损害, 不能获得全部损失的赔偿。 此外, 许多网络服务商在侵权过程中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了吸引网民的关注,部分论坛对于侵权帖子置顶讨论,增加点击率,提升广告收益,受害人需要花费非同寻常的成本去证明侵权事实的存在。正因为如此,受害人选择诉讼维权的几率将减少,其后果就是网络侵权愈演愈烈, 这也正是这几年网络侵权频发的主要原因。
由于以上因素的存在, 受害者的维权之路会变得更加艰难,因此,如何有效地激励受害者积极主动地寻求救济,遏制网络侵权行为的蔓延,就成为一个非常现实而紧迫的问题。 既然传统的填平损害的救济方式已不能有效地遏制侵权行为的发生, 寻求更有效的解决途径应当是必然选择。 惩罚性赔偿制度惩处侵权人高额罚金,同时激励受害人维权诉讼,对于有效地威慑、吓阻类似行为的发生,维护网络社会的正常秩序具有积极作用。
二、对美国人格权侵权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考察
在网络侵权的救济方面, 美国是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比较早的国家。 虽然惩罚性赔偿制度在美国学界、实务界一直争执不休,美国各个州的立法也不尽相同,但在美国,惩罚性赔偿制度普遍适用于保护人格利益的案件中, 无论是在现实环境中还是在网络环境下。例如,在2009 年,两名耶鲁大学法学院女生的不雅照被张贴在网络上, 受害人向法院诉求24.5 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金[10]。 美国对人格利益的保护分两个方向:以隐私权为核心,保护独居不受到干扰的精神权利;以公开权为核心,保护个人独特形象特征的财产价值[11]。波斯纳教授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构建了一个向外界不断展示的“公共自我”。对外,我们“销售”自己构建起来的公共自我,即公开权财产价值的体现;对内,我们防止人们用不实的言语伤害公共自我,即是隐私权自我独居的体现[12]。 《美国法理学》一书指出,惩罚性赔偿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有效地救济被侵害者的隐私权或者公开权。 侵犯隐私权或者公开权受到惩罚性赔偿裁判的案件在美国各州中比比皆是[13]。 美国很多州法院在涉及到隐私权或者是公开权的案件中, 当事人均诉求法院判决惩罚性赔偿金,具体适用条件是,受害人需要受到切实的损害, 侵权人实施侵权行为时要知晓受害人的真实身份,且侵权人的主观恶意比较严重。 在美国,对于侵犯隐私权或者公开权的行为的遏制采用惩罚性赔偿, 主要基于惩罚性赔偿具有以下功能:第一,惩罚当事人主观恶意的行为;第二,吓阻他人类似的不法行为;第三,阻止未来的不法行为;第四,激励当事人诉讼[14]。 在一起侵犯隐私权的典型案件中, 美国印第安纳州最高法院成功地适用了惩罚性赔偿制度[15]。
随着网络运用的频繁, 涉及网络侵权惩罚性赔偿的案例也在司法实践中出现。 例如, 被告Trans Union LLC 是全美最大的信用评估机构之一。 该公司的主要工作和收入来源就是撰写、出售个人或者公司的信用报告。该公司通过美国的银行、抵押担保公司、财务公司等途径,不断收集个人的身份信息和财务报告。1996 年至2004 年,该公司不断地暗中出卖个人信息给第三人。据统计,该公司的网络数据库每个月接受大约收集统计85 000 份个人信息报告。此外,该公司还收集个人的房产信息、税务单据等,并将这些数据信息一并出售。 作为一个信用评估机构,该公司滥用收集到的私人信息,以此盈利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受害人的人格利益。 伊利诺伊州法院初审裁决,该公司的恶意侵权行为适用惩罚性赔偿金。罗伯特法官认为, 尽管每个人受到的实际损害微乎其微,但是惩罚性赔偿金可以激励当事人诉讼,惩戒公司的不法行为[16]。
在美国,适用惩罚性赔偿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惩罚性赔偿金的适用以有财产损害为前提, 且以侵权人获利的情况作为惩罚性赔偿数额的参考。在美国诸州,法院通常要求惩罚性赔偿与实际损害之间必须具有某种相关性, 尽管这种相关性的判定十分的主观。 例如,加州法院就认为,仅在受害人的经济受到损失的情况下, 即有切实损害的前提下才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17]。
第二,主要针对侵权人主观恶意的情形。美国大多数州法院对于提请惩罚性赔偿的诉求, 通常会要求提供初步证明或者明确被告人的主观恶意。 一般而言, 行为人的主观恶意是裁决适用惩罚性赔偿金的核心要件,即“针对那些恶意的、在道德上具有可非难性的行为”[18]。 如侵权人主观是恶意的,邪恶的,有意的[19]。 适用惩罚性赔偿金的案件,需要侵权人是明知且故意而为的侵权行为。 某些不法行为也可以被视为具有主观恶意。 例如, 对于未经受害人的许可,利用受害人的声音做广告牟利。
第三,对惩罚性赔偿金的用途做出明确规定。以印第安纳州为例, 该州法院对判处惩罚性赔偿金的用途有详尽的规定。 惩罚性赔偿金数额的75%归州财政所有,这部分资金将主要划拨给一个公益组织,即州暴力犯罪基金会,由该基金会掌控。惩罚性赔偿金剩余的25%则属于受害人所有。
第四,对惩罚性赔偿金的数额做出限制。印第安纳州规定惩罚性赔偿金最高额不得超过5 万美元,佛罗里达州规定不得超出补偿性赔偿金的3 倍,新泽西州规定不得超过补偿性赔偿金的5 倍。
实际上,在美国,人们已经越来越多地认识到惩罚性赔偿在制止那些具有主观恶意的侵权行为方面的优势[20]。
三、网络环境下人格权侵权适用惩罚性赔偿的现实性分析
我国关于网络人格权保护的立法可谓先天不足,《侵权责任法》第36 条对于网络侵权问题虽有所关注,规定了网络用户、网络服务商在网络侵权中的民事责任, 但仍是以传统的补偿性赔偿为责任方式的, 对于网络时代的人格权侵权责任的特殊性的关照不够。网络世界虽然是虚拟世界,但是存在于网络世界的侵权行为仍然是现实世界的人所为, 网络空间不应当成为法治盲区。 将惩罚性赔偿制度移植到我国的网络人格权侵权责任的法律框架内, 需要考量我国当前的社会与法律环境:一方面,惩罚性赔偿制度必须与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土壤相适应;另一方面,还需要对其予以吸收、同化和改造,使其更加符合我国的现实国情。
(一)精神损害赔偿不能替代惩罚性赔偿
目前,我国对于人格权侵权的损害救济,主要采取的是精神损害赔偿。 对于精神损害赔偿与惩罚性赔偿的关系,学界有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可以通过健全精神损害赔偿法律制度, 达到充分补偿受害人的目的,不需要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 ”[21]但也有学者认为,“作为民事责任的一种, 精神损害赔偿与财产损害赔偿一样,应只具有补偿与抚慰的性质,仅限于‘填补’损害,至于其惩罚功能,应让位于专门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22]
精神损害赔偿是指侵害人不法侵害他人名誉、姓名、肖像、生命、身体、健康等人身权益,致使受害人遭受精神损害的,应给予受害人一定的赔偿金。惩罚性赔偿则是指当被告以恶意、故意、欺诈或放任的方式实施加害行为而致原告受损时, 法院以判决之方式确定由加害人或对损害负有赔偿义务的人对受害人承担超过实际损害范围的额外金钱赔偿。 惩罚性赔偿与精神损害赔偿有如下区别:第一,两者目的不同。精神损害赔偿不同于财产损失的填平损害,其目的不是为了填补受害人的财产损失, 而是为了抚慰受害人受伤的心灵, 对受害人精神上的痛楚给予物质上的弥补。 惩罚性赔偿的目的是惩罚不法行为人,防止类似的不法行为的发生。 第二,适用的前提不同。精神损害赔偿不需要发生实质性的财产损害,只要被害人受到严重的精神伤害, 即可诉求损害赔偿。 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并不以受害人实际遭受了精神损害为前提,即使没有发生精神损害,只要加害人主观上具有恶意,则可以请求惩罚性赔偿。惩罚性赔偿金与精神损害赔偿金可同时适用, 这样可以为受害人提供更加充分的保护。
(二)惩罚性赔偿是遏制侵权行为的有效手段
笔者认为,激发受害人的维权积极性,是遏制侵权行为发生的有效途径, 而惩罚性赔偿制度则是调动受害人维权积极性的有效方法, 也是当下遏制网络侵权行为的首选之举。 因为:
第一,通过惩罚不法行为人,才能有效地制裁网络侵权行为。陈聪富教授指出,侵权行为人不法侵害被害人的名誉、尊严与人格,属于“加重损害”之范畴。 此种损害无法以刑事惩罚或者一般救济原则加以救济,因而以惩罚性赔偿金补偿之[23],惩罚性赔偿是对侵权人的可责难性进行严厉惩罚, 促使社会资源配置趋近最优化的选择。 罗尔斯在“无知之幕”的背景下,提出差异原则是指“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时,适合于最少受惠者获得最大利益。该原则反映出对最少受惠者的偏爱, 希望通过某种补偿或者再分配使得一个社会成员处于一种平等的地位。 ”[24]网络已形成一个现实社会的无知之幕, 每个人都不知道幕后个体的状态。 侵权行为人在幕后发泄私怨或者谋取利润的行为成本低廉, 而受害人维权则困难重重,处于弱势地位。惩罚性赔偿制度是法律对弱者的倾向性保护,体现着法律对实质正义的价值追求。
第二,通过威慑不法行为人,预防网络侵权行为的发生。 网络社会是网民获取信息、发表言论、公开探讨问题的平台, 不是揭露他人隐私, 侮辱他人人格,侵犯他人权利的平台。惩罚性赔偿的惩戒功能是威慑功能的前提要件,“惩罚是手段, 吓阻才是真正目的”[25]。 惩罚性赔偿的威慑功能具有两层含义:第一,对加害人予以威慑。巨额的惩罚性赔偿金可以防止侵权人继续从事侵权行为;第二,对潜在的不法行为人予以威吓,以预防潜在不法行为的发生。 值得注意的是言论自由与侮辱、诽谤的界限,针对网络人格权的侵权适用惩罚性赔偿需要严格的证明标准以及程序限制,避免产生寒蝉效应,依靠“司法的智慧与正直,在个人隐私与大众知情权之间,取得适切的平衡。 ”[26]
第三,通过高额的赔偿金,激励受害人诉讼,维护网络社会的和谐秩序。“古代侵权行为法的功能并非填补受害人的损害, 而是通过复仇的方式来消除仇恨。 ”[27]而当代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不仅能填补受害人的损害,更重要的在于解决纠纷,替代当事人之间的私人报复或械斗。 “法律不会自己实施。 一定要有人来执行法律, 一定要有某种动力来推动个人使他超越规则的抽象内容及其理想正义或社会利益理想的一致性之上。 ”[28]在网络环境下,惩罚性赔偿机制通过提供利益驱动的方式鼓励受害人成为 “私人检察官”,这对于实现个案正义,维护网络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惩罚性赔偿是当下实现法律调整妥当性的需要
鉴于公法、私法的严格划分,我国对于惩罚性赔偿一直采取非常审慎的态度。但笔者认为,鉴于网络人格权侵权的特点,尤其是损害后果的严重性,应当考虑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在民事领域引入惩罚性赔偿机制是打破了传统民法刻意强调的衡平, 但实际上, 与其将那些有必要予以规制的行为统统纳入行政管制或刑事管制的范畴, 不如将其中能够通过当事人自治方式实现规制, 甚至通过当事人自治方式可以更容易并且更好地实现规制的不法行为交由当事人自主。 这种作为‘管制辅助工具’的自治规范当然不可避免地会有带有几分管制的色彩, 其功能在于借助私人的执行,来实现管制的目的,以私益为诱因,来追求公益的实现。 ”[29]规定网络环境下侵犯人格权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可有效弥补公、私法的严格划分所造成的法律调整的真空地带, 从而实现法律调整的妥当性。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对人格权的保护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挑战,需要司法和立法予以应对。 ”[3](P22)惩罚性赔偿的制度设计就是立法应对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我国已有《侵权责任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 等法律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这些法律的实施, 为我国在其它领域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提供了一定的参照。 毕竟,“我国并不存在像英美法系国家那样在侵权领域广泛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基础,因此,只能根据社会现实情况的需要,选择既可以发挥该制度功能, 又不至于引起太大负面效用的领域加以适用。因此,在我国现阶段适用惩罚性赔偿必须选择最有必要、争议最小、最有可执行性的领域。 ”[30]网络环境下侵犯人格权益的特殊性表明, 传统的救济方式已不能有效地遏制侵权行为的发生,如果符合一定的条件,要求侵权人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是非常有必要的。
四、网络人格权侵权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制度性要素
近年来已有学者关注到严重的人格权侵权应当采取特殊的责任方式,例如王利明教授指出“应在人格权法中规定网络环境下的人格权规则”[31],“对网络环境下的人格权做出特别的保护性规定”[32],“在网络侵权的情况下, 应该比现实空间中侵权损害赔偿数额更大”[33](P6)。 袁雪石认为“应对网络服务商的恶意侵权行为适用惩罚性赔偿”[34]。 王兵认为“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从一定程度上可以大大调动受害人的维权积极性。 从而减少个人信息侵权案件的发生”[35],冯军认为“网络隐私侵权责任中也应适用惩罚性赔偿”[36]。
徐国栋教授主编的《绿色民法典草案》第1634条规定, 对于故意侵害他人人格权并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法院除判决赔偿受害人损失外,还可判决向受害人支付与损失额成倍数的惩罚性赔偿金。 第1635 条规定, 惩罚性赔偿金一般为全部损失额的1倍至3 倍[37]。 需要对侵害网络人格权的损害救济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
笔者认为,在符合一定的条件时,网络环境下人格权侵权应当考虑采用惩罚性赔偿的民事责任制度。 具体而言,应主要考虑以下要素:
第一,适用前提。 在网络环境下,惩罚性赔偿金的适用以有实际的财产损害为前提。 受害人必须受到切实的物质上的损害, 包括积极财产的减少和消极财产的不增加,才得以请求惩罚性赔偿。 例如,侵权行为人擅自使用他人的肖像、声音,将它们合成视频广告投放在网站上,使得受害人积极财产减少。对于非财产损害, 受害人可以通过请求精神损害赔偿金寻求救济。
第二,适用类型。 网络环境下,适用惩罚性赔偿金的人格权需具备以下特征:第一,虚拟性。 该类人格权需可以在网络中以虚拟数字的形式实现;第二,商业性。在信息网络社会,人格权的财产权属性一面得以凸显, 网络环境下受到侵害的人格权需要具有商业价值;第三,集合性与扩展性。 网络中各种类型的人格权相互交织, 边界模糊,“人格利益的范围较之以前任何时代都有所拓宽。 ”[33](P1-2)侵权人的一个行为会侵犯受害人的数个权益。 如网络服务商收集个人信息碎片,整理后出售给第三人,该行为可能会侵犯隐私权、肖像权、个人信息等多项人格权益。符合以上特征的权利主要是精神性的人格权。
第三,主观要件。网络人格权侵权适用惩罚性赔偿,最重要的构成要件应是行为人的主观恶意。在一般情况下,惩罚性赔偿主要是针对恶意的、在道德上具有严重可非难性的行为而实施的法律措施, 因此惩罚性赔偿需充分考虑行为人的主观过错程度。 主观恶意比主观故意更注重行为的恶意动机, 追求对他人的潜在利益造成的伤害[38]。 由于惩罚性损害赔偿的主要目的是在于阻吓潜在的侵权行为人, 所以对于过失的侵权行为人不应当适用惩罚性损害赔偿,只有行为人具有主观恶意的情况才得以适用。美国至少有13 个州明确规定,必须有切实的证据证明被告具有恶意才能适用惩罚性赔偿。 单纯的过失行为,不得判定惩罚性赔偿[39]。 笔者认为即使是行为人有重大过失,也不应适用惩罚性赔偿,因为在网络环境下,出于技术因素的考量,侵权人若不熟悉电脑操作,容易误造成对受害人的侵权,但其行为并不具有严重的可非难性。
第四,主体范围。网络侵权主体包括网络用户和网络服务商。 对于网络用户,如前文所述,网络环境下恶意侵犯他人人格权的,适用惩罚性赔偿。对于网络服务商是否适用惩罚性赔偿,则需要与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6 条的规定进行衔接。一方面,若网络用户发布的内容具有明显的侵权特征, 如涉及第三人的个人信息或是已确定的侵权内容, 网络服务商没有履行事前审查、删除义务的,应与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共同适用惩罚性赔偿;另一方面,网络用户发布的内容无法准确判断是否侵权的,例如,侵权人利用他人的姓名、肖像做广告,当受害人提出删除链接的请求且具有初步证明的情况下, 网络服务商没有采取任何删除、屏蔽举动的,应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共同适用惩罚性赔偿。
第五,赔偿数额。涉及惩罚性赔偿金数额的问题主要有三个:其一,惩罚性赔偿金的基数与倍数。 惩罚性赔偿以财产损失为基础, 人格权的财产损失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机会性的损失。至于赔偿的倍数,依据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的规定是接受服务费用或购买商品价款的“1 倍”;《食品安全法》的规定是价款的“10 倍”;《侵权责任法》并未明确规定倍数,只是规定了“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规定是不得超出补偿性赔偿金的3 倍,台湾地区《公平交易法》的规定为损害的1 倍至3 倍。 笔者认为惩罚性赔偿金基数应为受害人的实际损失, 倍数应为所遭受损失的1 倍至3 倍。 其二,惩罚性赔偿金的衡量因素。 一般需要考虑以下因素:“侵权人可非难程度, 财务状况,获利可能性,受害人损失程度,以及侵权人遭受其他处罚之可能性等。 ”[40]其三,惩罚性赔偿金的去向。在美国,惩罚性赔偿制度设计之目的并非完全是为了保护受害人权益的需要, 更多的是出于对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的考虑。我国可借鉴国外的做法,考虑将一部分惩罚性赔偿金交给国家或者特定的社会组织,成立特别基金用于公益事务[41]。
注:
①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一中民终字第09328 号。
[1] 第3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EB/OL]. http://www.cnnic.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301/t20130115_38508.htm, 2013/1/15.
[2] See Tom Downey. China’s Cyberposse[EB/OL]. http://www.nytimes.com/2010/03/07/magazine/07Human-t.htmlpagewanted=all&_r=0,2013/01/15.
[3] 王利明.试论人格权的新发展[J].法商研究,2006,(5):22-23.
[4] 姚辉.关于人格权商业化利用的若干问题[J].法学论坛,2006,(6):11.
[5] 2 亿公民个人信息泄露,多张信用卡被盗刷200 万[EB/OL].http://finance.people.com.cn/bank/n/2012/0829/c207834-18867816.html, 2013/1/19.
[6] 2011-2012 中国互联网安全研究报告[EB/OL]. http://www.ijinshan.com/news/20120217001.shtml, 2013/1/19.
[7] Buzz 隐私权诉讼案和解, 谷歌将支付850 万美元[EB/OL].http://www.techweb.com.cn/news/2010-09-05/675720.shtml,2013/1/19.
[8] 赵本山诉天涯谷歌侵犯肖像权索赔405 万[EB/OL]. http://ent.cn.yahoo.com/10-05-/352/2adap.html, 2013/1/19.
[9] 一封电子邮件引发侵权纠纷[EB/OL]. http://old.chinacourt.org/html/article/200207/18/6962.shtml, 2013/1/19.
[10] See http://www.newstimes.com/default/article/Yale-onlineslur-lawsuit-settled-185825.php, 2013/01/15.
[11] 王泽鉴.人格权保护的课题与展望——人格权的性质及构造:精神利益与财产利益的保护[J].人大法律评论,2009.51-103.
[12] [美]理查德·A·波斯纳.超越法律[M].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608-609.
[13] Eleanor L. Grossman, American Jurisprudence[M]. 62A Am.Jur. 2d Privacy § 258, 2012, p1.
[14] See J. Thomas McCarthy, The Rights of Publicity and Privacy[M]. § 11:36 (2d ed), 2012, p1-3.
[15] See Doris CHEATHAM v. Michael POHLE. 789 N.E.2d 467(2003)
[16] See Andrews Privacy Litigation Reporter[J].3 No.1 Andrews Privacy Litig.Rep. 10, p1-3.
[17] See Donnel v. Lara, 703 S.W.2d 257 (Tex. App. San Antonio 1985)
[18] 王利明.美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J].比较法研究,2003,(5):8.
[19] See Clark v. Celeb Pub., Inc., 530 F. Supp. 979, 984, 8 Media L. Rep. (BNA) 1261(S.D. N.Y. 1981)
[20] See David F. Partlett, PUNITIVE DAMAGES: LEGAL HOT ZONES[J]. Louisiana Law Review, 56 LALR 781, p781-822.
[21] 孙效敏. 奖励制度与惩罚性赔偿制度之争———评我国《侵权责任法》第47 条[J].政治与法律,2010,(7):90.
[22] 项先权. 惩罚性赔偿与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功能比较[J].广西社会科学,2005,(2):76.
[23] 陈聪富.侵权归责原则与损害赔偿[J].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03.
[24]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76-90.
[25] See A. Mitchell Polinsky, Steven Shavell. PUNITIVE DAMAGES: AN ECONOMIC ANALYSIS [J]. Harvard Law Review, 111 Harv. L. Rev. 869, p869-901.
[26] 高圣平. 比较法视野下人格权的发展——以美国隐私权为例[J].法商研究,2012,(1):32.
[27] 尹志强.侵权行为法的社会功能[J].政法论坛,2007,(5):154.
[28] [美]罗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M].沈宗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36.
[29] 参见苏永钦.走入新世纪的私法自治[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12.
[30] 张新宝,李倩.惩罚性赔偿的立法选择[J].清华法学,2009,(4):17.
[31] 王利明.人格权法制定中的几个问题[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7.
[32] 王利明. 人格权法的发展与完善——以人格尊严的保护为视角[J].法律科学,2012,(4):173.
[33] 王利明.论网络环境下人格权的保护[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1-6.
[34] 袁雪石.从“艳照门”事件看网络侵权民事法律规制的完善[J].政治与法律,2008,(4):21.
[35] 王兵,郭垒.网络社会个人信息侵权问题研究[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20-21.
[36] 冯军.网络隐私侵权行为探析[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1):79.
[37] 徐国栋.绿色民法典草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725.
[38] See Oliver Wendell Holmes, PRIVILEGE, MALICE, AND INTENT[J]. Harvard Law Review, 8 HVLR 1, p1.
[39] Punitive Damages Reform [EB/OL]. http://www.atra.org/issues/punitive-damages-reform, 2013/1/21.
[40] See Thomas C. Galligan, Jr. AUGMENTED AWARDS:THE EFFICIENT EVOLUTION OF PUNITIVE DAMAGES[J]. Louisiana Law Review, 51 La. L. Rev. 3, p20-24.
[41] 李林启.论人格权商品化侵权责任[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9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