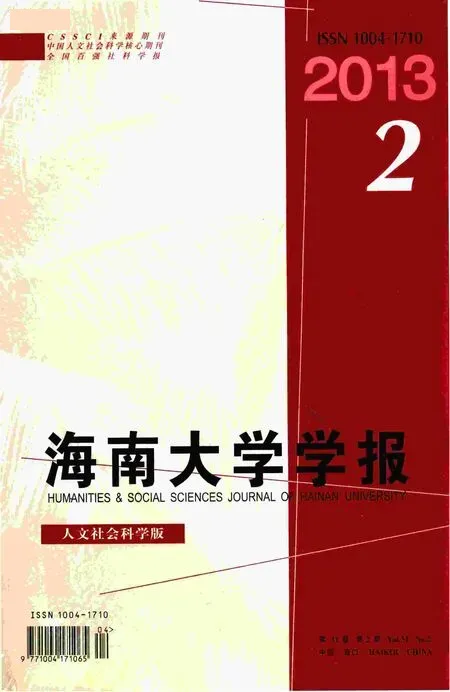“样板戏”女性形象的历史反思
李 松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430072)
新中国成立后男女平等、女性解放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改造的时代主题,这种主导观念也进入到了文学艺术的话语生产与形象建构之中。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国社会,妇女既是当代中国人口生产的主体,也是社会物质生产的重要力量。“文革”期间“样板戏”中出现了大量个性鲜明、英姿飒爽的时代女性,这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体现了时代潮流的投影。目前学术界从女性主义的批判视角对戏剧中的女性地位进行了深入审视。他们总的看法是,“样板戏”中的女性人物虽然翻身做了主人,但是在阶级、男权的话语遮蔽之下仍然无法发出作为女性独立的声音,因而对女性解放的意义持有限认同的态度①。的确,基于女权主义性别研究的立场,可以揭示被革命意识形态幻象所遮蔽的问题,从而以女性为本位寻找自由、独立的话语表达的可能。但是,本文的写作,并不想通过“样板戏”文本分析继续为女权主义性别批评提供经典案例,而是打算深入历史语境,分析历史事实,重新认识“样板戏”文本中女性自立、自主的社会历史意义。
一、“样板戏”女性性别形象溯源
从性别气质的角度来看,“样板戏”中女性人物的性别气质呈现出明显的气质杂糅状态。“样板戏”女性的阴性气质原本受制于社会文化的建构,例如温柔、依赖、被动、柔弱、慈祥等特质,但是融合了男性的阳性气质的强壮、勇猛、刚强、坚毅等品质之后,从而出现了“样板戏”作品中一系列女性气质男性化的女性英雄形象。通常的形象是齐耳短发、浓眉大眼、脸色红亮、宽肩粗腰、身体矫健、嗓门响亮、快言快语。
其实,这种具有左翼革命色彩的英雄主义女性文化可以追溯至延安时期。1936年12月30日,毛泽东赠给丁玲一首词《临江仙·给丁玲同志》:“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他勉励刚刚在国统区出狱、奔赴延安的女作家丁玲为投身抗日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战争时代的延安,武装斗争是最大的政治。人力、财力、物力与意识形态生产都必须服务于这一战争机器的统一分配,那么,无论是群体还是个体的人都必须成为这一机器最标准合格、最高效节能的螺丝钉。具体情形可以从1944年重庆《新民报》记者赵超构的系列通讯《延安一月》中略见一斑。赵超构以记者的严谨与务实记叙过延安女性的精神和生活。延安的女性几乎已完全融入高度“革命化”、“一致化”的男性社会。“由于党性,同志爱必然超过对党外人的友谊;由于党性,个人的行动必须服从党的支配;由于党性,个人的认识与思想必须以党策为依归;由于党性,决不容许党员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独立主义’、‘分散主义’、‘宗派主义’。”[1]661在延安高度军事组织化的战争环境里,党性高于人性,尤其是“从那些‘女同志’身上,我们最可以看出一种政治环境,怎样改换了一个人的气质品性”[1]662。“所有这些‘女同志’都在极力克服自己的女儿态。听她们讨论党国大事,侃侃而谈,旁若无人,比我们男人还要认真。恋爱与结婚,虽然是免不了的事情,可是她们似乎很不愿意谈起。至于修饰、服装、时髦……这些问题,更不在理会之列。”[1]662她们以“不像女人”为荣,反而提出“为什么一定要像女人”的问题。“政治生活粉碎了她们爱美的本能,作为女性特征的羞涩娇柔之态,也被工作上的交际来往冲淡了。因此,原始母权中心时代女性所有的粗糙面目,便逐渐在她们身上复活了。而人们也可以从她们身上直感到思想宣传对于一个人的气质具有何等深刻的意义!”[1]663个人气质的变化还不仅如此,赵超构发现党性观念规范了男女婚姻关系。“至于女党员的丈夫,那就一定是有党籍的人;女党员嫁给非共产党的男人,可以说绝对没有。”[1]662个性细腻敏感的丁玲在延安的政治社会化气氛中也出现了风格的突变。赵超构记叙道,在文艺界座谈会后的午餐上,“她豪饮,健谈,难于令人相信她是女性。……当甜食上桌时,她捡了两件点心,郑重地用纸包起来,似乎有点不好意思,解释道:‘带给我的孩子。’然后非常亲切地讲了一阵孩子的事情。只有在这时,丁玲露出了她母性的原形”[1]670。延安时期,高度规整的军事化组织方式试图抹平性别差异,从而凝聚群体力量,激发个体融入群体之后的最大潜能。这一社会整合的思路在建国之后并未根本改变,只是由服务战争目标转向了服务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政治意识形态观念对社会性别的形塑与延安传统是有直接关系的。女性被认为是能够与男性平起平坐、担负天下使命的“半边天”,女性身上寄托着社会主义新文化对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等理想价值的表达。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②这是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游泳时同青年谈话的一部分,辑录自1965年5月27日《人民日报》通讯《毛主席刘主席畅游十三陵水库》。。毛泽东为江青摄影作品《为女民兵题照》题诗道:“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该诗句在当时极大地鼓舞了女性献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毛泽东对女性性别形象的期待,反映在个人艺术趣味方面,也影响了建国后文学形象的气质类型。据《毛泽东遗物事典》一书的记载,在毛泽东喜爱的京剧作品中,他对《穆桂英挂帅》情有独钟。1945年8月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第一次看到该剧,建国后又多次提到。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天津的一次谈话中说:我们应该做战争的准备,要武装起来,全民皆兵。前天你们唱的《泗州城》的戏,要学唱,多唱打仗的戏,少唱点《梁山伯与祝英台》。1958年8月17日,在北戴河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又说:全民皆兵,有壮气壮胆的作用。我就赞成唱点穆桂英,《泗州城》那些讲打的戏。《梁山伯与祝英台》也可以唱,要少一点,祝英台太斯文了。女将穆桂英比较好,还有花木兰。为进一步扩大穆桂英的影响,1959年4月24日,毛泽东特意给周恩来一信,说:“曾在郑州看过河南豫剧《破洪州》颇好,说穆桂英挂帅的事,是一个改造过的戏。主角常香玉,扮穆桂英。可调这个班子来京为人民代表演一次。”[2]而“样板戏”中的沙奶奶、铁梅、李奶奶、阿庆嫂、喜儿、吴琼花、江水英、方海珍等形象系列,与传统戏曲中女性气质的刚健清新有着自古而今的延续。尤其是《海港》中方海珍的扮演者李丽芳,她曾是军旅演员,在部队剧团经过了多年的摸爬滚打,因而军人气质鲜明。而且李丽芳擅长以小生反串而闻名。她宽厚的肩膀、高大的身材、浓黑的眉毛,加上唱腔、声情与形象的内外统一,体现了豪气冲天的革命气质。
“样板戏”中女性的男性气质与当代中国社会的“铁姑娘”价值导向有着互文性关系。“铁姑娘”③据笔者对1949—1979年《人民日报》检索后发现,最早出现“铁姑娘”一词是在一篇通讯《铁姑娘大战荒砂》。该文记叙了山东寿张人民公社夹河洪峰大队的五位铁姑娘:赵凤岭、赵继荣、卢焕岭、程凤云、赵玉梅。赵继荣16岁,其余四人都是17岁的女孩。“铁姑娘”这名称是怎么叫起来的呢?是因为我们五人和沙荒打了三年的交手仗,终于取得了胜利,使百余亩土地来了个大翻身,并且在沙荒地上创造了高产卫星。她们为了开垦荒地腿酸不嫌累,冰天不嫌冷,下雪不停工,骨断不哼声,流血不叫疼。(赵凤岭,《铁姑娘大战荒砂》,《人民日报》(第八版),1958年11月11日。是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对女性的特有描述,这一词语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战线上女性英模的代称。例如知青邢燕子、侯隽、大寨铁姑娘郭凤莲等人。“文革”时期,河南辉县修渠的农民中有一个青年女子组成“石姑娘队”。这些信仰坚定、意志坚强的女性从事着最苦、最累、甚至最危险的工作,以此证明她们丝毫不比男性差。垦荒队[3]、打井队[4]、架线队[5]、炼钢炉[6]、采油队[7]等各种艰苦行业都出现了社会主义女性激情满怀、忙碌不停的身影。汉学家费正清以西方人的视角解读了“解放”前后女性地位的变化给家庭伦理关系带来的影响,他认为,“中国传统的尊祖、家族一体和孝道等观念早已受到侵蚀。共产党的‘解放’加速了这一过程。根据1950年5月1日的新婚姻法,妇女在结婚、离婚和享有财产方面获得完全与男子平等的权利。这一摆脱家庭专制的解放,给予自古相传的家族和氏族制度以沉重的打击。在50年代的各项运动中,检举父母的孩子受到表扬,这样就把自古以来强调的百善孝为先的教导完全颠倒过来了。延续的家庭关系被贬称为封建关系,谈情说爱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情调。新政府以其无所不在的分支机构力图取代父系家族制度,使一夫一妻的简单家庭变为规范化,使个人失去家族的支持”[8]。他揭示的一个更为深刻的变化是,政治意识形态在家庭关系中取代了传统的宗法制父权话语。族权、夫权、父权退场了,一种新的政权话语上场了。“样板戏”女主角们大多根据英武、健壮的标准来塑造,切合的是主流意识形态对于男性性别气质的期待。
“样板戏”作为文艺形式在特定的时代,具有非常强烈的宣传性质。不能脱离创作者所要达到的观众效果去理解“样板戏”中的人物塑造。“样板戏”中的女性形象固然显得不食人间烟火,但是,这恰恰是政治宣传中的一种偶像化的做法。塑造性格鲜明的甚至模式化的人物形象,这其实也是好莱坞电影的通常手法。既然如此,也不得不接受的事实是,由于单一个性的人物形象缺少复杂、深广的人性深度,往往不能带来解读上的广阔空间。而且,以通俗文艺的模式化方式塑造程式化的人物形象,必然会出现的结果是,观众多次接受之后往往出现审美疲劳④参见李松:《抵制与厌弃:“文革”期间“样板戏”传播的困境》,《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甚至还会编出顺口溜来讽刺这种人物塑造模式。不能完全脱离社会历史语境来理解“样板戏”中的女性英雄。从当时的性别观念来看,这些女性英雄无疑是追求男女平等、摆脱家庭束缚的榜样。也许现在大家觉得这些女性英雄如同神明或修女,但是在当时,这些女性形象却是社会价值公认的一种理想追求。它反映了100多年以来,中国女性对于自由、民主、平等、解放的渴求,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具体的做法显得有些矫枉过正(例如安排女性承担与其体能显然不相匹配的繁重劳动)。然而,这一笔女性解放的思想遗产是值得去珍视、反思的。
二、文学社会学视角中的性别问题
笔者并不否认运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可以为文本解读带来别开生面的结论,如果这种研究思路并不牵强附会、张冠李戴的话,甚至可以从不同视野的解读中获得陌生化的启发。但是,国内性别研究的问题是,有的学者简单套用西方的女权主义思想,从中国文学寻找可资证明理论正确的案例,而忽视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性别观念的形成与变迁有具体复杂的历史背景。站在理论角度去否定臧否人物、评说历史很容易,因为研究者可以自认为真理在握,同时却不得不冒着架空历史的风险。
从文学社会学视角来看,有必要重新反思今天的性别研究立场。对于当代中国研究的性别视角,社会学家黄平从社会学角度进行过深度反思。他认为对于西方的性别诗学理论,“我们中国的研究者应该比较客观和冷静地看待这些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因为我们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从秋瑾她们开始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努力才走到今天,也就是说我们中国自己近代以来的历史一开始就和女性解放有关系。像辛亥革命,一开始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妇女的缠足问题。‘五四’以后,不但是解开了足,而且很快,女性也可以穿裙子了,可以上学了,至少在大城市的知识女性,比较有地位的家庭的女孩子是这样,她们甚至也可以参与政治,这个在所谓的‘发展中国家’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又是一个几千年的男权—父权—夫权的社会,其实女性是被压迫得最深的,因此从一开始起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反抗形式,它通过革命的形式,甚至女孩子参军的形式,用一种暴力革命的形式来解放自己。我们中国近代这段历史和中国这段妇女通过参加革命来获得解放的运动,本来应该作为世界阐释20世纪的整个女性主义或者性别平等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和理论资源,但这样一个资源直到现在我觉得还没有进入到社会科学的基本叙述里,这是非常可惜的”[9]。因而,中国社会学理论应该立足于中国自身的语境、历史与问题,建构中国自己的解释框架和理论,提出中国自己的解决策略和办法。在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革命政治的认识上,黄平并不像某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样片面否定,他认为,“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我们有很多很多问题,但另一方面还有一个比较宝贵的遗产,即使这个遗产也有很多不尽人意之处。有些板子打在这场革命上,为了这场革命女性也付出了极大的牺牲,甚至包括当初有人写文章也说女性似乎是被利用了,成了革命的工具,后来非性化的社会就形成了,这个平等是拉平,叫什么拔苗助长。但是我觉得,当然这可能是事后诸葛亮了,过30年,从1979年到现在,30年过去了,再来看,其实1949年到1979年这30年有相当多的性别问题上的不尽人意之处,与其打在急风暴雨的革命上,还不如打在几千年的父权、夫权、男权上,几千年的男女不平等,想通过30年的革命就把它彻底改变,怎么可能呢?你不能因为30年没有彻底改变,就说你的革命是虚伪的,被愚弄、欺骗了。通过这个就宣布整个都搞错了,然后又回到把女性商品化、包装化、被玩弄的状态,好像也有一种‘地位’,但这个地位其实是非常屈辱的。当她被商品化、被欣赏,我觉得是非常屈辱的,是对女性的侮辱。不但是把洗澡水倒掉了,甚至是一种背叛。你可以说铁娘子、铁姑娘,女子钻井队被搞得不男不女,但是那是一种对几千年压迫的一种反抗,通过那种反抗,包括所谓女性男性化也好,中性化也好,其实她是把自己的地位提升了”[9]。黄平在历史的长河中犀利地看到了性别问题的症结所在,尤其是通过今昔女性地位的对比——即革命的女性与商品的女性——反观革命历史阶段女性地位的现实进步。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黄平认为,革命年代激进的性别观念带来的客观的现实结果是:“铁姑娘”们通过自己不让须眉的劳动能力提高了自身地位。“样板戏”女性恰恰是对这一历史现实的艺术再现。可见,新中国这种矫枉过正的女性解放运动并非完全没有历史成就。在介绍、运用西方理论的时候,往往更多注意的是话语表层的实用性,而没有对异域话语的产生语境、价值系统与具体所指进行细致的考辨。其结果往往是,用中国案例为西方理论提供佐证的依据而已。
当然,历史地看待文学形象的演变逻辑,也不能停留在皮相的相似而忽视本质的差异。孔庆东也从长远的历史眼光来动态审视当代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他说:“整体上看,文革作品确实存在着拔高人物形象和泛阶级斗争等左倾幼稚病,但在性别问题上,那个时期的女性,不是作为供男性观赏的意淫对象来塑造的,而是作为至少与男性一样的‘不失声的人’来塑造的,那样的女性,可以敬,可以爱,但是不可以亵渎,更不可以买卖。正是在这样一大批文艺作品高扬的女性价值观基础上,才产生了新时期之初舒婷的《致橡树》。这首要求两性在极高的精神境界上完全平等但又各领风骚的爱情诗,在思想上更属于‘文革’,而与‘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的改革开放美学,是风马牛不相及的。”[10]127孔庆东从“文革”与新时期的历史延续性角度看到了女性地位的同一性方面,但是他看到的是表面的趋同而非深层的差异。其言论有两点需要辨析:第一,这两个时期女性地位平等的内涵是不同的。“文革”时期虽然女性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和尊重,但是整个社会处于政治意识形态的钳制之中,女性在思想意识上仍然处于失声的境遇。而新时期与之最大的区别在于,《致橡树》体现的是女性在思想观念(尤其是婚恋观念)上自我意识的觉醒与主体身份的出场。因而,他说:“正是在这样一大批文艺作品高扬的女性价值观基础上,才产生了新时期之初舒婷的《致橡树》。”二者是不是存在这样一种因果逻辑?笔者存疑。第二,孔庆东认为“文革”时期的女性是“作为至少与男性一样的‘不失声的人’来塑造的”。这一判断与他文章前面的论述是自相矛盾的。孔庆东在前面说:“即使在最注重男女平等的社会主义革命文艺中,我们也可以发现,革命,仍然是由男性主导的。比如《红色娘子军》,不论电影、舞剧、京剧,从艺术上说都是一流的精品,从思想上说也是革命的经典。但是,里面最重要的人物不是代表女性的吴清华(吴琼花),而是代表男性的洪长青。”[10]127可见“文革”文学中女性依然没有获得与男性同等的地位。从宏观视野历史地看问题是必要的,但是不可忽略事物微观的本质差异。
三、“样板戏”女性的历史原型
从“样板戏”《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原型来看,最早没有洪常青这个历史人物。为什么要设置呢?首先,有人从审美人类学的角度认为,“洪常青”背后隐藏着民族集体无意识心理。中国传统戏曲的观众心理需要一个男女搭配的故事模式,如果缺乏两性平衡,则会十分乏味。其次,有人认为,两性关系经过了传统父权制的思维改造。电影中的女性吴琼花原来只为个人仇恨燃烧,只有在男性洪常青的带领下,最终才发展到为全国人民的阶级利益而燃烧,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而燃烧。也就是说,女性只有依附于男性才能获得发声的可能。
上述第二种看法如果脱离历史的实际语境是可以自圆其说的。然而,实际的情况是,《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原型并没有党代表洪常青,而为了凸显党的领导生硬添加了这一男性领导。这样做的结果是,这个文学作品实际上恰恰低估了女性在革命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样板戏”《红色娘子军》的前身是报告文学,据该作者刘文韶介绍,1956年,广州军区政治部发出开展建军30周年征文活动的通知,当时在海南军区政治部做宣传工作的刘文韶受命到海南负责征文事项。有一次在查资料的时候,刘文韶正巧从一本油印的关于琼崖纵队战史的小册子中发现有这样一句:“在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师部属下有一个女兵连,全连有一百廿二人。”这30个字给了他很大的震撼,因为在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上,女指挥员和女英雄有很多,可是作为成建制的完整的女兵战斗连队,过去还很少听说过。刘文韶凭当兵十几年的经验觉得这是一个重大题材,于是就到她们活动过的乐会县采访。刘文韶回忆:“女兵连的老同志很多牺牲了,革命材料保存的很少,有关资料就是琼崖纵队战史小册子上这一句话。很幸运我找到了女兵连的连长冯增敏,采访了她四次,后来又找到了十来个女兵连的女战士,还专门拜访了琼崖纵队的负责人冯白驹将军,当时他是广东省副省长,记忆力很强,提供了很多材料。如果当时没有去挖掘这些材料,我想以后恐怕就更难挖掘了。”[11]《红色娘子军》的名称怎么来的呢?刘文韶说:“我想应该从更大的主题和背景来考虑,把它作为我们解放军的一个建制连队的代表来定位。我考虑到中国历史上从花木兰到杨家将,一直以来就有‘娘子军’的说法,为了说明现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所以就加了‘红色’两个字,当时都喜欢用‘红色’两个字来代表革命。”[11]从历史真实情形来看,刘文韶说“洪常青和南霸天,都是虚构历史”[11]。据当时娘子军连长冯增敏介绍,当时娘子军连里根本没有一个男性党代表,惟一的指导员是女的,叫王时香。多年后的今天,刘文韶从文学创作的艺术角度反思添加男性人物的得失,他说道:“这样写是败笔。第一,它不符合历史真实;第二,洪常青的戏一多,琼花和女战士们就无法给人留下那么深刻的印象。本来是写琼花从一个受苦的女奴翻身成长为一个革命者,但是后来电影和芭蕾舞剧都没有把主题摆在中国妇女的英雄气概上,所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琼花的形象远远没有我们所熟知的诸如花木兰、穆桂英这些古代女英雄形象突出。”刘文韶所不满的,并不仅仅是吴清华等红色娘子军在后来的言说中已经成了洪常青这一男性英雄的陪衬。从文学再现历史的社会价值来看,刘文韶认为,“电影和‘样板戏’中宣传最多的还是男性,如果从宣传娘子军的角度来说,我认为是不成功的。女性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觉醒、精神和力量,在这些本子中很难看到”[11]。京剧版的《红色娘子军》同样存在主角倒置的问题。为了突出洪常青作为党代表的一号人物地位,吴琼花被相应地压低影响。虽然为洪常青设置了很多唱段,但是艺术效果始终无法有效凸显。对照“样板戏”文本和历史事实,人们就会发现,虚构了男性英雄洪常青是为了突出党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而客观历史告诉人们,事实并非如此。从实际的艺术效果看,《沙家浜》的核心场次应该是阿庆嫂的“智斗”,核心唱段应该是“风声紧”。但是为了凸显正面武装斗争,郭建光的“坚持”一场作为中心唱段得到强化。这也就说明,上述作品不仅违背了真实的历史状况,而且刻意拔高中心人物的做法,在艺术效果上也并不见佳。
四、结语
“样板戏”中大量角色的家庭关系被不断纯化,避免儿女情长这些伦理与情感对人物政治观念的侵袭。文学研究者通常喜欢从文学形象的丰富性、复杂性或者“圆形人物”的标准去指责:英雄人物李玉和没有老婆,成年女子方海珍、江水英等人没有丈夫,而阿庆嫂的丈夫去外地跑单帮去了,柯湘的丈夫牺牲了,洪常青与吴清华的关系始终只是同志关系。从人性的标准来看,上述人物形象的确显得单调、干瘪。据此,可以批判“文革”时期政治意识形态对人性的挤压与控制。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样板戏”塑造的是一种英雄神话:通过这幕神话再现了革命历史年代无数为了理想而抛家弃子、奉献生命的志士。而先烈们的革命道义和献身精神应该得到历史的理解与同情。当人们今天在享用国家建设成果的时候,却以人性论、人道主义为名横加指责革命者不够儿女情长、不够仁慈怜悯,是不是不够厚道?
综上所述,对“样板戏”女性人物形象的认识,笔者认为应该注意如下三条原则:第一,“样板戏”女性人物阴性气质阳性化的历史缘由。第二,“样板戏”女性形象作为社会历史的再现产物,她们所烙上的时代印记。第三,从“样板戏”女性的历史原型出发去理解客观的历史真实。以上述三条原则作为前提,女权主义批判视角的“样板戏”研究才会更有历史感、更有说服力。
[1]赵超构.赵超构文集:2[M].上海:文汇出版社,1999.
[2]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毛泽东遗物事典[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6:102.
[3]赵凤岭.铁姑娘大战荒砂[N].人民日报,1958-11-11(8).
[4]“铁姑娘”打井队[N].人民日报,1970-03-05(4).
[5]前进,郑健,天兵.毛主席教导我们:“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N].解放军报,1975-03-08(4).
[6]炉前新歌——记北京铁合金厂“三八炉”[N].人民日报,1975-03-07(3).
[7]“铁人精神”开新花——记大庆油田第一个青年女子采油队[N].人民日报,1972-03-08(4).
[8]费正清.美国与中国[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358.
[9]黄平.性别研究的几个“陷阱”[M]∥谭琳,孟宪范.他们眼中的性别问题:妇女/性别研究的多学科视野.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40-41.
[10]孔庆东.四十五岁风满楼[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
[11]贺敏洁.历史上没有洪常青?[J].晚报文萃,2003(6):23-26.
——评张丽军《“样板戏”在乡土中国的接受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