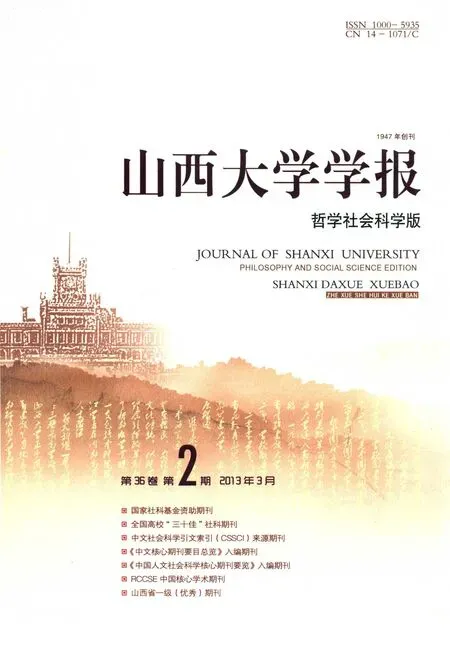古代通俗小说女大师形象与佛经翻译文献
王 立
(大连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辽宁大连116622)
女大师,特指古代通俗小说和野史笔记中的一类近乎女超人的人物形象,她们一般都具有反正统的特质,在下层民众里有较高的声望,聚众结伙反抗朝廷,甚至具有法术异能,而实际上知识素养和价值追求品位不是很高,最后往往因为受到统治者镇压而被处死或逃亡。女大师这类形象突出地体现女性异能所带来的缺点,在倡扬性别文化研究的视野中,是一个人们较少关注的相关现象。
一 明清通俗小说女大师形象种种
明清通俗小说中的“女大师”,首先往往有一个神秘幻术的特长。《平妖传》就设立了一个“狐精母女以幻术鼓动凡俗男子称王造反”模式。烟霞散人《幻中真》第七回也描写老妖狐母女擅长撒豆成兵,剪纸为马,鼓动强大梁“以法术动众”,召集众饥民“共享富贵”,于是众饥民依言,“只见水中的身影,是个冕旒的强大梁在内”,众人惊拜,聚集了数万人入九尾山中立寨,老狐自称老圣母,强大梁称为扫地王,小狐胡灵儿称小圣姑。[1]65-67老狐在与官军作战时能袖出怪兽坐骑,以葫芦中出的怪兽天兵杀败官军。[1]74-75
其次,除了讽刺天书刺激作乱动机外,女大师的文学描写往往带有浓重的历史投影,小说比野史更注意标明对女性谋反者情欲追求的极端憎恶。在母题所表现的应用天书招致失败的事例中,这些本已有半仙之体的女大师们几乎全是酒神型的,她们的生活理想本来不高,当然一旦天书在手就急于满足自己的个人需求了:“那从李就是女大师,他(她)英雄盖世,为何一见昌年[便]有许多相亲相爱?不知他(她)出柳林时本意要寻个才貌兼全的人,做些有趣的事。”[2]39抑或演练道术时为人所惑,做些“不伶不俐”的勾当。她们倚仗会法术当首领的特权,在性与求偶方面比小说中屡屡描写的番邦女将还要开放。这种沉溺于男色的性放纵态度,尤其为男性为中心的文化所不能容忍。《归莲梦》写白莲岸没听取猿公仙书“不可轻易授人”的叮咛,术成不久即当了白莲教女大师,将主要精力放在讨好如意郎君、兴兵作乱上,天书被收回,人也被斩。[2]7-124《平妖传》里胡永儿的性放纵,更直接促成、加剧了其夫王则强占民女,于是有了烈妇赵无瑕被逼死,冤魂为官兵首领文招讨报讯。而鬼魂复仇事件成了王则和永儿一军被剿灭的关键。[3]226-241《幻中真》第八回也写二妖狐搜寻民女给强大梁宠用,“助他元阳,使他强壮”,夜里狐精就把民女害死,而强大梁和小圣姑则占据宝寺,“终日在内奸淫取乐”。[1]69
明代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载:“永乐十八年,山东鱼台县妖妇唐赛儿,本县民林三妻,少诵佛经,自号佛母,诡言能知前后成败事。又能剪纸为人马相斗;……而赛儿终不获。一云:‘赛儿至故夫林三墓所,发土得一石匣,中有兵书宝剑。赛儿秘之,因以叛,后终逸去,盖神人所佑助’云。”[4]749而所传神人相助,则往往就落实在天书上,王圻《稗史汇编》卷三十七称民妇唐赛儿祭夫墓发现石匣中藏的宝剑妖书,究习其术聚众造反,被捕逃遁不知所终。朱克敬《瞑庵杂识》卷四也称嘉庆时齐二寡妇以白莲教起事,据山为王,“齐亦改服,置面首,不复初志矣”。[5]说明现实中此类事的确难免。而《女仙外史·卷首》刘廷玑“品题”称:“小说言兵法者,莫精于《三国》,莫巧于《水浒》,此书则权舆于《阴符》、《素书》之中,脱化于《六韬》、《三略》之外,绝不蹈陈言故辙,虽纸上谈兵,亦云奇矣。”[6]又,贝州王则假托弥勒出世起义事,在宋仁宗庆历七年,后失败被杀,见《宋史·明镐传》。一般认为,两个世纪后的与弥勒教合流的白莲教起事继承了弥勒教传统。
母题何以对于女性谋反者如此反感?原来,明清民间宗教教派,由妇女创教或妇女成为教派首领的,真的为数不少。如北京黄村西大乘教,系正统年间吕菩萨(即尼姑吕牛)所创。《破邪详辨续刻》曰:“吕牛本系男身,假称女身”。园顿教张翠花,《古佛天真考记龙华宝经》《祖续莲宗品》中,称她“中央圣地翠花张姐”,是一方之主,会下有十善大护法。龙门教,系米奶奶所创。《邵文毅公奏议》卷四十一称米奶奶是万历时人,嫁与刘姓,曾勒封掌道收园老母名号,是龙门教教主。龙门教刘氏妇女,世代传教,至嘉庆时查出刘龚氏母子传教,已是米奶奶第十二代子孙。龙门教投入了明末反抗朝廷统治的斗争,很有叛逆性。《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二十二载京城宣武门外善果寺街,有高张氏称教祖奶奶,和伊女李高氏共同传教。《清实录》卷二七一乾隆十一年七月载,宛平县查获以刘氏、赵王氏为首的弘阳教。《皇明嘉陵两朝闻见记》嘉靖二十六年三月条:“汶上人田斌及其妻,啸聚数千人。”
江左樵子《樵史通俗演义》第四回写郓城县丁寡妇变纸人,与《灯草和尚》同名人物类似:“……又在布袋里取出四五个像是柳条做成的人儿,也有男的,也有女的。他拣了两个眉清目朗的男人,……都顷刻间变成七八尺长的大汉子了。”[7]王同轨以僧人不法实例说明,恶僧不法行为得逞往往也与民家妇女持有宗教信仰,使其有机可乘:“愚民易惑,求福于冥冥,而失女于昭昭,佛何不救?今白莲之法甚盛矣。夫随妇与僧奸谓之‘结缘’,揭竿而起,啸聚俄顷,豮(阉割过的猪)牙之剪,责必有在耳。”[8]僧人对于良家妇女的性骚扰,往往从妇女及其丈夫的佛教信仰上打开缺口,甚至有的丈夫还成了恶僧的同谋帮凶。
明人还十分关注秘密社会的蛊惑力和对于社会的负面影响,这有助于说明女大师纷纷兴起的社会背景和民俗心理:
今天下有一种吃素事魔及白莲教等人,皆五斗米贼之遗法也。处处有之,惑众不已,遂成惑乱,如宋方腊、元红巾等贼,皆起于此,近时如唐赛儿、王臣、许道师皆其遗孽。而吾闽中又有三教之术,盖起于莆中林兆恩者,以艮背之法教人疗病,因稍有验,其徒从者云集,转相传授,而吾郡人信之者甚众。……[9]164
因而论者指出:“白莲教继承了弥勒教‘反抗政府,夺取政权’的一贯宗旨,无论政府为何族所建,皆在被夺取之列。”[10]其实这也就是女大师们反正统的一贯作风。只不过,明清小说中所表现的女大师们总是把事情设想得那么简单容易,而又不约而同地总是有始无终、虎头蛇尾,稍微得手后就沉溺于眼前私欲,结局基本上都是令人失望的。
二 特殊小团体中男女平等带来的女性自由
当明代民间宗教和农民起义相结合时,女大师实际上起到了团体中女领袖的实际作用。除了永乐年间自称“佛母”的唐赛儿,嘉庆时川楚白莲教大起义首领王聪儿以外,《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二十七载,嘉庆时天理教林清、李文成起义,文成牺牲后即由其妻张氏指挥,后城破自缢死。杨缙《菊溪节相除邪纪略》载嘉庆二十年江南园教起义首领李玉莲自称“开创圣母”,怀孕弥勒。《丁清惠公遗集》卷一《擒获妖犯乞正典刑疏》载万历三十四年,凤阳刘天绪自称无为教主造反,教民寡妇岳氏号称“观音”。《临清纪略》卷一载,乾隆三十九年山东清水教王伦起义,王伦嫂于氏,称五圣娘娘,年六十余,跨马挥双刀,英勇善战。乾隆四年,河南查获伏牛山女教主“一枝花”,民间谣传:“一枝花,十七八,能敌千军万马。”乾隆十三年福建无为教起义的首领普少,也是女性。这些承领“女大师”地位的少女、妇女似乎往往有一个突出特点,喜好标榜自己的身份,带有依附宗教攀附辈分的倾向。
首先,女大师身份的确立,在男性中心社会中是以冲破男女大防禁律和抬高并神化某一女性为前提的。明清民间宗教中,男女聚会,男尊女卑、男女大防等观念较淡薄,且有朴素的男女平等观念。因其明显地对于现存秩序构成了挑战和威胁,统治阶级对此切齿痛恨,激烈攻击和百般谩骂。黄育楩《破邪详辨》指斥:“男女混杂,恣行淫欲,为邪教中第一要诀也。”他批驳《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说无生母是创世主、至尊天神时说:“噫!天神之至尊者为玉帝。自邪教言,则无生又在玉帝之上矣。试观古来女后专权,必致祸乱,假使无生老母,职掌天官,则阴盛阳衰,安能成化育之功?”对“吩咐和会男和女,不必你们分彼此”,则批驳是:“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男女授受不亲”、“外言不入于阃,内言不出于阃”。对“邪教”所谓邪淫混杂,男女不分,深恶痛绝。他把“邪教”之产生和发生,归结为人之好色。为此载录者还曾经引用一个廪生教徒赵爽的话:“吾习邪教,非信邪教也,徒与少年妇女朝夕会合,由吾选用而已。”[11]陈登原《国史旧闻》第三册注意到这方面的史料和日人研究,如《太平广记》卷三八五引述:“隋炀大业九年,唐县人宋子贤,善为幻术,每夜楼上有光明,能变作佛形,自称弥勒佛出世。”《有学集》卷四四《景教考》:“若夫末尼,则志磐《统记》叙之特详,开元二十四年敕云,末尼本是邪儿,妄称佛法,其教自行,不须科罚,大历六年,回纥请于荆扬等州,置末尼寺,其徒皆白衣白冠。会昌三年,敕京师女末尼凡七十二人皆死。朱梁贞明六年,陈州有末尼反,立母乙为天子,发兵捦(擒)斩之,其徒不茹荤酒,聚淫秽,画魔王高坐,而佛为之洗足,云佛为上乘,我乃上上乘,盖末尼为大云白莲之流。”志磐《佛祖统记》卷四七:“绍兴初,吴郡沙门茅子元,自称白莲导师,相见傲憎慢人,无所不至。”[12]《元史》卷一八七《张桢传》写至正间:“頴上之寇,始传白莲,以佛法诱众,终饰威权,以兵相抗距,其势不至亡我社稷不止。”[12]而明清女大师纷纷涌现,成为这一时期白莲教为代表的诸多民间秘密宗教活动的一大特色,实积势有自,托佛自重。
因此,尽管在明清时期民间宗教的众多经卷中,提出了朦胧含糊的男女平等观念,如《救苦忠孝药王宝卷》:“或是男,或是女,本来不二。都仗着,无生母,一气先天”;《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排造法船品》:“吩咐和会男和女,不必你们分彼此”;如明嘉靖时黄天道讲求夫妻双修共同悟道,“一夫一妻,阴阳和合,善男子,善女子,同习修炼”[13],在该教五位佛祖中妇女占了四位。但小说描写出现了较为复杂的情形。如《平妖传》第三十五回一方面写了胡永儿“饱暖思淫欲”的人性弱点;附加了某些平等思想和佛教因果观:“凡男女相就,都是夙世姻缘。如做夫妇的是正缘,私合的也是旁缘。还有一节,七情六欲,男女总则一般。……男子三妻六妾,兀自嫌少,如何怪得妇人?”[3]221在倡扬男女平等中,又不免呈现出了正统文化的拒斥力。对女性不平等处境的关切同情、尊敬和信任的同时,天书母题提出了形象化警告,力图说明女性如掌握了知识法术,充当犯上作乱的首领,该是多么严重。
其次,也不排除民间不少小家碧玉的家长抱有“挟女自贵”动机,且千方百计实施女攀高门的企盼。就像汉乐府《孔雀东南飞》中刘兄力主兰芝再嫁以攀高门一样,下层民间人士也巴不得茅屋出个光宗耀祖的女大师。如民女王满堂容貌美艳,因入选皇宫又归乡的特殊经历,有了新的自我角色期待:
正德初,尝与选入内,既而罢归,耻不肯适人,数感梦,谓必有万兴者来聘,乃许,其人贵不可言。一游僧出入智家,知其梦,间以语人。道士段鋹挟妖术,因潜易姓名,且赂僧,使谓智曰:“而家明日当有大贵人至。”明日,鋹至,问其姓名,与梦协,智家欢呼罗拜之,即妻以满堂,鋹乃出妖书,转相煽惑,乡民神其梦,从之者日益众。鋹恐事觉,挟满堂逃山东。峄县儒生潘依道、孙爵策杖从之,时称臣主。鋹遂僭号,改元大顺平定,往来牛兰、神仙二山。久之,鋹为新城人所获,并得其妖书,抚按官以闻,诏释其诱从者,鋹及依道。爵皆斩于市,满堂有中旨,特令全之。……[14]
角色期待就是社会的客观期盼和个人的主观表演,显然有过入宫经历的王满堂自己个人条件不错,因而更加自命不凡,而如果借机不升格“作秀”,乡里舆论会对于她的名节抱有怀疑。梦是不可求证的,感梦多半是昼生幻想所致或索性假托。黄瑜《双槐岁钞》卷八也称:“自中官崇尚释氏,为奸凶逋逃薮。妖书谶纬,惑民扇乱,正统间尤甚。”扶风人才兴就为僧创庵自言知兵与寺僧真海、道人谭福勾结起来,而民间美女则成为他们纠结作乱的进一步凭依:“真海素与义勇后卫百户段旺母张氏通,媒其女妙果为才兴妻,立为后。方举兵,为官军缉获,伏诛。”伙同天台山僧韦能作乱的王斌,得脱后也祝发为僧名悟真,“建置百官,称帝改元,立所淫女子王氏为后,攻掠傍近诸县,得数千人。……”[15]这些起事谋乱者,总是不约而同地娶民间女性为妻封后,遂使得其号令民众时显得更加“正统”,因为这符合早期儒家“修齐治平”的人格设计模式,而这其中民间女性乐于攀附正统、夫荣妻贵的心理,也是不可忽视的。衍化后的佛道二教杂糅了民间秘密宗教,其中的男女平等思想也被这些男男女女在“共谋大事”的活动中所实践。
其三,在明清秘密团体丛生的丰厚社会土壤里,小说野史多所出现的女大师现象带有明显的区域性、复杂性和悲剧性。其中处于南北交界地区的山东、苏北、河南、河北居多。而有的竟以武勇称擅,如明末京城南勇力过人的“母大虫”:
貌亦不陋,双趺甚纤,能于马上用长枪,置一豆于地,驰骑过之下,一枪则剖为二,再驰再下,则擘为四,其精如此,遇之者不知其能,或与格斗,必为所杀,横行者三四年。前后有夫数人,稍不当意,即手刃之。有一徽人王了尘者,善用铁鞭,闻此妇绝艺,拼死与角,半日未解,此妇遂放杖讲解,留以为夫,有嫪毐之能,恨相见晚。王寻见此妇所杀太多,官兵渐谋取之,恐并入网,遂潜逃入京。此妇恨极,挈精卒数骑入京踪迹之。都下见其异,亟集选锋军往捕,此妇驰出城,追骑及之郊外,内一人败,为所杀,然诸军愈盛,其从骑俱逃散,就阵生擒之,磔于市。[4]757
而据说天魔禅院是通州名妓广怜(广莲)创建,她密授女弟子房中术,趁齐鲁饥荒而广收弟子九十余人,势力增长后私结贵戚,为害乡里:“大家姬妾误至庵而受其诱辱者岁不乏人,年少子弟淫至奄奄锢地穴中死者,又指不胜屈矣。”后来郑冯二姬欲出水火,看中了任生,任生终向朝廷告发,铲平尼庵。[16]宣鼎《夜雨秋灯续录》卷三也写善角觝戏的寇四娘是白莲教,女儿阿良女扮男装,以幻术将秦二官身体变轻,携走同居。她窃得老父“符箓禁书”,可变房屋婢女。后阿良父母将其缚归嫁人,而她重逢二官后,却残忍地将其父母杀死,并给二官服食媚药,被二官告发遭刑。[16]136-144女大师的性格特征是:好男色,能幻术,残忍好杀。似乎小说中这类女大师形象,比起野史笔记中的相关载录,还更注重揭示其人性本能的劣根性。1913年林纾在《剑腥录》第二十六章以女大师形象揭穿义和团法术荒唐:“明日,黄莲圣母至津,俞禄顶礼如张德成。圣母年三十许,龙衮庄严,俞禄跽迎,傲然径入。众皆哗然,称为‘仙真’。时俞禄未弁侍侧,少年也,善浪游,窃告人曰:‘此吾所善娼也,数月之间,何由证仙如此之速?’然无学,卒不悟其诈,亦随人拜跪墀下。俞禄问天津休咎,圣母曰:‘天津不要紧也。’声如梨园中旦角,尚有数语,亦均效旦角所言者言之,丑态百出。俞禄心知其谬,然惕于冈梓良、褚侗、兰公淫威,亦媚团以自结。”在男性中心的中国传统社会,毕竟女性的生活视野限制了其素养识见,这也是女大师们难于回避的共同性格特点,也是其在小说中和野史笔记中悲剧性命运展现的根本缘由。
三 中古汉译佛经故事中的女大师形象
与女大师形象紧密相关的天书母题,在通俗小说中大多具有一种宣示正统文化的倾向,此当来源于知识阶层对于书本上佛道文化接受和衍发。道教的戒律,其强化是由于内部的混乱和派系间矛盾斗争而趋于完备严格的。道教上清派《上清众真教戒德行经》卷上称:“秽思不豁,鄙吝内固;淫念不断,灵池未澄,……”用中贞一子《女金丹》卷上入门戒规更盛称:“妇女之情性易荡。一贪淫事,则欲火焚身,情难自禁,无夫以遂其欲,必有丧廉之行。即使不至失身,淫心一动,火迫一身,精气已不存于中矣。”[17]而东晋后期,针对天师道组织内部的混乱,早期灵宝派的《太极真人敷灵宝斋戒威仪诸经要诀》,就载有太极真人徐来勒严厉的针砭:“……不学至道经教,而好学巫术杂书不真之事。其会同之日,唯酒肉为先。口是心非,诡黠相攻,淫欲纵横,放心所为,嗜物无厌。或复为师,初无教善之怀,强弱相凌,恒欲其虐意,意中唯贪妒谮害,淫盗作伪,凶悖逆乱。此人身常有十恶。何以知其人有如是之行,不遭罹罪网?”其实,早期的天师道就传下来一套戒律,国外研究者提出有的认为形成于刘宋初中期,有的说形成在梁陈间,还有的说是发源于3世纪的中国南方[18]。因地区气候的原因男女两性关系相对开放,女性所受到的礼教束缚较少一些。后来的《女金丹》还吸收了剑仙韦一娘学道蒙考验达到境界的故事,表现出道教经典十分注意女性修炼者道德自律上所体现的素质。
事实上,不仅道教对于女性修行有许多的戒律,佛教也针对女性的性别特点,制定出来种种戒律规则,有理由认为,佛经翻译文献对女大师形象塑造的基调奠定,是决定性的。
佛教的教义体系包括戒、定、慧三方面,戒律,指的是僧徒应遵守的约束个人行为规则和规范,用以处理出家僧尼与僧尼之间、僧俗之间、个人与教团之间关系,制约教团成员一致,按照教义从事修行和传教。仅从东晋到南北朝就有四部完整的戒律被译出——《十诵律》、《四分律》、《摩诃僧祇律》、《五分律》此外还有《比丘戒本》、《比丘尼戒本》等多种译出。其中“波罗夷”(极恶、重罪、断头、根本罪)是最重的,其中就包括婬(不净行、非梵行、大婬)指与人、非人(畜生)性交[19]。
东汉译经《沙弥尼戒经》便已告知:“不得淫泆,何谓不得:一心清洁身不婬泆,口不说淫,心不念淫,执己鲜明,如虚空风无所倚著。身不行婬,目不婬视,耳不婬听,鼻不婬香,口不婬言,心不存欲。……”[20]937a东晋《沙弥尼离戒文》对比丘尼“十戒”即有如此规定:“三尽形寿不得婬,不得教人婬。”在“威仪七十事”中,规定在施主家,“不得与婢共私语,不得独至舍后,不得与人共上厕,不得上男子厕上”[20]938b-939c。男女有别的程度,要达到如北凉《大爱道比丘尼经》卷上所诫:“行迹不与男子行迹相寻,不得与男子同舟车而载,不得与男子衣同色,不得与男子同席而坐,不得与男子同器而食,……不得别行,独止一室而宿也。有犯斯戒非沙弥尼也”[20]948a。这些戒律在后世渐与道教戒律等会通。总之宗教文化对文人阶层的正统思想建构,不可低估。事实上佛教世俗化传教活动中早已注意到,在教众团体中倘若女性得到较大自由度所可能产生的无法控制的弊端。如果我们不拘泥于这类故事中的主人公之性别,可知中古汉译佛经实际上还有一个“幻术者因技艺高而思淫逸,导致失败”母题。
佛经母题在明清多种小说中都有体现。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第九十六回金碧峰长老(博物者)就讲出摩伽罗鱼王前身为中天竺国王长子,“专一习学戏术,鬼魅诙谐,无不通晓”,他在南天竺国以种植速长术等得宠,怎么地位跌落的呢?只因蝴蝶对国王爱妃说“摩伽罗是个活佛临凡,你若肯与他一宵恩爱,就可升天”,爱妃即以其语告诉国王,国王晓得是摩伽罗弄仙术调戏他爱妃,即时差兵驱逐了摩伽罗。[21]此外女性越轨还可作为有非分之想者的神物不灵、神不佑护的验证。如冯梦龙《平妖传》第二回玉帝所言:“这如意册乃九天秘法,不许泄漏人间,只因世上人心不古正,得了此书必然生事害民。……”[3]6天书——兵法谋略及相关的法术,被统治者看做是统治阶层的禁脔。即使会了一些法术,能一时间获取有限的胜利,毕竟这些民间的女大师们,还很难脱离当时早婚风习,她们也很难在失去世俗舆论规范约束时严循戒律,无忧无虑享受着男女情爱乐趣,就理所当然被视为法术效能的一个果实。而识见短浅、功力有限,更由于她们总是耐不住相思煎熬,急不可待地试图以自己刚刚获得的特权来消解相思,也就成了法术换来的特权的牺牲品。
女大师形象的享乐本性、悲剧命运表明,借助于这类遭到民众舆论关注的盛衰浮沉的女性形象,有针对性地体现了佛教戒律的世俗化,带有明显的劝世讽喻意味。
四 宋元之前女大师形象及相关观念
早期女大师与道教女性崇拜密切相关。而女大师的涌现,又往往跟女性不良生存状态相关,即陷入生活困境时不得不采取超常的生存方式来应对生存挑战。因此,早期女大师其多为能够行医疗病的女巫。《南齐书·孝义传》称诸暨东洿里屠氏女,乡里不容,“女移父母远住苎罗,昼樵采,夜纺绩,以供养。父母俱卒,亲营殡葬,负土成坟。忽闻空中有声云:‘汝至性可重,山神欲相驱使。汝可为人治病,必得大富。’女谓是魅,弗敢从,遂得病。积时,邻舍人有中溪蜮毒者,女试治之,自觉病便差,遂以巫道为人治疾,无不愈。家产日益,乡里多欲娶之,以无兄弟,誓守坟墓不肯嫁,为山贼劫杀。”[22]这位少女实为南方民间的弱女子,所谓“闻空中语”事实上不可求证,谁说没有可能为假托之以自重的招数呢?至《南史·萧昂传》则增补了《梁书》:“时有女子年二十许,散发黄衣,在武窟山石室中,无所修行,惟不甚食,或饮少酒,鹅卵一二枚,人呼为‘圣姑’,就求子往往有效,造之者充满山谷。昂呼问,无所对。以为祆惑,鞭之二十,创即差,失所在。”[23]江浙滨海一带是产生女大师的较早地域,后则北渐蔓延。
宋代也流传着这样具有特异功能的女大师:“山阳有一女巫,其神极灵。予伯氏尝召问之,凡人间物,虽在千里之外,问之,皆能言。乃至人中心萌一意,已能知之。坐客方弈棋,试数白黑棋握手中,问其数,莫不符合。更漫取一把棋,不数而问之,则亦不能知数,盖人心所知者,彼则知之,心所无,则莫能知。……”[24]《太平广记》卷五十二引《会昌解颐录》写蜀人张卓入深山与仙人之女成亲,归前蒙仙人赠二朱符、二黑符。卓至京师又见一女,卓以符领之潜于中门。宅中发现失女请法师叶公作法夺回该女,还是张卓仙妻施法化一飞桥才使他解脱。[25]324唐以降还传闻肃宗曾支持地方官员对女大师的镇压:“肃宗以王屿为相,尚鬼神之事,分遣女巫遍祷山川。有巫者少年盛服,乘船而行,中使随之,所至之地,诛求金帛,积载于后,与恶少年十数辈,横行州县间。至黄州,左震为刺史,震至驿,而门扃不启,震乃坏锁而入,曳巫者斩之阶下,恶少年皆死。籍其缗钱巨万,金宝堆积。悉列上而言曰:‘臣已斩巫,请以所集资货,以贷贫民输税,其中使送上,臣当万死。’朝廷厚加慰奖,拜震商州刺史。”[26]女大师们放荡行为也渊源有自。唐人称贞元年间某少女被一僧迷倒,昏迷中上天得悉自己的仙女身份。[25]416-418看来,明清女大师男女关系方面的不检点,在吸收融汇佛经的修道故事中屡见。似乎仙术高了人就胆大妄为,不在乎别人议论,这不就是文学中神尼、后世造反起事队伍中女大师形象的原型么!《太平广记》卷七十二引牛肃《纪闻》称王旻其父修道有成,有姑亦得道,常在衡、岳、天台罗浮:“貌如童婴,其行比陈夏姬,唯以房中术致不死,所在夫婿甚众。……”甚至南方有些地区还普遍流传着野女掠男的传闻,与此互相影响。[27]
宋人还将“伪造仙姑”个别现象推究其普遍和必然成因。说瑞州高安县旌义乡郑千里之女定二娘以刲股和药疗父疾愈。次年女成仙升空,人们相传愈神,立庙旌表以劝孝。立仙姑祠后祷祈辄应,县宰密遣县胥访查,适新建县有阙氏雇一婢来历不明,讯问“郑仙姑”:“盖此女初已定姻,而与人有奸而孕,其父丑之,遂宛转售之傍邑,乃设为仙事以掩之。利其施享之人,以为此耳。”载录者推测:“昌黎《谢自然》、《华山女》诗,盖亦可见,然则世俗所谓仙姑者,岂皆此类也耶?”[28]由于女大师在明代造反起事风潮中的位置,谢肇淛《五杂俎》还重温了上述“女大师”炮制过程中的“托词惑众”现象:“宋瑞州高安县郑氏女定二娘者,临嫁汲井,忽有彩云掖之升天,州县以闻,立祠建庙,祈祷辄应。既而廉之,则因与人通而孕,父母丑之,密售于傍邑而托词惑众耳。无何,新建有阙氏者,雇一婢,讯之即仙姑也。昌黎谢自然华山诗意,亦可见。”[9]164看来,女大师在一些地区瞬间声名鹊起,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下层民众顾及到未婚女性性命攸关的名声,在其贞节方面出现问题时不得不造假以免遭舆论之谴的策略。而这些,也与“大风吹来女人”的民间幸运传闻及其生成机制互通互动。[29]
古代中原乡土社会信息相对封闭,邻里小范围内又难保住隐私,因而像定二娘这样婚前怀孕的女性,只好离开故土,假托成仙可免于被追究而又不至影响家族名声,还可借此抬高声望,愈传愈神。先前那些女大师故事,有利于俗间人们信以为真而不会对消息的可靠性产生怀疑。但限于条件和重新生活难度还不能离开太远,只要遇到有头脑的官员追究并不难弄清真相。如此欺世盗名者还有为《平妖传》吸收的沈俶《谐史》故事:
庆历中,贼王则倡乱,率众闭门为不轨。知城中之女,无如赵氏女美,致金帛万端,金千斤,聘为妻。且曰:“女若不行,即灭尔族。”父母不敢违,独女不可,……女登舆,自残于舆中。贼盛礼待之,闻报皆失色。而贼之亲信自杀者三人,缒城逃者七十四人。惧为贼所鱼肉也。自此贼焰渐衰,以至于败。[30]
这说明,女大师一类形象不仅是反正统的,而且还经常被正统话语所贬损、丑化。
然而何以女大师们的兴起那样迅猛,而人们对于女大师的超凡能力,最初又是那样推重,与其后来的浪荡表现和结局,每多构成鲜明对比,而让人在失望中叹息呢?洪迈曾揭示出对有异能、有勇气的女性格外看重的普遍心态:“妇人女子,婉娈闺房,以柔顺静专为德,其遇哀而悲,临事而惑,蹈死而惧,盖所当然尔。至于能以义断恩,以智决策,斡旋大事,视死如归,则几于烈丈夫矣。”[31]男性中心的社会中,人们对于女性弱势群体的期待不高,因而一旦出现异能超群的女性,人们最初的震惊钦赞无须经过考察和审视,但这些女性一旦陆续失败、被杀,人们却往往盯在跟她们性别有关的行为上,就她们个人生活不检点说事。于是叙事文学中出现了共同的趋向和伦理谴责。
明人树丕《识小录》指出:“十余年来,苏城女戏盛行,必有乡绅为之主,盖以娼兼优。而缙绅为之主,充类言之,不知当名以何等,不肖者习而不察,滔滔皆是也。有某比部狎一女优,而此优者全部为之主,以比部每挟之出,出必旬日,有妨其戏,遂至相诟,语不忍闻。女优者复好与无赖作缘,不乐士君子还往。亦遂与比部绝。比部怏怏,作《踏莎行》七阕,词亦可观。”[32]明清民间女艺人社会地位低下,在野史笔记中的口碑不佳,与她们具有类似女大师的性情和男女交往活动有关,这虽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女性群体本身的弱点,但女大师形象的存在和人们普遍性的鄙视态度,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烟霞散人.幻中记[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
[2]苏庵主人.归莲梦:第四回[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4:39.
[3]冯梦龙.平妖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4]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59.
[5]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十三册[M].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21.
[6]吕 熊.女仙外传:附录[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1108.
[7]江左樵子.樵史通俗演义:第四回[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27.
[8]王同轨.耳谈类增:卷五十三[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450.
[9]谢肇淛.五杂俎:卷八[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10]戴玄之.白莲教的本质[J].第十二卷.台湾师大学报,1976(6).
[11]喻松青.明清时期民间宗教教派中的女性[J].南开学报,1982(5):29-33.
[12]陈登原.国史旧闻:卷六十.白莲教[M].北京:中华书局,2000:631-635.
[13]苏联科学院历史部东方研究所藏.普明如来无为了义宝卷:离垢如来分第十二.
[14]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三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59:768.
[15]黄 瑜.双槐岁钞:卷八[M].北京:中华书局,1999:167.
[16]宣 鼎.夜雨秋灯续录:卷五.天魔禅院[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87:204.
[17]詹石窗.道教与女性[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92-94.
[18]王承文.早期灵宝经与汉魏天师道——以敦煌本《灵宝经目》著录的灵宝经为中心[J].敦煌研究,1999(3):34-45.
[19]杨曾文.佛教戒律和唐代的律宗[J].中国文化,1990年秋季号:5-14.
[20][日]高楠顺次郎,等.大正新修大藏经:卷二十四[M].中国台北: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0年影印.
[21]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第九十六回[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242-1243.
[22]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十五.孝义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2:60.
[23]李延寿.南史:卷五十一.梁宗室下[M].北京:中华书局,1975:960.
[24]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八.山阳女巫[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900-901.
[25]李 昉,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416-418.
[26]周勋初.唐人逸事汇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790.
[27]王 立.野女掠男故事的主题学分析[J].山西大学学报,2005(5):83-88.
[28]周 密.癸辛杂识:前集.“郑仙姑”条[M].北京:中华书局,1988:30-31.
[29]王 立,等.明清“大风吹来女人”幸运故事的生态学意义[J].东南大学学报,2011(3):77-82.
[30]吴曾祺.旧小说:丁集三[M].上海:上海书店影印,1985:43.
[31]洪 迈.容斋随笔:续笔卷十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355.
[32]江畲经.历代小说笔记选(金元明)[M].上海:上海书店,1983:269-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