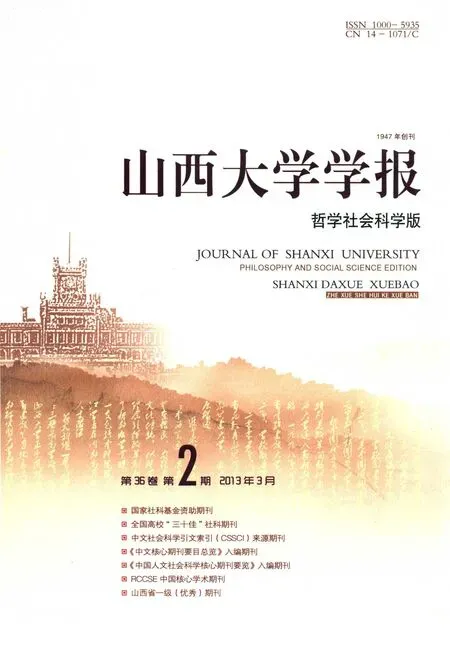《新石头记》与清末民初的文化变迁
陈文新,王同舟
(1.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2;2.中南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430074)
在近代思想史上,从“中体西用”到“全盘西化”,这是一个过程,是一个产生了重大后果和深远影响的过程。回顾这一过程,我们将获得若干耐人寻味的信息。也许是偶合,吴趼人的《新石头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供观摩的标本:《新石头记》即“新红楼梦”。这表明,吴趼人写《新石头记》,其比照对象正是曹雪芹的《红楼梦》。从人格理想的角度考察,《新石头记》与《石头记》(《红楼梦》)表现出哪些重要的不同?这些重要的不同,对我们理解清末民初时代精神的变迁有何特殊的价值?本文即以此为线索展开。
一 《新石头记》的叙事与新人格理想的展示
《新石头记》是晚清小说家吴趼人的一部长篇小说,大致可分两个部分。前二十回,叙述贾宝玉凡心再起,为了遂自己的补天之愿,进入20世纪初的清末“野蛮社会”。他先到上海,遇到粗鄙的薛蟠,在薛蟠的引导下,看遍这汇集了欧风美雨的十里洋场。继之又游历北京、湖北等地,目击晚清社会的种种弊端。后二十回写贾宝玉为了寻找“自由村”,无意中来到“文明境界”的经历。在这里,贾宝玉由老少年引导,四处参观游历,目睹了政治、文化、教育诸方面尽善尽美的制度设施,更体验到这里科技的极端先进发达,见识了种种匪夷所思的发明创造。最后贾宝玉发现“文明境界”的缔造者东方文明,竟是《石头记》里的甄宝玉。贾宝玉见补天之愿已为他人所先,遂怅然归隐。临行留下的通灵宝玉,化为巨石,上面刻的就是《新石头记》的内容。
顾名思义,这部书本该是曹雪芹《石头记》的一个续本,实际上却与原书情节基本没有什么关联。“宝玉与二十世纪相见”,也可以转换为“宝玉与西方相遇”。《新石头记》对原书主旨和形象所作的翻新处理,具有强烈的典范重构性质,颇能具体地指示西方压力带来的文化变动。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薛蟠、焙茗三个人物出现在《新石头记》中。总的来说,这里的贾宝玉、薛蟠、焙茗,实际上是不同的文化心态(观点、立场)的象征,而许多场面、细节,也都具有象征意味,显示出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批判态度。
这种批判的态度首先表现在对贾宝玉、焙茗和薛蟠再入尘世前的生活状态的描述中。进入尘世前,贾宝玉在一座破庙里巧遇昔日小厮焙茗。对破庙的描写意味深长。这座庙山门已倒,门下已难避雨;周围是参天古树,把那殿上遮得黑魆魆的。景物带着残破而阴森的色彩,隐喻1840年后的中国,国门洞开,列强威逼。原来的玉霄宫“金碧辉煌,十分显焕,有一百多道士”,现在的玉霄宫“外面原来是三间正殿,却是剥落不堪,两廊多已倒了,两旁神像,也是七歪八倒。出得山门,回头看时,那敕建玉霄宫的匾,还歪歪的在上面未掉下来”[1]4。这一对比显示出近代中国的衰落、凋敝、混乱。作者点明这神庙坐落在“无为村”,暗示中国的衰落,正是由于无所作为的文化心态造成的。宝玉心如槁木死灰的“苦修”,薛蟠的陶然而醉,焙茗的昏睡不醒,也都只是不同形式的“无为”而已。作者通过“破庙”这一象征性意象,对主张出世、无为的佛道传统——旧的文化心态作出了批判。在吴趼人看来,“出世、无为”即等同于“旧的文化心态”。这一看法与胡适是相通的。五四学者大都鄙弃佛道,与吴趼人保持了高度的一致。
贾宝玉凡心再起,一心要去完成补天之愿,意味着传统文人开始了现代转化。贾宝玉在尘世的经历,象征着中国传统文人在新的历史环境中重生的道路和方式。贾宝玉自觉地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化,这样的情节,无异于否定了《红楼梦》中贾宝玉的人生理念。
对贾宝玉离开青埂峰走向尘世的路,作者这样描写:
出了茅庵,不辨东西南北行去。心中只盼遇见了人,可以问路,谁知尽着行去,偏偏一人不见。看看已经日落西山,也不知走了多少路,喜得脚力尚不见乏,回头看时,连青埂峰的影子也不见了。此处又不知是何所在,正在彷徨之际,猛抬头看见头上一块乌云,愈散愈大,不一会便洒下雨来。[1]3
贾宝玉的遭遇和心理活动,代表了中国传统文人觉醒后的最初感受:他们走出了与世隔绝的状态,却发现这世界已经变得很陌生,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种新的历史环境、新的文化格局;他们告别了过去,却又不知路在何方。他们因日暮途远而焦灼彷徨,而头上的一片乌云却明确提示,迎接他们的将是种种磨难。
第一回用象征方式预示了全书的情节指向,这一回之后,这种方法仍在继续,一直到第六回,作者反复写到贾宝玉对自己的身世、自己身处何世这两个问题的追问。他不断地观察、求知、思考,起初是“回想往事,有如隔世”,“印证今日的境遇,还似做梦”,后来逐渐模糊地意识到,他已经无法回到原来那个家里了,最终他认识到:“原来我是若干年前的人重新出世的”。与此同时,通过观察、求索,他也逐渐意识到眼前的世界已是处在另外一个时代。贾宝玉的隔世再生,他所采取的态度、方式,代表了最早觉醒的一代知识分子的选择。他们被迫与西方文化遭遇,并在一种屈辱的境遇中开始了解西方,开始以西方的参照系改造自己。
《新石头记》中,贾宝玉对于“时间”的敏感,对于自身所处的历史和时代的追索,具有深长的意味。吴趼人这一代知识分子,他们接触到进化论的思想之后,“时间”就显示出不同于传统的意义。在他们看来,再没有“无往不复”的不断循环的历史,投射在时间轴上的,是不断更新的“时事”和“新知”。《新石头记》中贾宝玉身上,集结着吴趼人一代人大梦初醒后的焦虑,也折射着他们新的理想人格。作品花费大量笔墨,叙述再世为人的宝玉如饥似渴地了解这个新世界,比如第四回的回目“慧神瑛下问启新知”,第五回回目“求知识拟借新书”等,都是极为明显的提示。
与此对照,焙茗和薛蟠对于“时间”的麻木也就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和宝玉一样,焙茗也是再世为人的,但他始终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认为自己不过是睡了一觉罢了,而且还指望着“回到京里”,那个原来的家中。他的形象,象征着那种对于新的历史环境、文化格局麻木不仁的守旧文人。作者描写了他的“原形”:“一面看焙茗时,那里是什么焙茗,竟是一尊木偶的仙童偶像,面目都剥落不堪了”。这实际上是对守旧文人的描写:它在精神上已经衰朽了,丧失了活力,本质上已经形同木偶,没有了思想和行动的能力。它不仅无缘进入“文明境界”,而且无法生存于变化了的现实世界。
至于薛蟠,他在陶然亭“也不知睡了多少时候”,一觉醒来,来到十里洋场上海。“除却跑马车、逛花园、听戏、逛窑子,没有第五件事”[1]32,居然如鱼得水,也因此还惦记着带信回“家里”,告诉家人自己过得非常开心自在。他仿佛无师自通地学会了一切新鲜的享受,抽吕宋烟,喝白兰地酒,但对于真正的新知和时事却没有丝毫兴趣。作品暗示,他只能将中国带入放纵糜烂的“野蛮自由”境界。焙茗、薛蟠与宝玉之间存在着对比的关系:它们都来自传统社会,只有宝玉不断地学习新知,又坚持自己的原则,最后能够理解维新的主张——作者心目中最高的、最合理的主张,他的经历标示着中国传统文人的重生之路。
《新石头记》第一部分用象征的方式和对比的情节完成了作者文化观念的表达:中国传统文人要获得新生,就必须刮去那层层魔障。吴趼人眼中的“魔障”,以佛道的“无为”为主,其参照系则是在清末民初广泛流布的进化论。
二 吴趼人对“中体西用”将信将疑
《新石头记》的前半部分主要是通过对《红楼梦》的翻新处理而写出作家心中的理想人格,后半部分关于“文明境界”的描写展示的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在吴趼人进行小说创作之时,“革命”话语正以铺天盖地之势弥漫开来,至少在海外的舆论环境中,“家庭革命”、“社会革命”以至“三纲革命”、“祖宗革命”之类的说法充满报端。作为一种对抗,吴趼人试图在“中体西用”的范围内展开理想社会的营构,对“国粹”的存续予以特殊的关切。
小说结尾对此有明确的交代。贾宝玉的通灵宝玉,落到了“灵台方寸山”,化作怪石,上面刻了一篇“绝世奇文”,被老少年“改成演义体裁,纯用白话,以冀雅俗共赏,取名就叫《新石头记》”。这一安排,发挥了传统小说中“楔子”的点题作用:
从此,女娲氏用剩的那一块石就从大荒山青埂峰下,搬到文明境界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去了。看官如果不信,且请亲到那里去一看,便知在下的并非说谎。然而,必要热心血诚,爱种爱国之君子,萃精荟神,保全国粹之丈夫,方能走得到,看得见。若是吃粪媚外的人,纵使让他走到了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也全然看不见那篇奇文。[1]319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爱国爱种与保全国粹具有连带关系,于是“补天”就化为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如何让中华文明延续、重生的问题。我们不必去评论这种观点是不是狭隘的、保守的,但是依据这个观点去看《新石头记》,我们就会发现作品中看似庞杂的材料其实是按照一个完整的结构紧密组合在一起的,而且,我们对于作品的叙述方式也会有更深入的认识。
对小说第二部分关于“文明境界”的描写,我们关注的焦点是,作者在发挥想象力的时候,在哪些地方产生了错位,以致造成与作者“中体西用”的宗旨之间的矛盾,并隐隐约约地预示了“全盘西化”的可能性。
贾宝玉在寻找“自由村”途中,无意起了登泰山游孔林之念,又无意中进入了文明境界。这暗示“文明境界”是建立在儒家文化的地基上。“这‘孔道’两个字,大约就是‘大路’的意思”[1]167,作家借助双关手法,进一步暗示这层意思。文明境界辽阔广袤,幅员之大,几乎拥有地球一半以上的陆地,境内分成东西南北中五大部,每部分成四个大区,每个大区用一个字作符号。作符号的字,中央是“礼乐文章”,东方是“仁义礼智”,南方是“友慈恭信”,西方是“刚强勇毅”,北方是“忠孝节廉”。这哪里是政治版图,分明是文化版图。章太炎曾提出“俱分进化论”,他以为,物质世界的进步是不断向前的,但人文世界的道德却可能不进反退。吴趼人的看法似乎也是如此:西方虽然“器数工艺”领先,但就精神文明而言,文武周孔之道仍远胜西方。不过,吴趼人的立场似乎不如章太炎坚定。且看《新石头记》的有关情节。
吴趼人为文明境界想象出了一种完美的政治制度,称为“文明专制”,远超欧美诸国之上。“举国一切政治,只偏重教育一门,教育之中,却又偏重德育”,以至人人都把“不明公理,不修私德”作为“人生的第一件耻辱”[1]282。
沿着这一线索发展,吴趼人似乎应该集中表现文明境界的“德育”的先进,像《镜花缘》那样,写出想象中的君子国来。但正是在这里,吴趼人的想象发生了错位:在文明境界中,道德风俗被置于次要的地位,仅作为背景穿插在对于想象中的先进科学技术的描写之间,先进的发明创造成了闪亮的主角,高潮迭起,令人目不暇接。于是,居于“文明境界”版图中央的“礼乐文章”处于叙述的边缘,而在“文明境界”边缘的“强”字一带的科技发明却成为叙述的中心。“礼乐文章”之“体”反倒不如“器数工艺”之“用”来得重要,这表明,吴趼人对西方的“器数工艺”是由衷向慕,而对中国的“礼乐文章”并无发自内心的信任。所谓“以中学为体”,在吴趼人那里好像是门面话。
贾宝玉来到“文明境界”,首先就落脚于“强”字区,他曾乘飞车追踪大鹏,一直到了非洲,也曾乘潜艇航行数万里到过南极。但“文明境界”中,别的区域,他却从未到过。在后来的叙述中,吴趼人仅有限几次提到“文”字区,“礼”字区,其他如“仁义礼智”、“友慈恭信”等区,再未提及。
这种想象的错位意味着什么呢?晚清一代,流行着这样一种思潮,认为中国政教昌明,文武周孔之道远逾西方,只是“器数工艺”落后于西方罢了。说中国的政教优于西方,未必没有崖岸自高的意味,承认西方的“器数工艺”的先进,却是由一次次苦痛的经历中得出的结论。况且道德虽优,不免有空中楼阁的嫌疑,强国保种,还得仰仗先进的“器数工艺”。吴趼人的想象错位,正是这种文化心态的无意识的流露。
从作者特殊的文化心态切入,我们对于这一部分的叙述方法获得了更深入的理解。反过来,我们从这种叙述方式,也能得到一种颇有意味的联想:在吴趼人明确否定了以出世、无为为核心的佛道二家,并将以“仁义礼智”为核心的儒家边缘化之后,我们离“全盘西化”的主张还有多远?“全盘西化”的最大障碍是说“文武周孔之道”胜于西方的“精神文明”,然而吴趼人对此已将信将疑。吴趼人将信将疑地坚持“中体西用”的立场,实际上对“中体”已自信不足。从这种立场再往前走,我们看到的是新文化人写下的“全盘西化”四个大字。
三 呼之欲出的“全盘西化”
如果在打倒佛、道之后,继而打倒“文武周孔之道”,那就像近代实际发生过的思想进程一样,就成了完整的“全盘西化”。从表面看,在这部议论成分颇多的《新石头记》里,吴趼人并没有公开否认“中体西用”,他倒是试图说明“孔道”乃是通往文明境界的途径,甚至在一些地方还以激愤的语气声讨疑似“全盘西化”的思想,把那些嫌疑犯称为“吃粪媚外的小人”。但实情真的如此简单吗?
吴趼人晚年很为“国粹”的沦丧而忧心,但这看来更像是一种文化上的怀乡病:之所以怀乡,乃是因为远离家乡,而不一定是家乡有多么美好。这种忧郁的怀乡情结正是抒情诗的好材料,但要转化为长篇的叙事结构,说明“国粹”优越于西方,说明“国粹”在中国维新进步中有巨大作用,却有明显的不足。为了替“国粹”赢得声誉,《新石头记》采取的一个策略是,将中国社会上一些糟粕现象归咎于西方。小说提到一个叫刘学笙(“留学生”的谐音)的人,他将薛蟠带往另一个“自由村”,在那里薛蟠可以过上更加放纵的生活。留学生是晚清输入西学的主力之一,吴趼人借批评留学生而影射西学本身。小说告诉读者,留学生讲“自由”,无非是他们生活放纵的借口;留学生又喜欢讲“革命”,特别热衷“家庭革命”,也无非是蔑弃伦常。吴趼人对西学以及晚清思想界的动态都非常熟悉,他很清楚地知道,将自由理解为放纵,是对西学的误解而不是西学的原意。至于从无政府主义的激进立场宣传家庭革命,例如主张“有男女之聚处,而无家庭之成立”,“家庭灭,纲纪无”①《三纲革命》,作者署名“真”,原载《新世纪》第十一期(1907),引自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三联书店,1963版,第1020页。,吴趼人也知道这些并非西方主流的社会政治学说,也不是晚清引进西学的主流。他明明知道西学的本来面目、西方的社会现状如何,但还是通过这样的策略给读者造成一种西方社会道德沦丧的暗示。吴趼人对西方的情况有着充分了解,例如,他在另外的地方借贾宝玉之口批评洋奴心态:“外国人最重的是爱国。只怕那爱国的外国人,还不要这种不肖的子孙呢!”[1]52可以说,吴趼人几乎是以他本人能够清晰地意识到的矛盾心态来进行这一方面的写作的。
《新石头记》的另一个策略是用想象中的最先进的社会——“文明境界”来彰显西方国家政治、科技诸方面的局限。他努力说明这种高度先进的社会是由中国的“国粹”支撑起来的,比如,在展示“文明境界”的发达科技时,他往往要声明,这些超越西方的科技成果却是源于中国古人的“理想”,这些理想包含在诸多古籍中,如“夸父逐日”的神话启发了绕日车(类似后来的卫星)的发明,刘琨“何意百炼钢,化作绕指柔”的诗句启发一种神奇的“软瓷”的发明,《镜花缘》的描写启发了“飞车”的发明……《新石头记》试图用“西学中源”的套路来说明中国的“国粹”足以支撑起科技的发展。小说所描写的“文明境界”里,人们对科技的热情与痴迷,其实在中国文化史上从未有过。其中写道,东方文明(甄宝玉在文明境界里的姓名)作为“文明境界”的开国元勋,其三子一女东方英、东方法、东方德和东方美,全都放弃从政,成为科学家、发明家。这种人格特质,完全是中国传统士大夫所不具的,它不是国粹,而是吴趼人在西方文明影响下产生的新的人格理想。
“文明境界”所实行的政治制度称为“文明专制”。按照《新石头记》的描述,它并不是西方民主制度的对立物,而是对西方国家民主制度的超越。它建立在民众拥有高度自治能力、享有高度民主权利的基础之上,废除了议会制度、政党制度,——吴趼人认为二者会带来分裂和低效率——恢复了君主政体。吴趼人在设想这种制度时,显然还受到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影响。这种制度,排除了权贵的专制,也排除了“富人为政”,不仅保证了民众法律上的平等,还保证了民众实质上的公平。这种完美制度的思想资源,吴趼人说,仍然是我们的“国粹”,具体说是《大学》:“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1]200-201不用说,吴趼人的想象资源基本来自西方国家的政体,也结合了当时的社会主义学说。《大学》中的说法,如果没有西方制度的启示,是很难让人直接产生“文明境界”的联想的。吴趼人把“国粹”从其文本语境和历史语境中剥离出来,赋予它以远超西方的先进性,其作法多少有点像后来冯友兰提出的“抽象继承法”。
按照实现理想国的要求,吴趼人虚构了贾宝玉等一批具有新型人格的人物。将这些新型人格与陈独秀在《敬告青年》里提出的六条新人格标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等——进行对照,其间若即若离的关系,足以引起许多有趣的联想。回到吴趼人的理想国上,我们可以发现,无论他如何强调“国粹”在理想国中的支撑作用,也无论他所说的“国粹”实际存在与否,他的理想国里到处都铭刻着现代化或者说西化的最明显标记——民主与科学。他越是强调中国传统中拥有丰厚的民主与科学的“国粹”,越是将传统学术朝着民主与科学的方向进行引申,就越能证明他在根本观念上的西化程度。除非我们采取“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观点,把现代观念视为东、西方殊途同归的发展趋势,就很难洗去吴趼人身上的“西化”色彩。
吴趼人以为自己可以守旧,如果他能抛开文化上的乡愁来审视自己的创作,或许会有一种爽然自失的感觉:原来他在西化的道路上已经走了那么远。
[1]吴趼人.新石头记[M].王立言,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