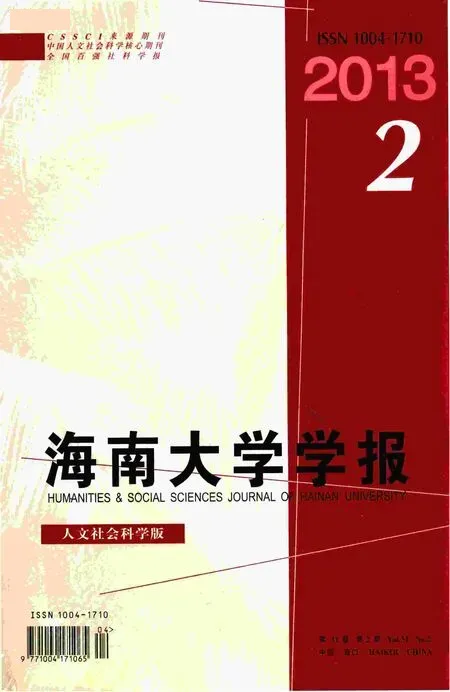中国生态批评建构的历史自觉
邓志文
(湖北科技学院 文学院,湖北 咸宁437000)
20世纪60年代以来,伴随着科学、信息技术的高歌猛进和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人类步入了后工业社会、后人类社会。然而,人凭借自身的理性能力所创造的无与伦比的物质技术文明并未给自身带来福音,反而成为压迫人、毁灭人的强大的异己力量。一方面,人类沦为机器的附庸而失去主体性,人非人,从而导致了人的全面异化;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对地球资源涸泽而渔造成了诸如环境恶化、气候变暖、人口膨胀、职业病增多、物种变异、资源缺乏等一系列的生态问题乃至生态灾难。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罄竹难书,自然的祛魅使人类面临着新的生存困境与危机。于是,西方生态批评应运而生。艺术方面也出现了浩如烟海的反应生态危机的诗歌、小说和影视作品,如生态诗人斯奈德的《大地》,卡森的《寂静的春天》与米都斯的《增长的极限》,电影如《猩球崛起》、《后天》、《风暴》和《生化危机》等等,不胜枚举。而像文学与环境研究会之类的进行生态批评的国际性学术组织也雨后春笋般地诞生了。
何谓生态批评?我国学者王诺先生总结了国外诸多定义,又根据生态批评的思想特征和审美原则,对其作出了较全面和准确的界定:“生态批评是在生态主义、特别是生态整体主义思想指导下探讨文学与自然之关系的文学批评。它要揭示文学作品蕴含的生态思想,揭示文学作品所反映的生态危机之思想文化根源,同时也要探索文学的生态审美及其艺术表现[1]。”
随着生态批评概念的外延和内涵的扩大,生态批评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批评。生态批评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又盛行于欧美,最后风靡全球。当今,生态批评研究方兴未艾,构成文艺理论批评中的显学。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才开始引进生态批评的概念和理论,并在本世纪初掀起了研究的热潮且硕果累累,如鲁枢元、王诺、曾繁人、胡志红和余谋昌等教授和学者的生态著作及论文。生态批评是在人类和地球的生存危机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人类对防止和减轻生态灾难的迫切需要在文学批评领域里的表现,是在具有社会和自然使命感的文学研究者对拯救地球生态的强烈责任心驱使下出现的。”[2]67
实际上,无论是从它形成的哲学基础还是从生态文学发展等方面来看,中国生态批评的历史渊源远较西方久远,只是中国一直没有正式提出“生态批评”这一概念。本文力图从中国哲学建构所蕴含的生态思想、中国古代文论对生态批评方法论的自觉运用以及中国生态文学作品建构这三个方面予以梳理,力求在新的角度下自开户牖、有所创见。
一、中国古代哲学构建中的生态批评思想
欧美生态批评的哲学基础主要是卢梭、达尔文、恩格斯的生态思想,海德格尔的生态哲学思想,利奥波德、罗尔斯顿、拉夫洛克的深层生态学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生态的和谐观与正义观,生态的主体间性理论。而在中国,先秦时期的文化典籍《周易》以及儒家和道家的著作中就包含了丰富的生态学观点,并成为后世中国生态批评理论的渊薮,这种建构的自觉在时间上比西方早了两千年之多。
作为“五经之首”的《周易》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它自觉包含了许多朴素的生态智慧:世界和生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克服了西方传统中人与自然对立的二元论;“观物取象”体现的对自然和世界感性直观的原则使事物的原生态的丰富性和完整性得以保持;人的道德实践和人格修养所赖以建立的对生命敬畏之心和对生命神圣的信仰等。这些都构成儒道两家生态思想的发端,虽然儒道当时并未形成系统的生态理论,他们对于生态批评的建构却是处于自觉之中。
生态批评最主要的思想特征是生态整体主义,它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人类对自然的控制和征服和无止境的欲望,主张生态的可承受发展、提倡科技发展与消费的适度以及简单生活等等。这其中很多观点都可以在儒道两家著作中找到思想源头。
先秦儒家举张天人合一,人与自然是联系着的整体,这正是和谐生态观的体现。这种思想一直持续到宋代,如张载的“大其心以体天下之物”,朱熹的“天地万物本吾一体”,程颢的“浑然与物同体”等。孔子和先秦儒家正是在这种整体中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由于人是怀着对天的敬畏,所以他们在实践中获得了行动的自觉制约力量,并在天道的指引下建构道德准则,将其用于人事与自然中。孔子也因此形成了一种厚重、质朴而温柔敦厚的生态审美风格
降及道家,老庄及其弟子在生态思想的建设方面显出更为自觉的精神和空前的热情,其著作中生态思想蕴含更为丰富。老子的生态批评理论可以说是源于中国古代先哲以及《易经》的“与时偕行”、“顺天应时”等基本法则。首先,他主张回到“小国寡 民”的原始状态,实际上是宣扬对自然的理性回归,其中承载着生态整体主义的联系观。这样人就抛弃了以自我为中心的理念,忘记自身而与自然融为一体。“寡民”其实还寄寓了要进行人口控制的前卫思想,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其次,老子也看到了科技发展给人类带来的负面影响,他的“使人复结绳而用之”即是反科技至上的生态学观点。再者,“道法自然”体现了老子“无为”的核心生态联系批评观。他认为,人是自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类应该顺应“道”的自然本性,尊重自然、平等对待之,不强为才能“无为而无不为”,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一方面要以‘自然’的方式对待自然,另一方面要懂得尊重自然。”[3]老子还在《道德经》第44章中说过:“祸莫大于不足足……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知止不殆”即是从发展观的角度提出要适度开发原则,以免导致自然资源的枯竭。“知足”、“知止”才“可以长久”,科学的发展在于把发展限制在生态系统可承受的限度之内。这显然和生态批评里的欲望动力批判论以及可持续发展战略异曲而同工。
庄子的生态批评理论在对老子生态观点的继承中又有发展。他反对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与自然中其它物事是平等而无贵贱之分的。他说:“若与予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意思是:你我都是万物中的一物,何必互相对立相轻呢?这反应了庄子物无贵贱、万物同源平等的生态观点,人类要尊重自然。不仅如此,庄子还在《齐物论》中继续阐述了他的生态整体论思想。“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表明了他是从整体论的角度来看待世界的。世间万物包括人类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它们相互依存,一损俱损。人类不能自大,用自己的发展来损害自然,否则会因此遭到自然界的报复而得不偿失。当今的环境问题、自然灾害都相继证明了庄子所言非虚。同老子一样,庄子也告诫人不要违背自然规律,应顺应自然,自然而为。如“以鸟养养鸟”是说如果喜欢鸟就不要把它关在笼子里,这是违背鸟的生长规律的,我们要按照鸟的自然本性而绝非凭着人的意愿行事。更为生动的一个寓言是说倏和忽为了报答浑沌的恩德,为他“日凿一窍”,由于违反了浑沌的生理本性而导致“七日而浑沌死”,结果事与愿违。庄子还列举了诸如“伯乐善治马”、“陶匠善埴木”等因为没有顺应本性而伤生的行为。另外,与老子“知足而止”的观点相似的是,庄子倡导绿色生态消费理念,即“咎莫大于欲得,祸莫大于不知足。故知足之足,常足矣”。他反对人类向自然过分索取和贪得无厌,告诫人类必须节制自身的欲望,树立正确的消费观。“殿堂无灯凭月照,庵门不锁待云封”——一副楹联道出了简单消费和生活的哲理:得道高僧心境澄澈空明,与云霞天光合二为一,月光为灯,云影当锁,节省了自然资源,亦无污染之虑。“这是一种典型的低物质能量消耗的生活方式”[4]。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庄子关于艺术的生态批评观,他认为那种大自然孔窍在自然力的作用之下所发出的声音是最美妙、最具审美特征的。这种天籁之音的审美价值远高于“地籁”与“人籁”,原因是天籁乃是“咸其自取”,是大自然由于自身的律动而发,没有人为因素的参与,无斧凿之痕。这与老子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如出一辙,成为后世文论追求自然化工之境的先声。
当然,老子和庄子的生态批评理论的丰富程度远非上面的分析所能涵盖的,这里列出的只是其中较为突出的部分。但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两位先哲的生态理论已广泛深入到生态整体主义、生态和谐观、环境保护、绿色消费、人口控制、科技发展、艺术审美等方面,可谓包罗万象。而所有的这些共同构筑了中国生态批评的哲学之基。无怪乎英国当代科学史家尼德海姆在读完《庄子﹒在宥》篇后感叹道:“请记住,当今人类所了解的有关土壤保护、自然保护的知识和人类所拥有的一切关于自然和应用科学之间的正确关系的经验,都包含在《庄子》这个章节中,这一章,和庄子所写的其他文字一样,看起来是如此深刻、如此富有预见性。”
现代工业社会剥夺了人类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机会,我们远离了事物的本真状态,所感觉和体验到的世界完全是经过了科技处理和包装的伪装品。人与地球的直接交流与体验成为奢谈,任何体验都是间接的。如何让人从精神上亲近自然为生态解困?我们从中国古代哲学家所奉行的“天人合一”的思想里找到了答案,人与自然的化合和无间交流正是解决上述问题的维度。而后世无论是罗尔斯顿倡导的“恢复大地与人类的亲情关系”,还是戈尔提议的“恢复自然与人的精神纽带”,抑或是怀特的“人与万物平等”的观点,均不过是“天人合一”的流风余韵。
二、中国古代文论建构中的生态批评方法论的运用
不仅是中国古代哲学蕴含了丰富的生态学思想,中国古代文论的构建也同样运用了生态批评的方法论,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学理论。
首先,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整体性思维就与生态批评中的生态整体主义系统观有相通之处,这种思维对于中国古代文论中创作论的构建影响深远、余音不绝。在西方哲学里,二元论根深蒂固。笛卡尔明确指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是人控制改造自然,将自然放在与人相对立的另一元上。这就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对抗,主体蔑视自然,把自然对象化。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物我一体、天人合一是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融为一体,以我观物同时物也呈现于我。就如李白的诗“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和辛弃疾的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所描述的,主体与大自然泯灭了界限,达到了化合的高妙境界。生态学也强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万物是相互联系且平等的。董仲舒最先将这种方法论用于指导文学创作,他认为人与天(自然)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因为人有着与万物相似的形体和感情意识。“人生于大自然,必然要与之发生各种关系,自然作用于人类引起人的情感效应。”[6]他的物我感应说是我国古代创作论的哲学基石,成为后来物感说、心物交融说的理论来源。之后诞生了诸多如陆机(“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钟嵘(“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和刘勰(“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等一大批持物感说的中国古代文论家。另外,中国古代文论在文本语言的架构方面也运用了生态批评中关于联系的观点。正是人与自然万物相互联系,文论家们发现了二者之间具有相似性。所以,在论述自己观点时,他们倾向于采用具有诗性的话语方式来组织语言,形象、直观、感性是其特点,如比兴的运用。司空图用具有道家审美趣味的景物意象来比喻描述作品的风格状态,李白用“清水出芙蓉”来赞美谢灵运的诗风,钟嵘用“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来形容谢在文学上的地位与建树等等,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古代文论中俯拾即是。
其次,“自然”作为生态批评中的一个术语和生态文艺学里的一个重要范畴,它的一层含义是方法论的,即尊重、顺应事物内部的运行法则。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自然轻人工和重直觉轻思辨,无疑是自然方法论的实际运用。从而建立了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独树一帜的文艺理论。如先秦的老子和庄子的自然无为的天道观就蕴含了崇尚自然朴素的文艺主张。庄子崇尚自然反对人为,他推崇的是不露斧凿之痕迹的作品,作品中人的自然流露又与客观自然融为一体。老庄的主张逐渐成为文学艺术的审美标准,也是后来相关文论的理论依据和立足点。此后的曹丕在论文气时,认为它是人先天禀赋的自然流露,“不可力强而致”。刘勰在《文心雕龙》定势篇以自然之趣为文章旨趣,以自然体势为文章体势。他在创作方面亦是遵从自然之道,《原道》篇的“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即是指那种自然天成的文章比经过“工匠们”精雕细琢的文章更胜一筹。钟嵘的“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亦是倡导写作要直抒胸臆、自由流淌。唐初文坛走的就是对流于浮靡轻艳的齐梁宫体诗纠偏去弊的回归自然之旅。苏轼的“随物赋形……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的自由风格,严羽的“别材别趣”和“透彻玲珑,不可凑泊”的提出,元好问的崇尚自然天成的诗美境界,李贽的童心说,清代某些戏剧理论,王国维的“其词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等等,无一不是生态批评方法论在文艺理论建构中的运用
三、中国文学构建中的生态意识
生态批评家都意识到,文学要为当今的生态危机负一己之责,因为与生态灾难颉颃而行的乃是反生态文学的助纣为虐。批评家和文学家理所当然要通过改造文学和文学观念来拯救自然和人类本身。文学从而应该扮演救世主的角色,履行救赎的使命。
生态批评家认为,生态批评的范围不仅包括理论、生态作家和生态文学作品,还应该将反生态文学作品囊括在内。中国在生态批评理论研究方面虽然滞后于西方,但生态文学写作起步早于后者,并具有很高的自觉意识。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晋的陶渊明的田园诗和谢灵运的山水诗,这又比西方梭罗的《瓦尔登湖》早出一千五百多年。我们这里把从中国古代到现当代中国生态文学作品(包括反生态文学作品)稍加厘清,试图从它们所表现的主题之维予以大略的分类,从中可以见出中国生态文学发展的自觉历程。
(一)自然书写中的生态作品
生态批评原则之一是提倡作家自然书写,即以大自然作为描写对象。这里就有两种情况需要辨明:一种书写自然的作品虽然是以自然为书写对象,但是这类作品的作者往往将自然视为低层次的美,他们将自然作为人的内在精神或本质力量的外化。作品中的自然被工具化、功利化了,自然只是作家为抒发感情的手段、符号或对应物,是表现、对应、暗示、象征人的内心世界和人格特征的工具。如中国传统写作中的比德手法的运用——如以“岁寒之松柏”中的松柏来比喻君子高洁的品格;另一种是生态的自然书写,这种作品旨在表现自然自身的美,而不是表现人的思想感情或人对自然的抽象认识。所以生态作家卡森认为的,要做到生态审美,就要摆脱文明和理性对人的种种束缚,回归到自然天性。
自然书写中的生态审美作家可谓代有其人,我们且以诗歌为例略加分析。陶渊明作为这方面的卓越代表首开其端,《桃花源记》里的“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描写的正是典型的生态社会图景,令人向往和留恋。而最后桃花源的消失,也寄托了作者精神文明的失落。他的《归园田居》系列写到田园风光的美好动人,农村生活的舒心愉快和自己回归自然后的惬意。陶何以如此享受农村和农耕生活?个中原因不过是在原始农耕社会,只有农业才有着与自然更亲密的关系。只有心不为物所役,就不会为丰厚的物质利益驱动而贪得无厌,人类就可以把大量时间用来与自然交流,从中享受天地间的精神愉悦和审美情趣。特别是他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其五)所描写的这种自然、平和和超逸的境界,这是浑然天成,物我一体的化境,完全没有主体的痕迹。再就是山水诗人谢灵运,“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之类的纯自然描写的诗句可以说难以胜计,具有很高的生态审美价值,从鲍照对他的评价“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中可见一斑。
唐朝山水诗更为繁盛,生态诗人众多,其中以王维(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和孟浩然(深巷斜晖静,闲门高柳疏)最具代表性。在他们的作品中,自然与人高度融合,人形迹全无的化入大自然,成为其中有机运动的一分子,人的精神转化为具有观赏性的艺术形态。特别是盛唐诗人群,出现了山水诗辉煌的局面。他们顺其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取向,使得其作品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出现了全新观念,从而提升了自然生态的文化品位,增加了山水诗的审美意蕴。即使是用于“佐酒言欢”的宋词也不乏这种纯自然书写的作品,如辛弃疾的“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让人心醉神迷、流连忘返。而在我们高度发达的信息社会里,这样的人间仙境已然是人类遥不可及的梦想。宋词中这类词人和作品比比皆是,这里不再赘述。
(二)反映人的社会化所造成人的自然性和天性的失落的作品
以晚清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婴宁》为例,婴宁是一个天性纯真爱笑的狐女,未经世俗污染时,其自然天性自由流淌,毫无伪饰。但当她投身到人际社会,在从自然的人变成社会的人这一过程中,由“无时不笑”到“笑须有时”,再到“矢不复笑”,,意味着她的自然天性的泯灭和对社会礼法的顺应。自然人成为社会人,在作者看来颇具悲剧意味,象征着人类无法解脱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矛盾,寄托了作者对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的生态主义思考,昭示了人类社会的生存困境。
(三)对现代文明或工业文明的批判和对传统文明认可的作品
这类生态文学作品以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为代表,试以《萧萧》为例。《萧萧》中的女学生是现代文明的化身,而以萧萧的祖父为首的农民则是传统文明的代表。在后者的眼中“奇怪可笑”、“行为也不可思议”、“正经事全不作”的女学生奢侈浪费、好吃懒做,也喻示了对中国传统文明中的勤俭节约、遵礼守法等优良传统的赞美和对现代文明某些方面的批判。而女学生看一场戏的钱在乡下可以买五只大母鸡以及请人照顾孩子而自己整天看戏打牌的恶习则寄予对非生态消费文化否定。人类异化消费导致了精神危机和生态系统的失衡,对人类的危害是毁灭性的。沈从文描写湘西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的生态作品很多,这里仅举一例。此外,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也属此类。
(四)经典的重读——反生态文学作品
对人类文明和社会变迁产生了重大影响作品,都可以从绿色的视角来审视和重读。“没有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不管它产生于何处,完全不能被生态地解读”[6]。如果我们从反生态的角度对许多表面看起来的非生态文学作品进行解构,就会发掘出其中蕴藏的反生态思想。有两个典型的例子:其一是《儒林外史》里描写的严监生,传统的阅读者在评价这一人物形象时,往往顺从作者原意,将他看成一个吝啬鬼。让人们津津乐道的最能体现他守财奴性格的细节就是他临死前还不忘记让人挑掉一根灯芯。但是如果我们从生态学节约资源的角度重新审视严监生时,他却是一个力行正确消费观和对资源有限度开发的人,这就和吴敬梓的原意形成了悖论,《儒林外史》也就成为了反生态的作品。其二,我们同样可以从反生态的角度对铁凝的小说《啊,香雪》进行生态学的批判。小说以闭塞落后的北方山村台儿沟为背景,表达了姑娘们对山外文明的向往,对改变山村封闭落后、摆脱贫穷的殷切期盼,同时表现了山里姑娘的自爱自尊和她们纯美的心灵。但从生态批评角度来看,作者却由于忽略了现代工业文明与科技(小说中的火车)对台儿沟即将带来的负面影响——环境的破坏和人的自然性的丧失,这显然是铁凝始料不及的。作品也因此具有了反生态的意义。
(五)中国现当代生态文学作品兴盛
值得欣慰的是,中国生态文学创作的传统并未因为生态批评理论的相对滞后而止步不前。许多中国当代作家在生态观念上无师自通,能够与大自然达成谅解,获得了生态批评的智慧。较早的一部分作家的作品描写了在现代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和消费文化笼罩下的人类走向自我毁灭的悲剧命运,人陷入与人隔离、人与自然生命隔离的困境,作家们以此提醒人类进行反思,这无疑是在为人类寻找新的出路。贾平凹的、张炜、张承志和铁凝等均属此类。由于生态批评的概念和理论是二十世纪末才正式被引进到中国,因此现当代的上述作家并不是在其理论的指导下才开始生态文学创作的,所以他们的创作还是一种高度的历史自觉。
还有一些作家如陈应松、杨志军、杜光辉、于坚、郭雪波、叶广芩、苇岸、迟子建、李存葆等作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密切关注大自然,并用生态意识对其进行充满诗意的自然书写。虽然他们的生态写作多少受到西方生态批评思想和西方生态文学的影响,但在总体上并未受到西方生态批评思想的系统化理论化的规训,从本质上说,他们的生态文学创作还是一种自觉意识。他们作品的生态思想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态失衡、环境污染不仅伤害自然,也侵蚀着人类的心灵和精神世界,人在自然面前失却了同情心。物质文明隔离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亲密接触,导致人与自然的温情和道义荡然无存。一些作家以此为切入点,创作出一大批以动物为题材的生态作品。其实人性与兽心之间并无截然的界限,《列子.皇帝篇》就指出:“人未必无兽心,禽兽未必无人心。”让人联想到最近一条新闻:哈萨克斯坦的一条家犬为救出醉睡在铁轨上的主人竟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据统计,中国当代以动物为题材的生态的小说占所有生态小说的二分之一以上。中国的动物生态文本不仅数量多质量高,还有自己独特的书写领域。其次,部分生态作品反应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本来环境也要保护、经济也需要发展,但是二者碰撞必然会发生错综复杂的矛盾,并且这对矛盾之间又牵涉关联到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等矛盾。
此外,像沙青在1986年发表的第一篇全景式生态报告文学《北京失去平衡》和1988年创作出版《依稀大地湾》,开创了中国生态文学的先河。还有徐刚于1988年在《新观察》第二期发表的报告文学《伐木者,醒来!》,它用刺耳的砍伐声给在现代化进程中乘风破浪、一日千里的中国拉响了警报。这些作为中国生态文学的开山之作,它掀起了生态文学的创作高潮。
四、结论
从古代哲学、古代文论和文学作品三个大的方面总结了生态批评的在中国的自觉建构,既有纵向梳理也有横向的分类。其实,中国很多方面的建构都包含了生态批评的观点,限于篇幅,以上所论只是冰山一角,这有赖于更多学者的开发。另外,在具体的分析时,也未免挂一漏万,例如对中国哲学所包含的生态批评的论述不够全面,对中国现当代生态小说进行分类方面没有将诗歌囊括在内等。然而这些都足以证明,中国的生态批评研究虽然较西方略为滞后,但中国在以上三个方面的历史建构中已经自觉地有意识地运用了生态批评思想和方法论,这是生态批评在中国建构的历史自觉,也是后来提出生态批评这个概念的西方国家无法比拟的。中国先贤们在生态批评创建方面的筚路蓝缕之功,值得人们重视和关注。
与此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其一,虽然中国哲学、文艺理论以及文学作品中包含着丰富的生态学思想,但遗憾的是中国并未形成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生态批评理论体系。究其原因:中国人深受天人合一的一元论思想之影响,认为人与自然是和谐共存的,再加上中国工业化程度远远落后于西方,没有充分认识到物质技术进步给人类带来的生态灾难和危机,因而未能在理论上予以深刻地探讨;另外,中华民族近现代深受内忧外患困扰,文学家们的任务主要是救亡图存,因而较少关注生态写作与批评。其二,即使在西方生态批评理论传入中国后,中国的生态文学创作艺术上还存在着模仿和角度稍嫌单一的毛病,诸如以人与动物的关系(特别是人与狼)为主题的作品居多,有的作品有模仿西方作品之嫌。这正是缺乏生态批评理论指导所产生的局限。
[1]埃德加·莫兰.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M].陈一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69
[2]王诺.欧美生态批评[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
[3]赵保佑.老子思想与人类生存之道[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450
[4]鲁枢元.文学与生态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2011:29
[5]李建中.中国古代文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92
[6]BRANCH,Slovic.The ISLE Reader:Ecocriticism,1993-2003[M].Athens: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