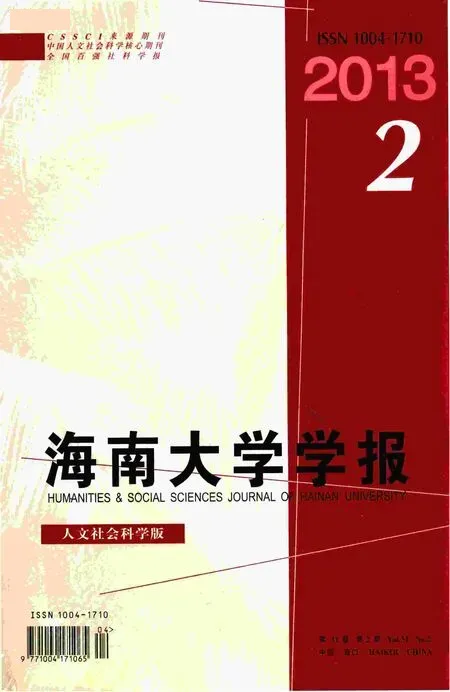林译小说“思想性误读”根源探析
王金双,范晓霞
(内蒙古民族大学 文学院,内蒙古 通辽028043)
林纾及其译作是中国近代文学、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存在。林译小说之所以能在清末民初成为“畅销书”,尽管有与爱国维新思想的时代主题合拍等时代政治因素,但最为关键的还是源于他出色的小说译笔和极富林氏特色的“思想性误读”。
一、林译小说中的“误读”及成因
“误读”(misunderstanding)最早是作为一个文学批评的概念由当代美国著名文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提出的。这一观点认为后人对前人诗作的评论或解读就是一种“误读”和修正。而翻译领域中的“误读”是指一种文化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去阐释异己文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必然现象。
多元共生的世界文化尽管形态各异,但彼此都具有一定的共性,这就使相互交流与对话成为可能。而它们之间的差异性既是相互交流的原因和动力,又是彼此对话的障碍。因此,只要有两种或多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这种思想、文化上的“误读”就不可避免。译者的核心任务,就是要努力将“误读”程度降到最低。他们对这种差异的理解与把握程度影响着“误读”的具体表现情况。对“误读”的分类可从两方面来进行:从造成“误读”的客观原因来看,可分为语言“误读”和文化“误读”;从造成“误读”的主观原因来看,可分为有意“误读”和无意“误读”。通常,它们相互兼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分清。
钱钟书先生认为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是“化”。他说,“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文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1]。但这只能是翻译界所追求的一种“乌托邦”罢了。因为正如钱先生所说,一国文字与另一国文字之间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与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间也有距离,且译者的体会与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有距离,这样的三种距离导致了“讹”(即人们所说的“误读”),也就是说,与原文相比,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这是翻译中无法避免的宿命。根据钱先生的阐述,可以发现,这里所说的“讹”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种是疏失谬误的“讹”(无意“误读”),就是由于译者的无心之失所造成的对原文曲解、漏译或者误译的现象,这种“讹”是无法避免的;另一种就是所谓明知故犯的“讹”(有意“误读”),即译者对原文刻意的加工改造。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可以克服的,而有分寸地把握全在于译者。
林译小说中的“误读”可以说是难以尽数。造成这种“误读”的既有时代社会原因,也有合作者的原因。当然,最为关键的还是与林纾本人翻译古文的水平尤其是与他的自身文化心理结构息息相关。而由此形成的“思想性误读”也成为林译小说最具林纾个性化特色的部分。
二、林译小说中的“思想性误读”
所谓“思想性误读”就是指由译者自身的文化价值观与伦理道德观所决定的有意“误读”。考察林译小说“思想性误读”的根源,当然与他所处社会的政治、文化背景密切相关,但更离不开其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及伦理道德观,而后者正是笔者考察的重点所在。林译小说中“思想性误读”归根结底是由林纾本人的文化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其核心是儒家的文化价值观与伦理道德观)所决定的,是译作及译者的思想及价值层面,表现出林纾本人的思想倾向和意识形态目的。这当然与他本人较为独特的中西文学观密不可分。
(一)林纾的中西文学相通观
在中西文化的对比、碰撞与交流中,维新派与守旧派都强调中西文化之“异”,但前者认为中劣西优,主张“全盘西化”,“以西化中”;后者认为中优西劣,主张固守传统,“以中化西”。而张之洞、林纾等人则强调中西文化之“同”与“通”,认为中西文化并非格格不入,而是“中西兼通”,主张“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并最终达到“以中化西”。正是这种“不西不中”、“又西又中”的貌似“维新”实则“守旧”的“中间派”,在清末民初那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对中西文化的交流尤其是西方文化向中国的传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媒介作用。尤其是林纾,他不但以自己的思想观点,更以自己身体力行的译书行动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林纾对中西文学相同相通性的认识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可以这么说,他不断译书的过程,也是他自身思想及中西文学观念不断整合发展的过程。
林纾最早翻译西文小说是为了排遣丧偶的寂寞,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可为何到了后来此举竟走向了必然呢?笔者认为,除了《巴黎茶花女遗事》问世后的畅销及读者的好评之外,更重要的是他找到了翻译西方小说的政治化与道德化的解释,并最终将原著思想及译书行为整合到了自己根深蒂固的文化价值观与伦理道德观中。当然,这一认识与整合有一个由浅入深、逐渐发展的过程。
大家知道,林纾不懂西文,因此对西文的小说、戏剧、诗歌、散文四大文学体裁发展较为成熟的格局几乎是一无所知。他最初对西方文学的认识几乎完全来源于他周围懂外语的翻译合作者。魏易——曾经是林纾最好的口译合作伙伴之一——曾经向林纾说过“小说固小道,而西人通称之曰文家,为品最贵”之类的话[2]154。朋友的这些开导,无形中会促使林纾在文学观念上认同西方小说的“雅”。既然如此,他以传统士人一直认为“大雅”的古文进行翻译,正好是“以雅对雅”。以中国的古文来类比西方的小说,真可以说是“才子配佳人”,那可正是“门当户对”了。退一步讲,尽管在当时,中国小说的社会与文学地位还无法同西方小说相比,从事与小说有关的文学活动似乎与士人的身份很不相称,但林纾本人也会下意识地认为:自己涉足的是“外国小说”,不是中国小说,而外国小说是“为品最贵”的。既然如此,那自己翻译外国小说的行为也就不会受人鄙视了。正因如此,林纾的不懂西文及西方文学,使他越过了语言和文体的界限,摆脱了中国人视“小说为小道”的文体观念,能直接进入文本的内在审美形式中,在西方小说与中国史传的巨大文体差异中感受到了它们之间的“通”与“同”。大家不能否认,在艺术作品中,无论中西还是古今,其内在精神肯定有相通或相似的部分,不然人类文化就无法交流。但林纾对中西文学相通性的认识,应算是他的“误打误撞”,而这正是通过他的“思想性误读”来实现的。林纾中西文学相通的观点,总结起来大约有两点:
一是技法层面(不是文体层面)。在西方小说中寻找与中国史传和唐宋派古文一致的审美契合点。林纾所遵循的古文义法,所谓“开场”、“伏脉”、“接笋”、“结穴”、“开阖”等,都类似于西方小说的叙述技巧。他最崇尚的左、马、班、韩四大家的作品,在情节与叙事方面与西方小说有相同之处。钱基博说林纾的翻译小说,“虽译西书,未尝不以古文义法也”[3]189。在译述西方作品的过程中,林纾感受到了它们与左、马、班、韩文章“蹊径正同”的妙处[3]188。正因为在翻译的过程中,林纾亲身体验到了西方小说与中国史传文气的相通,这更进一步坚定了他西方小说“为品最贵”(大雅)的观念,由此也坚定了他用古文翻译西文的信心。同时,他将这种“中西精神是可以沟通的,以古文翻译是恰当而自由的”观念通过史传式的古文,通过作品传达给读者。这无意中打破了时人对西方文学与文化的隔膜,提升了西方文学在国人心目中地位的同时,也无形中提升了中国小说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二是政治与伦理道德层面。以儒家道德规范阐释西方文学与风俗人情,使国人认识到中西小说共同的“政治载道”功能及相同的伦理道德观。林译小说刊行之时,正是梁启超等大力倡导“小说界革命”与“政治小说”之日,林纾的翻译实践正好与时代潮流合了拍。翻译西方小说不仅能有卖点,更重要的是还能与爱国和载道相结合,真可谓是一举两得了。当小说这一“小道”在新小说家的倡导下也获得了“载道”功能时,时人开始对中国小说另眼相看了。林纾通过翻译告诉中国读者,不仅在文学上中西有很多共同点,就是在人性与人伦关系上,西人也并非是无父的野蛮之人。在《英孝子火山报仇录·序》(1905年)中,林纾说:“‘欧人多无父,恒不孝于其亲’。辗转而讹,几以欧洲为不父之国。……于是吾国父兄,始疾首痛心于西学。”[2]155而实际情况则与传言相反。当然,这种政治与伦理道德层面的相通,林纾是通过他的甚至不无牵强附会的“思想性误读”来实现的。当然,无论怎样“六经注我”,翻译过程中完全的中国化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西方小说本身所承载的一些现代思想与道德评价如“恋爱婚姻自由”、“民主”、“女权”等,通过林纾的翻译,不仅为那些想呼吸异域新鲜自由空气的新派读者提供了平台并进一步刺激了他们求知西方的渴望,而且连林纾本人也未能“出污泥而不染”。在儒家伦理道德的架构中,他也潜移默化地接受了一些西方的现代话语与观念。如译完哈葛德的《红礁画桨录》(1906年)后,林纾对婚姻自由很有感慨地说:“婚姻自由,仁政也。苟从之,女子终身无菀枯之叹矣。”[2]182当然,他还是主张在“礼”的规范中实现婚姻自由。
(二)林纾“中体西用”、“以中化西”的矛盾思想
林译小说“思想性误读”的根源就在于林纾本人“亦中亦西”、“中体西用”、“以中化西”的矛盾思想,即:既想通过西学维新救国,又想固守封建礼教,维护封建制度。
说到“中体西用”,必须提到这一思想的代表人物张之洞。其代表作《劝学篇》以“中体西用”为本书的“一贯之道”,主张在维护封建纲常名教的原则下,谨慎地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的“西艺”与“西政”,以此来“补”封建制度之“阙”,“起”清廷统治之“疾”,在西方文化、政治、经济、教育等的强烈冲击下,维护中华民族的生存权利。《劝学篇》的核心问题是要求人们“保国、保教、保种”。张之洞认为,西方之强,中国之弱,这是不可否认的现实。但是,导致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不是外在的军事技术和军事实力的悬殊,而是由于中西文化与教育的重大区别。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从本质说来,注重治道人心,沿续了几千年的纲常名教,对于维护封建统治和社会伦理秩序有重大作用,这是西方基督教不可替代的。《劝学篇》着重阐述了“保名教”即是“保中国”和“保种”的根本措施问题。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中化西”思想是中西文化猛烈撞击、新旧文化急剧交替时代张之洞、林纾这类由传统文化塑造出来的近代文人所特有的文化心态。由于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和国内守旧势力的双重夹击,造成内心尖锐冲突。他们的行为方式与价值取向在不同程度上也存在对立倾向:思想先进而心理传统,理论激进而人格保守,是西式学理与中式伦理、责任感与负疚感的奇妙混合,结果是理性选择与民族情感的牴牾此消彼长,从而陷入了两难的困境。
林纾提倡学习外语,学习西方工商业,了解西方文化,但清末民初的“文化与文学自大”的心态使他并不完全醉心于西方文化。在《块肉余生述·序》(1908年)中,他一方面“敦喻诸生,极力策勉其肆力于西学”,另一方面又说:“不必醉心西风,谓欧人尽胜于亚,似皆生知良能之彦。”[2]349在《吟边燕语·序》(1904年)中,他指出:“欧人之倾我国也,必曰:识见局,思想旧,泥古骇今,好言神怪,因之日就沦弱,渐即颓运。而吾国少年强济之士,遂一力求新,丑诋其故老,放弃其前载,唯新是从。……顾必谓西人之夙行夙言,悉新于中国者,则亦誉人增其义,毁人益其恶耳。”对那些偶通西语,“其自待俨然西人”的人十分鄙视,称之为“无志之人”(《伊索寓言·单篇识语》,1903年)。他主张学习西学,为的是“以彼新理,助我行文”,并希望中西文化互补,认为:“将洋汉两门,分道扬镳而指授,旧者既精,新者复熟,合中西二文溶为一片”(《洪罕女郎传·跋语》,1906年),才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理想境界。这是林纾作为儒家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的思考,以西方文化为参照,通过翻译与西方对话,在认识到东西文化差异的基础上,为整合中西文学和文化,让两种文化达到优势互补寻找契机,并以此再造民族精神的气魄,积极开拓传统文化,振作民族精神。但林纾的这种中西文化交融的理想境界,明显带有“乌托邦”性质,言说性更大于实践性。其实林纾内心真正固守的观念是“以中化西”,“中体西用”只是他最终实现“以中化西”的一种过渡手段而已。这是由林纾自身的知识文化及心理结构所决定的:林纾终其一生,始终未能超越儒家的伦理道德。对儒家伦理道德的恪守,既是他的感情依恋,也是他的精神寄托。这不仅表现在他的译书思想上,更表现在辛亥革命以后的实际行动中。他以清朝遗老自居,多次拜谒皇帝陵,并声称“一日不死,一日不忘大清”[4]。其实林纾翻译西方小说不是出于一种文学的自觉,而是把译书作为一种实业,既可以布道又可以赚钱。在《爱国二童子传·达旨》(1907年)中,林纾写道:“畏庐,闽海一老学究也。少贱不齿于人,人已老,无他长,但随吾友魏生易、曾生宗巩、陈生杜蘅、李生世中之后,听其朗诵西文,译为华语,畏庐则走笔书之,以冀以诚告海内至宝至贵、亲如骨肉、尊如圣贤之青年学生读之,以振动爱国之志气。人谓此即畏庐实业也。”还说:“吾但留一日之命,即一日泣血以告天下之学生,请治实业以自振。更能不死者,即强支此不死期内,多译有益之书以代弹词,为劝喻之助。”他把翻译外国小说看作是自己救国的一种实业,通过译书,“畏庐赤心为国之志,微微得伸”[2]290。在《雾中人·序》(1906年)中,他感叹到:“余老矣,无智无勇,而又无学,不能肆力复我国仇,日苞其爱国之泪,告之学生,又不已,则肆其日力,以译小说。”[2]185
林纾不像梁启超,他对自己翻译小说的“革命性”意义没有自觉意识,他更为关心的是“末世”之中儒家学说与古文的命运。最能体现他文化价值观与伦理道德观的是1924年他去世之前所写诗《留别听讲诸子》中的一句话:“学非孔孟均邪说,语近韩欧始国文。”[5]这是林纾一生为人、为学、为文的夫子自道。这里,“语”(韩欧古文)是“学”(孔孟之道)的语言载体,“学”是“语”的内容,二者合二而一,不可分离。这也就不难理解,林纾在晚年竟然将古文之盛衰、文运之盛衰与国运之盛衰联系起来的原因了。因为大清立国之本是孔孟之道,而古文之盛衰又表征着孔孟之道之盛衰。
尽管以古文家自居,但实际上却是翻译小说使林纾一举成名。但林纾本人却不这样认为。尽管翻译和绘画使他名利双收,可林纾最恼别人恭维他的翻译和绘画。在正统的观念中,绘画与小说只能是“器”而不是“道”,只能是“用”而不是“体”。只有集道德学问于一身的古文,才是真正的“道”和“体”,才是士大夫安身立命、耀祖扬名的正经事业。一个颇为有趣的例子是:1912年,康有为为答谢林纾为他作的一幅画《万木草堂图》,特赋诗一首,其中第一句是:“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将林纾与严复相提并论,以赞美他翻译小说的功绩。不料林纾与严复都不买账,严复认为连外文都不懂的林纾根本就称不上是翻译家,没有资格与自己相提并论,羞于与他为伍。而林纾认为自己最为人称道的应该是古文,当然可能也有对自己排名于严复之后的不屑。
因此,林纾在翻译时没有用清末民初的小说标准去看待“为品最贵”的西方小说,而用中国“为品最贵”的史迁笔法与之相比。在对“小说”这一文体上,林纾是重外轻中的,一方面体现在他把外国小说与中国的“史迁”相类比,盛赞外国小说;另一方面体现在他把中国小说与外国小说对比,贬低中国小说。例如:在《伊索寓言·叙》(1903年)中,他认为中国古代的寓言、志怪小说不能像外国寓言一样“益童慧”,只可供人“侑酒”[6]。在《蛮荒志异·跋》(1906年)中,他认为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除了能“志狐鬼也”外,并没有什么更高的文学价值。这说明在晚清那个时代,中国的小说还不受重视,很多人对其有偏见。如果把外国小说与中国小说相类比,结果可想而知。中国正统文人一直认为小说是“小道”,无法与“史传”的“真实性”相比。这就是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的“史家成见”[7]。而如果把西方小说与中国的史传相比,才正好能克服传统文人对小说的偏见,扩大西方小说在中国的影响,这在客观上来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史迁笔法”不仅是林纾评判西方文学的价值尺度,而且还是他认同西方文学的基石。这与其说林纾是对西方小说本体特质的发现,不如说是他的文化心理结构的自然显现。在这种类比的背后,林纾以自己既有的文化心理结构为基础,在翻译过程中对西方文学融入了自己的理解,把西方文学纳入到了自我所认同的中国文化中。
在200多种林译小说中,用“记(或纪)”、“录”、“传”、“史”、“迷”、“志”、“略”、“遗事”等字来翻译的有近百种。由此看出林纾的思想倾向,他总是喜欢给自己翻译的作品起一个历史书一样的名字。在其译作中,他将英国的迭更司、司各特,法国的森彼得、小仲马同中国的司马迁、班固相比,说外国作家的小说笔法“处处均得古文义法”(《块肉余生述·序》,1908年)。他称赞迭更司的《块肉余生述》(原著《大卫·科彼菲尔》)可与《史记》、《红楼梦》媲美[2]348,盛赞《撒克逊劫后英雄略》(1905年)的作者司各特“可侪吾国史迁”[2]160,译完哈葛德的《斐洲烟水愁城录》(1905年)时,感叹“西人文体,何乃甚类我史迁”[2]158!这都是他的“史家成见”作崇的结果。
至于在翻译文本中,林纾所作的政治化及伦理道德化的“思想性误读”更是难以计数。
三、总结
林译小说最主要的贡献不在它究竟传播了多少西方现代话语及其所承载的现代思想,而在于它在充分发挥了自身“媒”的作用的同时,也以自身的魅力提高了中国近代小说的社会及文学地位。而之所以能充分发挥其“媒”的作用,最为关键的因素就是林译小说中的“明知故犯”的有意“误读”(“思想性误读”)。尽管后人对林纾的这种“明知故犯”多有批评,但历史地看,正是他的这种对西方文学的有意“误读”,开拓了中国文学现代性发生的价值转换空间:“它打破了中国文学长期的雅俗阻隔,使‘异端’与传统得以调和;同时,这个空间所容纳的西方价值,成为孕育反叛传统的温床,相当大地影响了‘五四’一代的文化选择。”[8]由此奠定了林纾“译坛泰斗”的地位。
任何事物在孕育着生机的同时,也在孕育着危机。没有“思想性误读”,就不会有林纾及林译小说的风行。但也正是因为他的这种“一叶障木,不见森林”的“思想性误读”,西方文学经典思想的丰富性与内容及创作方法的多样性被抹平了。当然,这是历史使然,人们无权去责怪林纾。世易时移,随着中西文化交流与沟通的深入,随着越来越多的更能体现原著精神风貌译作的出现,以“思想性误读”为其个性化特点的林译小说,最终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走向没落,已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
[1]钱钟书.钱钟书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269.
[2]林纾.迦茵小传·小引[M]∥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3]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M].长沙:岳麓书社,1986.
[4]张俊才.林纾评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7:158-160.
[5]朱羲胄.林畏庐先生年谱:2[M].上海:上海书店,1991:65-66.
[6]林纾.伊索寓言·叙[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1.
[7]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鲁迅.鲁迅全集:9.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1.
[8]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84.
—— 百年林译小说研究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