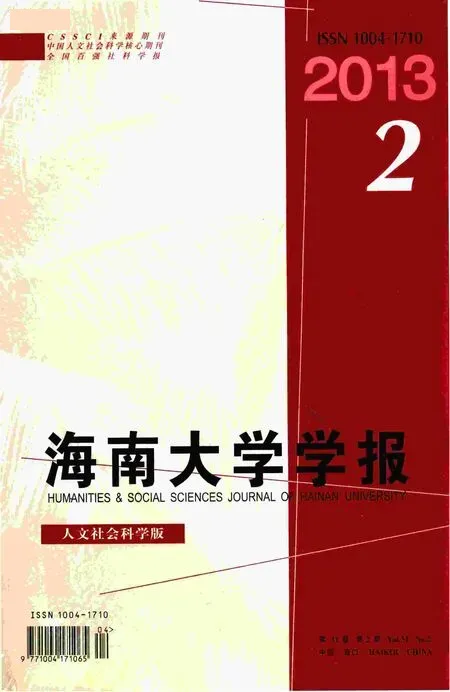归去来兮:贾平凹的城乡游走与家园梦寻
许心宏
(安徽财经大学文传学院,安徽蚌埠230030)
XU Xin-hong
(School of Literature,Art and Media,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Bengbu 233030,China)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几乎每位乡土作家都有其“文学根据地”,贾平凹自然也不例外。在其“没有商州就没有中国”[1]小说创作中,商周是其起笔之源,也成全了他作为一个作家的存在。就其文学创作的心理结构而言,内中潜藏着一个基本的“文化参照”与“文化发现”机制,用作者本人的话说,就是“商州永远是在我心中的,它成为审视别的地方、别的题材的参照。”[2]但是,作者的经验之谈,应该说只讲对了一半,因为城乡游走间“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的双向文化心理体验,使“农裔城居”与“商周回望”演绎成了文学视域中“城—乡”互看的文化视角。20世纪90年代以降的小说文本中,深层结构的“离乡—进城—返乡”的文学性书写,内中存有空间结构性、视角互视性、文化裂变性、家园失依性的审美现代性意义。基于现代化与现代性的二律背反,内隐于城乡时空间意象中的,是叙事者文化心理根植与调适、文化身份焦虑与认同、城乡情感与家园归依等问题。
一、居城望乡:乡土祭礼的文化伤怀
《废都》是其首部关于“城的小说”,但也是文化拒斥性的城市书写。“废都”之“废”体现在文脉的鬼气、妖气与暮气的灰暗之网中。就寓居于西京城的庄之蝶而言,其好友孟云房说他“别看庄之蝶在这个城市几十年了,但他并没有城市现代思维,还整个价的乡下人意识!”[3]城中的庄之蝶,他眼中的城市意象并未定格在现代城市文化景观上。相反,城中的孕璜寺、双仁府、古城墙等却成为其寻根访古的文化心理体现形式。即便身在西京,他钟情的还是农耕文化传统中土制的埙所发出的“土音”。究其因由,作者在《关于“埙”》中说到:“我喜欢埙,喜欢它是泥捏的,发出的是土声,是地气。埙音的声响宜于身处的这个废都,宜于我们寄养在废都里的心身。”[4]与《废都》中的“埙”形成文化意象交叠效应的是《白夜》中的“古琴”,两者暗合了古代文人雅士文化心理的乡土根性。从器物到动物,在文化访古的境由心造中,《废都》中来自终南山的奶牛极具文化根植的象征意义。在牛活着的时候,庄之蝶趴在牛肚上喝奶,寓意其精神断奶的艰难。在牛死后,庄之蝶藏有牛皮和牛尾。一生一死之间,奶牛成了庄之蝶心性原型的化身。在动物视角的魔幻叙事中,牛进了城感觉是进了屠场,就城中人的生存处境而言,它认为“可悲的正是人建造了城市,而城市却将他们的种族退化了”,因而“城市有一天要彻底消亡”。在对城市的文化心理拒斥中,这头神来之笔的“哲学牛”认为只有重返乡野才能过着返璞归真的生活。然牛与人的双死城中,寓意的是文化原乡的空幻,用牛皮制成的大鼓在北城门楼上呜呜自鸣,传递出了庄之蝶文化心理的悲戚之感。从奶牛到女人,庄之蝶与妻子牛月清结婚多年却无子嗣,意味着扎根城市的无望;心慕景月荫却又是在意淫中占有这位“城市高贵女人”。相反,庄之蝶在与乡下的唐宛儿与柳月的性欲狂欢中又显得欲壑难填,性成为其精神上的救命稻草,反证了其文化心理与文化身份的始源。但是,随着柳月的嫁人与唐婉儿被前夫抓回乡下,“女子温柔乡”成了失去的天堂。自此,古代士大夫意义上的“寄情山水”与“女子温柔乡”的两种“乌托邦”都已化作一去不复返的心魂惆怅。因而,奶牛的死去、乡下女的别离、庄之蝶命丧在离城的火车站等,庄之蝶乡土文化心理的坚守与家园渴求成了被悬置的问题。
承续《废都》家园梦寻的搁浅,《高老庄》中身为省城大学教授的子路返乡,形式上是为过世三周年的亡父祭祀,其实是文化寻根的祭祖仪式的表达。从省城回到故乡,生身故土的现代村庄在工商业社会洗礼中,庄内的权力争夺、仇富心理、为富不仁等,昭示的是村庄瓦解、乡土式微、人心不古的文化颓败线。就子路的文化身份而言,他从“本是农民”到“城籍作家”,在其一番乡土文化逡巡之后,撕毁了记载有高老庄地方土语的笔记本,在其“向后转”的文化怀旧中,既定的文化寻根梦成了黄粱一梦。在“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城乡游走中,他最终丧家犬一般逃离了高老庄,家园梦寻成了家园失依。其实,从作者创作史上来说,《废都》与《高老庄》还是在思维定势的“居城望乡”书写中,对桑梓之地尚抱有精神原乡的切望,然《秦腔》则在釜底抽薪中,内爆性地剥开了乡土文化的颓败书写。
《秦腔》中乡土文化颓败的沉郁与悲涩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就是农民的离土。在城市“轴心时代”,农民离土是经济理性使然,这使得越来越多的耕地因为村民外出打工而荒芜,整村整庄剩下的只有老弱病残,以致夏天智去世时“三十五席都是老人、妇女和娃娃们,精壮小伙子没几个,这抬棺的、启墓道的人手不够啊!”[5]在城市化发展中,就农民的离土而言,老辈人悲叹“后辈人都不爱了土地”,夏天义也说:“土农民,土农民,没土算什么农民?”随着夏天义的死去,其墓穴下葬的七里沟成了文化隐喻的象征,因为七里沟地形则呈“女阴型”,村里老辈人说:“七里沟是个好穴位,好穴位都是女人的×。”夏天义的“生于斯长于斯”,体现的是深厚的乡土文化情结,寓说的是农耕文化坚守者重返“自然—女性—土地”的地母世界。其次是秦腔艺术的衰落。扎根于800里秦川的秦腔有其丰赡的文化土壤,然在城市化、工业化社会发展中,乡下人的离土又离乡,使秦腔所根植的地气与人气日益稀薄,秦腔成为乡土文化守望者夏天智暗自饮泣的寂寥心曲,由其精心绘制的《秦腔脸谱》也成为“乡土挽歌”的文化寓言。夏天智的儿媳白雪虽也痴迷于秦腔,然她所供职的县文化剧团也是名存实亡。因而,以秦腔为代表的乡土文化的衰亡赫然可见。小说通过“农裔城籍”作家夏风的“离去”与“归来”见证了乡土文化的衰败,他说:“有父母在就有故乡,没父母了就没有故乡这个概念了。”这正如该书“后记”中作者写到的:“现在我为故乡写这本书,却是为了忘却的回忆。”再次,《秦腔》中体现了作者的“问题意识”,即“难道棣花街上我的亲人、熟人就这么很快地要消失吗?这条老街很快就要消失吗?土地也从此要消失吗?真的是在城市化,而农村能真正地消失吗?如果消失不了,那又该怎么办?”戋戋数语,体现了作者虽有时代关切意识,但却无从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留下的只是一个思索与迷惘并行的设问。这种迷惘颇似沈从文《边城》中“白塔”的坍塌与重建,隐蕴着文化悼亡意味。不同的是,《边城》结尾写的是文化冲突中的希望与绝望并存,《秦腔》则存有乡土落寞与审美现代性的文化哀伤。当然,学界有人称《秦腔》为乡土文学终结的“挽歌之作”。但是,在城乡文化的交锋交融中,乡土文化是否只会是一败涂地还是有着浴火重生的可能呢?其实,“终结”既是农耕文化形态的某种“结束”,也是现代文化形态形成的某种“开始”,它在意味着一种断裂的同时,恐怕也意味着一种过渡、新变、铸模与创造。
二、据乡失势:城市化的历史怪兽
李培林先生在翻译法国学者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一书“译者前言”中指出,在中国目前近八十万个村落中,很多村落的农民正在大量地失去土地,数千万农民在城市化的圈地中失去了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每一年都有上万的村落在中国行政版图上消失,这种巨变在任何国家的工业化历史上都不曾发生过,这些数千年的村落解体以后,原有的传统村落社会网络被打碎[6]。据统计,从1985年到2001年,中国的村落的个数由于城镇化以及村庄兼并等原因,从940 617个锐减到709 257个,仅2001年1年就有25 458个村落消失[7]。基于这一事实,反观贾平凹《土门》中的地处西京城乡结合部的仁厚村,村庄在政界、商界的钱权勾结与助推中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口,文本再现了“最后的村庄”的消逝史。
《土门》中的村长成义在孤愤的反抗中,他从外在形式到内在精神都对仁厚村的“被城市化”做了决绝的反抗。其治村理想是“要保持和建设一个都市里的桃源。要求家家户户整端自己的屋端和庭院,必须粉墙,必须修饰门楼,门楼上都要写上字匾,如‘耕读传家’、‘山明水秀’、‘吉星高照’、‘三阳开泰’一类的话。不要植草坪,城里的草坪那是学洋人哩,中国人历来栽花,农村更是在院内门前栽葡萄,栽石榴。栽芸豆,又好看又实用。”[8]208不难发现,内在文化心理的根植与外在花木栽种的表现,其文化根脉皆扎根于中国都市的乡土文化品格。相异于城市社会的规章制度,成义拟定了“村规十五条”,如“乐土,勤劳,亲善,孝道,卫生,计划生育和摊派……”然而,在外拒被城市化的同时却又“后院失火”,即村里有造假的、超生的、做小姐的等,因而,仁厚村的“藏污纳垢”是对仁厚村“仁厚”的反讽。对于村庄的病态,村长成义认为:“都是城市造的孽!西藏为什么就没有这些?仁厚村原先怎么就没有这些?这西京城越来越大,病人多了,犯罪分子也多了……”[8]288在其决绝的反抗背后,隐含的是作者对诗意乡土的审美回溯,寓说的是器物文化与制度文化的先进并不代表精神文化的先进的这一主题。再者,就是云林爷医治了很多患上“肝病”的人,巧合的是,这些患者多是城里人;神奇的是,患者在云林爷的中医治疗下,几乎是药到病除。“中医”的如此“神力”,在隐含作者看来,是因为“仁厚村是土地上的平房村子,只有土地能容纳病人,地气能消灭病菌!你们城里人离开了土地和地气,你们只有肝在报伤和坏死!云林爷若是神的话,他并不是医神或药神,云林爷实实在在是一个土地林!”[8]211小说中的“肝病”作为文化隐喻的一则镜像,象征着人类生存越来越远离了土地。“土地林”的云林爷代作为乡土自然的化身,与人造“城市森林”相对立。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的远离土地与脱离地气,意味着农耕传统的生活方式被连根拔起,言说的是乡土世界的消亡。在此意义上,“肝病”作为“疾病的隐喻”,是对“病态城市”的文化排斥感与情感疏离感。
其实,村长成义之死明显存有“杀身成仁”之意。为了仁厚村不被城市化的“历史巨兽”所吞噬,其绝地反击“偷盗文物”的“乱为”,无非是在内外无援的绝境下,解决仁厚村继续存在与发展所需的资金难题,然在与走私贩交货时败走麦城。随着成义的死与仁厚村的被拆迁,仁厚村成了“没有村子的村子”,村里的农耕文化遗产——明王阵鼓、墓地、水井、旧家谱、石碑等,随着仁厚村的消失而不复存在。于是村民梅子问“乡村智叟”云林爷“去山区还是留在城里?”云林爷说:“从哪儿来就往哪儿去。”然而,如是避实就虚的作答,解决的只是人的最终归宿问题,即人来自于土地最终归于土地,但活着的过程却成为悬而未决的问题。因而,云林爷的回答只是对生存现实的回避与躲闪,潜藏的是解决现实问题的无力与无奈。不过,《土门》中通过知识分子范景全说到:“南方的一些地方,城市和乡村已不截然那么分开了,农村的乡镇企业已经是农村在实行工业化,农民就是工人,工人也就是农民。现在不是一味地反对城市或一味地否定农村,应该有健全的意识!……走出浮躁,超越激愤,告别革命,于人于事都会有益。”[8]106因而,与《废都》相比,《土门》倒是迈出了城乡文化冲突的二元对立,用叙事者的话来说,就是“国家工业化,表现在社会生活方面就是城市化,这一进程是大趋势,大趋势是能避免的?!”在城市化的历史席卷中,在文化冲突的退守与调和中,作者为仁厚村构想了“神禾源”这一托身得所的“世外桃源”。“神禾源”是“一个新型的城乡区,它是城市,有城市的完整功能,却没有像西京的这样那样弊害,它是农村,但更没有农村的种种落后,那里的交通方便,通讯方便,贸易方便,生活方便,文化娱乐方便,但环境优美,水不污染,空气新鲜。”[8]107其实,“神禾塬”是“土地自然”与“人造城市”的择优化合。只是这般构想也并不新奇,因为早在1983年,英国学者霍华德就在其《明日的田园城市》中就写到:“事实并不像通常所说的那样只有两种选择——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而有第三种选择。可以把一切最生动活泼的城市生活的优点和美丽,愉快的乡村和谐地组合在一起。……城市和乡村必须结婚,这种愉快的结合将迸发出新的希望、新的生活、新的文明。”[9]因而,霍华德的“田园城市”(Garden City)和“城市—乡村”(Town-City)的文化整合构想与贾平凹《土门》中的“神禾塬”具有异曲同工之处。
三、崇乡鄙城:文化身份与家园意识
在《废都》、《怀念狼》、《高老庄》、《白夜》、《高兴》等小说文本中,叙事者的崇乡鄙城成为文化心理根植的一种潜在。从商周到西安,“当我已经不是农民,在西安这座城里成为中产阶级已二十多年,我的农民性并未彻底退去,心里明明白白地感到厌恶,但行为处事中沉渣不自觉泛起。”[10]22身为“农裔土著”作家一员,他是身在城市而心系故土,是可谓故土难离,这种身心分离的矛盾冲突,使作者对城市的否定乃至敌意转化成了创作心理的无意识。《废都》中庄之蝶在与妻子行房之际,意淫的却是汪希眠的老婆。对城籍的高贵女人景雪荫来说,庄之蝶也是在意淫中“占有”了她,尔后说:“在这个城里,我该办的都办了。”如是“精神胜利法”的一己慰安,体现的是其文化身份的自卑感,反向证明的是庄之蝶在乡下女人的阿灿、柳月、唐宛儿那里得到一种切实的满足。从文化身份根植上来说,性取向上的差异,体现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文化身份的同源性与文化心理的相通性。
从“文化闲人”的庄之蝶到农民工的刘高兴,《高兴》中刘高兴身份证上的名字为“刘哈娃”,进城后自改其名为“刘高兴”,然“改名”只是表象,背后则是文化身份的“阉割”。随着五富的死去,刘高兴自言:“我也会呆在这个城里,遗憾五富死了,再不能做伴。”其实,五富只是刘高兴精神面影的另一种存在,因而五富之死意味着刘高兴文化心理的无援与落寞。从身体器官上来说,“肾是人的根本”,刘高兴将自己的一只肾卖给城里人韦达后,就窃喜自己成了西安人,然器官的移植却也无从改变文化身份的始源性。他后来得知“韦达换的不是肾”,这对刘高兴来说是一种心理重创,因为他“之所以信心百倍我是城里人,就是韦达移植了我的肾。”在其文化身份的自我解构中,不禁联想到他进城后住的地方叫“剩楼”,这一“剩”字的皮里阳秋,就像《红楼梦》中女娲补天的“顽石”一样,即“剩下的”的意思,隐喻他的“边缘人”与“多余人”的文化身份。再看刘高兴与五富在西京城外麦田里的对话,对话地点“麦田”的设置,成为乡土情结的无言追思与文化身份的根植。五富说:“还是乡里好!没来城里把乡里能恨死,到了城里才知道快乐在乡里么!”刘高兴则问:“城里不如乡里?”五富说:“城里不是咱的城里,狗日的城里!”高兴则说:“你把城里钱挣了,你骂城里?”五富说在城里“不自在。”高兴说:“不自在慢慢就自在了,城里给了咱钱,城里就是咱的城,要爱哩。”对话体现的是生存理性与文化身份的矛盾性。就离乡进城的文化心态而言,五富是人未进城则心已恋家,内中的原因如五富说的:“西安城里都是凤凰就显得咱是个鸡,还是个乌鸡,乌到骨头里。”他对一己文化身份的卑微确认,看似消极,其实是乡下人“人不自贱,贱却自生”文化身份的无奈认同,意在说明城市不是农民工的城市。最终死在西京城的五富被“火葬”而非“土葬”,消解的是乡土中国“落叶归根”、“故土难离”、“入土为安”的乡土情怀,五富成了西安城里的“一个飘荡的野鬼”。
在《我是农民》的作者自传中,他说:“我的家原本在乡下,不是来当农民,而是本来就是农民。”[10]24这种文化身份“以退为进”的坚守,规约着作者对“城里人”文化身份的批驳。《高兴》中写:“城里人其实都是来自乡下,如果你不是第一代进城人,那么就是你的上一代人进的城,如果你的上一代还不是,那就肯定是上上一代人进的城,凡是城里人绝不超过三至五代,过了三至五代,不是又离开了城市便是沦为城市里最底层的贫民。”因而,刘高兴对自己文化身份的“屈己”之说,意在表明“自己是农民又什么时候认定自己是农民”,弦外之音就是自己是农民,但又不承认自己是农民。刘高兴会吹箫,吹箫作为一种文人雅艺,城里人据此认为他不是等闲之辈,刘高兴心知肚明却也不挑明自己的真实身份,认为:“别以为从清风镇来的就土头土脑,一脸瓷相,只永远出苦力吗?见你的鬼吧!”因而,孟夷纯在初次见刘高兴时就说:“刘高兴,你不像个农民。”刘高兴说:“是吗,羊肉怎么会没有膻味呢?”孟夷纯说:“她在城里见的人多了,有些人与其说是官员,是企业家,是教授,不如说他们才是农民。”刘高兴认为孟夷纯的话点到了自己心结上了,其实这些都是对自我文化身份的明证,一种文化身份的焦虑与渴求认同。城乡游走之间,从现实的“我”到紧紧拽住作品中的“我”,体现出文化身份与文化心理的始源,进而化作了对城市的心存敌意与文化厌弃。当然,这种文化心理的根植,作者是通过“民工潮”的农民工视角借以表达的。
实际上,正是在城乡游走之间,作者写出了家园诉求的审美现代性困境。《废都》中身置城中的“奶牛”认为“城市是一堆水泥”,且人造之城给人的种类带来退化,因而梦中梦见的高山流水、大片的草地和新垦的泥土等乡野意象,无疑是魔幻化的庄之蝶厌弃都市的心理写照,言说的是城市工商业文化越来越远离农耕文化的事实。《怀念狼》中,子明认为“城市就是水泥的街道和水泥的房子”,“不接地气”使得“生城市里生活了三代以上的男人,将再不长出胡须。”就“男人长不出胡须”来说,隐喻的是城市生活带来的人种的退化。小说开篇写:“西京城依旧繁华着,没有春夏秋冬,没有二十四节气,连昼夜也难以分清。”从生产形态上来说,时令的“春夏秋冬”与耕作的“二十四节气”皆为农事活动与日常生活的基本法则,然时令与节气的缺失,寓意的是农耕文化形态的缺席。《白夜》中的城市“白夜”,不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农耕文化时间的分配,“再生人”夜朗置身于妖气与鬼气的西京城,“家园何处”也成了怪诞的迷离与梦幻。对城市的厌弃与反感,使得“乡土—自然”的返乡情结与隐逸思想成为其文化心理的另一极。其实,早在文化随笔的《静虚笔记》中作者写:“在城里,高楼大厦看得多了,也便腻了,陡然到静虚村,便活泼泼地觉得新鲜了。”在《读山》中也写:“在城里呆久了,身子疲倦,心也疲倦了。”新世纪以来,除去《古炉》中“文革”题材的书写之外,这一主题可谓是一以贯之的。
四、结语
与西方工业文明相比,中国的现代化是“后发外生”的现代化。就西方的工业文明进程来说,有学者认为:“在文学里,也只有在文学里,人们才能排除与语言相关的那种粗俗的‘外在性’,找到一个精神之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理路的主题是都市出现之前自然史的反映,是对工业主义之前历史怀旧的回忆。”[11]20世纪90年代以降,从乡村中国转向城市中国,在社会转型的文化心理嬗变中,贾平凹小说中城市意象的建构,文化依据的始基是其农耕文化心理的在场。然而,当作者将文化视角扎进乡土文化根脉时,农耕文化的深层结构也在发生着裂变。因而,“据城怀乡”还是“崇乡鄙城”,文本中的“城—乡”皆有结构性文化寓意的生成;然当作者双向解构“城—乡”之际,却发现“城—乡”都是一个文化破缺的世界,“家园何处”成了“生活在别处”的精神流浪,城乡之间的归去来兮,成为一种焦灼性的文化体验与哀伤。《废都》中,庄之蝶梦想回到“终南山”,不料死在了火车站。他乘“火车”开往“废都”,然“火车”也是现代化器物而非农耕时代“乘牛车”离开西京城,在极强的文化“寻根”与“悼亡”中,表征的是传统农耕文明的渐行渐远。小说结尾写庄之蝶打算去“南方”,这里且不说庄之蝶没有去成,即便去成了,只是在他死前,他的怀里还抱着埙与牛尾巴。身为城里人的庄之蝶,其文化心理却是扎根于城市之外的,内中的乡土情结依稀可见。因而,从《废都》的“废城”到《秦腔》的“废乡”,在城乡“两废”中,“何处是家园”成了“何处都不是家园”的审美现代性困境。那么“家园”究竟在哪里呢?其实“真正自由的灵魂是注定的流浪者,只能居住在虚无之乡。它与物质或肉体的区别就在于它是‘无中生有’,是凭空创造。”[12]因此说,贾平凹的文化原乡不是经济学的实证分析;相反,则是美学的意象建构,她所代表的是童年、母亲、自然等意象,生发一种形而上的家园慰藉。
[1]贾平凹.商州:说不尽的故事序言[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2.
[2]贾平凹.贾平凹答文学家问[J].文学家,1986(1):5.
[3]贾平凹.废都[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314.
[4]贾平凹.平凹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94.
[5]贾平凹.秦腔[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538.
[6]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M].李培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7.
[7]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村的故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
[8]贾平凹.土门[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7.
[9]霍华德.明日的田园城市[M].金经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6-9.
[10]贾平凹.我是农民[M].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10.
[11]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M].王逢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38.
[12]邓晓芒.文学与文化三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4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