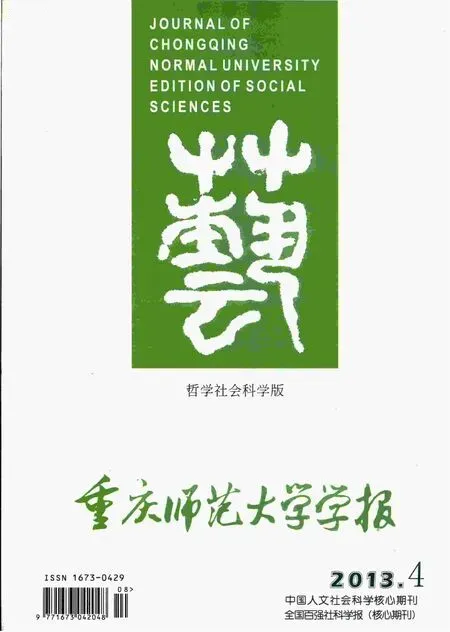巫巴山地远古巫文化的表象传承
邓晓 管维良
(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重庆 401331)
巫巴山地位于陕西、重庆和湖北三省市交界处,四川盆地和长江中游平原间,绵延数百里。这里的巫文化经过数千年的岁月留传至今,其许多基因与表象保存较好。文章将巫教、巫俗、巫艺这三方面放在同一层面进行考察,主要基于它们有着共同的载体——巫师,而巫师是最早的杰出歌手和舞师、最早记录历史的人、最早观察天象变化的天文家、最早的医师和最早的美术家。[1](5-6)是他们使得上述三方面有了互为表里、十分紧密的联系。
一、巫教的表象及传承
巫教是人类早期宗教活动的具体体现,它包括各种原始宗教、巫术以及祭祀、避邪、崇拜等,是巫文化的内核。巫巴山地人类最早的巫教活动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对重庆奉节旧石器时代晚期“鱼复浦遗址”的考古中,专家发现了有规律排列的12个烧土堆,“发现的石器、骨器多呈条带状分布在烧土周围。”[2](12)这可能就是一处原始宗教的活动遗迹。而属于新石器时代,巫山县大溪遗址发掘的人类埋葬方式则体现出宗教活动的典型特征,其埋葬的形式和随葬品的内容均足以说明这一点。[3](36)然而,巫教仅为宗教的低级阶段,它毕竟缺乏严谨的说教理论和成熟的程式化教仪。也正由于巫教还远未上升到高级阶段,所以直到奴隶社会时期的楚国,人民在处理信仰与形式的关系上还如《国语·楚语下》所载:“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
原始宗教最主要的体现是对鬼神的崇拜,因为鬼神是现实中与先民的想象最接近的,其流传下来的有昔时川东南的鬼教、沅湘间的娘娘教(美女教)、湘西苗族地区的苗教等等。川东南地区在巴族进入以前,是“鬼国”的中心,由“鬼族”所建。其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中心在今重庆的丰都县,即古之平都。鬼国的宗教——“鬼教”盛行于此,其大小统治者有鬼王、鬼帝、鬼帅、鬼官。由于鬼国在商代是西南的一个大方国,因而“鬼教”的传播范围颇广。“鬼教”既无经典也无组织,属于粗浅的原始宗教,崇拜鬼及与人们日常生活和生产最紧密的天、地、水三种自然物,崇拜方式主要体现为由巫师实施巫术,故又称巫教。自巴国于此建立后,“鬼教”便成了巴族部民笃信的宗教了。史载,东汉人张陵曾结合黄老之说,改造流行于巴蜀的“鬼教”,创立了五斗米道(后世称天师道)。“汉末,沛国张陵修道于蜀鹤鸣山,造作道书,自称‘太清玄元’,以惑百姓。陵死,子衡传其业,衡死,子鲁传其业。鲁字公祺,以鬼道见信于益州牧刘焉。”[4](114)因五斗米道继承袭了“鬼教”的内涵,当时人称之为“鬼道”。直到隋唐时,居于巫巴山地的巴族仍然对“鬼道”笃信不疑,《蛮书》引《夔城图经》曰:“夷事道,蛮事鬼,初丧,鼙鼓以为道哀,其歌必号,其众必跳,此乃槃瓠白虎之勇也。”又“白虎事道,蛮与巴人事鬼。”[5](卷十)巫教之二——“娘娘教”(也称“美女教”),在沅、湘之间流存。旧时,在湘鄂黔桂边界民间,人们信奉女娲神、花婆女神、萨神(或称“萨嫲”)、嫲神婆、春巴嫲妈,并视之为始祖,由此可见该教具有母权制社会的原始宗教特征。“娘娘教”的巫师立坛,称为“震古雷坛”。这表明该教在远古可能是以自然神为崇拜对象的。巫教之三——“苗教”,系湘西苗族地区本民族的原始宗教。其巫师称“苗老师”,举行重大祀典时需要戴冠穿袍,巫师所用法器为黄蜡碗、铃铛、筒、短剑等;而在其做小法事时,则身着便衣。“苗教”中地位显赫之神是“向汉向娘”(祖先)和“大索大戎”(雷公与龙)。苗家谚语中有:“天上雷公(大索)最大,人间舅公最大”,“雷管苗,官管汉”之说。湘西苗乡素有“三十六堂神,七十二堂鬼”之说,故苗俗自古便“淫祀”颇多,且其表象直到上世纪仍然保存较好。在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苗教》(民族出版社,2003年)中列举了“祭祖”、“吃猪”(椎猪)、“打家先”等16堂祭祀;石启贵《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宗教信仰》则介绍了“椎牛”、“接龙”、“祭雷神”等26种祀典。“苗教”祭典的目的大都在于避祸求福、清泰平安。
巫术“是史前人类或巫师一种信仰和行为的总和,是一种信仰的技术和方法。是施巫者认为凭自己的力量,利用直接的或间接的方式和方法,可影响、控制客观事物和其他人行为的巫教形式”[1](214-215)。巫术源于原始社会,是巫师控制客观事物和其他人行为的方法,巫术是巫教的表现形式。巫巴山地自古就有崇尚巫术和占卜的传统,其表象在闭塞地区甚至延续至今:例如在巫溪,民间巫术从远古流传至今的就有跳端公、告阴状、化九龙水、请七仙姑、请桌子神等多种形式。而“赶白虎”则是湘北土家族的巫术,当地人认为“坐堂白虎”是家神,“过堂白虎”是野神。如果有“过堂白虎”进门,就会死小孩,民谚称“白虎当堂过,无灾必有祸”。于是就得请巫师赶白虎,钉白虎。楚国曾经流行招魂的巫术,“魂兮归来,入修门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秦篝齐缕,郑绵络些,招具该备,永啸呼些。魂兮归来,反故居些。天地四方,多贼奸些。像设君室,静閒安些。”(屈原《招魂》)已被放逐的屈原,在闻楚怀王客死于秦,还专门写《大招》一文,以招其魂。在后世民间,招魂术仍长久保留,用旌幡,也用呼号。招魂并不局限于死者,如活人生病或受惊,也被归咎为魂不守舍、四处游荡,于是也需为其招魂。渝、鄂、湘、黔四省市交界处是古代巴族的直系后裔——土家族聚居之地,他们承继了古代巴人崇鬼、尚巫的传统,巫术活动盛行,主持巫术活动的巫师在土家族各地称谓不同,有“梯玛”、“土老师”、“端公”、“老司子”等。“在土家人中,梯玛通神灵,精巫术,会作古唱经,神通广大,有求则应,其权威远胜于当地的封建官员。”[6](434)在举行法事活动时,梯玛身着法衣,手持法器,其法事活动主要有“服司妥”(还愿)、“杰洛番案”(解邪——赶鬼驱邪)、占卜(预测吉凶祸福)等。
祭祀、避邪与崇拜。首先,巫教在巫巴山地体现为种类繁多的祭祀,如远古巴人的“人祀血祭”和“彼崖獭祭”、楚人的祭川与祀神。近代土家族还保留了远古的祭祀传统,“每岁孟夏,或设坛玉皇阁斋醒数日,文武官亦诣坛上香,为民祈福”;“同俗信事鬼神,乡里有争角,辄凭神以输服,有疾病则酬神愿,大击钲鼓,请巫神以咒舞……”[7](卷十九)类似记载,散见于各县地方志。在《川东南少数民族史料辑》(四川黔江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一书中,多有汇辑。其次,趋利避害是人类的共同特点,因此以某种方法避邪也是巫巴山地土著的常用手段。白虎巴人以白虎为图腾,在其剑、戈等兵器上大量铸以虎纹,其目的是用图腾符号保护自己,克敌制胜;龙蛇巴人的兵器上常见的所谓“手心纹”,其实是“蛇头”,它同样也是避邪求胜的图腾。在巫巴山地民居的门楣上方,常常挂有用桃木制作的“吞口”,该“神兽”的特点是巨鼻、大眼、大嘴、多毛等,其作用是防止毒蛇猛兽的入侵。再次,祈求自然神灵与祖先保护的愿望,则促成了民间崇拜的产生,在巫巴山地,古代巴人有白虎崇拜,楚人则有尊凤与太阳、火的崇拜。后世的土家后裔不但继承了巴人的白虎信仰,还流行对舍巴神(带领人民拓荒的祖先)、谷神(五谷娘娘)等的崇拜。
巫教是原始人类万物有灵观念的最早宗教表现,它虽然仅有粗糙的内核和简单的表象,但却形成了后世宗教最重要的基因。巫巴山地的巫教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发展变化,有的上升成了高级宗教;有的仍然保持着较为原始的状态。
二、巫俗的表象及传承
俗,“習也”。“習者,數飛也。引伸之凡相效謂之習。……大司徒以俗敎安。注。俗謂土地所生習也。曲禮。入國而問俗。注。俗謂常所行與所惡也。漢地理志曰。凡民函五常之性。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謂之俗。”[8](卷八,人部)由此可见,“俗”的含义一是学习——效仿,即习俗;二是特定地方所生的民间风气。巫风浓厚便是巫巴山地特有的风俗,这里山高、林密、涧深、流急、气候多变,猛兽出没,神秘莫测的自然环境给原始居民造成强大的心理压力和期待,久而久之便积而成俗。于是史书就有了“楚信巫鬼,重淫祀”(《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之后又因其地理闭塞,经济文化发展相对滞后,直到近代巫风、巫俗依旧残存。例如其信巫的民俗,独具特色的葬俗、禁忌和巫医等。
民间的巫俗体现于日常生活之中,梁代的宗懔对此不乏记载。在楚地:“正月一日……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避山臊恶鬼。”“正月十五日,作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祠门户。其夕,迎紫姑(神名),以卜将来蚕桑,并占众事。”“五月五日,谓之浴兰节(即端午),四民并蹋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以菖蒲或镂或屑以泛河。是日竟渡,采杂药。”“十二月八日为腊日……其日并以豚酒祭灶神岁暮,家家具肴核,诣宿岁之位,以迎新年,相聚酣饮,留宿岁饭。”(宗懔《荆楚岁时记》)而到唐代,这里巫风仍然盛行,人们不但祭本土本川之神,例如江南之水域“祭水神”,瑶族“祭盘瓠”,湘鄂“祭巫山女神”、“二妃”,甚至连一些名人也被位列仙班,诚如刘禹锡《自江陵沿海流道中》一诗所言,“行到南朝征战地,古来名将尽为神”。时至今日,我们仍能取到巫风深入民俗的例证,在三峡,土家人建房被称为“立百代基业,安千载龙阁”。除了动土、伐木、奠基均要择“吉日”外,上梁前还要进行名为“退煞”的巫术仪式。其中,选择栋梁之材尤其讲究:一是树木的倒向要朝着山巅,意即步步高升;二是选材以椿树或梓木为佳,寓意“春常在,子孙旺”;三是要选树蔸发有小树、枝上有鸟鹊搭窝的,意子孙发达。动斧之前要在树蔸处点三柱香,烧三堆冥纸,以祀树神;梁木运回后还要贴上红彩,小心照看,不能让人跨过,踩着。
葬俗历来被巫巴山地的人们所看重,当地俗语中便有“在生一栋屋,死后一副木”之谓。三峡地区巴人的远古丧俗多采用悬棺葬,在长江三峡内有不少悬棺高高地架在悬崖峭壁上,至今在大宁河上游巫溪县还有保存数量较多、质量较好的悬棺。学界认为悬棺葬主要是巴人所为,因为除发现棺里的巴人随葬品外,这些悬棺的制作多采用船的状貌或直接使用旧船葬人,而主要以鱼盐为生的巴人本就是水上民族,其以船为棺的方式显然是具有巫术意义的。[9]后世生活在巫巴山地的居民,其葬俗依旧保留着浓浓的巫风:①老人在世时他们要请巫师为之“看风水”精心选择墓地;②当家里有人去世时,要履行一整套丧葬仪式,包括为死者招魂,敲“断气锣”,烧“断气钱”,放“饭唅”;③家人举孝,身着孝衣,头扎孝帕,以麻系腰,持哭丧棒为之招灵;④设灵堂,置灵桌,放灵牌,插香烛点油灯;⑤作道场,请巫师念经,敲锣打鼓,摇旗呐喊求神保佑死者;⑥唱“丧鼓歌”,入夜时丧鼓班子还要“闹夜”,亲朋好友要来“赶丧”,巴、楚丧鼓有坐丧(坐着唱)、跳丧(边唱边跳)、转丧(围着灵柩转圈)之分;⑦出丧,于拂晓前念祭文,孝子告别,移灵于屋外,出丧后丧家用扫帚在停灵处使劲往门外扫,称“克鬼”,促亡灵远处投胎,不要骚扰生者。以上丧事程序,折射了生者对于逝者几乎所有的巫术心理活动。
禁忌也是一种巫俗。当人们对各种神灵的信仰渗透到其生产与生活中时,便形成了诸多的禁忌。早在楚国的占卜习俗中人们就已经注重时忌,“月忌”即每月禁忌,是避免与十二天神、十二时辰、十二月宿对应的五行、四时、四方相冲犯的种种忌讳;荀子曰:“式上十二神,登明、从魁之辈,工伎家谓之皆天神也,常立子丑之位,俱有冲抵之气,神虽不若太岁,宜有微败,移徙者虽避太岁之凶,犹触十二神之害。”(《论衡·难岁篇》)“日忌”即日禁,是以十干或十二支记日,或十干、十二支相配记日(甲子记日),然后根据每日的干、支名与太岁、岁星所处辰位、方位和日所行黄道、月舍、五行、四时等因素相配的占测吉凶,规定相应的日禁。确定某日宜做什么事、不宜做什么事。在后世巫巴山地人们生活中,各种禁忌可谓俯拾皆是:以土家族为例,清明、立夏日及农历四月八不能用耕牛,否则牛会生病;正月初一至十五大人小孩不能剃头,以免秧苗长成癞子头;吃年饭不能泡汤,否则来年涨水会冲垮田坎;正月初一不准扫地,以免将财气扫出去;正月祖坟前不准动土,否则会挖断祖宗灵气;对灶神要恭敬,不准脚踏灶和火坑中的三角架,不得将衣裤鞋袜等脏物放在灶上,不准在灶上煮狗肉;忌门前栽桑,屋后栽柳,因为“桑”谐音“丧”,“柳”谐音“扭”。人们甚至真诚地相信犯忌者会家运不顺。
在战国以前,巫和医是不分的,仅从“医”的繁体字“毉”便可以看出。同时,古书《山海经》在提到巫师时,也总是将其与药并论,如《大荒西经》中的“百药爰在”,《海内西经》中的“操不死之药”;而群巫之首巫彭在《吕氏春秋·勿躬》、《世本》等书中皆被尊为“初作医”者,这些至少表明巫巴山地是巫医最早出现的地方之一。于是郭璞在提到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六巫时,注曰:“皆神医也。”(《山海经·海内西经》)远古巫、医相通的现象,从客观上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自然与自我关系认识的模糊,同时从这些材料上亦可看出中国上古医药经验的积累,明显得益于巫师驱邪治鬼的活动。例如,古代巫医使用之药主要是丹砂,“丹砂味甘微寒。主身体五臓百病,益精神,安魂魄,益气明目。杀精魅邪恶鬼。久服通神明不老。”([清]孙星衍《神农本草经》)到战国时期,巫和医开始分离,《史记·扁鹊列传》有了“信巫不信医,不治”的记载。尽管分道扬镳,但在医生治病和巫师驱邪时,仍常常用到类似的药。除丹砂之外,《楚辞》中提到的如白芷、桂枝、瑶华等也是巫医们常用的药物。即使汉晋以后,楚地民间患病仍多请巫师。在如今的“湘北有一类与医疗有关的巫术,它表现在用符咒、法水治病,可称为灵符巫术或‘符水巫术’。”其所治之病有:“化九龙水”(以符水化掉误食的石头、鱼刺、鸡骨)、“治恶犬、狗咬伤”、“摘翳子”(摘除白内障)、“杀羊子”(使肿大的腹股沟淋巴结消炎)等。[10](65-66)巫医的代代相袭,使巫术疗法至今在巫巴山地尚存,探究巫医疗效尚存的原因,与其采取用药和心理暗示(驱邪)双管齐下的方法不无关系。
正是由于巫巴山地长时期巫风盛行,出于对平安吉祥的追求,人们想尽了种种办法、采取了许多手段,以求沟通天地、鬼神、阴阳,这些在如今被称为巫术的活动,却因为长期使用而约定成俗,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三、巫艺的表象及传承
崇拜图腾是覆盖全人类的精神活动,伴随其产生的原始艺术出现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宗教的信仰往往需要非理性的激情,而艺术正是激情的摇篮,于是巫艺便应运而生。从远古以至今日,图腾艺术的直接衍化不仅仅只是“避邪民俗艺术”[11](182-191),还应包括祈福。这里讨论的所谓巫艺,主要包括巫歌、巫舞、巫戏、巫画以及神话传说等等与巫文化相关的艺术种类,它们在巫巴山地的过去和今天都有十分突出的表现。
巫歌亦即涉巫的诗歌,曾盛行于三峡地区,尤以楚地巫歌为代表,它在相当程度上催发了楚辞的产生,并影响了其特征。楚辞就是楚人全面融汇南北诗歌艺术陶冶而成的伟大创造,其中就有不少涉巫的诗歌。如《九歌》,其名源自夏代,其内容为写巫者、记巫事,它是屈原为了祭神的需要而有意的改作;又如《离骚》,屈原借其超越现实世界,将自己想象成神巫,可以驾龙、御凤。相类似的还有《九章》、《招魂》和《大招》,其内容包括宗族祭祀、悼念仪式、巫觋作法等等。蔡靖泉先生认为:“楚辞在语言形式上的鲜明特征,就是以‘三二’节奏的五字句和‘三三’节奏的六字名为主要句式,并且在句中或句尾灵活运用语助词‘兮’字。楚民歌和楚巫歌都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这一特征,而楚辞则更直接地脱胎于巫歌,并在巫歌的基础上将这一特征突出和强化了。”[12](64-65)《梯玛歌》是巫师(梯玛)作法时唱的土家语巫歌,土家族语言无文字,其本民族文化只能靠口头传承,而梯玛便是世袭的传承者,随着与汉族的交往增多,汉字版的《梯玛歌》才得以产生。《梯玛歌》长达50章148节。在其第六章《开天辟地》中叙述其民族由来:“啊!人没有啊,不见烟升,只有姊弟俩啊,世上只有两个人。/那里,我们两人坐,二人来成亲,世上才发人,才有炊烟腾。/喜鹊开口劝,二人莫离分。燕子开口说,一团要箍紧啊。松鼠也来劝,这样事才成啊。黄鲤鱼旁边笑盈盈,团鱼团团说娶亲啊。”[13]在弄不清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弄不清人类自身来源的古代,巫师的解释是睿智的。尽管这样的解释没有科学依据,但却给了大家一个必要的说法,而该说法对于匡定古人的心、确立其精神支柱以从容应对强大的自然压力十分必要。
巫舞是古老的祭祀性舞蹈,它以舞的方式实施巫术,在巫巴山地自古便有巫舞的记载。古时巴族勇武善战,常在战阵前着戎装、舞干戚。史载:“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5](21)巴人的战阵舞实际上就是一种巫舞,其目的是借助神力战胜敌人,特有的化妆、诡异的舞姿、錞于与呐喊声以及兵器上的虎图腾,赋予了巴族战士强大的精神力量,从气势上打垮了敌人。该战舞的余威在巴人后裔土家族的“大摆手”舞中至今尚存。而“明发跃歌”、“男女相携,蹁跃进退”的巴人生产舞蹈,则演化成了土家的“小摆手”舞,其主要目的仍不外感谢神灵的护佑、祈求来年好收成。在过去,“土家各寨有摆手堂,每岁正月初三至十七日,夜间鸣锣击鼓,男女聚集,跳舞长歌,曰‘摆手’”;([清]《永顺府志》)到如今,“‘大摆手’三年举行一次,‘小摆手’每年都举行。”[14](178)在巫巴山地的民间巫舞中,流传比较广泛的还有男巫的“端公舞”和女巫的“仙娘”、“马脚”、“七姊妹”舞。端公是民间的巫师,粗通文墨,会施“法术”,因其能沟通人、神间的意念,被当成神的公差,故称为“端公”。跳端公又叫跳神,其目的是驱赶鬼邪、消灾除病、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仙娘”、“马脚”、“七姊妹”的舞者为女巫,其内容与“端公舞”类似。“长期以来,《端公》、《仙娘》、《马脚》、《七姊妹》等巫舞活动,都依附着民间传说和民俗活动而广泛传播和不断发展。”[15](343)三峡地区土家族人至今还流传的“打绕棺”舞,是一种击打乐器并围绕棺材跳丧的祭祀歌舞,一般于丧事中、殡葬前表演,“舞时除有土老师带领、民间艺人参加外,死者亲友亦可参加,人数不限,但必须为男性、双数。”[16](769)
巫戏是一种以戏曲形式表演的巫术活动,巫巴山地的巫戏主要有三种,它们是还傩愿、还坛神和茅古斯。“还傩愿”源于一种消灾仪式,古时先民凡遇灾难,便认为是鬼神作祟,于是向傩愿菩萨乞求庇佑,并许诺逢凶化吉后还愿感恩,即“还傩愿”。史料载:“方相氏(周代官名),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率百隶而难(傩),以索室驱疫。”(《周礼·夏官·方相氏》)后来,从该仪式衍生出傩舞、傩戏,并由原始宗教形式向世俗娱乐形式转化,终成为一种戏曲式的巫术活动。如今,傩戏在巫巴山地依旧残存,其特点一是演员均戴面具出场,二是表演程序复杂,前后共演八出法事(称“傩八朝”):发功曹、请神、安位、出土地、点雄发猖、姜女团圆、钩愿、送神等。表演者的面具被认为具有巫术功能,戴上不同的面具就意味着不同的神灵附体,其便拥有了该神的本领。表演时班主要登上高台,祷告上苍地府,求傩神、天神赦罪免灾,领取傩愿。[17](48-52)“还坛神”流行于鄂西土家族地区,“坛神”是指在阴间受封的家族祖先。倘若某家人旺岁丰,无病无灾,便被认为是自己家“坛神”保佑的结果,于是家人就会在秋后请巫师设坛以酬奠这位先祖,其间敲锣打鼓、献祭品十分热闹。还坛神与唱傩戏,目的各不相同,前者为驱鬼逐疫,后者是祈祷福佑。“‘茅古斯’具有戏剧舞蹈双重性质,是一种原始的戏剧舞蹈。”[18](624)它堪称巫戏的活化石,于舍巴日(摆手)祭祀中演出,目的是祈年求育。原始社会人类生产的两个最重要的方面——物质生产与自身繁衍——均在茅古斯表演中得到充分体现:茅古斯演员称“毛人”,他们身披稻草、头系五根草辫,其中一个年纪大的叫“papuka”,即老公公之意,他是茅古斯的主角。在漫长的传承期中,茅古斯融进了不同时代的内容,其中如《过年》、《做阳春》等突出了祈求丰收的主题,而《接新娘》和《舞神棒》等则表现了百姓对人丁兴旺的期盼。在《舞神棒》中,茅古斯扮演者将一裹有茅草的木棒夹在胯下进行表演,在表演过程中,甚至有不孕妇女用手去摸那根“生殖棒”,她们似乎真的相信可因此而怀孕。
巫画是具有宗教目的的绘画。出于对强大自然力的崇拜与讨好,巫巴山地的土著持有“事鬼敬神而近之”的人生观,他们在其绘画中,形象而生动地表现了包括禽鸟、动植物、人神,以及想象中的异类等各种事物。出于巫术目的,他们致力于营造意境诡谲、色彩斑斓的画面,这在楚地漆画和帛画中表现尤为突出,无论是擂鼓墩大墓的漆棺画,还是《人物龙凤》、《人物御龙》和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帛画,均在具象地展现其震撼人心的形式美魅力之时,强烈地向我们倾述了它们的巫术目的。《人物龙凤》与《人物御龙》图均为战国时期作品,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帛画则绘于西汉,它们均为表现墓主人死后升天的题材,其内容或祈龙凤引导、或驾龙舟入海、或附龙体升天,给我们还原了当时人对生命彼岸的认识。[19](49-50,73)重庆梁平年画的巫画性质也是十分显著的,无论是门神、灶神亦或五子登科、招财进宝的题材,都充满了当地人避邪求福的美好愿望,人物脸上那两块充满喜庆的桃红色便是其独一无二的标志。
对神话的巫术性质,马克思认为:“古代各族是在幻想中、神话中经历了自己的史前时期。……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20](113)在这里,马克思充分肯定了神话的进步意义——是初民认识和征服自然力的重要手段。巫巴山地是中国神话的源泉之一,《山海经》中的《海经》就叙录了这里丰富的远古神话;屈原的楚辞大多是集录神话以筑其基、熔铸神话以成其文的;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以其讲述巫山神女令人神魂颠倒的故事而流传古今;刘安曾在楚国故地组织门下宾客编撰了保存有大量上古神话的巨著《淮南子》……如今,流传在巫巴山地的不但有大禹治水、巫山神女、开天辟地、女娲补天以及烛龙等著名神话,而这里许多民间传说所讲述的则是人的传奇,例如巫山诸巫的传说、廪君化白虎、盐水女神、呼归石的传说等等。在这些神话与传说中,神与自然、人与神、人与自然以巫术为纽带交织在一起,和谐相处,结出了精彩纷呈、美仑美奂的文学奇葩。
综上所述,巫巴山地巫文化在其从远古到今天的传承过程中,拥有着相似的内涵和表象。一方面,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展与人们认识的不断提高,冲淡了该文化的古老积淀;另一方面,巫文化的内涵和表象又因为这里相对蔽塞的自然环境,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顽强地传存着,这就在相当程度上为我们动态地考察巫巴山地的远古巫文化提供了活的范本。
[1]宋兆麟.巫与巫术[M].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
[2]张之恒.重庆地区史前文化之特征[A].重庆2001年三峡文物保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科学出版社,2003.
[3]邹厚曦,袁东山.重庆峡江地区的新石器文化[A].重庆2001年三峡文物保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科学出版社,2003.
[4][晋]常璩撰,刘琳注.华阳国志校注(汉中志)[M].巴蜀书社,1984.
[5]向达.蛮书校注[M].中华书局,1962.
[6]重庆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编.重庆宗教[Z].重庆出版社,2000.
[7][清]王鳞飞等.酉阳直隶州总志·风俗志[Z].同治三年(1864)刻本。
[8][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Z].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9]邓晓.论巴人与土船[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6.(5).
[10]唐明哲.楚湘巫术类说[A].楚俗研究(第三集)[C].湖北美术出版社,1999.
[11]雷乐中.巴人避邪民俗文化寻绎[A].三峡文化研究[C].重庆大学出版社,1997.
[12]蔡靖泉.荆楚巫风与楚辞文[A].楚俗研究(第一集)[C].湖北美术出版社,1993.
[13]湖南少数民族古籍办公室主编.梯玛歌[Z].岳麓书社,1989.
[14]恩施州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编.恩施州土家族苗族资自治州民族志[Z].民族出版社,2003.
[15]三峡地区巫舞浅析[A].三峡文化研究(二)[C].重庆大学出版社,1999.
[16]重庆市文化局编.重庆民间舞蹈集成[C].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17]唐明哲.还傩愿与楚巫学撷谈[A].楚俗研究(二)[C].湖北美术出版社,1995.
[18]宜昌市文化局,三峡大学三峡文化研究中心.三峡民间艺术集粹[Z].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
[19]张光福编著.中国美术史[M].知识出版社,1982.
[20]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2)[Z].人民出版社,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