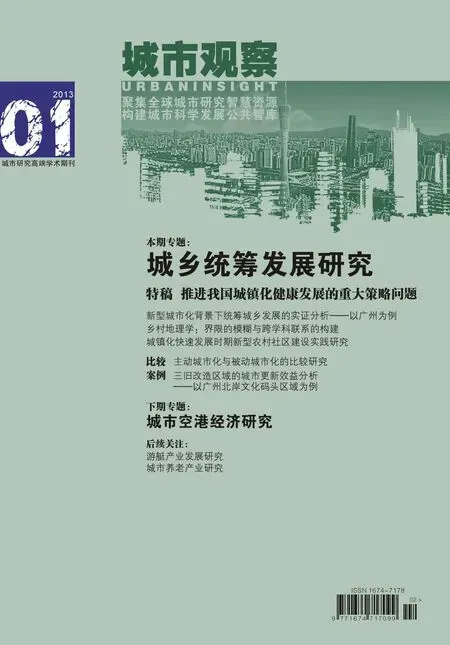旧村城市化改造中的社区转型与再造研究述评
◎ 温 莉 姚苑平
在我国城乡二元体制和快速城市化语境下,旧村城市化改造是城市发展的热点。本文所指的旧村,特指与城市关系密切的村落,主要包括城中村和城郊村。
旧村城市化改造,必然经历乡村地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该过程包括了原有社区关系的瓦解和新社区关系的建立。较之物质空间的城市化,社区城市化较为缓慢,需协调多方的复杂关系,需居民的共同参与,对旧村城市化质量更具影响。
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社区是以一定地理区域为基础的社会群体。社区理论研究发端于西方,1887年德国学者滕尼斯在其发表的《社区与社会》中首提社区概念。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吴文藻等社会学先驱将概念引入国内,随后社区理论在我国扎根发展[1]132、133。
一、社区转型研究综述
旧村城市化改造的社区转型研究,核心议题包括经济、社会、管理及人的城市化转变。
(一)经济转型
旧村城市化改造带来全面的产权、生产关系变更,直接冲击原有的经济系统。
首先是集体经济的转型。原先 “生产大队——生产队”的经济组织体系转变为“经济联社——经济社”或“股份公司——股份分公司”体系,以控制和管理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原村领导直接转为适应市场机制的“职业经理人”。由于改造前后管理层往往没有根本性变动,仍有浓重的乡村社会色彩,难以适应瞬息万变、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在经历投资失误后,往往又将集体经济的业务收缩为原来的物业出租[2]85。
其次是家庭经济的转型。经城市化改造后,居民已彻底丧失农业生产的条件,或主动或被动地进入非农行业。但受自身文化程度、工作经验及职业素养限制,他们多难以完全适应城市环境下的职业要求。由于改造之后居民往往掌握着一定数量的私宅可供出租,因此“包租公”、“包租婆”便成为许多居民的职业。过度依赖私宅出租和自身职业能力不高形成相互强化的循环,造成旧村城市化改造后普遍出现就业问题。
从本质上看,转型后的经济系统具有明显的食利性质,即集体经济与家庭经济主动承载周边地区城市化所溢出的红利,发展租赁经济[2]85。集体经济管理者和居民成为依赖集体分红和宅屋出租坐享其成的“食利阶层”[3]23。
这种食利经济并非毫无后顾之忧。尤其是依赖集体物业出租的集体经济,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提升,以及外来低端产业转移的日益萎缩,本地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更希望能够购地建厂,这种趋势必压缩物业租赁的空间[4],降低集体物业的议价能力。与此同时,城市化改造后,社区仍是较为独立的行政单元,不能充分获得上级财政转移支付,诸如环卫、安保、养老、医疗、市政基础设施等集体性支出均由集体负担,无形中增加集体经济压力,使不少村集体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
(二)社会转型
社会关系上,旧村城市化改造从根本上改变了社区的交往方式和人员构成,使原来的熟人社会向业缘社会转变。但是,对于社区居民而言,生活方式并未根本改变,思想上还比较守旧,重视情感生活,家族、宗族、乡里乡亲等传统关系还在起着主导作用,对于集体的认同感大大高于城市居民,其价值取向的集体性也颇为浓重。因此,社区事实上属于“半熟人社会”[5]628,或者“半业缘社会”。
社会保障上,在改造前后,土地都是经济的基础,仍扮演着社会保障的功能。集体经济管理者和个人只是由原来的“种田”变成“种房子”。但是城市化改造大幅削减村集体依赖物业用地扩张提高集体经济规模的可能性,从根本上降低土地对社区的社会保障能力。因此,政府在制订旧村城市化改造政策时,往往都会要求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例如,要求给全体居民购买社会养老保险、实行合作医疗等[6]。本质上,这些举措是对“失地”的一种补偿。
人口构成上,出租经济的发达吸纳了大量外来人口,形成社区的人口倒挂,原来均质、本地化的社区转变为候鸟式人群和本地化人群相混杂的社区,成为农村型社区与城市型社区的过渡体。加之低租金多吸纳了低收入阶层,进一步强化社区低素质的人口特征,出租屋管理不力、制度不健全,容易滋生黄、赌、毒问题,易成为社区社会治安的隐患[3]13。
(三)管理转型
管理架构转型。转型社区普遍实行“议行分设”,强调将经济管理和行政管理完全分开,实施“政企分开”[2]86。行政职能强调以公平公正优化公共物品的供给,经济职能强调以市场逐利行为促进集体财富的积累。
管理模式的转型。集体经济通过股份化改造和委任职业经理人提升效率。社区管理则通过引入物业公司实施公共设施统一管理[7]。村委员会向居民委员会转变,既继承了传统村委会的自治精神,又以城市社区为模板,实行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加大社区居委会职能[8]。
管理任务转型。转型社区既要管理本地居民,又要管理大量的外来人口;既要承担原有的集体经济发展、计划生育、社会治安、民政优抚任务,又要管理改造后出现的城管创建、环境优化、就业与社会保障功能[3]15。
(四)人的转型
不少旧村城市化改造后,人的身份由农民向居民转变,进入城市居民管理的序列。尽管他们难以在短期内拥有城市居民的等质待遇,甚至被认为是“住在楼上的农民”、“竖起来的村庄”[2]86,但是制度性的身份已经确立,由村民向居民转变的步伐已经迈开。
在都市文化渗透下,居民逐渐转变自身的传统观念。对于乡村文化而言,都市文化属于强势文化,在两者的碰撞、冲突和融合中具有文化优势,因此不断的渗入居民的思想意识之中。尤其是失地居民迫于城市生态压力,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强自身的市场意识、法制观念、时间观念、商业逐利观念和效率观念,以适应城市生活对人的要求[3]15。
事实上,旧村的空间改造已经从根本上奠定了城市型人际关系的特征。因为空间改造提高了人口密度,缩短了居民身体距离,但又扩大了彼此的社会距离。因为高密度会增强人们彼此之间的厌烦心理,促使人们丧失对他人“较有人情味的方面”[1]133。
人的转型本质上就是人的市民化,即由最初的村民、到改造初期的居民,再到最后的市民转变。它是城市化过程最核心也是难以一蹴而就的方面,它需要城市环境的长期熏陶,需要城市生活实践的长期培养。客观而言,人的市民化难有捷径可走。因此,在改造初期容易出现与环境格格不入的行为,例如利用社区车库开店甚至居住,直接往楼下倾倒垃圾等。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特有,新加坡早期推行组屋计划时,就经常出现新搬入组屋的居民在家中圈养禽畜的现象。
二、社区再造研究综述
管理学的再造理论认为,再造是组织的彻底变革,需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组织业已形成的基本信念。奥斯本、盖布勒等学者将再造理论应用于公共管理研究,提出政府再造命题,提高行政绩效,带来公共管理的革命[9],为社区再造(Community Reengineering)提供了诸多启示。
总体而言,社区再造是一项综合工程,是一个社会政治结构和社会化生活的建构过程,其作用不仅是物质性的,更是社会性。它需要从社区形象、社区成员、社区流程及社区制度等方进行总体营造[10]21,其关键在于社区共同信仰及价值观的重新建立[11]4。因此,社区再造不是对原有社区建设的全盘否定,而是以新的视角审视社区建设的地位、价值和方法,重点在社区的恢复、重建乃至再生。
社区再造是以社区的时空信息为基本尺度,从根本上重新塑造社区形象、培植社区意识、改造社区组织流程、提高社区绩效、促进社区和谐发展的变革过程。在这个舞台中,受政府利益和创新制度安排所获得的利益机会的诱导,居民为响应获利机会自愿缔结为社区团体,通过就社区环境、社区规划、社区史开发、社区NGO发展、社区活动等社区营造议题进行讨论,制定具有社区特色的发展计划,汇聚社区共识。就策略而言,社区再造主要包括长期经营与短期应变。长期经营主要重视社区居民的成长与学习,例如社区读书会、成长营、教育培训、环境认养等;而短期应变则是为应对社区出现的急迫性公共议题,通过“社区工作坊”在短时间内形成社区共识与行动计划。[10]18
旧村空间改造的合理与否,对社区再造的优劣具有直接影响。如郑州某城中村改造后,有80%的居民认为社区缺少促进邻里感情的场所,50%的社区居民认为由于城市社区生活空间的分隔性造成邻里关系趋于陌生[5]628。
从利益追求的角度来看,空间作为一种有限资源,必然受政府、市场和社区各方的争夺。占有一定地域空间,对个人而言意味着生计,对开发商而言更是一种资本。从权力关系的角度来看,社会各主体对空间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执行力越强意味着对空间的占有也就越充分[12]。这种博弈关系在当前的旧村改造中表现十分突出,如果某旧村由开发商投资开发,在规划设计阶段,开发商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选择好地段、好用地作为融资地块。无形中为今后再造和谐社区埋下隐患。
三、研究评论
(一)社区转型研究多,社区再造研究少
目前已开展的研究工作,涉及旧村改造中的社区转型和社区再造两大议题。但是,社区转型的研究明显多于社区再造的研究。究其原因,主要是社区转型具有显性的外在特征,易于观察或感受;社区再造属于隐性的内在过程,需要实践经验的累积,对社区发育程度不高、民间力量不足、自治意识不强的当前社会而言,议题的讨论难度较大,探讨和总结的空间有限。
(二)社区转型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完善
社区转型研究全面涉及经济、社会、管理和人的转型,较好地总结了转型的主要特征。但受我国转型阶段的影响,改造后的社区事实上仍具有明显过渡社区的特点,在表面转型之下,社会规则、经济结构、管理机制、社会关系、人文习俗等均仍有较大延续性,造成不完全的城市化、不完全的产权界定、不完全的市民化。因此社区转型研究的对象多是“半转型”状态的社区,它只是转变过程的中间体,而非转型的结果。它所总结的理论模式随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将有较大的完善空间。另外,研究缺乏对转型内在运作机制的研究,缺乏对整个动力系统的分析,多停留在现象的陈述上,缺乏深入的理性分析,并未充分揭示转型各要素的内在联系。例如,经济、社会、管理与人的转型对于社区转型的贡献权重及其主次关系;四者的相互促进关系等。
(三)社区再造的价值目标基本确立,但实施手段有待明确
研究已明确社区再造就是要建设适应新发展环境的社会关系,形成认同社区价值、汇集社区共识、联系紧密有机的社会群体。但是,适合中国国情的社区再造手段研究不足。虽然部分研究提出通过发展社区NGO、社区规划、制订社区共同行动计划来凝聚社区关系,但是这些提法多借鉴自西方行政体制下的社区建设手段,它与当前我国地方自治性不足、大政府小社会、自上而下管治、居民参与热情不高的适应性还有待检验,相应的成功案例还有待发掘。
(四)空间对社区转型和再造影响的研究不足
目前少量的研究文献涉及空间设计对于社区再造影响的研究,提出生硬地套用城市空间设计手法无助于社区的再造,要在空间规划中维护原来的交往环境和邻里关系[13],要重建原有的仪式空间[11]4,但是这些研究多只从改造前和改造当下的视点来讨论空间改造对社区再造的影响,缺少更长远视野的价值观、方法论的探讨。
(五)社区建设价值意义的探讨缺失
直观上看,旧村城市化改造就是要创造美好的城市生活环境。但是旧村城市化改造后社区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按目前普遍的改造方式,旧村改造往往创造的是一个个有围墙、安保的隔离社区(Gated Community),较之原先的开放空间,城市区域事实上更加破碎化[14]。这种改造的价值是否会大打折扣?
原来以宗祠为核心的社区仪式空间到底该不该传承,原来的邻里空间与关系到底要不要保留?再造的社区最终是要融入城市,还是在城市中再塑异样的孤岛?新加坡为打破种族隔阂采取的打散重组式安置,对我们是否有借鉴意义?凡此种种的价值问题都有待深入讨论。
四、未来研究展望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深化,城市增长边界将继续扩张,旧村城市化改造的问题将长期存在,社区转型和再造的理论研究价值依然存在。综观已有研究文献,结合未来社会进步节奏,本议题未来的研究方向将主要集中在:
①社区转型的价值方向。转型到底要再造一个什么样的社区。
②社区再造的策略手段。如何减少社区转型阻障,加快良好社区的形成。
③空间规划对社区建设的促进作用。如何通过合理的空间设计,促进社区新关系的再生。
[1]赵定东,杨政.社区理论的研究理路与“中国局限”[J].江海学刊,2010(2):132-136.
[2]李志刚,于涛方,魏立华,张敏.快速城市化下“转型社区”的社区转型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07(5):84-90.
[3]鄢琰.农村拆迁整体安置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型研究[D].苏州大学,2009.
[4]钟再勤,毛冬宝.城市化转制转地后社区集体经济的转型发展[J].特区实践与理论,2007(3):63-66.
[5]朱晓娟.中部地区城市化进程中“转型社区”实证研究——以郑州市燕庄社区为例[J].河南科学,2011(5):626-630.
[6]姚一民,谈锦钊.广州“城中村”转型和社区发展调研[J].规划师,2004(5):8-12.
[7]朱一中,隆少秋,臧俊梅.广州增城市农村社区转型问题研究[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43-47.
[8]林新伟.农村城市化进程中转型社区建设和治理研究[D].苏州大学,2007.
[9]David Osborne, Peter Plastrik.Banishing Bureaucracy: The Five Strategies for Reinventing Government[M].NewYork:PenguinGroup,1997.
[10]谈志林,张黎黎.我国台湾地区社改运动与内地社区再造的制度分析[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02):16-24.
[11]林志森,张玉坤.基于社区再造的仪式空间研究[J].建筑学报,2011(2):1-4.
[12]陈伟东,舒晓虎.社区空间再造:政府、市场、社会的三维推力——以武汉市J社区和D社区的空间再造过程为分析对象[J].江汉论坛,2010(10):130-134.
[13]宇啸.在村落向城市社区的转型中再造邻里空间——以马坊新城起步区规划设计理念为例[J].北京规划建设,2008(04):122-124.
[14]何艳玲,汪广龙,高红红.从破碎城市到重整城市:隔离社区、社会分化与城市治理转型[J].公共行政评论,2011(1):46-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