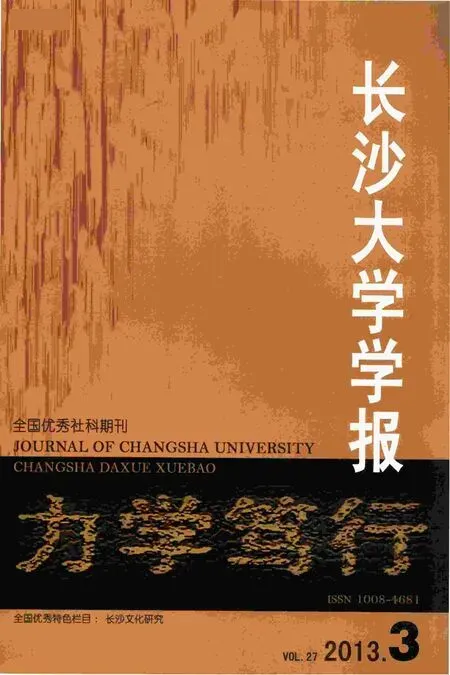从言到意的反讽
——论新历史小说的反讽
邵 艺
(青岛广播电视大学文法系,山东青岛266012)
反讽在西方文论中,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它经历了“苏格拉底式的反讽”、“哲学反讽”、“新批评派的反讽”等阶段,其表现形式的运用已相当的纯熟。中国文坛在20世纪中叶才明确提出反讽的概念范畴,但在古代诗歌和叙事文中,一直存在着一些代表性的术语,如“含蓄”等。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随着西方反讽学的引入和译介,以鲁迅、冯志等为代表的一些作家开始借鉴和吸收,但主要体现出对反讽运用和研究的一种个人化的、非理论化状态,而追求简洁、明朗的解放区文学和十七年文学注定与反讽无缘,因文罹祸的悲剧更使噤若寒蝉的作家们对反讽避之惟恐不及。一直到80年代,从先锋文学漫不经心的含沙射影到王朔若醉若狂的泛滥使用,反讽迅速地蔓延开来。克尔凯郭尔说:“事实上,一个人成长的环境越是聚讼纷纭,他越能从自然界里发现反讽”[1]。新历史小说在此基础上的呈现,就是一典型的反讽文本,它的反讽从语言层次的反讽一直抵达精神观念的内核。
一 言语反讽直指主宰正史的权力话语
言语反讽运用修辞学的特点,使文中的叙述语言与传统的成规定势造成偏离,使人物语言与人物承载的文化话语形成错位,在言与意的对立之间,表达作者自己的情感和价值取向,让读者在质疑中发现言语背后的真相与事实[2]。言语反讽作为反讽的一种重要类型,最具有显现性。
重释历史的激情使新历史主义小说家不遗余力地与官史划清界限,运用言语的反讽形成了词语的张力,造成了读者思想的冲击,使正史下权威的话语在语言的戏谑下失去了庄严高雅的气势,丧失了雍容华贵的姿态。例如刘震云的《故乡相处流传》,彰显出语言上的肆无忌惮:“在一次曹府内阁会议上,丞相一边‘吭哧’地放屁,一边在讲台上走,一边手里玩着健身球说:‘活着还是死去,交战还是不交战,妈拉个×,成问题了哩……真为一个小×寡妇去打仗吗?那是希腊,那是罗马,我这里是中国。这不符合中国国情哩。’”[3]作家藏污纳垢的语言与其人物身份特征及其不对应,丞相不再是正襟危坐、言语端庄的正史身份,而是口吐脏话、行为龌龊的市井俗人。当整篇小说都被这种阴阳怪气的语调统摄时,交叉的火力将主宰正史的权力符码击打得体无完肤,政治历史逐渐撕下了它宏大的面纱,露出了它荒唐的一面。
二 命运反讽撕揭出历史真实的另一端
面对历史转折,小说中的人物并没有欣欣然的按照历史规律预设的那样接受安排,体现正史的光明辉煌,而是在矛盾的选择中,通过反讽折射出个体命运的真实。苏童在《红粉》中描写了妓女秋仪,在面对新的历史时代时,她并没有脱离青楼火海的欣喜,而是对新生活的忐忑不安和敌意,在即将改造前本能地选择了跳车,舍弃了重新做人的机会,彻底地抛弃了幸福生活的可能性,最终清零、惨淡地度过余生。秋仪的朋友妓女小萼,虽然“被动”地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但她认定自己是卑贱的,依旧贪图安逸、自暴自弃,只想依赖男人过活,她引诱老浦,背弃姐妹[4]。为了满足她的贪念,老浦走上了贪污公款而被枪毙的不归路。秋仪和小萼的命运表明,她们在内心里就没有把政府当做拯救自己的人,在意识上也没有认为自己就是旧时代的受害者,反而,革命者鲜血换来的改天换地的新社会,仿佛打破了她们原有的命运轨迹,体现出对正统历史观下革命意义的颠覆。从秋仪、小萼这两个人物命运来看,新政府对于旧社会受压迫受侮辱的损害者进行的新改造,并没有正史话语下的那样取得彻底而全面的成功。作为“少数话语”出现的秋仪、小萼等小人物,形成了微卑的个体对强势历史的反讽式效果,暴露出了宏大历史地块上真切存在的细小缝罅。
三 文体反讽体现出更高层次的重构意义
文体反讽是文体形式和内容之间的错位和对峙。在接受心理的惯势中,文体意味着一种积淀的文本模式,但在新历史主义小说中,文体具有超越和重构的意义,承载着作者对文化和历史的理解和解构。戏仿小说是文体反讽的典范,余华在80年代创造出《鲜血梅花》和《古典爱情》,前者是对武侠小说的固定叙事程序的意义解构,而后者则是对才子佳人小说的传统故事模式的文本消解。《鲜血梅花》中为父报仇、浪迹天涯等在传统武侠小说中堪称经典情节,《古典爱情》中的穷苦书生赴京赶考、和富家小姐私定终生等是在古典爱情故事中的常用套路,但是两部小说只是戏仿了武侠复仇小说和古典爱情故事的外壳,情节的发展却突破了传统模式。《鲜血梅花》的复仇实则是场昏昏无涯、若行于梦魇的无目的的漫游,消解了人们有仇必报、因果报应的阅读快感,彻底颠覆了传统的复仇故事及故事所包含的一切价值,进入到对人生的关照。《古典爱情》以对现实社会赤裸裸的残酷描写和爱情的悲剧性结局,消解了人们对才子佳人“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愿望和爱情幻想,旨在告诉人们幸福美满只是心中的梦,存在的无奈与彷徨、人生的变幻无常、社会的残酷黑暗才是真切的存在。新历史主义小说在对传统叙事的成功戏仿中,实现了对官史文本的更高层次的颠覆和反讽。
四 情节反讽直指看似合理的正统性
历史理性的发展在新历史主义小说家那里遭到质疑,历史的必然性常常被甩出结局轨道,偶然性结局被安排在接受者的视界。为了更加完美地体现这一指归,新历史主义小说通常藉由情节反讽的形式,对合理发展的情节进行戏剧化的突袭,让现实对我们的主观猜想进行嘲讽,致使一切理所必然的原因重新被对望观测。格非的《迷舟》中,三顺马上就要杀了仇人萧了,此时,他却突然放下了屠刀,选择了放弃。到底是什么改变了他,致使故事情节突然斗转?作品中这样写道:“也许是萧对于一个已经废掉的女人的迷恋感染了他,也许是他内心深处莫名其妙的喜怒无常,三顺放弃了杀死萧的想法。”也许这些“也许”不足以解释他的真正思想动机,但偶然性确实直指了事件的因源。在李晓的《相会在K市》中,一心忠于革命、颇具才华的热血青年刘东,仅由于他人胡闹的行为,便被视为上海敌特派来的细作,成为了革命同胞的刀下冤魂。就这么一个微小的事情,如此偶然地裁决了一个人的生命。通过情节的反讽,新历史主义小说家告诉人们,历史的神秘也许就存在这众多的偶然性的秘密中,因而面对偶然性的“玩笑”,一切必然都必将感到无可奈何。
五 情境反讽探视出人类生存的本质
情境反讽通常追求一种整体化效果,是小说要素共同孕育的一种内在张力。所以,情景反讽具有较高的潜匿特性,但这种洒脱的不着痕迹的悖谬也赋予作品新的诠释角度和深广的意蕴。新历史小说家无论在讲述自己或者他人甜蜜和悲苦时,都以一种游戏的方式维持着冷静的历史叙述,至始至终把持着一种内敛的不落痕迹的语调,令人着实无法判断出其内在的真实情感,因而在作家和叙事对象之间建立了一个浑然天成的屏障,造成了一种审美的距离,形成了一种冷漠的情景反讽。在游戏的叙述中,美与丑、对与错、高贵与低劣通通遭到“新历史主义”小说家的冷酷打趣,在一幕幕滑稽表演中重构了他们对历史的态度和观点,让人在啼笑皆非的荒诞背后,陷入对历史的思考和人性的品读。在余华的《活着》这部长篇历史小说中,历史似乎不像我们教科书上写到的历史,不是什么前进与倒退的问题,也不能用什么螺旋式上升的模式来框定,而是一摊烂泥,一片混乱。历史被反讽成恶作剧加荒诞剧,随心所欲地同卑微的人类开着残忍的玩笑,人类在哭笑不得的历史面前变得祸福难料。小说家从头到尾都用一种平实的近乎冷漠的笔调进行叙述,直指精神内核的探寻,旨在带领大家在生命的层次进行灵魂的拷问和探寻:人,不要企图从历史那得到什么,更不要妄图幻想成为历史的主人,生活的真面目就是真实、残酷、自我抗争、坚忍。
新历史小说中有着如此多的反讽应用,根源于它存在的深厚的社会时代土壤。近几十年来,改革开启了中国社会的历史性巨变,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工业化、人口城市化等造成了意识观念的纷繁复杂,传统历史话语的权威地位遭到撼动,主流意识的合理性受到冲击,整个中国文化呈现出多元和悖论的特征。反讽叙述就是对社会文化泛文本的一种投射,就是对悖论中人的存在情境的透视。在反讽里,蕴含着一切生命形式在万事万物中最本质的矛盾存在,并因此引发的自我批判和深刻反思,当共同的价值标准和最高真理消解时,我们对生存的当下境况和终极意义会不断地表现出恐慌和困惑[5]。因此,新历史小说的反讽从根本上表明了作家这样一种观念:他们质疑崇高的形而上的概念,否认纯好纯坏的脸谱化,怀疑简单因果的历史必然,他们以解构的手段达到建构的目的。
[1]D·C·米克.论反讽[M].北京:昆仑出版社,1992.
[2]马珍萍,胡淼淼.《冲撞》中的反讽策略[J].电影文学,2010,(7).
[3]刘震云.故乡相处流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4]路文彬.游戏历史的恶作剧——从反讽与戏仿看“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后现代性写作[J].中国文化研究,2001,(2).
[5]任继敏,杨梦媛.众人皆醒谁独醉——论樊忠慰《精神病日记》的反讽特色[J].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