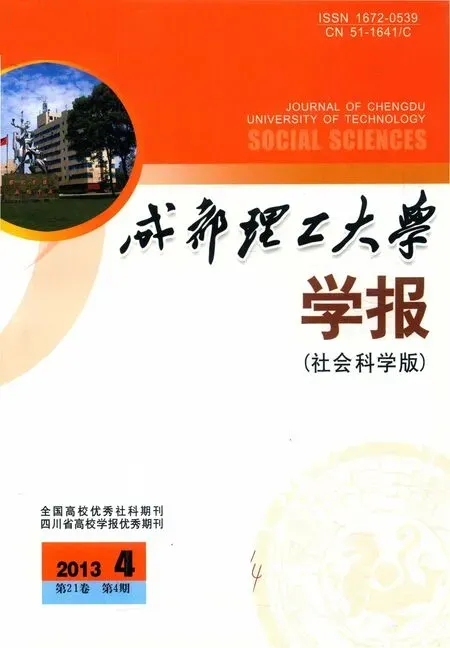论辛亥革命前后梁漱溟的革命观
祝 薇
(上海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0)
革命之义有广狭。其最广义,则社会上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变者皆是也。其次广义,则政治上之异动与前此划然成一新时代者,无论以平和得之,以铁血得之,皆是也。其狭义,则专以武力向于中央政府者是也。吾中国数千年来,惟有狭义的革命。今之持极端革命论者,惟醉心狭义的革命[1]1248。
——梁启超
辛亥革命前后,在中学和西学的不断演进中,知识分子关于“革命”的观念也经历从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如果说古代革命观强调的是“汤武革命”意义下的“君统易姓”、“更朝换代”;那么近代革命观的特点则是通过“君权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国或实行君主立宪,从国家制度上结束君主对国家政治权力的垄断;而现代革命观则是以追求经济平等为核心的社会革命。比照梁启超《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一文中对革命的广义和狭义的理解,我们大致可将近代以来的革命观分为三大类:最广义的革命指向社会革命;其次意指向的是政治革命即引起君权变化的政治革命,包括维新派的君主立宪主张和革命派的民主共和主张;狭义革命则指向的是“汤武革命”意义下的传统革命观。从狭义的革命观到广义的革命还蕴含着从单一的政治革命论到系统的社会革命论的内涵。这三种革命形态在辛亥革命前后杂出,不同程度地渗透到知识分子的革命观中。
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同样也推动着梁漱溟在辛亥革命前后不断地思索革命。在革命观念上,他经历了从最初从狭义的革命观出发来否定君主立宪主张的“革命性”,到接受“三民主义”从广义角度理解的“革命”主张;从立宪时期的“政治改造”的单一革命论到重视“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的系统革命论;从主张“君权革命”的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的近代革命观发展到突出经济平等的现代革命观的一系列转变;在革命行为上,梁漱溟则经历了从“行革命”到“说革命”和“想革命”日趋保守的行为过程。梁漱溟理解的革命问题的复杂性,既是当时复杂的革命形势的一个显影,同时也是近代知识分子通过革命手段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系列艰难尝试。
一、政治改造:君主立宪
生于甲午战争前一年的梁漱溟,青年时代就是在剧烈的社会变化中渡过。由于受到当时社会环境以及父亲的影响,梁漱溟从小就养成了关心“国事民瘼”的习惯,并从青年时代就开始通过各样的革命形式来参与到对国家命运前途的改造中。
直到1911年前,梁漱溟对于清政府的态度一直受君主立宪派的影响,对于国家的政治命运,他也形成了自己的主张:“我只热心政治改造,而不同情排满。在政治改造上,我又以英国政治为理想,否认君主国体民主国体在政治改造上有什么等差不同。转而指摘民主国,无论为法国式(内阁制),抑美国式(总统制),皆不如英国政治之善——此即后来辛亥革命中,康有为所倡‘虚君共和论’……这些理论和主张,不待言是从立宪派得来的,然一点一滴经过我的往复思考,并非一种学舌。”[3]684-685梁漱溟这里用“政治改造”而没有用“政治革命”来说明他要求变革政治现状的思想,这并非是他当时不知晓“革命”这个概念。在辛亥革命的前十年,“革命”一词已经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词汇了。而这其中原因正在于梁漱溟关注“政治改造”的时期正是维新派慎言革命的时期。
事实上梁漱溟所主张“尊王改革”之义的“政治改造观”在“戊戌变法”前后也曾一度被维新派称为“革命”。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发现日本人将英语revolution一词翻译成“革命”,不仅是指政权的激烈交替,也同样指向万事万物之间的“淘汰”和“变革”,尤其是在政治领域。他说:“日人今语及庆应明治之变无不指为革命时代,语及尊王讨幕废藩置县诸举动无不指为革命事业,语及滕田东湖、吉田松阴、西乡南洲诸先辈,无不指为革命人物。”[5]760康有为也在1898年的奏折中把日本维新引起的动荡称为“革命”,他说:“及倒幕维新,而革命四起”[6]104。但是这一时期康、梁都是从广义角度来理解革命的。而且梁启超从广义理解的“革命”一词的意义“带有鲜明的日本色彩,并与西方和平演进的革命意义相融合。梁氏由是接受了这一‘革命’的新义,并竭力鼓吹,希望中国能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榜样,以和平的方式实现政治现代化。”[7]8但是由于中日之间政治体制的不同,造成了当时知识分子对于革命意义理解出现了巨大的偏差。沟口雄三曾经指出:“两者之间横亘着难以逾越的两国传统之差异,即一方是根植于中国易姓革命思想的传统;另一方则是根植于日本万世一系的天皇观这一历史事实。”所以在中国的历史背景下来言说“革命”导向的不是“尊王改革”而是“改朝换代”。梁启超也很快意识到这个问题,1902年他在《释革》一文中指出“革命”一词蕴含着易姓和改朝换代的意思,所以应该用“变革”来翻译revolution,指的就是非改朝换代的变化。“变革”和“革命”的主要差异则在于前者往往是由当权者及社会精英自上而下推动的。1905年-1907年,梁启超以《新民丛报》为依托,与以《民报》为依托的革命派围绕着是“改良”还是“革命”展开了论战,作为“争论的结果,‘革命’被等同于政治结构的激烈变革,它与暴力密切相连,并与‘改良’相对立。”[7]4而这种对革命理解的趋势和维新派的改良主张是相背的,自然“革命”的观念从狭义的角度被维新派否定了。这一点从梁漱溟为维新人士彭冀仲被保皇分子所抓时为他打抱不平的话语可以看出:“彭先生虽只不过倡导维新改良,而在老顽固守旧者却把他混到革命方面而分不清。”[8]71在这样的背景下,梁漱溟用“政治改造”而不言“革命”的心态就可想而知了。但是作为维新派知识分子的立场其实很尴尬:在革命派看来,他们不够“革命”,但是在老顽固守旧派那里,维新人士又往往被当作革命者看待。
虽然没有“革命”的观念,但并不妨碍梁漱溟的革命行动。梁漱溟曾经评价维新人士彭冀仲先生,说他的思想虽然不外是一般维新人士的思想,但是他敢想敢作,勇于实践,不怕牺牲,所以,梁漱溟认为彭冀仲:“虽无革命意识,却有革命精神吧”[8](65)。同样具有这种“革命精神”的当然还有梁漱溟自己。梁漱溟自从中学就开始参与到革命的过程当中:“我在中学将要毕业的时候,一面考毕业试验,一面革起命来。本来在毕业时,已与革命党人相通,毕业后便跟着跑革命。”[3]77据美国作家艾恺的记载,梁漱溟12岁就去发传单,积极参加民族主义运动;在1905年抵制美货的运动中,他和同学冲进店铺,查禁美国货;他还被同学们推选为代表去请求学堂监督,要他去特聘一名军官来进行课余的军事训练,以便学生们用热血和武装来拯救国家,抵抗列强日益贪婪的侵略等等。[9]29-30
总之,到1911年以前,梁漱溟把君主立宪作为使国家强盛的唯一手段,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革命,将君主立宪的政治改革主张排除在革命的范畴之外;另一个方面他从“政治改造”的单一革命论出发,积极地拥护以西方模式为基础的政治改革,其革命观带有明显的近代色彩。同时,作为一个没有“革命意识”的近代知识分子,梁漱溟在这一阶段是切切实实地“行”革命的阶段,充分体现了勇于实践的“革命精神”。
二、政治革命:民主共和
然而无论是君主立宪派还是民主共和派,他们虽然在应当效仿西方还是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制上有分歧,但是他们对于要救国家于生死存亡的迫切心情还是一致的:“他们都坚信首先要进行政治变革,进而必须在一个具有政治意识和责任感的公民的坚固基础上重建中国。”[10]154基于这些基础,所以当立宪派还没有等来他们预期的政治效果时——辛亥革命就爆发了,革命后大量立宪派转而接受民主共和的主张的局面就不难理解了。
同样在迅速发展的革命情势面前,梁漱溟不得不选择接受革命派的政治主张:“后来清廷一天一天失去人心,许多立宪派人皆转为革命派,我亦是这样。”[3]685转入革命派对梁漱溟意味着他要接受并参与到激烈的政治变革当中,甚至不惜采用暴力的手段。事实上,梁漱溟很快就以实际行动践履了他的革命观:不久,“中学毕业期近,而武昌起义,到处人心奋动,我们在学堂里更是呆不住了”[3]685;1911年在他的同学革命派人士甄元熙的介绍下,梁漱溟加入了京津同盟会。作为革命派的重要组织,京津同盟会“充满着暗杀、秘密会议、军火走私和自制的炸弹。”[9]39为了革命,梁漱溟还第一次走出北京城去昌平,并经常去天津总部所在地去取武器和炸药;他还以经营一个煤店为名,使之作为革命者在北京的掩蔽所;随后又作为记者的身份用自己的笔杆子来宣传革命。
但很快,梁漱溟的革命热情被随之而来的现实所打击。从“学生”的身份直接转化为“革命分子”:一边是相对宁静的“象牙塔”,一边是变革时期矛盾重重、乱象百出的现实社会,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很快对喜欢思考社会问题的梁漱溟再一次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作为新闻记者一年有余,使得梁漱溟有机会与社会充分的接触,“渐晓得事实不尽如理想。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学校所遇不到底,此时却看见了;颇引起我对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3](687)但是真正使梁漱溟对辛亥革命彻底失望的事件是1912年国民党的成立以及《国民党规约》的颁布。
1905年孙中山创办了中国同盟会,在同年11月出版的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的《发刊词》中,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对于“三民主义”,孙中山指出:“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这三样有一样做不到,也不是我们的本意。达了这三样目的之后,我们中国当成为至完美的国家。”[11]79在孙中山那里,他将“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三类革命统一起来。但是在辛亥革命前,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是当务之急,孙中山希望在实现“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后,通过实行民生主义,能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从而使“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对于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关系,恩格斯也曾经说过:“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的和哲学的革命必定通向社会革命。”[12]17这些思想都说明在政治革命成功后,社会革命的必要性。1912年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梁漱溟认为这次改组“盖非止放弃了革命方略,还放弃了革命的宗旨目标”[8]41。因为同盟会会章的宗旨是“本会以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为宗旨”;而国民党的章程则改为“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了,只不过另外在政纲五条之中,列有“注重民生政策”一条。梁漱溟认为:“这明明是以社会政策代替社会主义,以改良代替革命。”[8]41
如前所述,三民主义从内容上来说是包括“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的“大革命”概念,是从广义上理解的革命,具有系统性变革的特点;从性质来看,三民主义中民生主义对于平均地权的重视也使得这一革命理想带有现代性的特征。梁漱溟对“民生主义”的关注,同样也说明他对社会革命的关注,这也是他后来关注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国民党对于民生主义的背弃,正是打破了同盟会对系统性革命的设定,继而使得社会革命无法继续进行下去。这也大概是梁漱溟对国民党成立后背弃同盟会的宗旨不满的根本原因。
国民党的成立,使梁漱溟意识到同盟会由“往日救国的英雄团体,如今变成了扩张权力的政客们的避难所。”[9]44所以,他最终选择离开了同盟会,离开了国民党。
陈建华在《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指出,辛亥前后社会心理由恐惧革命而转向欢呼革命,造成这一戏剧性的转变,除了因为清朝政府丧失了正统性外,“我认为更重要的是‘革命’一词已经突破了传统而具有世界性和现代性的意义,在宣扬暴力革命手段的同时亦包含着有关民主和民族内容的社会变革的种种许诺。”[7]19但是辛亥革命之后,这种种许诺都落了空:中国政治并没有走向正规,军阀擅权,武人专制,中国在推翻了满清皇帝后,政府的权威也丧失殆尽,中华民国在事实上也深受政权衰微之苦,社会秩序也远不如革命前。面对和革命理想严重偏离的现实,梁漱溟开始思索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首先,辛亥革命是由一群思想不成熟的学生主导的“学生革命”[3]686。而“缺乏社会经验”、对社会只有“虚见和臆想”和“认识不足”的青年学生主导的这场革命,失败是必然的。这说明梁漱溟意识到革命党组织不健全而且思想混乱,无法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导致革命失败的必然趋势。其次,梁漱溟指出辛亥革命并没有广泛发动群众,也没有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使革命丧失了主力力量:“无奈中国革命是社会内部自发的革命,缺乏西洋那种第三阶级或第四阶级由历史孕育下来的革命主力。中国革命只是最先感受到世界潮流之新学分子对旧派之争,全靠海外和沿海一带传播进来的世界思潮,以激动一些热血青年。”[3]685-686辛亥革命偏重上层的改造而忽视下层民众的组织,没有真正把民主共和的理念输到民众之中,为民众所掌握,也是辛亥革命的一个严重缺陷。梁漱溟对于辛亥革命失败原因的两点基本认识,也是民初社会对辛亥革命反思的主要点。
虽然“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主张,在革命目标和革命手段上的分歧是很明显的,但是当我们将之放到整个晚清革命的进程,它们都属于 “君权革命”,都是要从国家制度上结束君主对国家政治权力的垄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的革命都属于近代革命观的范畴。不同的是,“君主立宪”突出的是单一的政治革命,而“民主共和”凸显出的是一种系统的革命观,而且后者还带有现代革命观的色彩:从孙中山先生创办同盟会,到“三民主义”的完整提出,“从主张‘民族革命’到重视‘政治革命’再到提出‘社会革命’,中国现代革命观念可谓是步步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最初地位凸显的是‘民族革命’逐渐让位于‘政治革命’、‘社会革命’。”[14]可惜的是,辛亥革命前后,社会革命虽被提出来,但是相比较政治革命,始终还是处在边缘化的地位。在上述背景下,相比较前一阶段,梁漱溟的革命观仍属于近代革命观的范畴,但是由原来理解的单一革命论转向了系统的革命论。
三、社会革命:社会主义
辛亥革命前期,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梁漱溟也认为只要通过政治革命实现了宪政,那么中国也很快会成为像欧美和日本一样的近代国家,至于经济平等、世界大同都是会自然而然的随之而实现。但是,很快他发现,革命成功后,社会问题杂出,梁漱溟在此种情景下也不禁感叹:“人类日趋下流与衰败,是何等可惊可惧的事呀!教育家挽救不了;卫生家挽救不了;宗教家、道德家、哲学家都挽救不了。什么政治家、法律家更不用说。”[3]691社会种种不平等现象使梁漱溟认识到这些不平等的根源正是在于“私有制”:“不过很久,我忽然感觉到‘财产私有’是人群一大问题”[3]688,那些教育家、卫生家、宗教家等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根源正是在于“私有制”。
民国元年末、民国二年初,梁漱溟偶然从家里获得一本日本人辛德秋水所著的《社会主义之神髓》这本书,对其中反对财产私有的思想颇为关注,结合日常社会中所见,使得梁漱溟“不断地思索这个问题。愈想愈多,不能自休。终至引我反对财产私有的路上,而且激烈地反对,好像忍耐不得。”[3]689梁漱溟认为私有制是人类生存竞争的根源,由于生存竞争会导致巧取豪夺。巧取的极端就是诈骗;豪夺的极端就是强盗,而且这两大类型中又包含着人类各种各样丑陋的事例。所以他说:“人间的一切罪恶社会制度(财产私有制)实为至,不能全以责备哪个人。若根源上步解决,徒以严法峻刑对付个人,囚之杀之,实在是不通的事。”[3]689那么如何挽救人类日趋下流于衰败的事实,只有通过社会主义的革命才能实现,而对于社会主义,梁漱溟认为“只有废除私有制,以生产手段归公,生活问题基本上由社会解决,而免去人与人之生存竞争。——这就是社会主义。”[3]690-691这些说明,国民党成立后放弃了主张民生主义的社会革命,但是种种社会现实使梁漱溟不仅认识到社会革命的重要性,而且更进一步强调了在社会革命中经济革命的迫切性。
什么是“社会革命”?近代以来不少的知识分子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阐述。1906年,朱执信在《民报》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等文,对有关“社会革命”诸问题作了最初的系统阐发。朱执信指出,“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具有不同的性质:“政治革命”在于人民大众反对君主专制制度,这也就是“国民革命”;“社会革命”则在于现代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在性质上与“政治革命”并不相同。他说:“凡政治革命之主体为平民,其客体为政府(广义);社会革命之主体为细民,其客体为豪右。”[15]60这里所讲的作为“社会革命”主体的“细民”,即无产阶级;作为“社会革命”客体的“豪右”,即资产阶级。在现代社会经济生活诸因素中,他把引发“社会革命”的最主要原因归结为无限制的竞争和绝对的私有财产制度:“今日一般社会革命原因中最普通而可以之代表一切者,则放任竞争,绝对承认私有财产权之制度也。”[15]56李石曾也曾在1907年的《革命》一文中指出:政治革命的目标是转移国家政治权力,变更国家制度,而社会革命是实现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等[16]167。而近来金观涛指出“社会革命是指消灭经济分配和其他种种不平等,革命以平等为根据。”[4]387并且,他还进一步指出,追求平等和独立是“中国式现代革命观念的核心”。无论是在朱执信,还是李石曾,亦或是金观涛他们都强调的是社会革命最核心的内容是追求经济上的平等,这也是现代革命观区别于近代革命观的关键点所在。当然,辛亥时期对于社会革命的理解只是中国现代革命观的一个初步建构,而随后在知识分子的不断探索中并随着后来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有了更加清晰的显现。
如前所述,中国传统的革命观是以改朝换代为核心内容;中国近代革命观是属于君权革命,结束君主对国家政治权力为主的政治革命,那么中国现代的革命观则主要是通过社会革命来体现的。而梁漱溟所说理解的废除私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正是属于社会革命的范畴,体现出来的正是一种现代的革命观。
不过,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解在梁漱溟的头脑中只是一个初步的轮廓。关于现代革命的方法、手段、目标等关于革命的一系列问题都还没有纳入到他的思考范围中。尽管如此,对于社会主义的抽象理解却一直萦绕在梁漱溟的头脑中。王宗昱就曾指出:“从槐坛演讲可以看出梁漱溟当年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并没有很深入的了解,而多是针对中国当时社会问题的一些感受。”[17]9
从主张君主立宪到转变为民主共和,再到热心于社会主义的思想,梁漱溟的革命观经历从政治革命开始转向经济革命的过程。但是梁漱溟也知道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虽然好,可惜当时的中国还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势”。为了说明自己对于社会主义理解,他也曾撰成《社会主义粹言》油印数十本赠人,这是他为自己的社会主义理想仅仅所做的微力之举。所以,相比较他在前两个阶段的激进的革命行为而言,这一阶段仅是停留在“想革命”和“说革命”的阶段。
当梁漱溟对于社会主义的一阵狂热之后,发现他最后寄希望于的那个社会革命没办法实现时,用艾恺的话说就是“这种社会良心觉悟最重要的结果是‘厌恶并轻视人生’”[9]46,所以他开始转向佛学也求得一点安慰。与之相似的是,现代新儒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熊十力感受到民国时期的“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时,也“时或独自登高,苍茫望天,泪盈盈雨下,以为祸乱起于众昏无知,欲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于正见。”[18]659那种对国家前途命运担忧而又无能为力的悲苦心情,大概也是那个时代大多数知识分子的通感吧!
辛亥革命后,梁漱溟从杂乱丛生的社会现象中悟出了社会主义革命。他对于革命的认识也经历了从政治革命为主,到以经济革命为核心的社会革命的转变,在广义的社会革命中突出了经济革命的重要性,并初步显现了现代的革命观。
四、结语
对于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费正清曾指出其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国革命的广泛性和彻底性:“在西方世界,革命一般发生在诞生它们的文化中。一般说来,革命首先是政治变革,是一种政治制度的改变,这种变革有时候也使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改变成为可能。我非常怀疑,当人们讲到中国的‘革命’时,是否忽视了一个根本点,就是中国不仅进行了政治‘经济和社会革命,而且确实在进行整个文化的转变。”[19]49这说明了,受到西方革命观念影响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对于以“君权革命”核心的政治革命给予了超过政治革命之外的幻想。脱离了西方的历史文化背景所理解的政治革命,在中国的发生并不必然会引起社会全方位的变化。所以政治变革之后的社会革命在中国的文化历史背景之下,成为革命的必然趋势。中国革命的广泛性也造成了辛亥革命前后革命观念的复杂性:即包含有传统的革命观、近代革命观、现代革命观,也包含着狭义和广义的革命观念,以及单一革命论和系统革命论等等。
而在这个过程中,梁漱溟对于革命的认识经历从政治革命到经济革命、从狭义革命到广义革命、从单一革命论到系统革命论、从近代革命观到现代革命观的转变。
梁漱溟在辛亥革命前后,对革命理解与态度的转变,也正反映了近代以来第一批知识分子由热衷革命到对革命的失望后转向思想文化革命和社会建设的第一次分流。这也许正如一位美国作家所说的那样“1911年革命失败造成这些期望的破灭,从而为下一代提供了一个铭刻于心的教训。五四时期——大致从1915年到1925年这十年——许多中国发言人不再充任行动主义者和革命激进分子曾竭力扮演的革命发动者的角色。他们给自己选定的角色不是我们所谓的政治新手,而认为政治活动(至少在广义上)对具有共和思想的人来说只是一种适宜的业余爱好,它不能成为知识分子的理想职业。”[10]155
注释:
(1)对于单一革命论,是指认为革命就是以暴力方式推翻政府的行为,即通常所说的政治革命。持这种革命论的学者认为,革命不仅包括起义,也包括所有以暴力形式颠覆政府的行为,如叛乱、政变以及骚乱,例如布林顿在其代表作《革命的剖析》一书中认为革命是一个领土政治实体的统治群体被另一个没有操纵政府的群体猛烈地、突然地取代,而且一个革命群体取代另一个群体,可以采用实际的暴力起义的方式,也可采用政变、暴动或者其他形式的诡计。而系统革命论则认为革命不仅具有暴力性,而且具有系统性,必然导致这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以及意识形态的重大变革,而不仅仅是政权的更替。亨廷顿就认为:“革命是对一个社会居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神话,以及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体系、政治活动和政策,进行一场急速的、根本性的暴烈的国内变革。”(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41页。)
(2)其实从梁启超的《释革》一文中,在他对于次广义的“革命”含义规定中,“君主立宪”也应属于革命的范畴。
[1]梁启超.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M].梁启超全集,第三册第五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2]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三联书店,1996.
[3]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二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
[4]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5]梁启超.释革[M].梁启超全集,第二册第三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6]康有为.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康有为全集,第四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7]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8]梁漱溟.忆往谈旧录[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9]艾恺[美].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
[10]杰罗姆B·格里德尔.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M].单正平,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
[11]孙中山.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孙中山选集,上卷)[M].北京:中华书局,1956.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朱汉国,杨群.中华民国史,第二册[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
[14]李维武.辛亥革命前十年间中国现代革命观念的形成[J].学术界,2011,(7):5-28.
[15]朱执信.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朱执信集,上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16]李石曾.革命,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17]王宗昱.梁漱溟[M].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2.
[18]熊十力.尊闻录(熊十力全集,第一卷)[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19]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