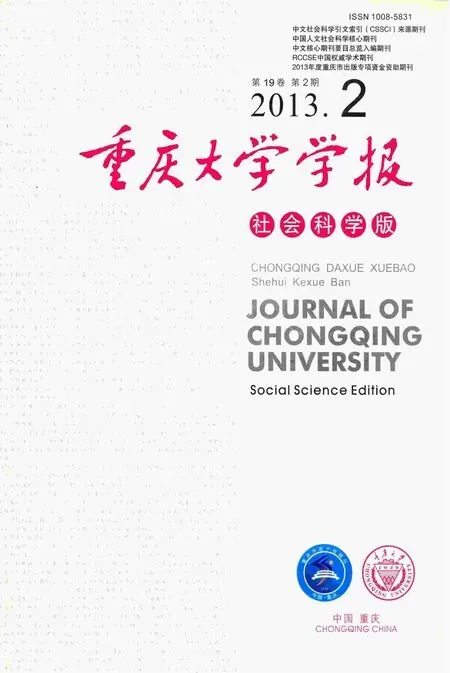检察机关非自侦案件侦查监督的博弈论分析
彭志刚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北京 100089)
检察机关非自侦案件侦查监督的博弈论分析
彭志刚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北京 100089)
检察机关依法对侦查机关行使侦查监督权,既要解决因侦查机关抵触和内部动力不足而导致的监督不力的局面,又要解决因信息不畅导致的监督不到位的困境。充分运用博弈理论能够较好地处理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互动,引入第三方即当事人及其诉讼参加人的力量介入可以实现博弈方的最大收益,实现监督实效的最大化。
侦查监督;博弈论;非自侦案件
一、问题的提出
侦查活动是在国家权力与个人有关自由与财产的激烈冲突的场域中进行的。侦查权因其主动性、干预性、独立性、单方性的特点,极易因侦查人员滥用职权而失控。侦查监督制度作为纠正侦查机关和诉讼参加人之间的力量不平衡的制度设计,其最终目的在于确保侦查权合法、合目的地行使,从而防止侦查机关滥用其公权力优势,打着惩罚犯罪的旗号,肆意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
司法实践中,让我们困惑的事,是侦查权与侦查监督权双方力量的对比处于失衡状态、侦查监督机关在侦查中的监督角色模糊、侦查监督的范围不明确、侦查监督的实效得不到保障,也就是说中国侦查监督长期以来处于“名大实小”的困境。针对这一问题,中国很多学者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从各方面进行了解读,并提出了相应的制度完善措施,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笔者发现,较少有人从法律制度和规则的角度对监督者和被监督者行为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也就是运用博弈论的方法,来分析该制度的优劣并提出完善意见。
根据博弈论的基本观点,一种制度或规则形成以后,并不一定会产生实际效果,“要发生效力或实现实效,必须是一种纳什均衡”①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是非合做博弈理论的核心概念,给定你的策略,则我的策略是最好的策略;给定我的策略,则你的策略也是你最好的策略。即一方在一定的策略空间中在对方的策略已定的情况下,自己可以选择的策略是最好的策略。[1],它必须能够使众多行为人的收益达到一种均衡。在这里,利益对规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根据经济学关于经济人假设的观点,人具有经济理性,“人是天生的经济人,他做什么,不做什么,都会本能地进行一番成本与收益的盘算,尽管确有少数人能够超越现实的功利计较,但绝大多数人都会按照人类自身的利益选择法则来行事”[2]。因此,“在社会中,一个人的收益最大化是以不损害别人的利益最大化为条件的,所谓制度安排就是在解决人与人的利益最大化目标的那种冲突中诞生和发展起来的,由于人们总是会赞同别人的有利于自己的行动,而反对和抵抗别人的不利于自己的行动,因此,在长期的互动过程中,在多次的重复博弈之后,就会形成对大家都有利或至少不损害任何人的制度安排”[3]。就刑事诉讼活动过程而言,由于在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以及刑事诉讼参与人之间存在若干组博弈,参与博弈的各方也会对制度安排做出各自的反应,使各自的利益最大化。
应该说,“没能充分利用博弈理论是不幸的,因为现代博弈理论为人们理解法律规则如何影响人的行为提供了非常深刻的洞察力”[4]。正是循着这个思路,笔者拟从博弈论的角度对侦查监督权的运行进行分析,旨在提供另一种视角,希望对中国刑诉活动有关侦查监督制度的设计与完善有所裨益。当然,应该指出的是,笔者关注的只是侦查监督一个方面的问题,至于其合宪法性、制度的协调性等问题,则不是本文关注的内容。
二、侦查监督中的博弈原理
长期以来,侦查监督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出台的文件堪称“汗牛充栋”,但问题仍然一大堆,司法实践中的问题似乎并未解决。长期以来,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的监督普遍持积极应对、消极处理的“阳奉阴违”的态度。强势的侦查机关对于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诉讼监督,反应冷淡,消极应付。有些人甚至认为侦查监督工作是检察院在找茬、挑毛病,因而在接受监督时不愿配合,甚至进行信息封锁,人为加大检察机关监督难度。其主要表现在:对检察机关立案监督的案件,不认真办理,甚至采取拖字诀,有案不立,立而不办,办而不结;对检察机关纠正违法的案件,找借口和理由拖延纠正,对不当立案而立案错误不及时纠正;对检察机关追捕、追诉的案件,找借口、谈困难、讲条件,应付了事;对检察机关针对刑事拘留后的下行案件的监督工作采取封锁信息、编造理由的做法,不愿被监督,或逃避监督。应该说,近几年来侦查机关对检察机关的监督工作配合不够主动的现状有所改善。但是,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工作目前仍然处于亟待改进和提升的状态。反观检察机关自身,虽然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有关文件多次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加大监督力度和监督实效,可有些地方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工作长期以来仍显得动力不足。如果不是内部考核的因素,侦查监督工作早就流于形式、形同虚设,更谈不上监督效果。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大量的案例呈现一种困境,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利害关系人对于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各种侵犯自由权、财产权的行为经常是控告、抗辩无力。
关于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很多学者对此都有深刻的见解,在此笔者不再一一赘述。笔者尝试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就是用博弈分析的方法,来剖析这个问题。
一般说,一个完整的博弈大致由四个方面构成:第一,博弈的参与人(players),即决策主体,可以是个人、团队、国家或国际组织。第二,参与人可能的战略(strategies)或行动(action),即规定每个博弈方在进行决策时可以选择的方法、做法等。第三,收益(payoffs),是指在一个特定的策略组合下,博弈者所得到或预期得到的效用水平,可以是正值,也可以是负值[4]。第四,进行博弈的次序(orders)。假如当博弈方同时行动时,那就没有次序之分。但在许多情况下,博弈双方行动是有先后次序的。前者,被称为静态博弈,后者,称之为动态博弈。
按照博弈理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及诉讼参加人(在侦查阶段主要是犯罪嫌疑人和辩护人)三方构成了三角博弈。前文谈到的检察机关侦查监督缺乏实效的主要原因其实表现为一种各方的非合作博弈状态。
笔者以为,其产生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其一,被监督者遵守规则的收益低于不遵守规则的收益导致公安机关不愿接受监督。从博弈论的角度看,公安机关和检察院正好构成博弈双方,双方均受考评指标的影响和驱动,前者以立案率、刑拘率和破案率为奖励指标,其中,“该立不立”和“不该立而立”等均影响其收益;相反,检察院也以有效监督为考核指标,剔除那些“该立而不立”和“不该立而立”的案件,对检察院没有任何不利影响。相反,假如检察机关对当立而不立,不当立而立的案件监督得越多,考评分值就越高。但是,不当立而立、当立而不立的被纠正就影响了公安机关的立案率,公安机关还可能要被扣分。因此,遵守侦查监督规则事实上对被监督者不利实属意料之中的事。
其二,博弈双方信息不对称导致检察机关难以监督。信息不对称不但指信息量的掌握与否,也包括信息获得的先后次序、信息多寡、信息真假的不对称。相对来说,无论在侦查过程的哪一个环节,公安机关都掌握着案件证据的第一手资料,尤其是涉及犯罪嫌疑人有罪或无罪、罪轻的信息材料,而检察机关只能通过公安机关的书面报送材料来对案件是非、正误加以判断。就信息的获取和筛选来说,公安机关明显处于信息优势的一方。在博弈论看来,信息无疑会影响博弈双方的策略选择和收益。信息的影响或作用对作为监督者的检察机关来说,有时候会使检察机关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想监督而无能为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三,监督者收益不大直接影响监督实效。一般来说,检察机关实施侦查监督势必会受到侦查机关的抵触,侦查机关往往假以专业化而认为检察机关是乱指挥、瞎指挥,警检关系甚至因侦查监督而遭受负面影响,这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检察院侦查监督的正收益。各级检察机关为了摆脱困境,试图以从内部施加动力和压力的办法来促进检察机关加强侦查监督工作,其主要手段就是考核指标,如立案监督、纠正违法、追捕的数量和质量等。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一方面,内部施压往往产生的是一种惩罚性的措施,从整体上看,可能是零收益;另一方面,从长远看,警检关系的和睦却能给检察机关带来更大的收益,因而,希望通过检察机关内部考核指标的压力来增强监督者动力的做法,可能会适得其反,至少是效果甚微。
那么,检察机关侦查监督的出路在哪里呢?事实上,笔者的上述分析已经指明了方向,即在现有刑诉法架构下只有改变博弈规则才能重新达到平衡。
第一,改变博弈双方的收益对比。(1)改变考评指标,即弱化立案监督、纠正违法、追捕率在考评中的分值地位;(2)加大处罚力度,但这又会挫伤公安机关的积极性,造成不做事优于做事的局面,因而不应当提倡;(3)增加检察院的动力,但是这种思路往往会加剧警检矛盾,亦不可取;(4)统合协调检察机关和侦查机关的内部考核指标和标准,使检察机关和侦查机关在立案、上行案件的侦办等能达成同向一致。
第二,改变目前信息不对称的状况。在现有刑诉法规定的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侦查格局和权力配置下,检察机关主动发现可以立案和纠正违法、追捕线索的动力和能力的严重不足将严重影响其行为的选择,也就是说会经常犹豫在监督与不监督之间。笔者以为,改变这种状况的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是信息通报制度。根据2010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公安机关与人民检察院应当建立刑事案件信息通报制度,定期相互通报刑事发案、报案、立案、破案和刑事立案监督、侦查活动监督、批捕、起诉等情况,重大案件随时通报。有条件的地方,应当建立刑事案件信息共享平台。但这种信息通报制度往往会涉及一些国家机密、个人隐私问题,有时候也会导致刑事案件的保密性不够,更主要的是信息通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会受到侦查机关及其成员主观意愿的制约,因而操作起来并非顺畅。从各地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法院的三方联席会议制度的实施情况不够理想就可以窥见一斑。第二种是引入知情的第三方。一般来说,涉案当事人与“该立不立”和“不该立而立”案件都有重大的利益关系,引入第三方的意见是提升检察机关监督能力和实效的一种比较可行的思路。可喜的是,新刑诉法第115条已经吸收了引入第三方信息来源的做法。
第三,弥补监督者动力不足的问题。前已述及,单纯从加大惩罚措施方面来增进监督动力并不可取。而每一案件的潜在犯罪嫌疑人以及受害人绝对会非常关心立案与否,追捕、追诉与否,这些第三方对促进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既不乏动力,也了解部分案情。因此,引入涉案第三方既能解决检察机关动力和能力不足的问题,又能避免警检矛盾的产生,比较可行。笔者认为,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引入第三方的主要路径有:(1)被害人或行政执法机关如果认为公安机关对其控告或者移送的案件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受理并进行审查。(2)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和《人民检察院信访工作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机关刑事拘留、逮捕不服,可以向人民检察院信访、申诉。目前,对于引入第三方促进侦查监督实效的方法仍然有待通过司法实践效果来观察。
三、侦查监督制度的博弈分析
(一)检察机关提前介入
“提前介入”指检察机关在公安机关提请批捕和移送起诉之前参与到刑事案件的侦查活动中,从而实施法律监督,规范侦查行为。“提前介入”是检察机关从法律监督的角度出发,为了提高刑事案件的办案质量而进行的一项刑事司法改革措施。“提前介入”是中国司法实践的产物,是伴随建国以来尤其是检察院恢复建院以来检察工作的发展而产生的,一定程度上是检察机关在总结自身检察规制基础上为应对现代刑事诉讼结构的举措。而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也始终在不断演进。2000年9月,在全国检察机关第一次侦查监督工作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了“依法引导侦查取证”的工作思路。2002年3月1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韩杼滨在九届人大五次会议上,向大会提出“深化侦查监督和公诉工作改革,建立和规范适时介入侦查、强化侦查监督的工作机制”。2002年5月15日至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了全国刑事检察工作会议,会议提出了“坚持、巩固和完善‘适时介入侦查、引导侦查取证、强化侦查监督’的工作机制”等四项改革措施。2008年10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人民检察院公诉工作操作规程》,第11条明确规定:“公诉部门应当加强与侦查机关(部门)的联系和配合,完善相互协调机制,保证案件质量。根据办案工作需要,应侦查机关(部门)要求,经检察长批准,可以派员提前介入侦查活动,引导侦查取证。”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地区就有检察机关开始尝试提前介入,具体做法一般是由侦查监督或公诉部门提前介入或适时介入重大刑事案件的侦查工作[6]。
在这种机制下,为了保证检察机关在案件侦查过程中的地位,以参与者和监督者身份参加案件的办理,从而发挥指导作用,侦查监督部门有时在侦查开始时介入,有时在案件基本成型时介入,公诉部门则有时在基本证据需要补强时介入。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相关规定出台后,部分地方检察机关更是积极探索提前介入的最佳模式,其中以河南省周口市人民检察院最具代表性。该院提出引导侦查取证的“三三制”,即坚持三个延伸(批捕向前延伸至自侦案件的立案环节,起诉部门向前延伸至批捕环节,起诉部门向前延伸至侦查预审环节)、实行三项跟踪(侦查人员对自侦案件跟踪至批捕、起诉、审判环节)、明确三段责任(侦查部门负责立案准确,批捕部门负责批捕准确,起诉部门负责起诉准确)②该制度是周口市院在1999年提出的在办理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中实行的一种办案机制,在“三三制”中,自侦部门负责案件的侦查,而批捕和起诉部门在向前延伸中除对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开展监督外,还对证据的收集、固定和完善从审查逮捕和出庭公诉的角度提出自己的建议和参考性意见,对适用法律提出指导性意见。参见李和仁、王治国《引导侦查取证:周口的理论与实践的碰撞》,载《人民检察》2002年第8期。。
从博弈论的角度看,检察机关的提前介入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解决其博弈过程中信息不足的问题。但针对非自侦案件来说,由于人力、物力的限制,检察机关不可能每个案件都参与监督,而只能选择一些检察机关认为有必要的大案、要案加以监督。但事实上,越是大案、要案受到关注的程度越高,公安机关违法侦查被发现的可能性越大,即使没有检察机关的提前介入,公安机关自己也会有意识地尽可能地减少违法取证的情况。不仅如此,目前也没有证据表明非大案、要案发生违法取证的比率比大案要案中发生违法取证的几率小。恰好相反,公安机关违法情形往往发生在一些容易打擦边球的案件上,因为这样做被发现的可能性更小,即使被发现,其严重程度也不高,且侦查机关可能会以主观认知上存在不同意见作为借口。但检察机关对这类案件往往并不会提前介入,提前介入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侦查中的弊端,这就是说,在博弈论上的收益仍然有限。
另外,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活动,由于侦查能力远不如公安机关,在侦查活动中往往地位尴尬。现有格局下,公安局长一般是党委政法委书记或常委,其地位在党内高于检察长,检察机关又是归党委政法委的领导,况且,中国刑诉法并未规定检察机关的侦查主导权或指引权,所以,公安机关往往会借口检察机关人员不懂侦查中的专业情况而我行我素。不仅如此,由于场景效应的同化作用,假如检察人员长期置于侦查环境中,也会不自觉地被公安人员所同化而采取相似的思维模式,影响监督效果,导致监督的收益有限。
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之间监督和被监督的地位和角色分配往往是暂时的,因为其共同追诉犯罪的职责和理念往往会影响他们之间的博弈。而提前介入制度安排也由于种种原因,容易导致两者的关系更近,形成追诉犯罪的同盟。根据责任分担的理论,公安机关在检察人员参与的情况下,由于其责任被分担,往往更有违法取证的动力,“只要检察机关没有明确反对的就是合法的”,而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碍于情面往往很难明确表示反对。
根据以上分析,提前介入并不能绝对有效地提高监督收益,也不能完全抑制违法侦查的发生。因此,提前介入较难取得完全、预期的实效。
(二)非法证据排除的博弈分析
新刑诉法第54条至第58条规定了较为完善的排除非法证据制度,其中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责,体现了对侦查取证活动加强监督的内在要求。新刑诉法第5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人民检察院依据本条规定,加强对侦查人员违法取证活动的监督,有利于保证证据的合法性,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也有利于保证司法公正。
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初衷是遏制警察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防止冤假错案发生、促进司法人员严格执法、维护宪法尊严和保障人权。但是,这种目标能达到吗?
从博弈论的角度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通过降低公安机关的收益来达到博弈平衡的,即通过对非法证据效力的否定来引导公安机关合法取证,这种制度本身在方向上没有问题,因而一度被寄予厚望。但是,这种制度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首先,这意味着有时候明知犯罪嫌疑人有重大作案嫌疑却无能为力。假如出现这种情况,在中国法治尚待进步的现阶段,普通老百姓主观上难以接受。其次,各级侦查机关长期以来备受打击罪犯和保障人权的双重压力,这两个要求和标准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孰轻孰重,较难权衡利弊。再次,检察机关据以博弈的案件信息不充分。也就是说,检察机关单独发现非法证据的能力并不充足,单靠书面审查有时候难以发现可靠的证据,即使检察机关可以依法询问嫌疑人,也由于证据的缺失而不能判定真伪。最后,检察机关由于在书面审查中难以发现非法证据,进入法院审判阶段时,受考核指标的制约,对于非法证据也只能硬着头皮坚持,和公安机关站在了同一战壕。正因如此,很多冤案错案一旦进入某种追诉的轨道,就会像高空的自由落体运动那样难以逆转。
由此可见,证据的难以发现和检察机关的动力不足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所幸的是,新修改的《刑诉法》有以下重要修改:第一,规定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应当全程录音或者录像。第二,规定拘留后24小时内应当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讯问必须在看守所进行。第三,规定公安机关对危害国家安全等严重犯罪案件可以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秘密侦查、控制下交付等特殊侦查手段;检察院对重大的贪污、贿赂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可以使用技术侦查措施;对上述侦查手段的适用期限、审批手续、侦查机关的保密义务以及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等内容作了严格规定。以上规定主要通过保留证据来规制侦查机关的行为,在侦查人员头上时刻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这对侦查人员无疑具有一定的威慑作用。
(三)律师提前介入的博弈分析
新修改的刑诉法关于律师介入的规定作了如下修改:第一,明确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身份。第二,扩大法律援助范围。适用阶段由审判延伸至侦查、起诉;应当指定法律援助的案件从死刑扩展到无期徒刑;对于因经济困难等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经申请符合条件的,也应当提供法律援助。第三,完善会见制度。除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恐怖活动犯罪案件、重大贿赂犯罪的共同犯罪案件外,辩护律师凭“三证”即可会见;会见时不被监听。第四,完善阅卷权。辩护律师自审查起诉之时起,可以查阅、摘抄和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同时规定辩护人收集的有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公安机关和检察院。第五,完善申请调查取证权。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过程中公安机关、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可以申请调取。
笔者认为,律师的提前介入是《刑诉法》修改中最大的亮点之一。律师的提前介入比较符合博弈论的原理,可以解决检察机关因为监督收益不大而造成的动力缺乏,还可以减少检察机关侦查监督信息来源不足的问题,提前介入案件的辩护律师更是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进行监督的重要力量。首先,律师提前介入可以增强侦查监督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监督实效,是侦查监督机关提升监督实效的有力手段。因为律师提前介入可以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全程监督,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全过程中,既是参与者也是重要的监督者。监督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违法是律师的权利也是基于当事人委托而来的职责。新刑诉法第47条规定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有权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其次,就侦查监督博弈过程而言,律师也是侦查监督机关监督信息来源的提供者。因为辩护律师最容易直接了解业已存在的公安机关违法办案的信息,其提供的信息来源有利于监督机关发现问题和线索,能够减少侦查监督的成本。再者,律师还是侦查监督机关监督实效的见证者。因为,辩护律师为当事人行驶权利救济一般也只能通过监督机关的公权力运行才能实现其效果,律师是见证侦查监督机关保障当事人合法权利的重要参与者。之所以辩护律师可以作为侦查监督的博弈重要角色参与侦查监督活动,在于律师代表当事人一方参与博弈不会存在动力不足的问题。在侦查阶段提前介入还可以及时告知当事人应注意自己在侦查活动中有哪些合法权益,这样可以防止当事人合法权益遭受损害时而浑然不觉的现象发生。辩护律师也可以在当事人可能遭受刑讯逼供、诱供时及时了解情况,保存相关证据,并代理当事人向有关机关申诉、控告。但是,律师提前介入在目前最大的问题仍在于证据的收集上,因为即使新刑诉法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就可以行使辩护权,但是,现实中,等到律师会见到当事人时可能已经为时已晚,即使存在刑讯逼供的证据也可能因为同步录音录像不到位而证据灭失。纵然侦查监督机关加大监督力度,可辩护律师缺乏信息来源,仍就不利于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笔者认为,为了使律师能及时掌握情况,可以设置一种当事人能申请即时会见律师的制度,这样在当事人遭受非法取证时,可以及时联系其律师,不至于使证据灭失。当然,律师提前介入还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即律师在中国现阶段的地位不高,有时候即使提出了有利于当事人的观点,仍然可以被司法机关简单、武断地否决。要解决这一问题,尚需时日。
[1]丁社教.法治博弈分析导论[M].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4.
[2]苏力.送法下乡[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02.
[3]盛洪.为什么人们会选择对自己不利的制度安排[M]//现代制度经济学(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93.
[4]道格拉斯·G·拜尔,罗伯特·H·格特纳,兰德尔·C·皮克.法律的博弈分析[M].严旭阳,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5]陈云龙,彭志刚.检察机关侦查指引权及其实现机制[J].中国刑事法律杂志,2009(9):64-71.
Game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Prosecutorial Supervision of Non-self-investigation Cases
PENG Zhigang
(Institute of Law,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89,P.R.China)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prosecutorial organs supervise investigative organs'exercise of investigative rights,which should not only fix the weakness in supervision resulting from the opposition from investigative organs and lack of inner motivation as well,but also improve the lack of efficacy in supervision because of unsmooth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A thorough analysis with the game theory may better deal wit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upervisor and the supervisee.Bringing in the third party, that is, parties involved and other litigation participants in specific cases may realize the maximum benefits for both game players and maximize the efficacy of supervision.
supervision of investigation;game theory;analysis
D916.3
A
1008-5831(2013)02-0103-06
2012-10-23
彭志刚(1966-),男,江西九江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博士后,教授,主要从事刑法、知识产权法、检察学研究。
(责任编辑 胡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