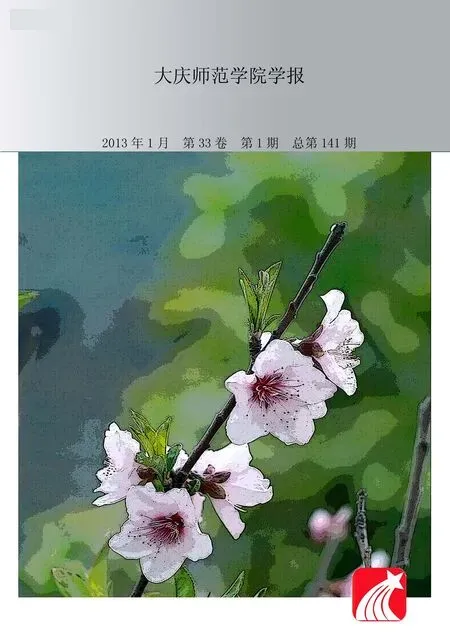论土家族作家蔡测海小说《非常良民陈次包》的语言艺术
胡用琼
(湖北工程学院 文学院,湖北 孝感 432000)
一
初读蔡测海的《非常良民陈次包》,觉得生涩难懂,不知所指。作家对三川半众生相生存状况的描摹,借助于语言文字的寓意象征和魔幻组合,借助于民间语言对历史和文明进行边缘化解构,表层的文字含义并非作者意图所指,作者的企向是需要打破常规的阅读,深入表层文字背后的隐藏义,这是作者一贯追求自己说话的独特方式。
正如作者曾经说过的这样一段话:
语言像阳光一样,让事物显影,让事物有色、有声,语言给事物以生命。阳光不会让一块石头发芽,语言能让一块石头成为语言的石头。阳光照不到的地方,于是长满青苔;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语言说它是阴影。人不可及,语言可及,于是有了诗歌、戏剧、小说,还有一种特别的文体———散文。语言同人的关系,如鱼跟水的关系,语言之水无始无终,鱼生于水,人生于语言。生,或者死。[1]
所以在自我呈现的欲望小说中,语言一直是作为叙述的材料,作为讲述的媒介存在和发挥其作用的。小说语言的个性化,尤其是1985年以后,在关注小说形式的实验探索中,对于语言个性的追求也逐渐成为小说家们的自觉意识,追求文学语言的艺术化、个性化、甚至超常性,逐渐成为创作的风尚,并且作为有意识地追求。蔡测海自己也多次表明他的写作经历,是语言的长途跋涉,他把小说中的语言作为自己的一种语言意识,一种自觉的审美追求。他的小说是其语言的实验,抒发的是对土家族生存状况的诗意再现。他以自己的语言方式解构庙堂话语,他的诗情的语言改变了小说语言严格的行军,语言不再是一个指向意义的所指,而是从惯常的组合中解放出来,用自己民族喜闻乐见的语言习惯表现出来,与庙堂期许的间隙拉开了语言的张力。这缘于作者始终把目光聚焦在自己熟悉的那片土地上。作者笔下的人物处于“边缘人“的处境,他们有望成为民间的社会精英,有能力进入基层权利中心,但他们对基层行政行为的不满,甚至感到与自己的人格操守相抵触,因而自觉或被动地游离于话语中心之外,以他们诙谐的方式生活着,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抵抗权威。如兽医站长给畜生屁股上画红以收取贿赂,陈次包乘着夜黑给全村的畜生的屁股上都画了红。憨老则画了一副猪头猴脸的动物给兽医站长,兽医站长看了很高兴,以为憨老顺了他的意思。他们以这种揶揄的方式对抗基层的权威。他们的语言和行动一样无不具有调侃性。如陈次包说的一段话:
刁民是骨头,良民是肥肉,干部是瘦肉,坏人是屎,我要当良民,我不要变成屎。……干部叫浩杆子,本来也是个良民,往上生了一节,就成了干部。[2]1
在这种简单而贴切的理解话语中表征着农民的实际的思维方式,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解构人们心中语义。他们对事物的认识都是以身边切身感受到的东西为基础,如陈次包对人的认识:
粪臭,可以做肥料,人臭就什么也不是了。体面人臭点没关系,他面子上还体面,好比马粪,面子光亮里面是糠,起码也是马粪。粪也分等级,有贵粪贱粪。一个人又穷又臭是贱粪,菩萨抱的娃比爹娘生的娃值钱。[2]23
作者笔下的语词指向现实很平常的东西,但寄予了主体的象征或隐喻意向,它们从浅层表意功能中滑脱,包孕了一种特有的意义。作者这样的语言填满了他的小说空间,表现了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特色。作者笔下的人物也常常处于边缘落后的文化环境中,他们对事物有着自己的理解方式,即一种民间的理解方式,他们常常以地方性知识来解构社会话语中心。房德里耶斯说:“语言是最好不过的社会事实,社会接触的结果。它变成了联系社会的一种最强有力的纽带,它的发展就是由于社会集体的存在。”[3]小说中三川半人们以他们的语言特色和语言习惯表明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如三川半管美元叫美国人民币,银行的人多次纠正了这种说法,美元可以叫美金,不叫美国人民币,美国只有纳税人。而陈次包们仍按照自己的语言习惯称呼游离于三川半的事物,因为这些东西不象牲畜那样为他们所熟知,他们喜欢以自己的逻辑来审视他们陌生的东西,把英国钱叫英金,越南钱叫越金。为什么可以叫美金呢?因为它合乎人们正统习惯,而三川半的陈次包们无视这种社会规范,其实也反映了边缘化的民族地方性知识对于正统话语的抵触。一般说来,民间代表感性的因素,主流文化意识形态代表理性因素,民间语言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他们的语言有他们自己的语义符码,无法用我们通常的分析方法来分析,他们拥有自由自在的解构语言的能力,具有丰富的内涵。我们知道严肃文学即庙堂文学的人物语言表征着某种权利和主流,他们是社会中大众的代言人。而在蔡测海笔下三川半的人们生活在社会底层,他们如同生活在大杂烩中,其语言丰富多彩,虽然这些语言杂沓相陈,但是它是对民间自在状态的发掘,用“乡土”的、“民族”的这一有意味的形式表现民间精神,来表明他们存在的合理性。
二
小说《非常良民陈次包》除了以地方话语来解构庙堂话语以外,作者笔下小人物的话语还闪现着智慧的光芒,以自己浅显的道理来解构很深奥的哲理,用特有的说话方式表现出来。他笔下陈次包和三川半的人们很少甚至没有离开过三川半,所以他们的视野只局限在巴掌大的三川半的地方,他们用自己的体验来传达他们的经验,抽象和具象用三川半的话语缀连在一起,作者往往在传达一个故事的同时更让你感到三川半的人生经验。如小说中被兽医站长阉割,老王担忧乡长陈化走了以后三川半的人再被阉割而一夜未眠,他痛苦地思考,觉得唯一的办法就是要选一个老实人,但老实人是什么呢?小说中这样写老王眼中的老实人:
老实人是什么?就是办事实实在在的人。老实人还有一些解释,这个人很老实,就是老实牛的意思,很驯良,不咬人的,没怎么长牙齿,怯懦的样子,一个弱势者,这样的人成为大多数人的选择标准。这样的人,好心。[4]151
老王眼中的老实人其实统一了三川半对老实人的认识,他们从历史经验中得出一个答案,三川半需要一个老实人,道理很简单,弱者必定是善者,不做恶事,他要恶起来也是善的。
三川半对事物的理解很朴实,他们用自己的语言诠释着和消解着对人的定义。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借助于一定的语言来表现,而每一种语言现象都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和社会背景之下产生的。就象三川半人对老实人的定义是从他们与干部的接触中用自己的体验来定义的,消解着庙堂文学的含义,但却更真实地体现了他们心中的价值观,诠释和体现着这个社会的文化精神 ,而且他们以所在环境的体验参与着这个区域文化的建构,塑造着土家族的语言群体或个体的文化心理。作者在《语言如此灿烂》里说:
在民间,语言永远是鲜活的。如果我不那么傻,象一个民间艺人那样写小说,象一棵树那样拥有生命,象树开放花朵一样说话,给自己加上诚实的、趣味的、意味的定语,我也能把话说好,而不失语言的灿烂 ![1]
作者从他创作伊始就一直在找他语言的表达方式,正如他自己所说:
我的写作经历,是语言的长途跋涉,我一直想找到自己的说话方式,我怎样说话?说什么?我想有我说话的份儿。事物的趣味、意味,让人产生说话的欲望。[1]
从他早期的作品我们也可以感到作者笔下语言的智慧,但我们更强烈地感到作者所要表达的是他以及他自己所属的民族在时代的强烈碰撞中要求出走的主题。而到了《非常良民陈次包》这里,可以明显地察觉作者打破了他以往一以贯之的叙事模式,更多的是关注自己脚下的土地和自己所属民族的丰富多彩的语言现象。在作者这儿语言不再被动地作为讲述故事的语义符码,而是再现了一个特定民族在某种社会下的文化现象。作者把三川半人独特的说话方式裸呈出来:
三川半人说话单音节多,比方说,吃、去、来、死、狠、坏、香、热、冷……等等。三川半人的话就象河里的石头,被流水洗练成圆而光滑的卵石,生活打磨了语言,不需要多少废话。有人苦不堪言,就问:苦?回答说:苦!有人疼痛难忍,就问:痛?回答说:痛!一切都还过得去,就问:好?回答说:好!一切都这样表达得明明白白。多说就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找话了。[4]149
这就表征小说的取向并不是向读者展示故事,而是展示小说语言的价值,一种三川半独特的说话方式。他们的语言是经过生活打磨的语言,充满了乡民的泥土味,也表明了他们率真而讲求实用的语言。彼得·特鲁基尔认为:“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与社会结构和社会的价值系统紧密联系在一起 的。”[5]三川半人运用单音节字来进行日常交流,已经形成一种习惯,这是与农民简单、干脆、直接、率真的个性联系在一起,是他们价值观的体现,这种来自底层民众的语言是庙堂文学的语言无法企及的。他们贴近生活,不需要矫饰,用最少的语言传达最真挚的情感。作者把这种再现本民族地区的语言作为他主观的自觉意识。
语言是人们感受社会、体察人生、理解世界的一种形式 ,作家深刻挖掘和着力去展示出这种特性的作家并非普遍 ,蔡测海的小说让我们清晰地感觉到了他对语言这种潜在力量的认识和准确把握。他小说的语言彰显自身的欲望和张力比彰显对象更为自觉和强烈。它让读者感觉到,作者或者作品中的主人翁们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是怎么做、怎么说的。而这也许正是蔡测海小说语言耐人寻味的原因。例如陈次包以捡粪为职业,常常对畜生胡言乱语,作者着重表现了他说话的方式,他往往顾左右而言它,讲究说话的策略。例如陈次包和兽医站长在赌场上肉食较量:
兽医站长抓了一根鸡骨头递给陈次包,陈次包从兽医站长手里接过鸡骨头,放在嘴里咂咂,说,酒吃人情人吃味,这肉味正是贴着这一层,好多人不知道这一层扔了让狗吃,那狗胡乱吃了也不知肉味,不是可惜!牲口贩子扑哧一笑,送给陈次包一块鸡脯。陈次包撕着吃了,抹一抹嘴,这么好的东西让我吃,吃进去上好的好香拉出来的好臭!真是糟蹋!
表面语义上陈次包说着吃食的问题,但我们只要把牲口贩子的所作所为联系起来,实际上陈次包在借题发挥,把这帮在三川半干尽坏事的人臭骂了一顿。狗正是他们的真实写照,对上摇尾乞怜,对下象畜生一样毫无人性。作者用形象的鸡骨头、鸡脯、狗等经验性的语词表明了官和民的游离,通过贴切的语言向人们展示出陈次包的深沉感悟,作者把陈次包观察和体味到的现实转化成一种经验性的语言,而这种转化正是作者的个性化语言。
三
小说的语言还可以消解传统的叙事结构,作者把中心放在语言的叙述技巧上,通过语言的跳越或延伸来推动情节的发展。蔡测海的小说《非常良民陈次包》打破了传统的叙述结构,以`散点透视法铺陈小说情节,这正好可以给他任意挥洒语言提供了自由的空间。全篇一共有58节类似于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人物和事件。蔡测海用一种轻描淡写的陈述,将人与人平行交错,事与事平行排列,在这些平行结构中可以感到作者的语言不受时间和空间的约束,作者在没有时间和空间关系的约束下可以让语言自由行走。如小说第11节写牲口贩子出去跑了一趟广州戴了一副眼镜揣了一个博士证回到三川半,而在第12节马上笔锋一转写憨老考上音乐学院误车骂了自己我是猪回到了三川半,第13节又另起炉灶介绍水生背猪的苦难。小说《非常良民陈次包》全篇都是这样跳宕叙事的。尽管这样,读者仍可以从作者叙述语言中察觉前后关联。
对一个小说家来说,选择一种适合自己的语言方式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它不仅分配着读者的注意,还决定着一部作品的生命价值。蔡测海显然找到了能够适合自己的说话方式。他的小说《非常良民陈次包》的语言消解着庙堂文学所谓的“高雅性”的光环,他将他获得的所有生活体验铸入进一种平淡无奇的语言形式当中。然而作者在消解语言高雅性的同时,由于驾驭不熟练往往走向另一个极端。《非常良民陈次包》体现了作者地地道道的民族语言和思维方式,为了追求尽可能显真的艺术效果,作者在小说里渗进大量的未加工的下层语言如:第14节作者把陈次包和翠花的私房话露骨的表现出来,象牛卵子,狗日的、屁眼等粗语随处可见。我们提倡文学还原生活的本来面目,但并不是为了使作品贴近生活而照相式地搬用语言,那种完全照搬生活中的鄙俗语言表达了粗鲁的情感。所以作者过于还原语言的本真化的同时相对削弱了作品的文学性。这是《非常良民陈次包》里语言表达的一个缺陷。但是瑕不掩玉,这部长篇小说的语言体现了作者朴实、智慧、哲理化的语言审美追求,用民间灿烂的日常语言表达民族文化心理和情感。
[参考文献]
[1] 蔡测海.语言如此灿烂[N].中国邮政报,2004-05-15.
[2] 蔡测海.非常良民陈次包[M].1版.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 .
[3] 约瑟夫房德里耶斯.语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14.
[4] 蔡测海.非常良民陈次包[J].大家,2004(2).
[5] 彼得·特鲁基尔.社会语言学[M].谭志明,肖孝全,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