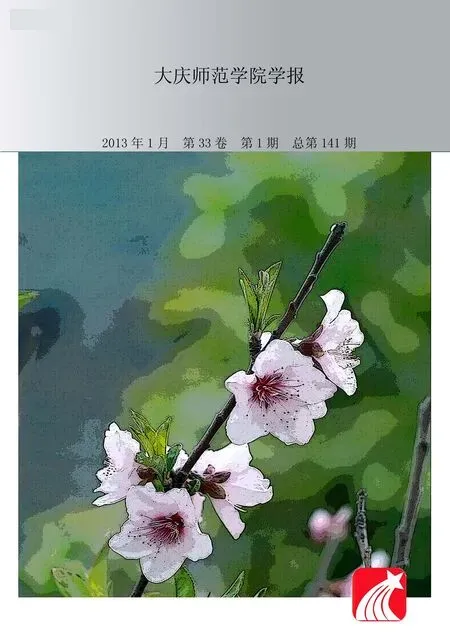反叛的维度
——论余华小说《鲜血梅花》的反形而上学特征
张宇宁
(大庆师范学院 文学院,黑龙江 大庆163712;)
余华发表于1980年代的中篇小说《鲜血梅花》曾一度引发学术界的热议,研究者对其思想主旨的描述,包括“寻找”说、复仇说、荒谬说以及戏仿说、解构说等多种论断,而鲁迅的《铸剑》、汪曾祺的《复仇》乃至于加缪的《局外人》等经典文本则成为研究过程的参照物。此外,写作于《鲜血梅花》同时期或稍晚的余华作品,也被当成研究这一作品的佐证材料。当然,这种“互文”式的阅读方法能够最直接、最有效地“发现”文本的思想特征,因为对比既可以看见差异,也能够找到联系。但是,由对比得出的结论真的能够切近文本的本质吗?在对比中原文本的地位(比照引入文本)必然会根据研究视角的变化而发生主/客体转换的现象,这样一来,对丧失了主体地位的原文本的研究活动所生产的学术话语,是否依然是从原文本出发的话语呢?基于上述思考,我认为有必要回到《鲜血梅花》这部小说本身最为根本的细枝末节,重新审视这个已经逐渐淡出我们视线的先锋文本。
一、“隐”的意义:反传统的观念与手段
从整体来看,《鲜血梅花》是一篇“残缺不全”的武侠小说。所谓残缺,主要表现在,作为主人公阮海阔的仇人——杀死阮进武的凶手,始终没有真正出场。在刚刚踏上寻仇之路的时候,阮海阔并不知道自己的仇人是谁,他所掌握的线索只有他母亲的提示:去找青云道长和白雨潇,“他们中间任何一个都会告诉阮海阔杀父仇人是谁”。故事的全部内容都是围绕着主人公对这两个人的寻找,或者说对仇人的身份的调察展开的。直到小说结尾,白雨潇才说出了真相:
你的杀父仇敌是两个人。一个叫刘天,一个叫李东。他们三年前在去华山的路上,分别死在胭脂女和黑针大侠之手。
梳理主人公的整个寻仇过程我们发现,他所要找的“仇人”从来就不曾出场,他(们)的存在一直处于“隐”的状态。那么,我们就有必要思考这样的“隐”究竟意味着什么。
形而上学哲学看重在场,认为“形而上学是存在者的存在的理论,这个存在是作为‘在场性’不断在这个方面被理解的”[1]。这一观念的根源在于,从古希腊的巴门尼德开始,形而上学便始终坚信,只有“在场”才能把握存在的意义。“在场”也就是“显”,与上文提到的“隐”相对立。按照形而上学的观点思考下去,如果“在场”产生意义,那么“不在”,或者说是“隐”就不具有意义。无疑,这样的推论是不可辩驳的。但问题是,上文所说的“在场”仅仅是形而上学框架内的认识论概念,在这个框架中,它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但如果换一种理论或哲学思想重新审视这个语词,其价值与地位便可能发生变化。当代西方哲学最根本的特征就是反对作为其社会思想观念之主宰而存在的形而上学,比如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他就是一位最为坚决的反“在场形而上学”者。在对德里达的著述加以阐释时,有学者指出,在德里达那里,“‘在场’和‘缺失’有特殊的含义:前者是‘白色的神话’(或形而上学),如果说它‘在场’,它只是白色的;后者是‘白色的神话’没有说到的,故曰‘缺失’或‘痕迹’,我又称之为‘隐’。”[2]需要说明的是,在德里达的观念中,“白色的神话”或形而上学意味着虚假性,他认为更为实在的则是“痕迹”或者是“隐”,其“踪迹”理论明确提出,在场只是痕迹化的效果。
基于上述理论,我们有理由认为,小说中“隐”——也就是阮海阔的仇人没有出场这一叙事模式,实际上向传统的小说创作方法提出了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即小说中的人物一定要具备性格特征吗?在当代文学话语中,一直被我们奉为圭臬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其基本要求之一是追求文本具有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似真性。这也就是要求,对于小说中涉及的人物,应当通过形象化的处理,也就是具有一定的性格特征使其达到“实体化”效果。因为在我们的观念中,“实”是“真”的基础。在《鲜血梅花》中,仇人不出场所导致的后果是,“仇人”二字成为一个独立能指,它的背后并不存在任何形象或观念,也就是说,这样的人物没有达到实体化而只具备符号性。关于符号的本质,也就是德里达所说的“痕迹”或是“踪迹”,“一个关于某种东西的符号必定意味着那个东西的不在场”[3]。由此,余华通过小说文本中为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创作论层面的秘密:现实主义所追求的似真性要求人物形象所具备的“实体性”不过是另一种“白色的神话”,在打破了“在场”的神话以后,文本中的人物可以是不具任何性格特征的文字符号。进一步讲,刘天和李东的“隐”意味着文本在思想层面蕴含着对形而上学所强调的“在场性”的质疑。
二、替补的根源:女性气质的揭示
余华的《鲜血梅花》表面上讲述的是主人公为父寻仇的故事,但不同于传统武侠小说,主人公自始至终都身无武功,所以,“寻找杀父仇人”这个命题在他那里则转换成了“寻找自己如何去死”。然而,就在他对杀死父亲的武林高手进行追寻的过程中,另外两个武林人物分别杀死他的仇人。在这里,复仇的动作被他人“代劳”了,这样的“代劳”无疑是一种“替补”行为。小说中阮海阔最终没有完成手刃仇人这一高难度动作,这样一来,他存在的价值便因为他人的“替补”而显得可疑。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是,文本中关于替补的叙述究竟隐含着什么,这样的替补对主人公的意义又是什么?
众所周知,“替补”理论是法国哲学家德里达解构主义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论文字学》等著作中德里达针对卢梭关于“语言是讲述的,文字仅是语言的补充”的观点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批判与改造,并由此打造出一套别具一格的“替补”理论。他认为,如果说“文字”是“语言”的补充,那么这必然说明文字本身是不完备的,是需要补充的。也就是说,语言必然有所“欠缺”,而文字则能够弥补这种“欠缺”。按照这个逻辑理解《鲜血梅花》中的替补叙述,我们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复仇活动中,复仇者是有所欠缺的,而这一欠缺正是一般意义上的复仇者自身所必备的复仇条件——武功。这个必备因素或者说关键因素的缺失,让小说中的主人公成为“江湖”中的无能者,而这样无可挽救的“无能”又暴露了这一男性形象身上所具有的女性气质。如果说男性气质意味着积极的、主宰的、理性的,那么阮海阔的性格特征则恰恰与之相反。首先,他的寻找行为——包括寻仇与寻人都是消极的,前者源于遵从母亲之命,后者则是受人所托。其次,他在整个故事中存在的状态一直都是被动以及顺从的,一方面,他从未拒绝他人——包括母亲、胭脂女以及黑针大侠的请求,另一方面,在青云道长拒绝回答他的第三个问题时,他并未作出驳斥性的质疑或者进一步的追问。再次,阮海阔不理性的表现在小说中比比皆是,如:
出现了这样一个事实,他并没有按照自己事前设计的那样一直往前,而是在十字路口处往右走上了那条指示着荒凉的大道。
显然,“事前设计”是理性范畴中的“筹划”,而他偏离了“筹划”,也就偏离了理性。再如:
阮海阔在离开黑针大侠茅屋约十来天后,一种奇怪的感觉使他隐约感到自己正离胭脂女越来越近。事实上他已不由自主地走上了那条指示着荒凉的大道。他在无知的行走中与黑针大侠重新相遇以后,依然是无知的行走使他接近了胭脂女。
在上述文字中,我们看到了阮海阔身上所具有的类似于第六感的神秘素质,而这与理性框架中的可知论南辕北辙。
弗洛伊德主义者荣格认为,“人类有两个最基本的原始模型即阿尼玛(Anima)和阿尼姆斯(Animus)。阿尼玛是男人的灵魂,它是男性的女性特征,是男性无意识中的女性补偿因素;而阿尼姆斯是指女性的男性特征,女人也具有潜在的男性本质,也就是说每个人的心灵中都有王子和公主的原型”[4]。基于此,我们有理由认为,阮海阔身上具有女性气质是可能的,而小说中关于替补的叙述有效地揭示了他的这一特征。众所周知,形而上学麾下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原则是通过设立二元对立来确定对立项之间的等级关系,如在美/丑、男/女、文明/野蛮这样的二元结构中,前者先验的处于优势地位。“替补”理论则通过拆解上述二元结构的等级关系来攻击并最终颠覆了逻各斯法则。就像上文所说的,语言因为欠缺所以需要文字来补充,那么小说中“无能”的阮海阔借助女性气质的补充才得以行走于江湖,而不是死于非命。可见,阮海阔这一形象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他的性格特征有效悬置了形而上学观念中的男/女二元等级关系,将“阴柔”因素填塞进貌似“阳刚”的江湖之中。此外,这种将传统的“英雄神话”篡改为一个“双重人格”者的流浪之旅的情节设置,使小说彻底脱开了武侠叙事的窠臼。
三、寻找的真相:放弃主体地位的虚无状态
推动《鲜血梅花》故事情节发展的根本动力便是寻找,这包括寻仇与寻人。表面上,阮海阔是上述两个寻找行为的主体,就是说他是在主动地“找”。但进一步理解小说文本,我们会发现不一样的情况。
作为寻找行为的“施动者”,阮海阔的主体地位是可疑的。作为形而上学理论的重要范畴,主体的概念一般被表述为:“同活动对象即客体相对的哲学范畴,主体是活动的发出者、承担者和执行者”[5]。那么无论是将寻仇还是寻人看成是一项“活动”,从严格意义上来讲,阮海阔都不能说是“活动的发出者”。寻人的情况比较容易理解,阮海阔的这一行为发生的原因是受人之托,并不是他要找到那两个人,他的根本目的在于帮助别人。既然他寻找的动机是帮忙,那么毫无疑问,他并非寻找活动的发出者。再看寻仇,按照传统的道德伦理来看,“杀父”与“为父报仇”之间的逻辑关系似乎是不证自明的,而且,这样的因果结构曾被各个时期、民族的作家所反复展现。以此为依据断定阮海阔便是寻仇“活动的发出者”,表面上好像说得通,但实际上我们忽略了这个逻辑的前提——传统的道德伦理的合理性和有效性问题。众所周知,为父报仇的根源在于儒家“尽孝”的思想,这一伦理观念将父/子之间设定为一对异形同质的一体化结构。就是说,父亲赋予儿子以生命和“血统”,儿子则是父亲生命的延续。但是,弗洛伊德主义的引进有效地颠覆了这种颇具温情的伦理关系想象,弗洛伊德呈现的俄狄浦斯情结、拉康关于父法的描述,都毫不客气地撕去了附着在我们传统文化脸上的“画皮”。新的伦理观念将父/子设置成相互对立的二元,其矛盾之深几乎不可调和。回到小说,有学者敏锐地指出,阮海阔的复仇过程事实上是“复仇者潜意识里在逃避复仇责任”的行为[6]。既然是逃避,那么就与上述提到的主体是活动的“承担者和执行者”相互矛盾,也就是说,从寻仇角度来看,阮海阔依然不具有主体地位。
小说中丧失了主体地位的阮海阔,其存在的意义也随之丧失了。那么应当如何看待这种没有意义的存在?萨特的哲学命题之一是存在先于本质,所谓本质指的是为“存在者”预设的意义。上文提及有学者将阮海阔的身份定位为“复仇者”,这一定位就是含有“预设”的意味,以此为前提才能够推导出阮海阔存在的意义就是为父报仇。诚然,主人公自始至终都戴着“复仇者”的面具,但推敲他的寻仇之旅不难发现,那是一个不断使其自身“虚无化”的过程,也就是成为其所“不是”的过程。小说第一节的结尾的那段文字似乎明确了他的复仇者身份:
没有半点武艺的阮海阔,肩背名扬天下的梅花剑,去寻找十五年前的杀父仇人。
值得注意的是,余华有意无意地强调阮海阔“没有半点武艺”,这就预示着复仇很可能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也点明了主人公“虚无化”的根源。在此后的寻仇过程中,阮海阔不断偏离自己预设的道路,一次又一次与真相擦肩而过,而在结尾,他以回忆的方式总结了整个寻仇之旅:
那个遥远的傍晚他如何莫·名·其·妙·地走上了那条通往胭脂女的荒凉大道,以及后来在那个黎明之前他神秘地醒来,再度违背自己的意愿而走近了黑针大侠。他与白雨潇初次相遇在那条滚滚而去的江边,却又神秘地错开……后来他那漫无目标的漫游,竟迅速地将他带到了黑针大侠的村口和胭脂女的花草旁。
上述文字有两个方面值得思考:一是在整个复仇之旅中,阮海阔竟然将大部分精力放在了为别人找人这件事上,复仇反而退居其次,这一点在他遇见青云道长时提问的顺序这一细节中得到了进一步证明;二是上文加上着重号的部分,即“莫名其妙”等词语,表面上似乎可以解释主人公延误复仇时间的原因,但实际上这些散发着“宿命论”气息的文字不可避免地让我们读解为主人公为自己逃避“应尽”的责任而制造的借口。如此看来,阮海阔的寻找活动其实是背离生命的预设意义的虚无化过程,这种虚无化的结果是,“没有半点武艺”的他,最终在充斥着血雨腥风的江湖中活了下来。
作为先锋小说的代表,《鲜血梅花》处处暗藏着离经叛道的动机,这样的动机表现了作家余华在写作中创新求变的欲望和勇气。海德格尔说过:“革命者的本质并不在于实施突变本身,而在于把突变所包含的决定性和特殊性因素显现出来。”[7]作为一个思想上的“先锋”或者“革命者”,余华借小说《鲜血梅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由形而上学向后形而上学“突变”的形象化依据,这既代表了先锋作家的思想特征,也证明了文学写作的一种可能性。
[1]H·博德尔.在场的特权[J].世界哲学,2006(1):13.
[2]尚杰.归隐之路[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8:198.
[3]俞吾金,等.现代西方哲学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405.
[4]蔡芳,谢葆辉.从《奥兰多》感悟伍尔夫小说创作的文脉:双性同体观[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12):32.
[5]李淮春.马克思主义哲学全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215.
[6]何小勇.非典型复仇——试析汪曾祺的《复仇》与余华的《鲜血梅花》[J].名作欣赏,2006(1):58.
[7]于丽娅·克里斯蒂娃.反抗的未来[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