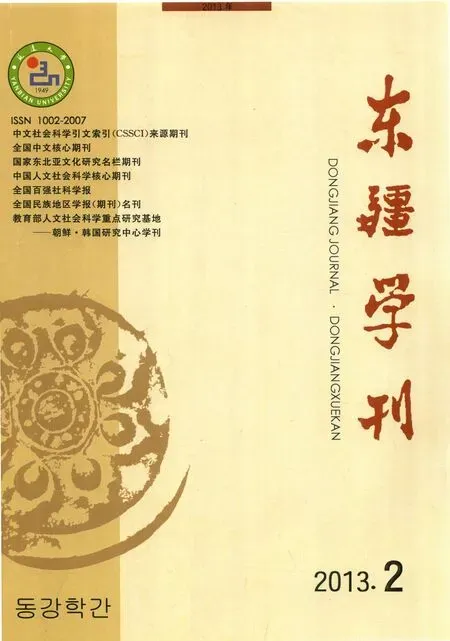朝鲜通信使眼中的日本器物形象
朴在玉,徐东日
一
日本与朝鲜半岛隔海相望,因而长期以来,两国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贸易关系。在朝鲜朝,随着大量的日本商品流入朝鲜半岛,品种多样、器物精良的日本形象也深深印进朝鲜人的脑海之中。从朝鲜通信使笔下描述的日本方物的品种数量来说,朝鲜朝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时代。譬如,日本的马、剑、腰刀、玛瑙、水晶、金银、金银粉匣、象牙、生红铜、牛皮、降香、木香、速香、丁香、檀香、苏木、乌木、硫黄等。从以上方物可以看出,日本器物主要是各类制品,即,武器类和工艺品类。其中,硫黄、木材、牛皮等是日本传统的原材料物品。除了这些传统原材料物品之外,日本的物品几乎都是制品。这些制品有两个特点:一是需要工艺技术,另一是与金玉相关。
前者与器物精良的日本形象相关。器物精良的形象使朝鲜人一直认为日本有很多能工巧匠,能够制造出精美的东西。资源匮乏、空间狭窄、景色秀丽、四季变化的东瀛岛国,本来就是一个能够培养能工巧匠的天然场所,由这样的文化风土产生出对技术的崇拜之心是非常自然的。唯有精湛的技术,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节省资源,对于日本这样一个岛国,这不啻是生存的法宝。[1](113~114)
后者与金玉之国的日本形象有关。金玉之国的形象与东海神山想像相关,同时也与日本僧侣的绘画相关。日本的绘画多用金碧,这使朝鲜人看到之后也会产生日本富有金玉的想像。
铜之白者,谓之白铜,我之所无也,多取北京而用之。今见日本所产,光泽俱胜于北京来者。[2](卷三,物产二十六则)
陆奥,产黄金;石见,出白银;播摩之铜,血殷红。[2](卷三,物产二十六则)
古代朝鲜与中国的诗文当中经常出现珠宝之国的日本形象。日本是珠宝之国,遍地都是珠宝,而珊瑚、松根、琥珀等却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无人珍视它们,这是何等富庶的景象。在此之前,只在道教仙境中出现过遍地金银白玉的人间天堂景象,而这种想象终于也落实到了日本形象上。不少诗歌描绘过日本海商的富有,但还没有把富有的形象扩展为日本的集体形象。从珠宝之国到富裕之国,是合乎情理的形象演变。日本被古代朝鲜人想象为珠宝金玉之国,但这只不过是想象的乌托邦而已,这种想象与日本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其实日本不生产黄金。为了迎合朝鲜人想像的日本形象,日本就选择了不少镶金嵌玉的制品。
二
日本文化器物中的人类形象是以日本人生产和工艺的水平为根据形成的。生产和工艺是人类智慧的产物,文化器物代表的技术也是日本民族文明的标志,对于文化器物的肯定就是人类化的表现。就具体的日本文化器物而言,有剑、马、纸、砚、漆器等物。“在百工皆善、器物皆精之中,显现出日本民族认真细致的性格特征。器物仅仅是器物,但器物精良与否,反映出了日本民族的民族性。急躁粗陋的民族不可能制造出精良的物品,而日本民族的性格也确实有细腻认真的特点,日本的器物正是这种民族性格的具体表现。[3](142)
(一 )剑
倭国器物皆巧绝,据说倭剑是以千年铁精铸造而成,它又埋于阴井多年。传说倭剑又分雌雄,剑上涂以人血,人见心悸。一旦佩戴倭剑,就勇武非凡,连鬼神都不敢靠近。
丰前之铁,雪色翻;萨摩之剑,锋利无比。[2](卷三,物产二十六则)
铁皆百炼。凡造器械,锋利且不计,才加拂拭,雪花模糊,眼看夺色,光辉射人。[2](卷三,物产二十六则)
日本曾是在东亚离中国文化最遥远的后进国家,在稻作技术、制铁技术传到日本之前,所有的周边国家都已具备了这两门技术。然而,日本的制铁技术有它的独特性,即专门以铁砂为原材料。日本与加拿大、新西兰并列为世界三大铁砂出产国,国内铁砂蕴藏丰富且易于开采,所以日本制铁业者对铁矿石完全不感兴趣。
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我们不应忽视铁砂所发挥的作用。日本的铁砂蕴藏丰富,用极小规模的原始设备就能进行精炼。在日本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经冲绳向中国出口的是日本刀、硫磺、马以及海带。日本刀确实是优质铁器,就连当时的基督教传教士也曾谈及其锐利程度。在丰臣秀吉征伐朝鲜时,作过俘虏的姜沆曾向朝鲜国王谏言,朝鲜刀与日本刀相比质量低劣毫无用处,应该尽快俘虏一名日本刀工让他为朝鲜制刀。进入元禄时代(1688~1704年)以后,日本的制铁工艺完全成熟。炉工们把木炭和铁砂交替投入制铁炉中,通过风箱持续送风,这样的工作持续3天在炉底才会出现铁钅母。3天后将炉敲碎取出铁钅母,再将它运送到邻近的大型轧铁厂。在那里有一个重约 300贯(1贯约合 3.75公斤)的巨大球形铜锤,通过水车的力量将这个铜锤吊到 10米左右落下轧碎铁钅母,通过观察铁钅母断裂处来判断它的质量。由此可见,铁钅母的质量并不完全相同,有些铁钅母直接可做钢材使用,有些则需要淬火敲打去除不纯物。用上述方法制造出来的钢材就是庖丁铁。
在西欧近代焦炭制铁技术出现之前,日本的铁比西方便宜,这一点在荷兰人的文献上已有所记载。用这些丰富而廉价的铁制成农具,降低了农田开垦的难度,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江户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建立在廉价铁基础之上的文化。
(二 )陶器
百工皆善,器物皆精显现出日本民族认真细致的性格形象。日本的这种民族性至今未变,因而日本制品大多质优形美。[3](142)这一点,集中体现在金世濂所记述的器皿上:
其器皿则常时皆用红黑漆木器及锱铁等器,至于土陶之器,涂以金银。其宴享皆有三五七之制,初进七器之盘,或鱼或菜,细切高积,如我国果盘;次进五器之盘;次进三器之盘,而取水鸟,存其毛羽,张其两翼,涂金于背,果实鱼肉,皆铺以金箔。献杯之床,必用剪彩花,或木刻造作,殆逼真形,此乃盛宴敬客之礼。而凡享客酒食,通谓之振舞矣。[4](430~431)
上文中提到的作为食物器皿主角的陶瓷器,其工艺水平是在朝鲜、中国的影响下得到提高的。最初是在公元 5世纪之前,朝鲜半岛过来的陶工带来了东亚大陆先进的烧制工艺,产生了日语称之为“须惠器”的一种新型陶器,它是一种将耐火度高的黏土用制陶用的旋转圆盘制作成型后,放入窑中经千度以上的高温烧制后做成的结构细密、质地坚硬的硬陶器具。唐代中国的三彩技术已传入日本,日本正式开始了铅釉陶器的生产,烧制出了光泽亮丽、色彩鲜艳的陶器。 16世纪末,丰臣秀吉出兵进攻朝鲜,强行带回一批陶工,其时中国的制瓷工艺早已传入朝鲜半岛。这些朝鲜陶工在日本的九州有田一带成功地烧制出瓷器,由此,日本的陶瓷器工艺不断突飞猛进。作为日本食器的瓷器,是一种细腻的瓷器,外形古拙,纹理清晰,其形状除圆形、椭圆形之外,还有叶片状、瓦块状、莲座状、瓜果状、舟船状,呈四方形、长方形、菱形、八角形。其色彩大多素雅、简洁,少精镂细雕,少浓艳鲜丽。
(三 )纸
在《海行总载》中,朝鲜通信使还多次写到了日本纸的质地:
美浓之纸 ,洁而韧。[2](卷三,物产二十六则)
纸有纹,无物不有,宜不借于江南,西蜀织造之局也。[2](卷三,物产二十六则)
纸,洁比于唐,韧较于我,此其所长。而近又一种西洋之纸,遍行其国,光滑夺目,浓厚如掌,而似纸非纸,还无足贵。以吾所见,不及其地之顶品也。[2](卷三 ,物产二十六则)
日本的纸光白而滑,以至于“非善书者不敢用”。《书法离钩》载:“纸有倭纸,出倭国,以蚕茧为之,细白光滑之甚。或云倭国无蚕,亦树肤也。”《格古要论》亦记载:“北纸用横帘造,纹必横,其质松而厚。南纸用竖帘,纹竖,若二王真迹多是会稽竖纹竹纸。唐有麻纸,其质厚。有硬黄纸,其质如浆,润泽莹滑,用以书经,故善书者多取其作字。今有二王真迹用硬黄纸者,皆唐人仿书也。五代有澄心堂纸,宋有观音纸,匹纸长三丈,有彩色粉笺,其质光滑,苏黄多用是作字。元亦有彩色粉笺,有蜡笺、彩色花笺、罗纹笺,皆出绍兴。有白纸、清江纸,观音纸出江西,赵松雪、库库子山、张伯雨、鲜于枢多用此纸。有倭纸,出倭国,以蚕茧为之,细白光滑之甚。”《格古要论》记载的是历史上有名的好纸,列举了著名文人书画所用的纸。倭纸亦被列入这些上等佳纸之中。
(四 )漆器
朝鲜通信使十分青睐倭漆器具,日本从文具到书房的家具都用倭漆器具。
余见倭人所用器皿百物,皆玄漆如鉴。宫室船板桥舆等处,亦皆施漆,漆光照耀,与我国所见判异。若专以漆木之液,而涂泽如此,则彼其庶民之家,一岁所用漆液,度不下数斗。而公侯贵人,当用十斛而不足。然所过闾里山野,亦未见漆林。心甚怪之,问于倭人。则曰:“青秭捣取汁贮之器,善藏于密,经年不变。日本漆法,先用秭汁而涂之,再三涂干,磨以彭叶。然后其光炯然,乃加漆液,所以漆小而色美”云云。其言又不可信。[5]([下 ],附闻见杂录)
方以智《通雅》记载:“漆皆出于日本。”但实际上,所谓的倭漆器具不一定都是日本原产,但油漆当初是由日本进口。倭漆器具颇受朝鲜人喜爱,除了文具之外,倭漆器具还成为收藏之物。
倭漆器具在明清文献中也频繁出现,这是因为,首先,倭漆是绝好的油漆。明代《天启宫词》记载:“上好弄油漆,凡所使器具,皆御用监内官监办。进作料,上手为之,成而喜,喜不久而弃,弃而又成,不厌也。宣庙青宫时,剔红填器俱,经裁定后厂制终不及前。倭漆中杂金屑,砂砂粒粒,光色莹然,亦为时所重。”倭漆不知何时传入中国,不过在明代倭漆为时重用,宫廷亦用倭漆。其次,倭漆工艺的仿造。倭漆器具在明人心目中是最佳器具。倭人漆器乃是天下的极品,明代亦有仿造。“仿制的倭漆器具几乎与倭国原产漆器仿佛,可见当时仿造技术已经很高。茶山描述道:日本的技术之所以如此发达,得益于日本人经常往来于日本与中国江浙一带,习得了其精妙的工艺。
漆器的餐具到了江户时代呈现出飞跃性的发展。其中一个比较显著的现象就是漆绘,主要是“莳绘”被普遍运用到了膳、碗、盆等食器上。“莳绘”是一种用漆描画出图案之后,再用金、银、锡等金属粉末黏上去磨制出来的图画,起源于奈良时代,在平安时代已有了相当的发展,到了室町时代诞生了为将军家服务的幸阿弥世家和五十岚世家两大几乎是世袭的画派,这两大“莳绘”的画派一直延续到了江户时代。将“莳绘”艺术大量运用到食器上来的,首先要推江户中期的尾形光琳。
(五 )纺织物
在《海行总载》中,朝鲜通信使对日本纺织业的描写尤多。他们写道:
绵布,摄津之产,而近又无处无之云。织造,一依西法 ,如所谓西洋布者。[2](卷三,物产二十六则)
又往纺绩所,而男女并集,亦以火轮弹绵成绪。凡造纸与纺绩,其巧其迅,难以形模。[6]([地 ]四月十七日戊申)
转往西阵织锦所小林绫造家,家主示一册子,粘各色锦片也。见织锦,而一机六人分坐机之上下左右,各成其工,一日才织三尺云。锦纹之浓彩,锦质之敦厚,始见于此。此为御用服。[6]([地 ]四月十七日戊申)
布帛之属,不可殚记。而赤地之锦,精好之织,今行初见。若其博物院及对马岛旧主家,所见片锦谱,凡各样锦缎,片割妆帖,谓之片锦谱。[2](卷三,物产二十六则)
在这里,作者毫无讳言地指出:日本人纺织的方法完全依照西方,“以火轮弹绵成绪”,其结果,“其巧其迅,难以形模。”而日本人的织锦,则是“一机六人分坐机之上下左右,各成其工。”作者对此不禁感喟道:“锦纹之浓彩,锦质之敦厚,始见于此。”在所有的锦缎中,最令朝鲜通信使们称道不已的还是赤地的锦缎,这是因为,“赤地之锦,精好之织,今行初见。”
不仅是对纺织,朝鲜通信使对日本的磁器、彩画、眼镜的制作也有所言及。他们不仅详细介绍了这些源于西方的各种器物的形状、大小、色彩,而且毫不隐讳地指出其“精巧出色”之处,以及给人“金碧眩目”的震撼力。但与此同时,丁若镛等人也不失时机地指出:日本的技术之所以如此发达,得益于日本人经常往来于日本与中国江浙一带,习得了其精妙的工艺。
(六 )其它器物
不仅陶瓷器是这样,在日本,以漆器为代表,瓷器、陶器、木器、竹器餐具材料多样、应有尽有,各自显示出不同的肌理和质感,适合于不同的季节、不同的食物和不同的场合;上面通常绘有风格淡雅的图案,拼合起来,又是一副美丽的绘画;种类也繁多,尤其是各种盛放佐料的盏盏碟碟。最使人心动的,是那种木碗,其花纹之精美自不待言,单就外观而言,那雍容大方的造型,丰满柔和的曲线,叫人爱不释手,观其形,想其态,味外之旨油然而生;而碗沿厚度恰到好处,与嘴唇相接,不滞不滑,天衣无缝,宛如与心爱的女人接吻。[1](154)显然,这已经不能单纯地从美学的角度来解释了,对装饰美的迷恋和不懈的追求,已成为日本人根深蒂固的感觉方式和思维方式,甚至是他们的一种本能。到了德川幕府后期,日本的这些工艺水平几乎可与中国并驾齐驱。[7](209)
磁器、彩画旧不及北京,近参西法,精巧出色。博物院有一花瓶,高可抵屋,遍体彩画,金碧眩目,渲染无痕,此亦仿西法为之。
[2](卷三,物产二十六则)
镜,旧有乌匣镜者,今不可见。坐镜、悬镜,皆从西法;惟铜镜,尚有旧制。眼镜亦旧有髹漆木为围,屈其虹腰,两圆相当,上圭下圆,髹匣而藏之,形如胡芦者,今则无之。只有轮小,才可遮眠而无郭。或银、或铜为郭,而加鹤膝,鹤膝两端,屈而下之,挂之耳后,牢着不脱,郭与膝俱细如丝,此亦西法欤。[2](卷三,物产二十六则)
在《海行总载》中,朝鲜通信使还对作为人类进入更高文明阶段标志的发电机做了大力推介:
所谓火轮之转迅如电,而器物之成速若神。造币、造纸焉,治木、治革、治丝焉,莫不以火轮。而轮船之一日千里,轮车之一时百里,尤岂人力可致哉。海上之灯台,国内之铁道,所由设也。所谓电信,先自东京、长崎,延亘欧罗巴国,直线、横线几十其条。而各国事为,咫尺可闻;万里书信,顷刻可通。此为公私并用也。[6]([天]闻见录)
可以说,蒸汽发电机技术的引进和使用,使日本的生产力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不论是造币、造纸、治木、制革、造丝,还是轮船、车辆、火车,乃至电信、海上的灯塔,都必须依赖发电机。因而,朝鲜通信使们都不能不为这项技术的使用大为动容,也十分迫切希望早日在自己的祖国得到广泛运用。正因为耳闻目睹了日本所发生的这些惊人变化,大多数朝鲜通信使才不无感慨地说道:
贵国自通商以来,器械工用,如夺造化。一人作百人之事,必利益莫大,而何为其受害云耶?通商是人民贸迁之利,且税关课岁之入,必多补国用,而何为空虚耶?贵国二十年前闭关斥和,称于天下矣。今日之和,又何其甚焉!而法度仪文,无一不更张耶
因而,就连日本天皇也是“躬临博览会,赏赐器物之精造者,以劝工匠之兴业云矣。凡此土俗物情 ,翻然舍旧 ,一切从新。”[6]([天][录]闻见录)但有些朝鲜通信使却从朱子学的立场考虑,仍然要愤愤地谴责日本:“机械精工,非不利也,然一时为夷人所怵。一一承命于夷狄,其害非言语可伸者存焉。贵邦果有人物,不受外人之制,听交商甚可。然若后来有小人如秦桧者当国,将奈之何?”[5]([上],九月初四日癸酉)所以 ,这绝不是日本的幸事!何况——
日本立国二千五百三十余年于兹矣,自有自家之制度。既承历世之传习,而不通西国以前,未尝非国富兵强、家给人足,而亦无待于外也。是故当初斥攘,不啻严邪正之分,到今服从,胡至此俗风之易乎?或曰时势使然,而归之时势,不思吾之自主乎?又曰强弱所致,而付之强弱,不勉吾之自修乎?大抵西国,其学焉耶苏之教,其事焉功利之贪,而惟以奇技淫巧为第一务也。概许相通,见闻相接,则凡于厚生之方、富强之术,有可效者效之,有可移者移之。犹或万一,而一事一为,无不仿之。一年二年,举皆变之;而忘我之古,取人之短。 宇内万国 ,宁有是理乎?[6]([天][录]闻见录)
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器物精良的日本形象主要是通过描绘日本的文化器物和工业器物营构起来的。朝日贸易使日本器物流入朝鲜,朝鲜文人由日本器物认识日本,并形成了关于日本的想象。在他们的笔下,日本大和民族是一个精于工艺、制品精良的民族。
在此,朝鲜朝通信使并没有盲目陶醉在朝鲜文化的优越性上,而是更多地去关注日本的技术文明。不少朝鲜通信使在他们的游记中,曾羡慕地语气详细描述了他们在日本期间所耳闻目睹的在造纸、纺织、冶炼业等方面的器物之制。他们将它与朝鲜的工业器物制度相比较,找出了中国之长与朝鲜之短,敏锐地认识到造成朝鲜贫穷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生产技术的落后。所以,他们在自己的《海行总载》中,积极主张导入日本先进的生产技术与工艺手法,改革朝鲜的劳动工具,改进朝鲜传统的操作方法,以达到提高生产效益的目的,这也可以说是当时大多数朝鲜人梦寐以求的强国富民的梦想。
[1]李兆忠著:《暧昧的日本人》,北京:金城出版社,2005年。
[2][韩 ]金绮秀:《日东记游》,《海行总载》第 10辑 ,首尔:民文库 ,1989年。
[3]张哲俊:《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4][韩 ]金世濂:《海槎录》,《海行总载》第 4辑 ,首尔:民文库 ,1989年。
[5][韩 ]申维翰:《海游录》,《海行总载》第 2辑 ,首尔:民文库 ,1989年。
[6][韩 ]日槎集略 ,《海行总载》第 11辑 ,首 尔:民 文库,1989年。
[7]李寅生著:《论唐代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成都:巴蜀书社 ,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