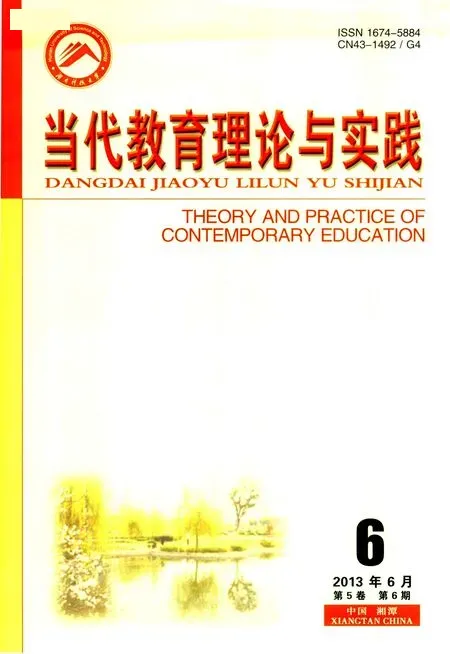“承继他的精神,承继他的遗志”——蒋牧良与鲁迅
徐续红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公共事务管理系,湖南娄底417000)
蒋牧良(1901-1973),湖南涟源人。在20个世纪30年代,蒋牧良是著名的左翼作家,解放后曾任湖南省文联副主席,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他深受鲁迅先生的影响,对鲁迅先生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将鲁迅先生奉为终生的楷模,像鲁迅先生一样做人,做事。
一 被鲁迅称赏的有前途的青年作家
1933年11月,蒋牧良在文学刊物《现代》月刊4卷1期发表处女作《高定祥》,获得了读者的一致好评,被认为是继茅盾的《春蚕》之后又一篇描写农村生活的力作。鲁迅先生对这篇小说很感兴趣,并问及《高定祥》的作者是否还有新作问世[1]。处女作得到鲁迅先生的肯定,蒋牧良深受鼓舞,创作激情被点燃,第二年相继发表了《夜工》、《当家师爷》、《懒捐》、《赈米》、《锑矿上》等颇有分量的短篇小说,确立了他在左翼文坛的地位,“是鲁迅称赏的十个有前途的青年作家之一”[2]。这一年秋天,蒋牧良辞去了南京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副官室司书一职,到上海从事职业写作,积极参加左翼文学活动。他与鲁迅先生更近了。鲁迅的作品滋润着蒋牧良的心田,他决心以文学作为自己终身的职业。
蒋牧良在文学创作上最初受张天翼的影响较多,后来又受到了鲁迅先生的影响,在思想倾向和艺术构思以及表现手法都留有这种迹象。他的小说大多取材农民的苦难和抗争,揭示旧中国农村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也有写矿工、旧军队和公务员的,反映城市下层人民的穷困潦倒和旧军队的尔虞我诈,表达了他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和对国民党政府的愤懑。他的作品没有复杂曲折、惊心动魄的情节,但注意构思和剪裁,人物形象鲜明生动,语言朴素简炼,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鲜明的讽刺艺术特点。蒋牧良笔下的作品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触目惊心的社会黑暗图。《航程》展示了一幅幅“吃人”的图画:在船上,不仅大人欺诈小孩,而且城里人欺诈乡下人,男人欺诈女人,上司欺诈下属,外国人欺诈中国人,人们在“吃人”和“被吃”中生活着。《赈米》一方面极力渲染严重的水灾给农村造成的凄凉景象,一方面又细致地描绘了官吏和商人勾结,迟迟不发赈米的卑鄙行为。一面是饿殍遍野,易子而食,一面却是灯红酒绿,权钱交易。《从端午到中秋》如实地写到了农民与城市小商人的破产景象,反映了社会腐朽黑暗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城里人准备下乡求生计时,乡下人却来到城镇逃荒,在农村与城镇一样没有活路[3]。蒋牧良的有些作品烛微探幽,甚至能够跳出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深入到人性的层面,剖析了鲁迅所说的那些“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且介亭杂文二集·什么是“讽刺”?》)的人物的灵魂。
蒋牧良继承了鲁迅的传统,在中国现代讽刺艺术的园圃里,辛勤耕耘,努力劳作,培育出了鲜艳的讽刺花朵,塑造出了不少讽刺的典型,丰富了中国现代小说讽刺人物的画廊。蒋牧良笔下的韩八太爷(《雷》)和胡远程(《一个撤职,一个开除》),仍然闪耀着强烈的思想艺术光芒,在中国现代讽刺小说的人物画廊中占据着重要的席位[4]。蒋牧良的讽刺以质朴冷峻见长,寓谐于庄,以庄中内在讽刺力动人心弦。蒋牧良的讽刺接近鲁迅的某些小说。
在各种斗争中,蒋牧良坚定不移地和鲁迅站在一起。1935年底,鲁迅当年参与筹建的文学团体左翼作家联盟在无声无息中解散,而且鲁迅事前一无所闻。对此,鲁迅深为不满,从此对左联的一些领导人失去了信任感。1936年4月,徐懋庸、何家槐等人发起成立作家协会,后改名为文艺家协会。鲁迅拒绝参加。鲁迅的追随者在中国文艺家协会正式成立之后,于6月中旬另外发表一份《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在这份宣言上签名的文艺家有78人,蒋牧良就是其中一位[5]。1936年,左翼文学界内部发生了“两个口号”之争,在这次论争中,尽管赞成国防文学口号的人数多,声势大,但蒋牧良还是毫无保留地拥护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6]。
1936年7月,《现实文学》创刊,蒋牧良参与了编辑工作。他主动向鲁迅约稿,创刊号上发表了鲁迅的《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这个时候托派给鲁迅写信,挑拨鲁迅与党的关系。尽管鲁迅已重病在身,但他毫不犹豫写了一封公开信《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热情称颂刚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国共产党,也以无比的愤慨怒斥了托派配合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这份讨檄的文献原打算在大报上登载,但大报不敢登,其他进步报刊也怕担风险。经蒋牧良与编辑部同仁商量,《现实文学》毅然承担了这个光荣的任务,在第2期上刊发了这篇文章。文章发表后,影响很强烈。但《现实文学》却被查封,不能再出了[7]。这是蒋牧良与鲁迅配合默契的一次并肩战斗。
二 高度评价鲁迅先生
遗憾的是,被蒋牧良称为“导师”的鲁迅先生健在的时候,蒋牧良一直没有和他见过面,没有直接聆听到他的教诲,“直到鲁迅先生的遗体已经躺到了胶州路万国殡仪馆,在千万人的瞻仰中才这样见到他一面。”蒋牧良为此后悔终生。1936年10月19日5时25分,鲁迅先生在他的寓所与世长辞。敬仰他的民众络绎不绝地参加到治丧的活动中,表达对这位“民族魂”的敬意。鲁迅逝世后,成立了治丧办事处,蒋牧良是成员之一。从19日下午3时移鲁迅遗体至胶州路万国殡仪馆起,至22日下午安葬于万国公墓时候止,整整4天,蒋牧良怀着深沉的悲痛参加了治丧办事处的紧张工作。10月22日鲁迅出殡时,蒋牧良、欧阳山高擎着写有“鲁迅先生殡仪”的特大白布黑幡,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面。当时曾为鲁迅先生扶灵的陈白尘先生后来回忆:
“1936年鲁迅先生逝世,在出殡的那天,送葬者不下万人。中外巡捕早在万国殡仪馆门外巡逻了。葬礼进行中会出什么事,是难以逆料的。送葬行列最前头是一幅巨大的门旗,上书‘鲁迅先生殡仪’,是天翼写的。但谁来执掌这面门旗呢?当时我在经管杂务,牧良跑来说:‘我来!’我自然喜出望外:这门旗不啻是这万人行列的‘帅旗’,而且,如遇到捣乱破坏的歹徒时,他们又是冲锋手。他这位行伍出身的壮汉,自然是我们这班文弱书生所不及。另一位也是自告奋勇的大汉则是欧阳山。在他俩高举的门旗之后,肃穆的行列缓步前进了。四十七年来,牧良的那副刚毅勇猛的神色还深深印在我的记忆里!”[8]
从陈白尘先生的介绍来看,蒋牧良是自告奋勇担任旗手的。一方面说明蒋牧良敢于担当,对鲁迅先生无限崇敬,另一方面也体现出蒋牧良当时在文学界的地位,因为一般人是没有资格来担当这个重任的。
鲁迅先生逝世不久,蒋牧良含泪写出了《悼鲁迅先生》一文,刊登在1936年11月5日出版的《中流》半月刊第1卷第5期上。此文与其他印象式的悼念文章不同,侧重于对鲁迅先生作出评价,指出他的逝世对当时中国的损失和影响,并提出希望。今天来看这篇写于70多年前的文章,蒋牧良对鲁迅先生的评价还是没有过时。评价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
一是肯定鲁迅作品的意义:“我所认识的鲁迅先生,完全是由他的作品认识的。他在这些作品中间告诉我(还有不可数计的劳苦大众)认识世界,认识一切,指出了我们的敌人是谁。他唾弃那些人,冷嘲热讽地暴露了他们的丑恶,使我们对这些人认识更清楚,并且教给我们拿起自己的武器,勇敢地,悲壮地,向他们冲锋。鲁迅先生不止于在文学方面告诉我们掉几个字句,使我们走向那艺术的宫殿里去。他的作品,主要的还是领导着青年大众,无情地向着恶势力猛烈搏斗,摧毁它们的壁垒,在这样动荡的大时代里,使我们的民族求解放,使每一个劳苦大众争生存。”
二是分析鲁迅逝世的影响:“现在我们这位导师已经死去了,而且躺到了土里,广大的群众,失掉了这架喊出心坎儿里的痛苦的播音机,苦斗着的战士,失去了排头这位领队者,这是我们无数万没有见面的人的哀愁,也就是我们无数万没有见面的人的衷心的哀悼。尤其在今日——当我们的民族危机达到了最后关头的今日,这位为整个民族求解放的战士,停止了他的搏斗,默默地躺到了土里,使我们有着加倍的痛惜,加倍的悲惨,我们在这痛惜的中间,不单是要向鲁迅先生的遗体致哀,更应当为整个民族致哀,整个被压迫的大众致哀。”
三是提出怎样纪念鲁迅:“我们要继承死者的遗志,结合这不可数计的大众来向敌人进攻,求我们整个民族的解放,争取劳苦大众的生存。朋友们,不要灰心!不要灰心!我们这位领队者虽然死了,可是我们这位领队者还留给了我们不少的可珍贵的遗教。他的精神没有死,他仍旧在排头领导着我们。只要我们把我们的眼泪化成血,化成力,化成庞大的决斗,我们依旧可以得到胜利的!……只有承继他的精神,承继他的遗志,才是我们安慰他的,哀悼他的最好的方法。”
毛泽东在1937年10月19日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论鲁迅》,是我党最高领导人所作的最早也是最全面的一次评价。毛泽东说:“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鲁迅先生的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治的远见,他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学习鲁迅的精神,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与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比较来看,蒋牧良的评价尽管没有达到那样的高度,但也是非常中肯的,有前瞻性,非常敏锐。蒋牧良作为一个普通的文学青年,在鲁迅刚刚逝世就写出这样内涵深刻的文字,是难能可贵的,这说明他对鲁迅先生的认识非常深刻,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这为他日后继承鲁迅先生的精神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三 像鲁迅一样生活和战斗
在离开鲁迅的日子里,蒋牧良一直在“承继他的精神,承继他的遗志”。蒋牧良的女儿蒋子丹说:“他是为鲁迅扶过灵的人,一生崇敬的是鲁迅。要是我们讨论一下说鲁迅也可能有缺点,鲁迅有些做法也不是很恰当,我爸爸说不定会立马跟我断绝关系。”[9]可以说,蒋牧良是鲁迅的虔诚守护者和追随者。
40年代初,由于时局所迫,蒋牧良回到了家乡涟源。他的学生张翅祥回忆:“那时,附近的中心学校有个爱好文学的青年教师常来向蒋师求教。见面多了,我们就无话不谈。一次,我们见蒋师案头一个旧笔记本的首页写有书愤的八个字:‘上苍赦我,莫作文人。’于是相与慨叹文人生活清苦,要做作家,就得准备吃苦。那个青年教师说,他有一个打算,湘西某县税务局局长是他的亲戚,他想上那儿去捞一把钱,打下经济基础,然后安心安意搞文学。那个青年教师走后,蒋师对我直摇头说:‘某某叫人灰心,他以为贪官污吏、强盗骗子都可以做作家,真不知怎么说他!’那位青年教师再来时,蒋师大谈他所熟悉的文学家的高尚品德,鲁迅先生是他讲得最多的一个。”[10]1946年10月,鲁迅逝世10周年时,蒋牧良又满怀深情,写了纪念文章《十年后的墨泪》,抒发对鲁迅先生的怀念之情。
到了晚年,蒋牧良的为人处世都有鲁迅先生的遗风。蒋牧良对自己的作品要求很严格,他在解放后写的两部长篇《湖边风雨》、《国防在后方》,都脱了好几稿,几家出版社向他索稿,他都不同意马上发表,还要继续修改。他一直牢记鲁迅在《答北斗杂志社问》中所说的:“文章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50年代末,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版《蒋牧良选集》,选目早已列出。可是他觉得重新出版旧社会写的东西,应该更慎重地选择一下。他认为,“作品不是商品,为了稿费滥发东西是要不得的,那是最低级的作风。”[11]以后,因为工作忙,《选集》一直拖到文化大革命也没有出。而他在解除专政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补发工资得来的一千元,寄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偿还出版社为《蒋牧良选集》预支的稿费。
蒋牧良像鲁迅先生一样无私指导文学青年。蒋牧良与湖南省的青年作者们有着很深的感情,晚年,他把极大的精力投入到了对青年作者的培养上。为了帮助青年作家张行完成长篇小说《武陵山下》,蒋牧良前后花了5年时间。在这期间,由于肺病严重,他不得已住了院,可是,就在医院的病床上,他还专心致志地给张行改稿子。为了充实这部小说的素材,蒋牧良把自己在湘西剿匪时搜集的一些材料,毫无保留地提供给了张行。张行回忆:“我在朱校长家与蒋老朝夕相处了一个星期,每天除陪他散步、治病外,我便坐在他身旁读我的稿子。他有时候坐着,有时候躺着,一边听,一边指出行文中的毛病。最后3天,他病势较重,不让我面对面念稿,以免传染,叫我坐在枕头后边念给他听。小说中有些情节令他激动,有些败笔使他生气。他常常打出手势要我停下来,喘着气,咳着,指点着那些令他满意或使他生气的地方,用微弱的声调,娓娓地谈着看法。……有一次,他正谈着意见,忽然大咳起来。我移过痰盂,他竟吐出了一口带血的浓痰。我放下笔记本,一股强烈的感情直冲脑海,泪水涌进眼眶。他咳完,发现我在发呆,便指着稿子说:‘读呀,往下读。’”[12]这感人的一幕,与鲁迅带病为青年改稿多么相似啊!在《三闲集》中,鲁迅曾经这样说过:“过去的近十年中,费去的力气实在也并不少。即使校对别人的译著,也真是一个字一个字的看下去,决不肯随便放过,敷衍作者和读者的,并且毫不怀着有所利用的意思。”李霁野回忆鲁迅先生:“记得有一次我去访问先生时,见他的神色很不好,问起来,他并不介意地答道:‘昨夜校长虹的稿子,吐了血。’我的心立刻沉下去,几乎流了泪。”[13]
正如蒋子丹所总结的,蒋牧良“一生走过了一条艰难坎坷的路,然而,他始终保持着自己阶级的本色。没有追求权力的野心,没有贪图安逸的侈望,他像一头勤恳的老牛,在文学园地里耕耘,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他一世清贫、两袖清风,问心无愧地走完了自己的全部路程。”[1]浮现在蒋子丹心头的父亲印象,依稀出现了鲁迅先生的身影。
[1]刘 勇.困境中奋起的名作家——蒋牧良记略[C]//湖湘文艺人物上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
[2]严怪愚.怀牧良[J].芙蓉,1983(2).
[3]李夫泽.深深扎根于现实土壤中——蒋牧良小说浅析[J].邵阳学院学报,2004(6).
[4]杜方智.张天翼与蒋牧良——试论他们讽刺艺术的成就、地位及其异同[J].零陵师专学报,1984(1).
[5]陈漱渝.巴金起草《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J].世纪,2004(3).
[6]姚 辛.左联画史[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
[7]草 明.张天翼和《现实文学》及其他[C].沈承宽.张天翼研究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8]陈白尘.湖边风雨忆故人——蒋牧良选集代序[N].人民日报,1983-12-26.
[9]蒋子丹,单正平.两栖人生——蒋子丹访谈录[C].蒋子丹小说精粹.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10]张翅祥.时间冲不淡的哀思——怀念蒋牧良同志[J].湘江文学,1983(4).
[11]蒋子丹.写在春天的深夜里——记我的父亲蒋牧良[J].新文学史料,1979(5).
[12]张 行.为下一代开路——忆老作家蒋牧良[J].作家通讯,1983(1).
[13]李霁野.鲁迅先生和青年[C]//李霁野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