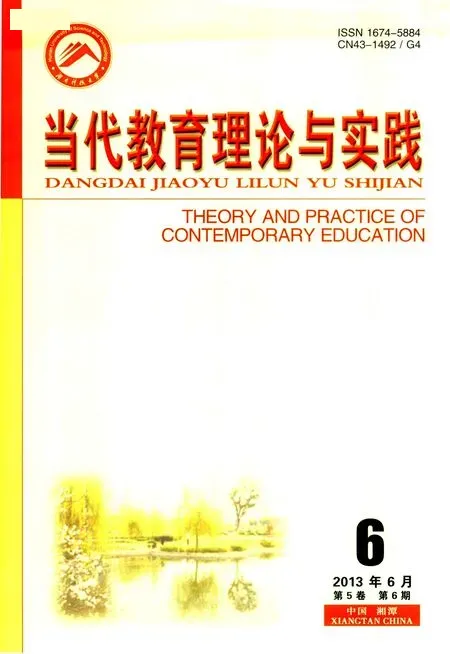“红色经典”电视剧改编中人物形象的再塑造——以《红色娘子军》为例
张 瑜,彭在钦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湖南湘潭411201)
“红色经典”改编堪称近年电视荧屏的一大气象,《林海雪原》、《小兵张嘎》、《红色娘子军》、《闪闪的红星》、《红旗谱》、《青春之歌》等一大批红色经典被改编为电视剧。电视剧《红色娘子军》改编自1961年谢晋导演的同名电影。初登荧屏便在第二届“南方盛典:2005年度颁奖礼”上,以4.9%的收视率获得了“最受欢迎电视剧奖”。获得受众这样的认可,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电视剧在人物形象上的成功再塑造。
一 个体与群像
相对于同名电影,电视剧《红色娘子军》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最大的特点就是,从个体的描写到“红色娘子军”一个群像的表现。1961年谢晋导演的《红色娘子军》,描绘了主人公吴琼花在党的指引下,从一个女奴逐渐成长为一名红军战士,并最终成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过程。影片主要塑造了娘子军吴琼花这个形象以及党代表洪常青这个人物。而对于娘子军其他人物的描绘则相对甚少。相对于电影,改编后的电视剧《红色娘子军》,则在塑造吴琼花这个典型人物的同时,还描绘了洪常青、连长、红莲、黎妹、小光头、南洋女、大个子、海草等人物,让观众真切地看到了娘子军这一个群体形象。这样从总体上丰满了人物形象,让观众看到了人物形象上的厚实感。
人物对白是电视剧承载信息的重要表现方式。对于对白的积极作用,卢蓉认为,“对白的积极性和结构性对于场景是不可缺少的,而这种对白对情节的积极建构可以毫不费力地超越试听具象的局限,依靠语言内在的戏剧性张力推动故事和行动。”[1]对于红莲这个形象,电视观众很难忘记她在婆婆面前哭诉自己非人生活境遇的一大段对白。琼花在洪常青的帮助下终于逃出南府,她没有直接去五指山参军,而是来找自己的好姐妹红莲,劝她与自己一起去参军。正在二人准备走时,红莲婆婆带着一群人前来阻止。红莲跪地向婆婆哭诉了自己这么年来在婆家守着木头男人的非人生活,并对婆婆守寡几十年的苦深表同情。
红莲:“婆婆,你就放红莲一条生路吧,自从我嫁到你家,你见过我笑吗?我每天抱着冰冷的木头人,不知流了多少泪。婆婆,你也是受苦人,你从二十几岁就开始守寡,一直守了几十年。这种苦,这种滋味,你比谁都清楚呀婆婆!您就真的忍心,让红莲也跟你这样过一辈子吗?”
两个有着类似经历的女人回忆着各自悲惨的生活。在回忆中,婆婆反思自己,终于答应了红莲的要求,这是一场关于人身自由的论争。在这一段对白中,我们清晰地感受到了红莲以往不堪的生活,也看到了平时霸道刻薄的婆婆人性的一面。
面对敌军的围剿,红莲为了救吴琼花、为了救自己的女儿,而跳崖自尽的场景,也是感人至深。剧中仰拍镜头下,红莲站在悬崖边,大声喊到“报仇啊”,然后纵身一跃。镜头上,红莲双臂张开着,双眼微闭,脸上带着微笑。剧中用特写镜头表现了红莲的表情,并且拉长了红莲跳崖镜头内的时间。红莲这一组动作表现了她内在的本质,完成其行动美学承载的含义。
此外,在电视剧《红色娘子军》中,拿着手榴弹冲向敌人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大个子;战场上被炮震晕后又坚强地爬起来作战的小光头;榕树下,被绑着,大声背诵《共产党宣言》走向火场的洪常青;敌人多次围剿后,想要逃跑回家,面对吴琼花没有惩罚反而给路费的举动,失声痛哭,认错再也不肯离开这个队伍的海草;被南霸天抓住,逼着在群众大会上控诉娘子军,而选择用刑场婚礼预祝革命胜利的南洋女和医生……电影中我们看到了吴琼花这个红色娘子军个体的精神特质,而在电视剧中,这些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让观众看到了“红色娘子军”作为一个整体的群像,看到了这一群像的坚强勇敢以及对革命的坚定信念。
二 脸谱化与个性化
所谓,“人不立,剧无魂”,人,是艺术作品的灵魂。人物形象塑造的好与坏直接决定了作品的优与劣。对于电视剧作品,尤其如此。许多具有持久艺术魅力的电视剧作,观众在看过很久以后虽然对剧中的具体情节记忆不是很清晰完整,但是对于剧中一些人物却是印象深刻,如电视剧《士兵突击》中的许三多,《亮剑》中的李云龙,《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的石光荣等等。这些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支撑起了电视剧。可见,任何一部电视剧作品,要想赢得观众,要想获得持久的艺术生命力,就必须要塑造好人物形象。“作品中的人物必然是富有个性的‘这一个’,必须是独特的艺术形象,以形象的生动性、丰富性、深刻性来吸引观众。”[2]而恰恰很多作品却悖离了这一点,人物塑造不是个性化而是脸谱化、抽象化。表现在红色剧上,就是将正面人物塑造成“高、大、全”式的。
电影《红色娘子军》受到电影本身的篇幅限制以及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存在着人物个性扁平化、人物立体感不足的缺陷。电影中对于主人公吴琼花由一名只想着报仇的女奴到一名合格的红军战士的成长描述显得过于简单,有一蹴而就之感,因此让观众感觉这种成长叙事过于单薄,说服力不强。而电视剧则比较注重人物个性的塑造,特别是注重让人物在行动中展现其性格的成长。剧中吴琼花改掉野脾气不是一蹴而就的,她由一名普通的战士成长为一名能带兵打仗的党员的过程也是一波三折。吴琼花参军不久就违反组织上不得对俘虏用私刑的规定,为了给小光头报仇,带着姐妹们棒打正被带下山准备放走的人贩子。在娘子军第一次作战——抢夺南霸天布匹时,吴琼花勇而无谋,无组织纪律性,在还没有听到命令时就带头开枪冲锋。而后又因为急着想入党,误解连长杀南霸天也算是一种考验的话,而在雨夜偷偷溜回镇上,去杀南霸天。后又在执行侦察任务时,不守侦察纪律朝南霸天开枪。并且自以为打死了南霸天,高兴的回到驻地、骄傲的告诉大家她的“光荣行动”,被关禁闭后,还准备逃走……在这一次次的犯错——改正——犯错——改正中,吴琼花一步步地成长起来。电视剧中对于红莲的成长描述也不像电影中描述的那样简单。电影中,红莲出场时就已经坚定的要去参军,和吴琼花聊了自己不堪的生活后,就和吴琼花一起到了五指山。而电视剧中,在一个个的行动中完成了红莲由胆小懦弱到坚强勇敢的成长叙事。这样的安排,大大丰富了人物形象,让我们真切的看到了人物性格发展变化的痕迹。
三 女性身份的回归
诞生于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之下的电影《红色娘子军》与同一时期诞生的其它红色经典相似,在女性形象塑造上,有着明显的符号化特征。女性形象说到底是为了政治而服务。恰如范玲娜在《作为符号的女性》中一文所说的:“细细品读作品,会发现她们只是作为一个个符号存在于文学作品之中,是阶级、政治的符号,是男性界定的符号。”[3]
电影中,吴琼花是作为苦大仇深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阶级符号存在的,最后也是根据当时的阶级政治需要,在党的指引下,顺利成长为一名党员、女英雄。可以说吴琼花的成长完全是一种意识的显现,一种理想状态的书写。这恰如胡牧所言:“在《红色娘子军》这类关于女性成长为英雄、成长为战士的电影中,女性只是一种符号,女性的成长只是一种理念的显现,一种理想状态的可能性表征。这种叙述一旦与社会主流意识相联系,表达的只是一种关于女性的觉醒与成长。女性对封建专制的反抗,对阶级敌人的反抗,都共同指向一个民族的梦想。这种梦想的表述与表征,既是一种主流话语的询唤,又是一种契合大众心理的通俗叙事,个人意识被抛入集体合唱和时代情绪之中,性别意识也在宏大叙事中淡去和消隐。”[4]
诞生于那个特殊年代的红色经典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电影作品,在对待女性身份时,都更多的是把目光聚集在她们是“受压迫最深的阶级”这一面,而较少的关注于她们作为“女性”的一面。而在近年的“红色经典”改编剧中,导演们开始挖掘那些曾被刻意淹没的“女性”身份的一面。
首先,改编者一改红色经典作品中,褪去了女性传统观念中温柔、惹人怜爱的性别色彩、“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英雄”“女强人”形象。剧中的吴琼花一改电影中衣衫破旧不堪的穷苦形象而显得青春靓丽,是“这一带出了名的靓妹”。电视剧还增加了许多女性人物,这些女性形象一改原著中近似于男性的“女强人”形象:被要求剪去长发时,大个子等人不愿意也不敢剪;红莲在第一次作战时,竟吓到一枪未发;为作战和行军方便,连长发放捆胸布,令战士们捆胸,可不论大家怎么劝说,黎妹就是不肯捆,最后还是在连长的死命令下才哭着捆了胸……此外,在电视剧中,娘子军们会争相传看镜子;黎妹和小光头会调皮地施计让吴琼花与洪常青在海边相遇;吴琼花和南洋女会因为一些小事时常比试较劲……这些在人物容貌上以及性格上的改编处理,丰富了女性性别身份的表现,不仅多了展现人性的一面,而且也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
其次,关于女性身份的回归,还表现在改编者对于情感特别是爱情因素的描写。在革命文艺中,对于男女之间的情欲往往会刻意回避。“在经典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阶级差异成了取代、阐释、度量一切差异的惟一社会存在;因此,在工农兵文艺中,阶级的叙事不断否定并构造着特定性别场景。此间,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话语或不言自明的规定,将欲望、欲望的目光、身体语言乃至性别确定为‘阶级敌人’(相对于无产者、革命者、共产党人)的特征与标识;而在革命的或人民的营垒之内,则只有同一阶级间同志情。”[5]在电影《红色娘子军》原来的剧本中也有一段吴琼花和洪常青的爱情戏,只是“在准备拍摄的时候,剧组有同志提出反对意见。谢晋认真考虑了这个意见,在当时,剧本都已经基本完成,如果按照这个路数来拍摄的话,将会省不少事情,但是在后期的审查上会不会有麻烦了?我们要知道,这段故事的年代是1962年,那时候,爱情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是得不到认可不被社会准许的感情。只有同志之间的同志情才是最亲密的,最伟大的。”[6]于是吴琼花与洪常青的恋人之情变成了同志之情。
而在电视剧中则充分加入了爱情因素。剧中,当南洋女与洪常青笑着聊天时,吴琼花会吃醋;在庆功会上,大个子称赞南洋女懂得多、有文化时,琼花会表现出不悦;洪常青得了痢疾卧病在床时,她质疑南洋女带来的西药的疗效,并随后到附近的山坡上采草药,用土办法为心爱的人治病,并彻夜守护在其身边,并在随后与红莲的谈话中,表露了自己的心迹;当洪常青被南霸天抓住,要用他设圈套诱骗更多的娘子军,连长要带人冒死营救时,琼花分析出是圈套,不同意救人,“我们这样做,不仅救不了党代表,整个娘子军连也会全部牺牲掉的。到时候党代表会更痛心的”。连长质疑琼花,“你的推断是没有根据的,党代表现在心里想什么,你怎么会明白呢?”琼花:“我能感觉到,我能明白他的心。”这些场景的描述无不体现了琼花对洪常青浓浓的爱意。此外,电视剧也通过细节展现了洪常青对琼花的爱意。琼花负伤,刚从战场上下来的洪常青没来得及休息片刻,立刻赶到师部,请来最好的医生为其做手术。手术时,由于没有麻药,琼花难以忍受巨大的疼痛而拼命挣扎,就在此时,洪常青将自己的手递到琼花的口中。琼花紧紧咬住了常青的手,直到鲜血流淌,从而保证了手术的顺利完成。剧中我们没有看到二人爱情的直接抒写,更多是用含蓄间接的场景和细节描写表现二人的爱意。这种爱情因素的加入,让观众看到了战火中的温情,体现着女性身份由符号化抒写到性别身份的回归,让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立体。
四 结语
“人物是剧作诸艺术元素中属于核心地位的要素,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剧本创作的中心任务。”[2]人物形象塑造的好与坏直接决定了作品的优与劣。红色经典改编也要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尽力塑造出丰满化、立体化、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在注重主人公形象塑造的同时还要注重群像的塑造。
[1]卢 蓉.电视剧编剧艺术[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
[2]宋家玲,袁兴旺.电视剧编剧艺术[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
[3]范玲娜.作为符号的女性——论“样板戏”中革命女性的异化[J].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4(4).
[4]胡 牧.《红色娘子军》:关于女性成长的神话[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
[5]戴锦华.雾中风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6]申志远.《红色娘子军》之缘起[J].大众电影,2004(24).
——观歌剧《红色娘子军》